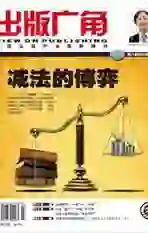品味经典
2012-04-29胡亚权
出版广角 2012年3期
杂志杂志,五味杂陈其为志。但五味之中须有主位,于是有了专题策划。《出版广角》今年第2期的策划案是“经典”。这两个字使我们立刻想到四书五经、三坟五典、离骚、神曲、欧几里得几何学、相对论这些。总之,是可以传承的文明。但到了信息爆炸,大师缺失,泛阅读浅阅读的今天,经典的概念恐怕已悄悄地被改变。
欣慰的是,正直的出版人依然坚守传统的经典理念。在本期韩进的《经典出版》中,提出启动国家级经典保护工程的建议。周绚隆《经典热读背后的冷思考》抒发了他对经典的伪化泛化浅化钱化的忧虑。动漫在当下是朝阳产业,殊不知动漫的经典在50年前已由迪斯尼造就。我颇欣赏丹飞先生《动漫产业:可为与可不为》一文。他讲出了实情,也许会给高层的守望者一些决策的参考。当前大热的数字出版也是如此。要紧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执其牛耳。牛耳又是什么,它在哪里?
作为教材,铁定了是经典之经典。现在50岁以上的人都记得《狼来了》的故事;60岁以上的人还记得《两只小羊过独木桥》的故事。一个讲诚信,另一个讲礼让。都来自当年教材,主题在于向孩子传播中华美德,这些经典已然深植于心。在中国古代,幼儿的启蒙教材也不外乎“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数种。可是那些旧教材老故事渐渐被新的、更新的故事教材所替代。可是上世纪80年代有一次“古代启蒙读物热”,本世纪又有一次“民国教材热”。反映出读者对旧教材的留恋。这里面究竟有何玄机?孙曙《原罪还是替罪羊?》一文作了较好的剖析。作者说“教育从来是国家意志”的工具,可是这个严肃的意志却被由“权力意志、政治立场、应试教育、阅读时尚、各种现行语文教育的得利者”形成的“利益共同体”所影响。于是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教材的功能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