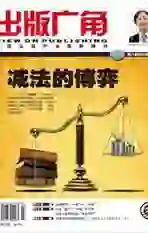让阅读回归本真
2012-04-29李新祥
李新祥,现为浙江传媒学院副教授、编辑出版系主任,武汉大学出版专业博士在读。脉旺传媒工作室发起人。
读者的阅读习惯需要做“减法”,不是读得多、买得多就好,而是精读,即读优质的、有益的图书。当大家谈起阅读,觉得那不再是负担,而是一种舒适和幸福时,阅读也就回归本真。
提出“给出版做减法”,在当下中国,颇有挑战意味。但其本意并非追求无为,而是力求简单、克服浮躁、回归本真。这无疑是合时宜并有建设性的。
日本出版专家松谦二郎说:“好的出版人出自好的读者,好的读者培养好的出版人。”看来我们讨论“给出版做减法”这个话题,需要回归到图书的消费者——读者,从读者阅读习惯角度探讨给阅读做“减法”,提倡读者阅读健康有益的图书,充分发挥图书的精神食粮作用。
当下读者阅读呈现的整体图景
给阅读做“减法”,当然不是基于某个读者个体,而是基于当下我国国民阅读整体行为提出的命题。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工作生活压力的增大,读者的阅读习惯也在发生改变,“快餐式”阅读走入读者的生活。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承认,与机械时代相比,数字时代我国读者阅读行为发生了嬗变,总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阅读主体方面:读者作为阅读主体,数量激增,总体阅读率上升。但阅读主体的素质是参差不齐的,结构异常复杂。潜在高素养阅读群体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快速扩大,但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存在功能性阅读障碍的群体规模也不小。简言之,读书家不多,读书人还是多了,当然不会读的还是不少。
阅读媒介方面:数字媒介的出现将读者带入了一个色彩斑斓的虚拟世界,构建起读者的阅读需求和丰富的电子文献资源之间的桥梁,使读者投入比以往更多的时间来关注在线文献的阅读,网络阅读、手机阅读增长迅猛。相反,图书、报刊等传统纸质媒介的阅读率提升乏力。
阅读内容方面:流行阅读超越经典阅读,信息获取超越知识习得,新闻关注超越文学感受,娱乐追求超越理论探讨,虽然这并不代表经典、知识、文学、理论内容的缺失,但这些内容被其他内容遮蔽、掩盖、消解是不争的事实。
阅读方式方面:快速浏览和扫读超越慢速凝视和审读,选择性阅读超越接受性阅读,跳跃性阅读超越连续性阅读,“F”式阅读(网页快速浏览)超越“Z”式阅读(逐行仔细品读),碎片化阅读超越系统性阅读。在使用数字媒体后,多种阅读方式所花的时间比例有所改变,浏览、选择性、非线性的阅读方式所花的时间比例上升,而在传统纸质图书文献上应用广泛的深度阅读所花的时间比例则明显下降。
阅读取向方面:功利阅读超越人文阅读,“浅阅读”(主要表现为阅读兴趣的单一,集中体现在对生活类、时尚类等通俗读物的偏好上)趋向明显。读者流于并开始安于浅薄,对深刻不再留恋。读者只关心自己是否听过、是否看过、是否知道,不关心是否想过,也不关心自己思考的深度,更谈不上把自己当成思想家。
分析读者阅读行为嬗变背后的原因,大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数字化技术引发阅读媒介发生变化,这是读者阅读行为嬗变的直接和根本原因。图书与媒介(阅读客体)形态变化了,阅读行为自然就跟着变化。第二,现代市场化运行机制下的图书与媒介发展的重合性和叠加性,恐怕是我国读者阅读行为嬗变的特殊原因。如今中国图书与媒介信息产业发展速度太快了,短短几十年就走过了西方社会媒介发展的数百年,读者大有招架不住的感受。第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体制的影响,是读者阅读行为嬗变的间接和基础原因。信息渠道的多元化和娱乐方式的多样化,读者浮躁心态和功利性目的的增长,包括出版者与作者在内的传播者系统创新能力的不足等,是读者阅读行为嬗变的相关因素。
这种阅读行为的嬗变,从个体读者而言,有其积极影响:数字时代的阅读可呈放射型树状或网状阅读路径,可以直线阅读、比较阅读、寻找阅读,读者既可纵向探索,又可横向比较,还可以交叉、重叠、转折、反向地研讨、思维,读者思维容易处于活跃、兴奋乃至亢奋的状态,一改纸媒体或平面媒体线状阅读路径限制创造型思维的局限。而消极影响也不少,主要表现在:阅读缺失绵延的历史感,读者失去传统意义上的耐心,怀疑传统经典,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质的变化。综合而言,数字化阅读为人们所向往和钟情,并必将为人们所接受和习惯。
不过,读者在当下的中国出版生态中包袱重重。他们不是不想读,而是没有心境读;不是没有选择,而是苦于选择;不是好书太少,而是烂书太多;不是读书太累,而是读屏更方便;不是没有时间,而是时间被打碎。从表面上看,中国读者更自由了,实则是更不自由了。因为读者在数字时代的当下往往需要不由自主地“在碎片化的时间里、在无处不在的屏幕上、在太多的烂书中辛苦地选择”。由此,读者的阅读习惯需要做“减法”,不是读得多、买得多就好,而是精读,即吸收前沿的、有营养的信息,读优质的、有益的图书。
如何给阅读做“减法”
在价值取向上,应该站在整个社会发展的立场上促进国民阅读,而不是为了某一部门或某一集团的利益。这一取向大体又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个体层面,即帮助国民个体正确认识阅读,科学实施阅读;二是社会层面,即为了改善和促进国民阅读,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采取相应的对策。
现实中的国民阅读促进运动在取向上存有一定的非理性。一些图书出版界的人往往只知道抱怨读者买书不够、读书不多。很多人感叹,中国人不读书更多是源于与海外读者调查的购书情况比较,但把中国读书人的比例与国外发达国家比,是不甚科学的。对阅读的理解仅限于纸本图书阅读太过狭隘,将读教科书、培训书视为非阅读也不合理。文学界也有不少人片面担心读者不读文学经典。其实,读者对经典阅读的理解不应该迷信。在《获得教养的途径》中,黑塞就曾说:“世界文学的辉煌殿堂对每一位有志者都敞开着,谁也不必对它收藏之丰富望洋兴叹,因为问题不在于数量。有的人一生中只读过十来本书,却仍然不失为真正的读书人。还有人见书便生吞下去,对什么都能说上几句,然而一切努力全都白费。”
在实践操作上,就个体读者来说,首先,要认识到阅读能力的大小,直接影响到他的成长、职业能力和其对社会作用的发挥。无论如何,读书还是十分重要的。其次,要提高获取信息的能力,提高阅读素养,可选择阅读一些合乎自身发展定位的图书。这对任何一个读者个体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最后,在浩瀚的知识库里建立自己感兴趣的知识站点,建构自己的意识框架,将阅读作为一种善念,将自己视作与世界有关系的人。追求“阅读数量”,更要讲究“阅读质量”;鼓励“阅读屏幕”,更要坚持“阅读纸本”。但每一个读者个体,大可不必异化阅读,更不可被阅读所异化,应着自己的心念去阅读就够了。
从社会层面看,需要政府部门和教育、出版等行业共同应对,帮助读者给阅读做“减法”。阅读自由不仅是一种可贵的状态,更是一种生活的权利。政府要采取措施切实推进国民自由地阅读,保障读者实现这种状态和权利。肯定“阅读有用”,更要倡导“阅读无用”。要让读者认识到,一心想着黄金屋、颜如玉、优则仕,一旦得不到,读书就难以为继。读书本是一种生活状态,大可不必作如此多的附加诱惑。褒扬“苦读”,更要倡导“悦读”。读书一定要悬梁刺股、十年寒窗么?难道就不可以开心快乐地读么?出版行业应继续开展扫盲工作,推进“农家书屋”工程,并切实提高使用效益。各级城市在发展大书城的同时,应着力发展社区书店和社区图书馆。图书馆也要扩大对国民开放的水平,大学图书馆更应向社会公众开放。
此外,改革教育体制尤其是中小学教育体制,逐步摆脱应试教育的束缚,是给阅读做“减法”、改善国民阅读状况的重要基础。全民读英语实属浪费,针对英语学习占用大学生太多阅读比例这一现状,普通高校要彻底改革英语教学。学术理论界则更应该摈弃门户褊狭,携手研究,为社会实践操作提供指导。
所有这些,都是在为读者争取阅读自由,在为读者的阅读做“减法”。当大家谈起阅读,觉得那不再是负担,而是一种舒适和幸福时,阅读也就回归本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字时代我国国民阅读行为嬗变及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