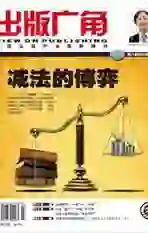“小时代”,“大情结”
2012-04-29庄庸
庄庸,博士,中国青年出版社副编审,新青年读物工作室主任,从事“90后”出版、经典再造和小历史读物的策划与编辑。
出版业缺的,其实不是宏大的“出版理想”和“文化情结”,缺的,其实是做人的底线伦理和做事的高标准则。否则,文化繁荣发展得再花团锦簇,我们仍然会像是一具没有灵魂的巨人的空壳躯体。
迈入2012年,我以为,出版人的状态,只有一个关键词可以形容——“纠结”。
我们仍然处于各种各样的困境之中,变得更加现实,或者,更加逃避现实——在出版业普遍被这种集体情绪所绑架的前提下,来谈出版“减”“加”法的博弈,无异于是在这双重态度中,展望未来,回顾过去,找到第三条道路——美好,但却艰难。
我不是在为这个专题泼冷水。恰恰相反,我觉得此时,此地,此刻,这个角度选得很好,由此切入整个出版业所面临的行业困境,“如果逻辑上能够创新,或许能够点出行业现在面临的危机本质”——但若谈的只是老套路,却容易像过去一样沦为清谈和空谈,而没有实操性。
出版人首先也是“人”,在席卷整个中国的困境和纠结之中,多数情况之下也只有这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面对房子、车子、孩子和票子等问题,变得更加现实;要么就是在无力干预重大事务甚至连自己生活小事都无力驾驭的渺小感之中,更加逃避现实——你如何要求他坚持所谓的“出版理想”和“文化情结”,重塑自己的“出版之路”?
这不是“一个人的困境”,而是一种“体制性的困境”——出版人在自身职业生涯之中所面临的“行业性困境”,不过是中国人在这个时代普遍遭遇 “集体生存困境”的浓缩和映射。一方面,信仰追求和理想情结缺席,功利主义导向,“以市场为中心、以效益为中心、以利益为中心”的价值观取向,导致整个出版界必须“媚俗”,才能养活自己——如果你连自己都养不活,明天的太阳再好,都跟你没有关系。
十年里,畅销书、类型书、跟风书甚至伪书潮起浪涌,源于此。另一方面,当建国60年以来习惯于“宏大叙事”的中国人,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里逐渐发现重大的世界事务完全在我们的掌握之外——“这个世界是靠少数有权势的人运转的,小人物没有什么可为的”;而个人事务又往往控制着我们——“有时候我感觉无论如何都不能控制自己的生活”——尽管我们无不努力用双手牢牢掌握着自己的方向盘,但“无论我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按我的方式进行!”于是,“大叙事”必然转变成“小叙述”,“大历史”让位于“小历史”,“大时代”就成了“小时代”—— 这个时代就是一个“小时代”,人人都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寻找“小温暖” “小清新”“小亲爱”……而对自身周边的大世界和大时代“漠不关心”,或者说“无力驾驭”——所以,我们只能一起“自媚”:我们取悦不了别人,至少能够悦纳自己。十年里,相当数量的图书品种都仅是从“编辑个人的兴趣”出发来策划的,就是从此而去。
这是两种支配着出版人的极端的思维方式。从“媚俗”到“自媚”,就像一个彩虹一样的光谱,中间还有很多“轨迹点”,我们可以一一在上面找到自己的身份和位置,什么都有,当然也有所谓的“出版理想”和“文化情结”。只是被挤压得只有喘气的余地,以及,残存某种“予人玫瑰,手有余香”的味道。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说,要谈论出版人的理想,实在是一种很奢侈的行为。
然而,我们又不能不谈。人异于动植物,就是人是“能够思想的芦苇”;而出版业,更是让人在思想的大地上行走的职业。如何不谈,我们又与其他人何“异”?何必非要在人前面加一个“出版人”的界定。这表明,我们在像其他人一样变得更加现实(做书就像印钞票,或者,我们自己也要变成一台赚钱的机器),或者一样逃避现实(对现实生活无力驾驭,对他人漠不关心时,只关心自己杯中的小情小绪)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承担一些东西:这个行业、职业或事业,赋予了我们一些需要担当的东西——但那真的不是“理想”“责任”“使命”等等空洞的字眼、虚无的概念和抽象的原则,而是做人做事的那些最基本的事儿,是基于人性、人际、人伦等基础性的东西,是让我们落地生根的东西。
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来说——2012年,我有个朋友做编辑正好做了10年,聊到这个话题时,她突然问我:“一直做书、做书、做书,你没有厌倦?”她说她现在不但是“厌倦”,甚至是“厌恶”——总是在重复,不断地核算,仿佛永远没有尽头。我很认真地想了想,说,假若我不是做工作室,假若不是在探索新的出版模式,并且把她所说的那些重复而无意义地东西,转嫁给工作室内外的其他人,假若我一直还在做图书编辑,假若我在2012年没有一个“身份”的重大变化……我也是会厌倦的——但是,现在,我似乎重新发现了做图书编辑的意义。2011年到2012年,我做了现在8个月大的女儿的父亲。这改变了我整个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职业观和事业观。
然后,在iPad等新媒体的变局之中,我开始探索童书以致图书的基本阅读功能。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之中,我不断重复地发现这几个基本的事实:第一,国内童书的出版泡沫化繁荣到了极致,书多到你都不知道如何选择的地步;第二,国内童书的出版已经跟国际接轨到了相当令人惊诧的地步,国际上知名的童书90%的都有引进版,剩下的10%——“噢,正在洽谈版权之中”;第三,童书的版本也混乱到了让人无从选择的地步,不要说那些年轻的、行业外的爸妈,就连我们这样身在出版业的从业人员,也很难鉴别童书的各种版本。要知道,版本的微妙差异,对于孩子的阅读和未来有着难以低估的影响……这使我意识到一个很基本的、但却是核心的问题:当童书的品种“繁荣”到了泡沫化的地步,从孩子到家长的“阅读者教育”却是残缺的,甚至,就连从业人员的“出版职业准则”也是缺席的。
童书如此,青少年读物如此,两性读物亦如此,那些经管励志读物,其实也是如此。我们只管出书,却不管如何选书和如何读书。所以,这其实无关“理想”“责任”“使命”等概念性的命题,而是关系我们做人做事的基本常识和基本准则。有了父亲和出版人的双重身份,在看书、选书和做书时,就会有一些迥异于以前的态度和观念。推导开去,出版业缺的,其实不是宏大的“出版理想”和“文化情结”,缺的,其实是做人的底线伦理和做事的高标准则。否则,文化繁荣发展得再花团锦簇,我们仍然会像是一具没有灵魂的巨人的空壳躯体。因此,我以为,出版业其实是“最后一个阵地”——是让中国人变得更加现实或逃避现实的这个浮躁的大时代的“最后一个上甘岭”。假若整个社会在底线伦理和道德准则都已经沦陷的情况之下,出版应该保留最后一块希望的净土,尤其是孩子、青少年,以及我们的身、心、灵。假若出版人也像其他人一样,在大多数职业生涯之中,不得不媚俗,或不可避免地自媚,那么,至少,应该有那么一炷香的时间,还能够保有希望和追求——因为,我们是父亲,是儿女,是爱人,或者,对整个社会来说,我们是一个还有点希望的“熟悉的陌生人”……
这真的是一个最低的做人做事原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以为,出版人在2012的困境和纠结之中,的确应该做做加法和减法。但是,减的,未必是变得更加现实的媚俗,或者,更加逃避现实的自媚;加的,也未必是所谓的“出版理想”和“文化情结”——这就像挂了一块遮羞布。有很多人都宣称自己出的书都是基于某种“出版理想”和“文化情结”——“亲,我不知道你们相不相信,反正,我是不相信的”。但是,如果有人说,他(她)是基于父亲、母亲、爱人或者其他有底线伦理和道德准则的角色,来做童书、两性读物等,我会欣欣然地拭目以待:他(她)可能会犯错,会走弯路,但是,他(她)走的,很可能是我们应该走的,真正正确的“出版道路”。
减掉空洞的概念,加上做人做事的底线伦理和道德诉求,即使今天我们集体媚俗、普遍自媚,明天,我们仍然可能会拥有一个灿烂的朝阳。出版如果还有明天,难道不是就这样给出版人的今天做加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