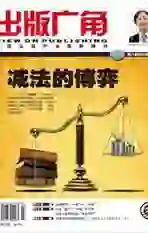集团化后的集约化
2012-04-29高立志
没有一个出版抱负,或者说一种文化传承和弘扬的抱负,出版集团只是一个利益团体,甚至只是一个政绩工程。
现在出版集团多起来了,有的以地域相近而联合;有的以业务相近而联合;有的以上市愿景而联合;有的以主管单位相同或相近而联合;当然还有些联合的秘密外人不易揣摩 。笔者作为这些集团的外人,想知道的是:究竟哪些联合是出于出版社发展需求而主动寻求的联合?这些联合是否是基于出版抱负的重大举措?
追求大,一直是政绩工程的标志,只需要协调相关领导的职位就可以搞定。但如果做大之后要做强,仅靠行政手段就不那么好使了。在出版集团林立的时候,要做强,笔者以为该做做减法了。
首先应该从管理上做减法。出版业有一定的行业特殊性,其科学化管理无疑需要一定的专业素养和经验积累,并不是谁都可以领导出版。出版业的领导遴选,不应该是主管部门拍脑门的事情。主渠道和民营渠道书业最大的差异,就在于管理。主渠道负担累累,要养活几个阶层的领导不说,用人成本也非常高昂。主管出版人才引进的人大概不会否认:出版业的行业感召力在下降。新近涌入出版业的很多年轻人,带着诸多这样那样的背景,出版业乐于纳进他们往往是为了维护领导的某些关系。不少出版新人不适合做编辑,也不愿意卖力做发行,于是涌入了出版业的管理部门,然后熬到管理层。管理部门的庞大,只是使领导出门很风光,但图书成本因此急剧增高,有的出版百年老店宁愿把出版业务外包,来增加效益。非常多的出版社管理部门人数都超过了其核心业务的编辑部门,这严重削弱了编辑的积极性——一个人干活,有几个人看着;外行管理内行,出版社管理被变为圆形监狱管理,这样让编辑多窝在单位,出版创意无从产生。即使有一个好的出版创意产生,也会被层层审批消磨掉其本身的激情,更致命的是:拖慢了出版节奏,延误了最佳出版时机。管理部门庞大还有一个潜在恶果:出版的专业特征逐步丧失,出版社陷入尾大不掉。
第二,并非其次,要从选题上做减法,减少重复出版和跟风出版。如果说,以前各个小出版单位各自为战,为了生存,或者趋利(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不存在顺畅的沟通机制,重复出版在所难免;那么现在在同一个集团的领导下,不同兄弟单位的重复选题无疑是管理高层的失职。其实,集团化对选题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哪位或者哪些集团领导有责任有能力来规划选题,协调选题,优化选题?毋庸讳言,管理高层是目前出版的瓶颈。我们必须统一认识:重复出版是对自然环境的犯罪。浪费人才倒在其次,浪费纸张,浪费木材,垃圾图书涌入市场又形成环境污染,大大污损了出版的行业形象。
第三,并非最后,要从图书质量角度做减法。出版集团高管层应该对所属各单位的优势,各编辑的专业背景和优势有清晰的认识,并不是每个出版社都可以做国学读物,也不是每个编辑都可以做学术书,更不是每个编辑都可以做青少读物。即便是门槛较低的教辅也需要其特殊的素质,起码应该明白,目前社会对老师、家长和学生的新要求,好的教辅策划编辑还应该能够把握未来教育的动向,做出符合时代潮流的创意来。
我们承认:集团化有集团化的优势,除了优化选题外,还可以集中力量优化图书质量。统一集团下,也许甲出版社提出一个好的策划,但其编辑实现这个策划有难度;是不是可以联合乙出版社来完成?也许乙出版社的发行渠道限制了一些图书的销售,是不是可以借助丙出版社的渠道?当然,这里面有名分问题,也有利益分成问题,集团管理层能不能协调好?另有一些攒稿和资助图书,质量非常低劣,被甲出版社拒掉以后,能不能被同一集团下的乙出版社也拒掉?出版业不该盲目助长学术界浮华逐利的风气。特别是一些国字头,“人民”和“教育”字样的出版集团应该有这个责任来担当,出版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不管怎么说,它还属于国家意识形态的范畴,还没有专门的法律做保障。就是在这种有些乱无象的时代,抱负才显得尤为可贵。有所不为,有所必为才是真正的道义所在。
出版集团内部资源最好要带有互补性,而不是富人俱乐部。早些年,某核心大城市为了打造文化品牌,成立出版集团,先把一些效益比较好的大社网罗为一家,摒弃了该地最有历史也最有古籍专业性的一家出版社的理由竟然是:它效益不好。没有一个出版抱负,或者说一种文化传承和弘扬的抱负,出版集团只是一个利益团体,甚至只是一个政绩工程。出版业好歹算个文化业,如果在古代,起码是一个代表一种清议和舆情,它能否坚守底线,别主动凑近某些领导的政绩工程而自残。做大,并不是做强。做强也并非非大不可,大而弱实在是一种耻辱。现在有些民营渠道成长很快,前几代投机性书商逐渐淡出市场,这里涌现了很多不仅懂市场还有抱负有理想的人,例如青豆书坊的苏元提出:“市场之上拥抱理想”,例如启蒙编译所的汪宇坚持做高端学术图书策划。他们的公司都不超过10人,创造的图书品种也寥寥,但实现的图书码洋很惊人。这些在市场中寻求理想的出版人代表了中国出版的未来。
出版集团应该学学那些优质的民营渠道,看看他们如何打造产品,如何压缩管理成本的。当然,也有不少效益可观的大书商靠套出版社的钱,出版社靠套纳税人积攒起来的国家的钱,甚至上市套股民的钱。这个恶性循环链,出版集团是不是应该警惕,应该努力掐断这个链条?我并不认为出版集团把钱拿出来做别的事业有什么过错,毕竟出版业因为其相对的稳定性和比较长脸,也汇集了其他行业的钱,但这一切终非正途。出版集团的钱能够被限定在投资狭义的文化产业上?做出版和房地产、买盐卖盐终究不同,能够在几个领域纵横驰骋的不是天才就是骗子。特别是上市公司,股民把钱投进出版集团,是基于对文化产业的信任,希望相关管理者别毁了股民的信任,别毁了出版的行业形象。
出版集团应该从做“减法”的角度想想,如何扩大这个行业的吸引力,还有很多的事可以做:能否压缩成本给读者提供一些优质低价图书,在国民教育方面贡献点力量?书业的一个顽疾是价格的不平衡。就成本而言,中国图书定价太低了,甚至养不起一个高水平的作者,稿费多年原地踏步;但就国民平均消费能力讲,中国图书定价还是太高了,这就给大量盗版书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例如四书、前四史、四大名著,中国市场需要一个经典又廉价而适应于普及的本子。能否从选题角度协力掐断投机攒书的生路,不要只瞄着那点赞助费或者书号费甚至好处费,为书业的健康做点贡献?能否避免恶性竞争,哄抬引进图书的价码,客观上形成外人对我们中国书业的歧视?哪怕引进一些收藏界的买卖规则也好,应该杜绝让同一种引进版图书的各种形态和似是而非的各种原本或者修订版本充斥中国市场。
该是认真想一想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