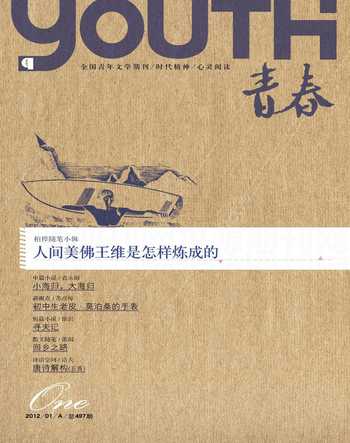等待下一次的偶然
2012-04-29安石榴
她蹲了下来,非常急切,厕所就在几步之遥,可是她知道自己跑不到那儿了。她太贪玩儿,玩得等不及去厕所。她蹲在仓房外墙下面,小小的园子里。她知道矮矮的辣椒秧、茄子秧遮挡不住她,她知道自己暴露在园子中的一条小路上,但是板障子很高,很密实,一张张平而宽的板皮夹起的屏障,可以保护她小小的却是满满的自尊心。
她蹲下来尿尿。透明的小河流急急地冲击小路上的浮土,一条曲折的小河流蜿蜒前行。这引起了她的兴趣。她只有五岁,对什么都好奇。小河流到底从哪里来的?怎么来的?她尽量把裤子往上拉,深深埋下头去,小屁股露出了些,可是还是看不到,她把头勾得更低,充满信心地去探寻,却突然像惊醒了一般停止了探寻。她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知道什么惊醒了自己的游戏,她只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惊惧。她抬起头来,一个男孩在半空中俯视着她,他笑咪咪地,食指一下下地刮他自己的脸,他在羞她!
她跳了起来,两条小腿磕磕绊绊往回跑。园子门虚掩着,一只刃口锋利的斧子拦在开合处。她仓皇奔来,踢翻了斧子,扑倒在地:“呜呜……妈妈呀……”
即使在这一刻,她也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男孩嘲笑的表情,眯起的眼睛,上翘的嘴角。
她还清清楚楚地记得,男孩左手搂着一只小小的梅花鹿,小鹿两只黑黑的眼睛,一眨不眨地和他一起看着她。
她羞得不行了。
她的右脚腕子被斧子划开一条口子,出了很多的血,她还没流过这么多血。
后来,绷带撤下来,缝线拆下来后,她再也不会贪玩儿到忘记上厕所了。她跟妈妈要求离开妈妈爸爸的房间,去和姐姐们挤一铺炕。她还知道换内衣时避开姐姐,她哭着喊着逼迫姐姐们转过身去,不许动。姐姐们把妈妈拖来,指着她说:瞧,这个小土豆知道害羞啦。
的确,她有了一点小小的心事儿。
从前她还不会自己玩儿,她一定要和小朋友或姐姐们闹在一起才高兴,要不然就死缠住妈妈,现在,她能安静地独处一些时候。
她坐在后园子中隐秘处一堆板垛上,两只小手搂着自己的腿,把她的小下巴抵在膝盖上,团成一只蜗牛。她静静地呆着,什么也不想,她会想什么呢?她的耳朵和眼睛追随着细细的风声,那些可爱迷人的声音,那些可爱迷人的摇动,总是从海棠树繁重的枝梢开始,轻轻的,长长的“刷……”,海棠树最高处慢慢地摇动了一下,马上一切都跟着积极地响应,树下的扫帚梅五片的花瓣迅速地翻了过去再翻回来,只有风才让人知道,花瓣的两面会是那么的不同;成片的藿香、茴香紧接着熬起中药来了,散发出浓浓的苦艾艾的味儿,一股一股地播散,不厌其烦;苞米似乎不想动,但是它们还是忍不住发出窸窸窣窣的“沙沙”声,于是,苞米穗子上停着的一只蜻蜓长长的尾巴卷了起来,翅膀颤着颤着,终于站立不住,有点趔趄地飞起来了。她看得出来,那只蜻蜓并不想飞走啊,它游移不定地嗅了嗅另一棵苞米长长的叶子,还在一朵藕荷色的豆角花上徘徊了一小会儿,最后选择了振翅高飞,翻过板障子不见了。哪里去了呢?她不知道,总之会飞得很远吧。天湛蓝湛蓝的,有白云匆匆而过,她想了想,还是不知道。可是,那只蜻蜓却像是融化在白云里了,没了踪迹。
她又呆住了,后园子也不能像从前那样长久地让她沉浸在无忧无虑的喜悦里了。那个男孩食指还在刮着脸羞她,小鹿黑黑的眼睛还是那么专注。她把头埋下去,漆黑厚重的童花头遮没了她的小脸。好久,她眨着湿润润的眼睛,又偷偷地笑了,有一点儿觉得他不是嘲笑她。
男孩长成了一个小伙子。长成小伙子的男孩对童年的记忆越来越少,他把通常男孩子那些“刀光剑影”的记忆潇洒地升华为恒久的哥们情意,可是,内心的一隅总有一处静谧的所在,仿佛秘密储存着的一个宝盒,偶尔打开一次,那个小巧的女孩子总是愣怔着盯着他。厚厚的黑头发像一朵浓郁芬芳的花朵,齐齐的刘海遮住了眼眉,齐齐的鬓角只露出两个亮晶晶的耳垂儿,衬得她的眼睛是那么的大,那么的深,那么的亮。只那么一瞬间,却让他永生不能忘却。他现在想起来,用一个成熟男人的目光回首,小女孩就那么黑洞洞地看着他,他知道小女孩的目光比他怀里的小鹿还天真无辜。那样天真无辜的小女孩,突然之间现出的惊恐和害羞,仅仅为了他食指刮脸那个“下流”动作吗?是他一个顽劣的手势,伤害了她珍贵的童真吗?
今天是周末,他难得宅在自己的单身公寓里。城市的云端处连风都难以光顾了,他拉开窗户,和他猜测的一样,城市的表面永远风平浪静。从他的窗口看去,绿化园林更像人为画上去的标识符号,也像楼盘工地上广而告之的宣传版效果图,或者售楼中心大厅展示的模型沙盘,全无生命的细胞。有生命的东西都在遥远处,时间的前面……
他记得那一年他八岁。举家从大山深处一个叫做大石沟的林场,搬迁去八百里之外的林管局所在地牡丹江市。所有的家当都被学工科的父亲妥帖地放置在解放牌大卡车里。姐姐和妈妈坐在驾驶室内,他和父亲就稳坐在高高的家什上面。父亲简直是在半空之中、透明的风里造了一个温暖安全的小窝,父亲就在他的小窝里心满意足地躺平假寐,谁知道,也许真的睡着了呢。路过石河林场时,汽车缓慢地穿行在一趟趟白墙红瓦之中。他怀里的小鹿突然微微颤抖了一下,挺直的脖子转向一边,他知道小鹿发现了什么感兴趣的事情,他的目光追随着寻了过去,就在这时,小女孩完全暴露在他的面前了。
女孩家就在路边,板障子挡住了解放车的大箱板,可是,他在更高处,远远超越了大箱板的高度,如同舞台之于台下第一排座位的关系,如同君临下界,真相大白。
他羞了她,只是觉得好玩,女孩慌张着逃跑了,随后在一片浓郁蓬勃的绿叶下面,传来女孩的扑倒声、被撞的木门发出摇摆不定的翕张声和尖利的哭声,他的心揪起来了,他知道这些声音和自己的关系,他尽可能地探出身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是,卡车把他带走了,小女孩的哭声不见了,整齐的小园子随即消失。
好长时间他不能释怀。有时候,他玩着玩着会忽然想起小女孩,她怎么了?为什么有噼噼啪啪的声音?她受伤了吗?伤在哪里了呢?重不重啊?他会因为这些问题把自己搅得心神不宁。
以后的日子里,当他长高长大,需要每天刮胡子的时候,看着自己身上的肌肉块子,他渐渐地明白,他喜欢那个小可怜儿,他没有嘲笑她。
等他和女朋友分手、复合、再分手、再复合不断的折腾,以致重新有了女朋友的时候,他想,他喜欢的那个小童花永远是个小童花,那个小可怜儿,他没有真的嘲笑她,他喜欢她。可是她那么一丁点儿,似乎永远就那么一丁点儿。
他默默地在心里笑了一笑,有个潜意识的思绪,轻风一样拂了一下他的脸,柔柔的,有一点惬意,有一点哀愁:美丽的小童花!她是他的一个少年梦而已,只适合暂短的回味。
他都没有想象过小童花儿长大的样子,是啊,梦醒了之后,谁也无法再回到那个梦里啦。
她在一派明丽而温柔的春风中,一条繁华不尽的大街上,行走,大步行走。
她高挑的身材,匀称修长的四肢,优雅的步态和时尚的装扮,是这个大都市炫彩的元素。只是她的眼睛,如孩童般大而清澈的眼睛,不属于繁华之地的风情。
她在大步行走。长长的双臂轻轻地荡漾着,一小节细而结实的小腿也轻轻地荡漾着,她给予脚上的力带着路人不知的深意。一股清风倏地云一样掠过,她立即驻足,纤细的手小心翼翼地去轻拂一头黑发。
她刚刚从一个叫做沙宣儿形象设计室出来,顶着一头童花。
她的头发一丝不乱,城市的风更像一种风情,只缭乱人的心境。
她的头发一丝不乱,和她的心一样,不起微澜。
她有一个近乎决绝的想法,这个想法来自于她的梦。
昨天晚上她做了一个梦。是的,她为什么剪掉了多年精心护理的一头长发?为了昨夜的一个梦。
这个梦更像一个截图,没有前因,也没有后果,他就那么突然地出现在她和他的私密空间里。他们都长大了,他待她很亲切,他正像她期待的那样高大、稳重、细心。
她怎么就知道他就是那个长大的、一直羞着她的那个男孩呢?没有交待,她就是梦醒之后,拼命回忆,也无从想起,但是,她知道,并且笃定。
就那么没有前因,没有后果,没有羞涩、等待造成的焦虑,也没有怄气、误解演绎的烦恼,更没有金钱、礼物的累赘,他和她直接走进彼此的心里深处,进入美丽的故事情节。
她依偎着他,诉说了所有的委屈,从她脚腕子受伤,到情窦初开的少女时期,直至上大学、工作,她因为他而不能恋爱。她倾诉她的烦恼,她不能忘了他,可她又找不到他。她甚至回到过那些深藏在大山里面的林场,可是仍然寻不到那个羞着她的小男孩的任何踪迹,因为他除了他羞她的顽劣表情,再也提供不了任何信息。她诉说着,真的好委屈,眼泪一颗一颗地流下来,他就一颗一颗的吸了去。她轻轻地呜咽,他就热烈地呓语,我的小傻瓜,我的小傻瓜!
他寻找她的脚腕子,一个泪滴样子的突起。他向那颗粉色的泪滴埋下头去,温热柔软的嘴唇仿佛要化解二十五年来时间叠起的迷雾,直抵一个五岁小女孩的心灵。她感觉到了热流,电一样迸射着火花向躯体飞窜。她痉挛般地哦了一声,低下头,伸出手,拉起他,他们拥抱了……
她醒来的时候,空洞的黑暗之中,仍然缭绕着热烈的呢喃与低回,她聆听着她们,来自幽邃隐秘花园的天籁之音,直到她们又一点一点零落并回归空洞的黑暗之中。
她打开灯,起身,慢慢地踱到梳妆镜前,坐下,燥热的嘴唇,爆动的心跳,湿润的身体,让她一览无遗。
一切都静止了,只有思绪飞扬。她就那么坐着,坐着。
当灿烂的晨光汹涌地投入到她的梳妆镜里的时候,她有了无比清醒的头脑。她微微地对着镜子笑了:谢谢你。她默默地说,我终于可以把你放下了。
她觉得完成了一件生命中的大事。她的那些同是一九七八年出生的女朋友们总在戏谑她,她想她可以告诉她们,那个她们口中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后一个处女终于不存在了。她不再是一个另类。
也许因为是一个梦,火爆的女友们还会笑她,但她不在乎,她感谢那个梦,虽然她的身体一如从前,但那又有什么呢?梦里,她的灵与肉都有了最美妙的归宿。也许,她当然相信那是最好的,虽然暂短,仅仅一个梦。而且,一辈子又能怎样呢?关键是,她想,她可以大步向前了。
她大步行走,因为她刚刚剪了她一头飘逸的长发。此刻,她顶着一头类似五岁时的童花短发,是告别还是诀别呢?
她大步行走,目的地是前面的地铁车站,她要在那儿乘地铁去见一个男人,她心里称那个男人是优秀的,那个男人真的已经追求她很久了,而且,如果感觉好,她相信她会考虑对方倾诉给她的人生计划,随着那个男人去深圳。
今天是周六,他难得有一个不加班的周六。
他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约会,约会对象是他的女同事。这没什么特别的吗?可女同事已婚,他承认他是第一次玩这种心跳。
他早早地起床,打理自己。一路的歌哨追随他这儿、那儿的忙碌。
他喜欢这个……偶遇。也可以称作冒险。那么他就是喜欢冒险。和女同事在办公室交欢是他这一段情感的第一个创意,他一直在烘焙女同事在家里偷欢的热望。他知道女同事的丈夫没有离开这个城市,他喜欢这样的刺激。女同事的丈夫今天加班,他知道这里面有变数,可是他喜欢隐藏着的变数。冒险,因而刺激。他对着镜子抖了抖胸大肌,强壮的胸大肌加大了他承担风险的系数。
似乎要验证自己的体魄,他没有坐电梯,从十楼狂奔到地面,心脏起伏着的是兴奋的律动,不是力不从心的衰音。
他开着车整整奔跑了一个小时,去一家很有名的情趣内衣店。他要送女同事一件礼物,一件很特别的内裤。它的尺度当然是成人的,创意却取自幼童的开裆裤。他把它拿在手上的时候,并没有像愣头青似的亢奋,却莫名其妙地,心底的小童花突然冒了出来。他想,那时候,小东西如果穿着开裆裤,就不会那么让自己吃力了。他的心跳了一下,也许是习惯。虽然他已经太久没有想起小童花了,可是,只要小童花一闪,他就歉疚。
他从店里出来,朝着车的方向操作电子钥匙,没有反应,才发现车不见了。旁边的闲人告诉他被交警的叉车拖走了。他的右臂向天空用力挥了一下,就朝着地铁站走去。他去赴约,他不会因为车不见了就不去见美人儿。
进入站台,很巧,两列相向的地铁均已进站,一个人匆匆超越了他,那是一个修长高挑的女人背影,迅速吸引了他的眼球。他的眼球总是对美有超常的敏感。因为疾走,那个女人短短的头发流苏一样传递着一种醉人的俏皮。女人向一列地铁冲去,他觉得很遗憾,他不仅不能看到她的面容,还无缘与她同乘。他向对开的另一列走去。
他乘的这一列地铁缓缓启动了,他的眼睛在对面的车厢里搜寻,看到那个高挑的女人站在车门前,整个人被框在窄窄的门玻璃里,像一张平面广告那么醒目。她正专注于接听电话,小小的脸深深地倾下来,一双大大的眼睛却一同向上注视,厚厚的童花头遮盖了她的眼眉,那双眼睛夺人心魄。千分之一秒之中,他把他眼前的景象和二十五年前小女孩儿的脸重合在一起,他下意识地,然而又是迅即地举起右手,展开食指,在他自己的脸颊上刮动。可是,那双大眼睛一定流连在她电话里的情景当中,地铁在加速,转眼即逝。他知道,对面,她,没有看到他,更没有接受任何暗示。
他的心飞翔起来,他发现,二十五年漫长的酝酿,一颗成熟的果实终于从豆荚中炸裂出来,他甚至听到了叮叮咚咚急促下落的声音。他的眼睛立刻充满了泪水,小童花,我的小童花。不会错的,你就是我的小童花。是的,他从来没有想过小童花长大的样子,可是,他笃定,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她。
这时候,他的手机响了,女同事的号码在跃动,他短促而清晰地说:对不起,我不能赴约。随即按下键子。
地铁一停,他第一个出来,等到对面的车迅速返回上一站。他当然知道她不可能在了,他知道她坐的地铁早已跑出好远了。可是,几乎就在刚才、十几分钟之前,她走在这个站台上,从那么高的台阶上一路小跑下来,并从他的身后超越他。他和她曾经那么近,只有一肩之隔,比二十五年前的第一次相遇还近。然而,他仍然找不到她的踪迹。就像他在高中毕业那年,利用上大学前的时间,偷偷回到那条山路去寻找她。可是他到了那个曾经叫做石河的地方却没办法下车了,一片落寞的破败样子。乘务员告诉他,这里是莲花湖水库将来的蓄水区,林场解体了,这里的人都分散搬迁了。
他倚靠着站台大理石圆柱,回望那一段高高的台阶。清澈的空气悄无声息地充盈着偌大的空间,它们不知道怜惜他,要么为什么不能在空气中保留或复制她的音容呢?
四条铁轨运送无数的人来来往往,在交替的空寂和喧嚣中,他孤寂成一棵树,一棵倔强的树。
这一次,他要倔强到底了。就在他“炸开”的那一刻,他就全明白了。他愿意自己是那棵长了二十五年的树,任谁也拔不掉的树,任谁!
他是怀着希望的,他希望这里是她固定乘地铁的站点,是她出行的必经之路,不是她的偶尔选择。
那么,他随即又想,就算是偶尔选择,他也要等候她下一次的偶尔。
这一天地铁关闭的时候,他疲惫地向出口走去,他已经有了打算,从明天开始,他不要他的工作了,连所谓的前程一并抛弃。从此以后,他将守在这个站点,直到他等到她。
是的,直到他等到她。
责任编辑⊙裴秋秋
作者简介:
安石榴,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2008年全国小小说新秀选拔赛第二名,新世纪小小说风云榜明日之星。《关先生》获《小小说选刊》全国小小说佳作奖,《大鱼》获《百花园》全国小小说原创奖。作品被收入《中国小小说大系》,漓江出版社、花城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等多种版本的年度小小说精选。出版小小说集《全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