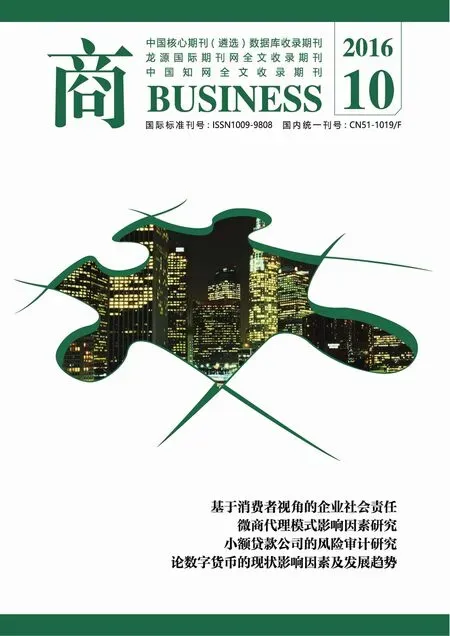詹姆斯·罗宾森:中国最大挑战是如何实现包容型制度
2012-04-29
2012年3月,哈佛大学的詹姆斯·罗宾森教授(JamesRobinson)和麻省理工学院达隆·阿赛莫格卢(DaronAcemoglu)教授一起出版了著作《国家为何失败:权力、繁荣和贫困的起源》(WhyNationsFail:TheOriginsofPower,ProsperityandPoverty),引发了国际政治学界的高度关注。在这本书中,两位教授比较了两种制度,即萃取型制度(ExtractiveInstitutions)和包容型制度(InclusiveInstitutions)。
他们认为:“国家的经济成功程度不同,是由于制度不同、影响经济运行状况的规则不同、激励民众的奖励手段不同。”“萃取型”经济制度目的是牺牲大众利益来确保少数人的富裕。“包容型”经济制度的宗旨是让所有人平等地参与经济;而萃取型的政治制度会创造出萃取型的经济制度,包容型的政治制度会创造出包容型的经济制度。
该书也被认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后进工业国的种种政治问题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但同样也引来很多的批评和质疑。《时代周报》独家对话该书作者之一、世界知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者詹姆斯·罗宾森教授,探讨相关的议题。
经济增长并不会必然促推政治改革
时代周报:很多人评论,你的书对分析“中国模式”有着重要的意义。你是否认可有所谓的中国模式?
詹姆斯·罗宾森:我并不认为有所谓的中国模式。从1978年起,中国政府停止了那种试图控制经济生活中所有方方面面的计划经济模式。比如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在乡村地区采用了具有刺激效果的“分产到户”的家庭责任承包制,结果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但是这些经济政策谈不上一种模式,因为仅仅是在经济上的放松管制,虽然由此产生了高速的增长,可是并未改变政治上的权力集中。
时代周报:至少现在从表面上来看,中国的经济形势还不错,而美国和欧洲正处于相反的状态中,这是否如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因为中国模式的优越性使然呢?
詹姆斯·罗宾森:在过去一段长达40年的时间里,每个人都在讨论,苏联已经创造了一种特殊的经济模式,并且可以凭借这种模式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但是最终苏联解体了。
同样,美国和西欧在上世纪30年代和上世纪70年代都经历过很黑暗的低谷,但是他们最终反弹成功。我说这些并不是一种自鸣得意或者自我吹嘘,究竟何种原因,值得研究。
时代周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成为世界级跨国巨头,不少还成为了自己领域的头号王者,这是否能够成为一个为中国经济模式辩护的重要论据呢?
詹姆斯·罗宾森:允许我做一个反问,中国是否在技术领域拥有领导权或者优势呢?我对此深表怀疑,我相信这也可以作为我的答案。
时代周报:你在书中提到西班牙模式和英国模式。西班牙和英国都曾受惠于地理大发现的成功,但是之后两国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财富让英国的资产阶级变得强大,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而西班牙则加强了封建专制并很快陷入了长期的沉沦。你觉得中国会在未来走哪一条道路?
詹姆斯·罗宾森: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制度变得越来越向“包容型”靠拢。经济增长有可能会刺激经济制度的改良,催生一个中产阶级,从而促进政治上的变化,就好像在台湾发生过的一样。但是这不是必然发生的,也有可能出现一种结局,即政治层面的挑战反而废除了目前的经济模式,犹如曾经差点发生的那样。要预测中国是走英国道路还是走西班牙道路是非常困难的,就如我在书中指出的那样,即使是看似接近的体制,也有差异性,还受到一些外界因素的影响。但是一定要我说一个答案的话,我个人认为中国可能会走向西班牙的道路。
这个环境并不是为了中产阶级而设计的
时代周报:中国的精英阶层正处于一种困惑,即他们总体认可必须采取该改革措施,让国家走向更现代的制度,但是他们非常担忧失去经济的高速增长、陷入分裂和内乱。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詹姆斯·罗宾森:我的建议是,目前中国的政治改革并没有和经济发展同步,在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下,这种“状况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不在政治层面做一些改革的话,很可能会丧失掉经济改革的成果。
时代周报:中国的中产阶级正陷入了一种极度不安的境地,他们担忧通货膨胀,担忧各种生活物资价格的上涨,也不满于目前的法治和行政环境。你是否认为一个国家应该全力防止中产阶级的衰落和陷入不安呢?
詹姆斯·罗宾森:这个问题其实让我有些困惑,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造就了一个新的中产阶级群体。毫无疑问,他们显然生长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这个环境的制度和系统并不是为了迎合中产阶级的需要而设计的。当然,出于寻求稳定的需要,国家可能会作出一些改变来帮助中产阶级。
从历史上看,很多内乱发源燃烧于乡村地区,但是在目前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下,显然已经不同了。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认为那些城市精英更有可能形成冲击。
重大的政治改革是先于经济改革的
时代周报:你认为当今中国面临的最严峻挑战是什么?你是否认为中国有能力跨越这些挑战?
詹姆斯·罗宾森:简而言之,关键在对于中国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去实现朝“包容型”制度的转变。关键在于能否建立一个能够让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得以保存的社会。
时代周报:简单来说,你的理论能否理解为政治改革必须先于经济改革,而非我们传统理解的用经济改革推动政治改革?
詹姆斯·罗宾森:其实我们看中国的历史,就会发现实际上重大的政治改革是先于经济改革的。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末期,“四人帮”被打倒了,“文化大革命”被推翻了,整个中国有了巨大的改变。尽管这不是朝向民主制度的改变,但依然是非常重要的。我的书并不是说为了更好的经济制度,就需要政治民主,但是需要让政治和经济制度相匹配。当然了,那种认为经济增长就会带来更好制度的观念也不会得到统计学证据的支持。
时代周报:你在书中论述发达国家被大垄断企业(特别是大银行)绑架,而有转型为掠夺制度的危险。这会是一种现实的危险吗?
詹姆斯·罗宾森:是否会发生这种情况,要取决于一个官僚系统的组织方式,比如公务员是如何被选择,是不是符合精英治国的理念等。如果在普惠型的社会制度下,公民的权利是高于官僚系统本身的职权的,在这种状况下,是不会发生类似的问题。(据《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