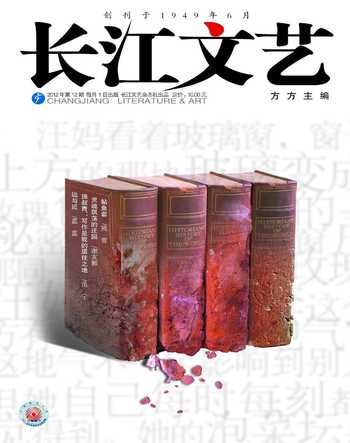鲇鱼套
2012-04-29残雪
残雪
汪妈看着玻璃窗,窗子左上方的那块玻璃变成了玫瑰色。
这是汪妈的一个秘密:每回她一看窗户,那同一块玻璃就变成了玫瑰色。
汪妈认为鲇鱼套这个地方有一种特殊的“地气”, 这地气不一定影响到别人,
但她自己每时每刻都感觉得到。
她的泡菜坛是首先享受这地气的。
半夜里,她清晰地听到坛子盖边上的封坛水“咕噜”一响,立刻就会闻到泡菜的清香。
这个地方叫“鲇鱼套”,是靠近市中心的一片两层木楼,汪妈就住在一栋木楼靠左边的那个房间里。她是孤老,去看望她的熟人也特别少。这地方快要拆迁了,拆迁之后,所有的人都要搬到高楼里面去。人们对拆迁有种惶恐情绪,都在相互打听:“住高楼是好还是不好?”只有汪妈对拆迁的事毫不在意。拆迁通告送到屋里来时,汪妈正在整理她那个巨大的泡菜坛子。她抬了抬头,对工作人员说:
“放在茶几上吧。”
然后她用筷子夹起一个鲜红的长辣椒,仔细地码到坛子的底边。接着又码了两块黄灿灿的老姜。
“您对补偿方案有什么意见?”小伙子问道。
“没有意见,没有。你走吧。”
那人像猫一样溜出去了。汪妈低着头忙乎,她将青梅,豆角,小黄瓜,榨菜头等一样一样地放进泡菜坛。她每放进一种菜,就闭上眼想象一会儿她将美味放进口中时的感觉。当然,她并不是光给自己吃,这么大的泡菜坛,她一个人吃不了。瞧,那两个小家伙不是在探头探脑吗?街头的大炮和二炮,两个馋鬼。
汪妈从床下拖出另外一个较小的泡菜坛,揭开盖,熟练地夹出一块刀豆。那两兄弟立刻跑过来了。汪妈将刀豆用手撕成两块。
“我要这块!”
“我也要这块!”
“闭上眼!”汪妈严厉地说,“好了,出去吧。”
两兄弟一阵风似的跑了。
隔了一会儿,又有人在探头探脑。是一个小女孩, 叫小萍的。她慢慢地走向汪妈,小眼睛溜来溜去的。
“汪奶奶,我想吃红辣椒。有青梅味儿的那种。”
“你得先告诉我,捡到了几分钱。”
“两分。”
汪妈唆使小萍整天守候在糖果店门口,如果有顾客掉下了零钱,立刻用脚踩住,等那人走了再去捡。对于这项游戏小萍乐此不疲,坚持好几个月了。
“给你辣椒。”
“谢谢汪奶奶。”
小萍用手握着辣椒,却并不马上吃,也不马上离开。她听大人说汪妈房里闹鬼,她想看到那个鬼,越怕越想看。
汪妈将泡菜坛放进床底下,站起来,转身走进后面的厨房,洗干净手,打算上床休息一会儿。她突然发现小萍站在她床上挂的蚊帐后面,嘴巴一动一动的,正在一点一点地啃那只酸辣椒。汪妈忍不住一笑,觉得这小女孩真会享受。
汪妈躺在床上,半闭着眼睛问小萍:
“小萍,你将来长大了要干什么工作?”
小萍没有回答。阴暗中,汪妈感到木床摇晃了一下——不对,是地面在摇晃!她猛地坐了起来,下床,穿鞋,往外跑。跑到门那里又停住,回过头喊道:
“小萍!小萍!!”
但小萍不在她家里了。汪妈想了一想,又回到了床上。
汪妈看着玻璃窗,窗子左上方的那块玻璃变成了玫瑰色。这是汪妈的一个秘密:每回她一看窗户,那同一块玻璃就变成了玫瑰色。汪妈认为鲇鱼套这个地方有一种特殊的“地气”,这地气不一定影响到别人,但她自己每时每刻都感觉得到。她的泡菜坛是首先享受这地气的。半夜里,她清晰地听到坛子盖边上的封坛水“咕噜”一响,立刻就会闻到泡菜的清香。她幻想着美味的小黄瓜,在这个国家的大地上走啊走啊,一直走到落日坠到地平线以下才停住脚步,隐没在一道长长的黑影中。这种时候,她就会喃喃地对自己说:“鲇鱼套啊,我的家乡。”
但是鲇鱼套却很快就要消失了。汪妈想,如果鲇鱼套消失,鲇鱼套的汪妈也会消失,她将成为高楼里的汪妈。这可是一件大事。是因为这,刚才小萍才躲在蚊帐后面的吗?这个女孩几乎是个万事通,什么都懂。
又一个小孩出现了。他先彬彬有礼地敲门,然后轻轻地推开了门。他叫小瑶,他总是这样谨慎,像个小大人。
“汪奶奶,我想念您的小黄瓜,就是有姜味和辣椒味的那种。”
汪妈睡眼朦胧地看着他,然后弯下腰拖出青瓷坛子,揭开,用筷子夹了一块小黄瓜给他。
他一本正经地吃着,口里发出脆脆的响声,两只圆眼东张西望。
“你看什么,小瑶?”
“我看见小萍进来的,没看见她出去,怎么她不在屋里呢?”
“嗯,这个问题值得好好想想。”汪妈说。
汪妈催小瑶离开。男孩还没走,汪妈的脑袋里某个地方就响起了铃声。她抬头一望,那玻璃上的玫瑰色光晕消失了,屋里恢复了惯常的阴暗。那铃声隔一会儿响一阵,很遥远。
“汪奶奶,是小萍在叫您吗?”小瑶盯着她的眼睛说。
“有可能。你看我有没有忘记什么事?”汪妈的样子有点紧张。
“泡菜坛子都盖上了盖子吗?”小瑶热切地提醒她。
“你真是个警醒的小家伙,可是这一回啊,不是那种事。”
“那我走了。汪奶奶再见。”
他匆匆出门,好像生怕汪妈再问他什么。
汪妈重又躺下了。男孩的提醒令她的耳朵变得很灵光,她大致弄明白了此刻发生在家里的某件事。白天她去买菜时看到了铲土机,拆迁要三个月之后才开始,为什么早早地就开来铲土机?小孩子们大概会很喜欢这种事,如果高楼竣工了,他们会在毛坯房里跑来跑去。
汪妈闭上眼,她觉得自己的思维可以深入到地底五百米处,那里有石英层,石英里有空隙,一些无害气体就聚焦在空隙里。她说:“鲇鱼套真是一块宝地啊!”她又感到了地震,这一次,她已经完全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这地方的小孩该有多聪明啊,她自己从前可比他们差远了。她不再惊慌,她连眼睛也没睁开,就这样享受木床的摇晃给她带来的惬意。但摇晃并不剧烈,而且很快就停止了。
那块玻璃上掠过一道玫瑰色的光,又还原成了普普通通的玻璃。她听到住在楼上右边的老女人云妈下楼了。她总是那样,下两级,停一停,下两级,停一停。她在楼梯上观望小街上的风景。汪妈想,鲇鱼套的居民全是些观察家,连小孩也不例外。此刻她又盼望再来一下地震,她要看看——她要看什么?难道她不是在胡思乱想吗?但她还是满心盼望,有些事是要等待才能水落石出的。
汪妈吃晚饭比平时晚了些,因为心里有件事没放下。
她吃完饭,快要收拾完毕时,床底下的地板就响起来了。汪妈心头一热,拿了手电筒去照床底。泡菜坛子的后面,小萍正望着她呢。
“小萍,你捡到钱了吗?”汪妈的声音有点颤抖。
“没有,不,有的,两分。您瞧!”
她举起两分的银币,银币在黑暗中发出白光。
“那边的路上行人多吗?”汪妈问她。
“就我一个人——其实我哪里都没去,就躲在这下面。我用手摸来摸去的,就摸到了这两分钱。”
她慢慢地爬了出来,站起身,说自己要回家了。
“下一次我还要来这里捡,这下面的钱比糖果店门口不会少。我有耐心,在那些缝隙里摸呀,摸呀……”
“你摸到石英石了吗?”汪妈打断她问道。
小萍愣了一下,立刻镇静下来,用力点了点头,说:
“有的,有!石英石,还有花岗岩。大部分都是那些疙疙瘩瘩的湿土。下面怎么会那么湿?”
她不等汪妈回她的话,就急急忙忙地走了。
小萍离开后,汪妈又用手电往床下照了一通。她看见里面靠右的地方好像有个洞,再仔细照了几下,又觉得根本没有洞,地板好端端的。汪妈洗了手脸,又到床上躺着。奇怪,小萍已经走了,木床怎么还在微微颤动?女孩的话让她吃惊不小,汪妈不知她是如何窥破她的隐秘的。她算了算,小萍今年是十一岁。有好几年了,她总来讨要泡菜。她这不是快成她的同谋了吗?她贪恋金钱,汪妈就给她出了个主意,让她去糖果店门口捡钱。她没想到她会到自己床底下来施展她的技艺。那是哪一年?好像是父亲去世的那一年。她在女校读书,按事先约定的,她和她的同桌放学后就往山上跑,钻进了那岩洞。两个人都用手电筒向着崖壁晃来晃去的。那女孩向她热切地说到她自己的理想,她的理想让年轻的汪小姐很吃惊,居然是当一名飞行员。汪小姐觉得她在吹牛皮,因为她这么胆小,连条虫子掉到衣服上都要惊叫,还哭起来,这样的人怎么敢上天?但同桌身体力行地证实了自己的话。因为她忽然跑起来,消失在岩洞深处了。汪小姐左等右等,她却没露面。现在胆小的是她了。她出了岩洞,晕晕乎乎地回了家。第二天她遇到同桌,没有打招呼,垂下眼睛。汪妈很早就明白了自己不是一个勇敢的行动者。
她决心做一个等候者。她就这样等,一直等到了老年,其间也等来过她所向往的一些事物。她从四十岁起就住在这个木楼里,本来她是做好了永不搬家的打算的,可是现在忽然要拆迁了。她对拆迁这事一开始很漠然,她是慢慢将思路移到这上面来的,因为有实际的事务需要她应对。那女孩没能上天,她成了烧饼铺的老板娘,另外还开一家理发店,可见她的欲望的确比汪小姐高。
小萍所做的这件可疑的事让她想起了从前的同桌。小女孩比汪妈从前的同桌更有热情,男孩子们没有一个比得上她。汪妈早就看出了她的潜力。她自己的床底下怎么会有零钱的?她想,小萍在那下面呆了那么久,爬来爬去的,迟早会“梦想成真”的。
汪妈深夜才睡着,在那之前,泡菜坛子响了四五次,然而并没发生什么事。后来她走到那个深坑的边上,明知有可能掉下去,还是犹豫不决,不愿马上后退。她倒没掉下去,只听到有人在下面这样说:
“狠一狠心,不就海阔天空了吗?”
后来她就睡着了。不过没睡多久,又醒来了。开了灯,看见房子里有些烟雾,莫非起火了?她穿好衣服和鞋,走到街上,再回转身来看木楼。不,没有起火,只不过楼上云妈的房里有火光,也许她在烧掉一些文件,要拆迁了嘛。汪妈知道有些人愿意将家中的某些旧东西烧光,免得留下痕迹。这云妈必定是那种人。
汪妈无目的地往前走,没走多远,居然看见饮食店门口亮着灯。一张孤零零的桌子旁,有个人正坐在那里,好像是在喝甜酒糟。他埋着头喝得欢,额头上大概已经出汗了。他抬起头时,汪妈认出他是此地的瓦工。深夜里,饮食店里没人,谁给瓦工的甜酒糟?
“汪妈呀,我们的好日子快结束了。我想不通,来饮食店门口坐一坐,有人给我送出来一碗甜酒糟!那个人是谁?我没看清,总不会是鬼吧。这种时候,喝一碗甜酒糟,出一身大汗,什么不舒服都没有了!”
他从口袋里拿出火柴棍来剔牙,眼睛盯着那张门。
“什么叫‘好日子?你对鲇鱼套这地方很满意吧?”
汪妈和蔼地问他时,这位中年汉子就感到了茫然。
“满意?我没想过这种事。我害怕——要搬家了呀。我在这里住习惯了的,害怕是正常的吧?您觉得是不是?”
“不过你除了害怕外,是不是真的不想搬?”
“我?我不知道。我总是在梦里搬家的——搬过来,搬过去, 搬过来,搬过去。我忙得浑身冒汗,这是何苦?总算有机会醒着时搬家了,心里又害怕。”
他俩一齐笑起来。汪妈感到那笑声在黑夜里特别刺耳。
瓦工还是盯着那张门,也许他认为还会有人从里头出来给他送吃的,他是那种贪得无厌的人。周围都是黑暗,只有这里有一小块亮。汪妈从瓦工身边走过,隐没到黑暗里。
黑暗里有很多悄声细语,忽高忽低。汪妈看见瓦工从桌旁站起来了,他的身体倾斜着,像要扑向那张门。他喝醉了吗?门吱呀一声响,汪妈所站的角度看不见门开没开。几秒钟后,那瓦工就扑进去了。门口那盏灯随即便黑了。汪妈想,瓦工有可能是看到她走过来了才特意从饮食店出来,坐在那张桌旁的。在拆迁的阴云之下,各种图谋若隐若现。
她绕着小路往家里走,有人匆匆地赶上了她。汪妈就着朦胧的街灯的光线仔细一看,看见一张陌生的脸。
“您认为那里面有很多机缘,会不会越进去越狭窄?”他说。
“你也是做瓦工的吗?”汪妈问他。
“差不多吧。我老是想留后路,但怎么也不能如愿。鲇鱼套这种地方太古老了,到处都是号角声,每个人都得拼命往前赶。”
“你说得对。”汪妈停住脚步,看着这个人点了点头,“拆迁后你有什么打算吗?比如开个瓷砖店?”
“不,不开瓷砖店。我这种人,只适合于卖那种看不见的物品。”
这时汪妈发觉自己又回到了饮食店门口,那张门半掩着,里面黑黝黝的。陌生人在桌子边坐下时,门口的灯又亮了。陌生人显得很累,他的头伏在自己的手臂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那张门。汪妈觉得他内心在为什么事挣扎。
汪妈下决心回家了。她头也不回地走着,走得很快。
她终于到家了。开了灯,坐在饭桌边休息一会儿。
突然,她感到仿佛有人在外面拨她的门。声音不大,却持续不断。汪妈有点烦恼,本来她已打算再上床睡觉的。
她走过去打开门,看到第二个瓦工站在那里,忸怩不安的样子。
“我想同您谈话,可我又想不出谈什么才好。”
他说话时看着汪妈脑袋的上方。他真傲慢。
“谈你的买卖吧。”汪妈迅速地回应他,“你到底在卖什么东西?”
她没让他进屋。她想,这个青年人太不成体统了。
“我啊,我卖一些旧东西,说不清。每隔几个月,就会有人上门来谈生意。他们丢下一些钱给我。至于货物嘛,就在我的三言两语里面。有时我会有这样的念头:我是不是在出卖鲇鱼套?”
他显得很困惑,两眼发直。
“是啊,莫非你在出卖鲇鱼套?!”汪妈大声说。
瓦工很惊慌,转身就跑得没影了。汪妈捂着嘴笑起来。
她关上门,插好门闩,脑子里如同放电影一样掠过那些镜头。那是地裂的镜头,亮晶晶的石英叮叮当当地从裂口涌出来,全是些小方块。她感到头皮发麻,同时就有了睡意。
这一觉睡到大天亮。醒来后,心里想的还是那瓦工的话。他果真是鲇鱼套的居民吗?她怎么没见过他?这个地方并不大,方圆也就两里路。汪妈昨夜嗅出来了,这个人身上有石英石的气味,那气味当时令她的脊梁骨发冷。她认定这个人不是真正的瓦工。
她起床后,记起楼上云妈夜里烧文件的事。她走到外面朝那上头一望,发现门窗都关得紧紧的。
汪妈在菜市场里选非洲鲫鱼,她用眼角瞟见小萍的母亲过来了。
小萍的妈妈那双手很白,在那些鱼当中抓来抓去的,忽然一下被鱼刺刺到了,惊叫了一声,血从她手背上涌出来。
“啊呀呀!”汪妈说。
她掏出手绢为她包扎。包扎完后抬眼一看,见妇人眼中有笑意。
“汪妈呀,我家小萍打扰您很厉害吧?她是个问题小孩。”
“没有,小萍很乖,从不打扰人。”
“真的吗?我真想看到她在您家里的样子,可她不让。”
“您随时可以来我家的。”
妇人眼里的笑意消失了,她看上去既沮丧又阴郁。汪妈想,她真是个标准美人,小萍一点都不像妈妈。但小萍就应该是小萍自己的样子。
汪妈准备走了,但妇人又问她:
“您愿意去看小萍吗?她就在这菜场后面的门球场里玩一种自己想出来的游戏。我心里有点乱,因为她太上瘾了。”
她俩走到那个废弃了的门球场边上,看见小萍在地上爬。女孩的双眼用一块大手帕蒙住了。汪妈用目光在球场里仔细搜寻,没多久就发现了那些硬币,一共三枚,分别扔在三个角上。小萍慢慢地在场内摸索着,爬动着。
“您瞧我女儿多么有耐心。”妇人忧伤地说。
“可是我觉得您在为她担心。为什么?”
“不,并不是担心。我只是觉得,我觉得,她要去的地方是多么的遥远啊!她会不会半途而废?”
女人用手蒙着脸跑开了。她似乎不那么快乐。她在担心什么呢?汪妈一声不响地看着地上的小萍。小萍已经捡到一枚硬币了。她跪在那里将硬币举起来,硬币在太阳光中耀眼地一闪一闪。那就像一种仪式。
“小萍!小萍!”汪妈唤她。
“嘘,别出声!我在工作呢!”小萍细声回答。
她又聚精会神地爬动起来。汪妈离开门球场往家里走去。
她在家门口遇见云妈,云妈对她说:
“管委会的人又来了。我不明白他们老往我们这里跑干什么。我们都很乐意拆迁——不过是换个地方住罢了。你说是不是?”
“正是这样。拆迁嘛,我是无所谓的。”汪妈说。
“你无所谓?”云妈一下子抬高了嗓门。
她是那样凶狠地瞪着云妈,仿佛要用目光射穿她一样。
“我是说,我可以搬家的。我,我——这年头,连坟墓里的死人都在搬家嘛。我确实……”汪妈说不出话了。
云妈傲慢地从她身旁走过去了。
汪妈记起她夜里烧文件的事。从汪妈记事起她就一直住在这木楼的楼上,那时她还是个脸上搽白粉的单身女郎。她住在那上面,从来没看见什么人去找她,可她居然有那么多文件要烧毁。会不会正因为没有东西可以留在身后,心有不甘,就虚张声势地做出烧文件的假象?
汪妈剖好鱼,洗好菜,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她的手无意中触到自己的口袋,那里面有个硬东西。拿出来一看,居然是塑料薄膜包着的一小包硬币!她将硬币倒在桌上,又发现里面还有一些石英石碎片。汪妈将鼻子凑近去闻,闻到了硫磺的味道。她仔细回忆,确定了只有小萍的母亲在菜场里接触过她的身体。她传递的是什么样的信息呢?汪妈茫然的脑海里显出模糊的石英石的轮廓,她的手因激动而颤抖着。她想,原来母女俩是串通一气的啊!这些硬币晦暗无光,有的上面还嵌着污泥,一点也不吸引人,完全不像小萍捡到的那些。但石英石碎片又是怎么回事?也许小萍的妈妈钻入过汪妈幻想中的那种地方。汪妈想起了她那白白的手臂,还有手上流出的血。她也是鲇鱼套的女人,汪妈总觉得她身上有很多故事。
汪妈突然有种冲动。她抓了五个硬币,弯下腰,往床底下撒去。泡菜坛子都 “咕噜咕噜”地响起来,吃了一惊似的。
汪妈吃饭刚吃到一半,就听到鞭炮声。是最早奠基的那栋楼。那栋楼将改变整个钻鱼套的格局。她估计大概这地方的人都像她一样注意地聆听着。但汪妈真的不在乎搬家——她并不属于鲇鱼套。其实小萍的妈妈也不属于鲇鱼套,鲇鱼套太小,装不下她们的那颗心。在菜场里看见小萍妈妈抓非洲鲫鱼的样子,汪妈就感觉到了这一点,这位妇人体内有非同寻常的活力。
有人敲门,大概又是那瓦工。汪妈坐着没动,那人不敲了。
汪妈暗想,瓦工是很讨厌的,最好的办法是忽视他,可是她很难做到这一点。他属于城市里彻夜不眠的人,汪妈平时就如感觉到自己的呼吸一样感觉到他们。如果她那天夜里不出去,她还不知道饮食店门口会上演那种哑剧呢。这世界在发生什么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啊!她同他们的相遇只不过是邂逅罢了,他们却开始惦记她了。这里面是什么样的规律?
她收拾完厨房后,悄悄地走到门边,将门开了一条缝朝外看。那青年站在街对面,两眼茫然。一些人从他面前走过去了,他总想同别人搭话,很急切地凑近那些人,但没有成功。看来他根本就不是本地瓦工,但他又不像流浪汉。那天夜里,饮食店门口的灯不是也为他亮了吗?他不是一个与鲇鱼套无关的外人。
汪妈闩好房门,她要午睡了。
她睡在蚊帐里面,思绪像波涛一样起伏。那个在梦里不停地搬家的瓦工,他和那家饮食店的人半夜里在搞什么性质的活动?汪妈很少夜里出门,仅仅这一次,鲇鱼套就向她敞开了胸怀——它的夜生活沸腾喧闹,即使是沉默,也等于叫嚣。想到这里,汪妈不禁哑然失笑。
“小萍,我们都要搬进高楼了。”汪妈说。
“我已经去城里那些高楼看过好多次了。”小萍撇了撇嘴,“高楼没意思。不过消防通道里有不少东西捡。”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活蜥蜴,放在汪妈的桌子上。接着她又掏出一只幼小的麻雀,也放在桌子上。两只动物一动也不动,看样子吓坏了。
“你在高楼里捡的吗?”
“我往上走,又往下走;往上走,又往下走……唉!我从来没有一次下到底层。汪奶奶,您说那底下是什么样子?”
“我想,应该有很多麻雀,很多蜥蜴吧。小萍为什么下不了决心到那下面看看呢?只要一闭眼,咚咚咚咚咚咚,就下去了,毫不费力的。然后你就进了地下室,那里也住了不少人。”
“我要走了,汪奶奶。”
小萍将小动物收进口袋,脸色变得很阴沉。看起来她对汪妈的回答一点儿也不满意,她的小脑袋里装的事太多了,谁也别想敷衍她。汪妈看着她,心里有点后悔:这个女孩真难对付。
好多年前,女孩第一次来时,什么也不为,只为吃她的泡菜。汪妈此刻感到小萍就像一只羽毛丰满的小鸟一样飞到了天空里。她忍不住将头伸到门外,偷窥她的背影——小女孩已经显出亭亭玉立的样子了。
责任编辑 何子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