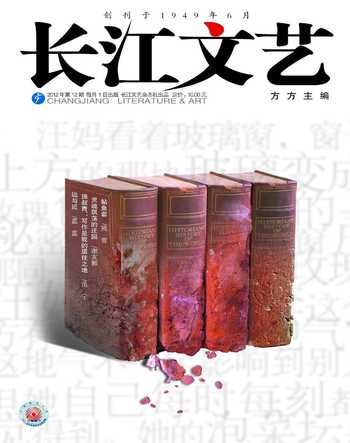解构“专制”
2012-04-29冯天瑜
冯天瑜
中国存在一个强势的宗法专制君主制传统,虽然在氏族制时代繁衍过“民自治”、“众治”和首领“传贤”的原始民主,但自跨入文明门槛以后,便与民主政治揖别,商周以下,不仅未曾出现古希腊雅典式的城邦民主制,也罕见斯巴达式的贵族政治,统驭万民的是“口衔天宪”的君王。这种“王权决定社会”的体制规约下的政治理念,其基本内容包括法家的极端尊君论和儒家的民本尊君论,它们共同组成中国式的君主专制主义的一体两翼。这一延传两千余年的专制政治,在战国建构,秦汉定型,唐宋得以完备,明清强化到极致。君主专制早成且又长期延绵,是中国历史的一大特色,中华文明的优势和弊端都与之紧密相连。
作为汉字古典词,“专制”有独享、独占、独断专行之意。略举几例——
“婴儿为君,大臣专制。”(《韩非子·亡徵》)
“范雎言宣太后专制,穰侯擅权于诸侯……于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国。”(《史记·穰侯列传》)
“周公事文王也,行无专制,事无由己。”高诱注:“专,独;制,断。”(《淮南子·泛论训》)
“权臣专制,擅作威福,是诛之而已也。”(苏轼《策略第一》)
上述诸古典,所用“专制”多指在君幼、君弱的情形下,贵戚、大臣独断专行,所谓专固君宠而擅权(如《申子·大体》说“一臣专君,群臣皆蔽”)。综观古典,很少谈帝王专制的用例,这大约因为认定帝王本应专权,所谓“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故无须议论帝王(即“上”)的专制。
至近代,受西欧及日本概念的影响,“专制”的含义扩大为一种政体的名称,梁启超将作为政治制度的“专制”定义为:
专制者,一国中有制者,有被制者,制者全立于被制者之外,而专断以规定国家机关之行动者也。 (《开明专制论》第二章“释专制”,《梁启超全集》第3册)
近代日本人用汉语旧名“专制”对译英语absolutism,井上哲次郎(1855—1944)等编译的《哲学字汇》,在absolutism条目下,对应的汉字词为“专制主义”。
在西方,absolutism(“专制主义”或“专制制度”)是法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的一种政制形式。孟德斯鸠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的三政体说(君主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基础上,提出“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三分法。君主政体、专制政体都由一人主政,然而君主政体的君主遵循成文法治国,专制政体则不然:
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
孟德斯鸠又将“主权者以胁吓为主义”的政体称“专制制度”,以与“主权者以温和为主义”的政制相区别。
严复把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译作《法意》,其三种政体的国家分别译名为:公治国、君主国、专主国。严复在《孟德斯鸠列传》中还陈列《法意》的三政制:“曰民主,曰君主,曰专制。其说盖源于亚里士多德”。
关于政治体制,近代日本的分类为:君主专制、君主立宪、贵族专制、民主制。 (参见[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
通常认为,专制制度多与君主政体相共生,也可以依存于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其特点是最高统治者独揽国家大权,实行专断统治。自孟德斯鸠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将中国视作专制制度的典型,并认为中国的专制制度与君主政体结合在一起,合称“专制君主政制”。当然也有不同意见——
欧洲自古希腊以来,多将亚洲国家的制度归为“东方专制主义”,至18世纪启蒙运动时代,依据16世纪以降入华耶稣会士带回的材料,欧洲人对中国政制有了较积极的评价,伏尔泰、魁奈等启蒙大师称中国政制为“开明君主制”。19世纪初以降,欧洲人的中国观发生改变,“东方专制主义”说又占主流,马克思大体沿用此说,他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称东方诸国是以部落的或公社的财产作为基础的“东方专制制度”。当然,西方学界仍有承袭启蒙派观点的,如现代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中国国家权力的基础和局限》中指出,中国帝王受到礼制和官僚体制的限约,其专制程度不及西欧中世纪晚期的某些君主。宣称“朕即国家”的法王路易十四,其专制性便在清朝康熙皇帝之上。
中国学者对传统政制的专制性有具体分析。钱穆认为,秦汉以来,“王室与政府逐步分离,民众与政府则逐步接近”(钱穆:《国史大纲》),在这一意义上,钱穆不主张强调中国传统政制的“专制”性。费孝通也认为不宜给中国传统政制简单地以“专制”一言以蔽之,他说:“中央集权的行政制度在中国已有极长的历史。自从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以后,地方官吏在原则上都是由中央遣放的。”(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费氏进而指出:“中国以往的专制政治中有着两道防线,使可能成为暴君的皇帝不致成为暴君。第一道防线是政治哲学里的无为主义。”(费孝通:《乡土中国》),“第二道防线”“那是把集权的中央悬空起来,不使它进入人民日常有关的地方公益范围之中。中央所派遣的官员到知县为止,不再下去了。自上向下的单轨只筑到县衙门就停了,并不到每家人家大门前或大门之内的”(费孝通:《乡土中国》)。费氏把中国传统政制概括为“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层”,“中央所做的事是极有限的,地方上的公益不受中央的干涉,由自治团体管理”(费孝通:《乡土中国》)。而地方自治团体大体是由 “宗法”组织承担,乡绅(或称“绅士”)在其间起主导作用。这些都是中国历史实态的一部分。
中国的帝制受到礼制、礼俗、法律与官僚体制及贵族与地方绅权的制约,故不能说中国专制帝王的权力是无限的,但中国专制帝王受到的限定缺乏法制规范,贵族特权常被限制甚至剥夺;而礼制与官僚体制及地方绅权又臣服于帝王的威权,“命为制,令为诏”的帝王随时可以变制、罢官,因而掌控“六柄”(生、杀、富、贫、贵、贱)的中国皇权,其专制性是毋庸置疑的。自秦以下,皇权至尊、至大,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中国的专制等级制固然与宗法制相为表里,但专制等级制往往更加强势。《红楼梦》第18回描写贾元春省亲荣国府,“贾赦领合族子弟在西街门外,贾母领合族女眷在大门外迎接”,祖母(贾母)、伯父(贾赦)、父亲(贾政)、母亲(王夫人)见了贵为帝妃元春,或“路旁跪下”,或“帘外问安”,所谓“未叙家人之情,先行君臣之礼”,这正是专制皇权至尊、至上的表现。行过君臣大礼之后,接下来才是孙女(女儿)元春“一手搀贾母,一手搀王夫人”,以行孝敬,祖孙三代洒泪话别。(见《红楼梦》)。
汉、唐、宋的专制帝制,大约只将权力伸及郡、县,而近古以至近代的保甲制度,则把“第二道防线”即“在专制和集权名义所容忍着的高度地方自治”加以冲溃,费孝通说:“保甲制度是把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筑到每家的门前,最近要实行的警管制更把这轨道延长到了门内。” (费孝通:《乡土中国》),故在近古(明、清),中国的专制集权政治有增无减,真正达于登峰造极的程度。
如果说,战国诸子争鸣,在政治文化层面是为方兴未艾、蒸蒸日上的君主专制提供精神支撑、理论指导,那么,降至明清之际,当君主专制运行两千余年,其弊害昭彰于世,对其作理论清算(或称“解构”),是新时代向思想界提出的使命。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1930—2004)在20世纪60年代以降撰写的《文学语言学》、《书写与差异》、《声音与现象》等论著中,阐发“解构”主义,所谓“解构”,指对现存理论的结构加以解体,打散诸成分,使之游离,然后重组。德里达的“解构”针对的是理论上的专制。后来人们使用“解构”一词,泛指否定、破坏原有制度或思想的既定结构,以谋求体系的重组、内涵的更新。从某种意义上言之,黄宗羲、傅山、唐甄等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是在对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这一庞然大物加以“解构”,以探寻新的政治文化组建之径。值得指出的是,那时的哲人是在基本没有受到西方政治理念影响的情形下,运用中国固有的思想资源从事这项工作的。这一使命的艰巨性超乎寻常,数代人前仆后继也未竟其业,直至沐浴欧风美雨的近现代,此项任务也不能说已经完成。值得景仰的是,作为解构专制先辈的明清之际哲人,以巨大的勇气,迎难而上,从学理层面挑战专制政治,其具体进程是:解析君主专制主义,猛烈抨击其两翼之一的法家极端尊君论,对另一翼的儒家民本论加以辨别,承继、发挥“重民”、“恤民”部分,扬弃、更替“尊君”、“卫君”部分,这样,在明清之际哲人那里,尤其是在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唐甄的《潜书》中,先秦以降的民本思想获得改造与升华,故我们称之“新民本”,以示其与《左传》、《孟子》以来的民本论的联系与区别;同时也指明:作为“解构专制”的未完成形态,“新民本”既同近代民主存在本质差异,又是近代民主最切近的民族文化资源与前驱先路。
承蒙长江文艺编辑部盛意,於、赵二老师与我联手辟“珞珈山”专栏,几期下来,与读者互动,颇获切磋之乐。天下无不散筵席,小专栏行将告一段落,就此与诸君别过,希望还有其它方式沟通。
责任编辑 吴大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