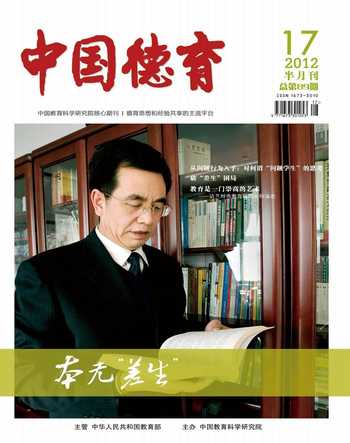以敬畏之心看经典文化
2012-04-29陈苗苗

1985年,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坐在窗前忧心忡忡地撰写《娱乐至死》,哀悼20世纪后半叶美国印刷时代的没落。但作为智者的他,也未必预料到,20多年后,“娱乐至死”在遥远的中国也成为一种公众话语甚至一种文化精神。孔子被逼婚,卖起了炸鸡,还成了不得志的广播员;李白“床前明月光”成了“牙齿掉光光”;屈原,被注册成猪饲料的商标……甚至连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也“晚节不保”,比如,新版电视剧《红楼梦》中黛玉竟然“裸死”。现在,诗圣杜甫也不能幸免。
2012年,是杜甫诞辰1300周年,怀念他的方式不是心存敬畏,而是大众消遣和集体恶搞。网友们以人教版高二《语文》上杜甫《登高》一诗插图为蓝本,涂鸦出五花八门的杜甫穿越图。在网友们的笔下,诗圣杜甫忧国忧民的形象被彻底颠覆了:他骑自行车、打篮球、打CF实战游戏、摆摊卖西瓜,甚至还变身为火影忍者、骑着扫帚的哈利?波特……
在一桩桩颠覆经典、恶搞经典的娱乐事件中,经典文化俨然成了一个娱乐大众的玩偶,其形象一落千丈,尊严和声望被丢进垃圾箱。
一、对“杜甫很忙”事件的分析:
价值迷失
伴随着“杜甫很忙”涂鸦事件的愈演愈烈,也有一方力挺。力挺者认为,“杜甫很忙”体现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批判思维,对提升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具有很好的作用,也体现了一种童心和童趣,应该给予理解和呵护。而且,没被涂鸦过,就不算是“大家”,娱乐一下大众,无伤大雅。
“杜甫很忙”力挺者从童心视角为恶搞经典做辩护。纵观“童心说”的历史渊源,老子“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李贽“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华兹华斯、蒙台梭利的“儿童乃成人之父”等等,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与文化形态下蕴藏着相同的价值取向——被异化的人类对本真的追寻、对灵性的呼唤。“杜甫很忙”力挺者强调批判精神、创新精神,这本身并没有错,但是把愚乐、亵渎、恶搞与童心混在一起,那就是对“童心说”的误读与肢解了。
我们不妨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来想一想:你若见到自己先祖的图像被涂鸦、恶搞,还能平心静气地赞曰“妙哉妙哉”吗?古代儿童启蒙书《警世贤文》意味深长地告诫后代子孙:“少年休笑白头翁,花开能有几时红。”戏谑经典、颠覆经典虽然从侧面反映了新媒体时代言论的民主性和文化的多元取向,但也显示了我们对传统文化和经典缺乏最起码的敬畏心。“敬畏经典并不拒绝真正的批判与创新,但如果为了制造受众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刺激感和迎合时尚市趣进行解构和颠覆,则是民族文化建设的悲哀而非幸事。”[1]
何谓“敬畏”?从敬畏观念历史演变来看,“敬”和“畏”的道德观念早就存在于先民心中。孟子说:“恭敬之心,人皆有之”,《礼记》中说:“在貌为恭,在心为敬”,而朱熹提倡“君子之心,常存敬畏”,并把“敬”视之为“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
经典何以值得敬畏?我国东汉刘熙说:“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南北朝刘勰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明代王阳明说,经典承载着“吾心之常道”。法国作家雨果说:“试将莎士比亚从英国取走,请看这个国家的光辉一下子就会削弱多少!”经典承载着普适性道理,经典文化承载着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代代相传的至今仍有生命力的审美价值取向和道德伦理观念,有机地展现出人性的深度和广度。道德主体在与之观照中,获得“惊知己于千古”的震撼,据此得以超越个体有限的个别性,获得普遍性的品质。“可以说,我们对传统精神理解得越深刻,我们的精神品格就越得到提升,也就越加能够消除陷入虚无的可能。”[2]
既然经典文化是人类智慧之源,是民族文化基础,为什么其在当代遭遇敬畏危机呢?这和当代人价值迷失,与新媒介时代、与现代性冲突有密切关系。就像当代著名文论家希利斯?米勒所说:“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在老百姓文化生活中,文学已经明显今不如昔。”[3]传统文化与现代性在当代人心中发生冲突:“从精神上,一切永恒的、终极的都化为乌有。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上帝,每个人都在建立着自己的价值系统与意义世界,每个人都不再需要从某种公认的、终极的、历史的传统和普遍的习俗中去获取价值的资源,人们匆匆离开一切历史与文化的依托。”[4]
但很多时候,信息的加速度反而会造成内容的肤浅化,意味着更少的意义,而那些深层的心理和哲学的价值,恰恰是构建一个人道德思维和人格的原材料,是价值观的基础。失去这些基础,道德主体看似膨胀,其实是价值迷失,这是信仰失却、行为失范的深层原因,同时也是“礼崩乐坏”“道德不一”的深层原因。现代化的成就让人获得空前强大的力量,但是,物质进步得太快,灵魂跟不上,人性的物性和自然性恣意张狂。伦理学家江万秀如是说:“当下中国社会道德建设存在一个深层痼疾,即社会转型期敬畏之心的普遍缺失。”[5]
二、来自“杜甫很忙”事件的启示:修补对经典文化敬畏心
“无畏”脱胎于“无知”,“无知”是“无畏”的渊薮。孔子说:“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调查显示:“青少年学生对儒家文化缺乏基本的理解和认同,很大一部分学生甚至连儒家文化的基本常识都不清楚。例如,有49.3%的学生不知道荀子是儒家的代表人物,43.3%的学生不知道孟子是儒家的代表人物。”[6]难怪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针对“杜甫很忙”涂鸦图,配上韩愈《调张籍》一诗:“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张扬主体性把道德主体从神谕中解放出来,从天上召回人间,为道德的新生开辟了新的可能空间,但同时,传统经典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如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在年轻一代身上的延续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道德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时间的连续性,不可能与历史、与传统、与文化彻底割裂。当普遍性、统整性、一贯性全都被抽离,道德就失去其存身之场域。”[5]敬畏经典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道德信仰的起点。万变不离其宗,离开了“宗”,我们的道德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前德育有必要在经典文化与当下文化之间搭建一个桥梁,修补二者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痕,提高全民族对文化的敬畏感和自觉性。
德育虽是小课堂,反映的却是大社会,德育有责任把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和发扬下去,也有责任和义务把这种传统的民族文化注入新鲜的血液,让其继续流淌在中国人的生命里。“没有文化,人什么都不是。”[7] 失去了经典文化,德育也会缺乏应有的道德力量。经典文化中传承倡导的诸如“天人合一”“兼容和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民为邦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道酬勤”“心底无私天地宽”“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等等理念、主张,流传千百年并深入人心,已成为一种善恶标准和行为规范。另外,中华经典文化,不仅能为当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也能为21世纪全球面临的经济危机、能源危机、生态危机、道德危机和精神危机开出救治的文化良方。西方哲学家罗素说:“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8]
特别是在今天,国际竞争比拼的固然是综合国力,但在人文领域的较量也是十分激烈的。文化竞争过程中的德育需要解决的是对民族文明成果的继承和推广,涉及政治认同、制度认同、国家认同等一系列复杂的价值挑战,这一切都离不开对经典文化资源的挖掘利用和传承发展。敬畏经典文化,并非故步自封。应该说,一种民族经典文化对于其所属民族来说,是绵延相继、更新常流的。
当然,如何培养对经典文化的敬畏之心,是需要探索的。敬畏杜甫们,不是靠华丽而空洞的仪式,或者抽离了血肉的概念说教。歌德说得好:“虔诚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通过灵魂的最纯洁的宁静达到最高修养的手段。”一个社会终究需要有无法消解、不会被“恶搞”的东西,那该是从年轻人内心里生长出来的敬畏力量。生成敬畏是有条件的,是建立在知识、思想包括经验之上的,是厚积薄发。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讲的“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是建立在“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基础之上的。比如,针对人教版《品德与社会》五年级下册第三单元“国粹”这一教学内容,如果只是肤浅地介绍一些有关京剧的知识,欣赏一些京剧的名段,很难让学生领略中华文化的风采和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教师应深入钻研教材,一手挖掘利用,一手传承发展,盘活德育教材传统文化资源,使之更鲜活、更真实、更亲切,也更有感染力,帮助学生获得不断深化的经验与体验,生成敬畏经典文化的价值观念,并内化为道德信念。除了课堂教学外,还可多借助学科融合和社会实践,有效拓展传统文化敬畏观教育。比如,北京三十五中鼓励学生们自己动手设计,制作“华夏服韵”,以此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到德育课程中。[9]这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培养学生对经典文化的敬畏之心,涉及一个关键变量就是教师。“当前,教师职后教育唯技术主义、功利主义和形式主义,令教师缺失了人文与科学的厚重根基。”[10]教师如果缺乏人文精神,那么他对经典文化的解读就会缺乏阐释力,导致学生远离传统经典文化。增强教师的传统文化底蕴,单靠外部干预和组织统一行动是不够的。要真正使经典阅读成为培养现代人智慧的主要途径,必须鼓励教师将经典阅读作为自我建构的过程,既能入乎其内领悟经典文化的智慧,又能出乎其外联系教育实践探索经典文本的现实价值。
参考文献:
[1]仲呈祥.敬畏经典与文化自觉、自信、自强[N].人民政协报,2011-03-21(C1).
[2]丁钢.历史与现实之间:中国教育传统的理论探索[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92.
[3]米勒.论文学的权威性[G]//文化研究:第4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78.
[4]鲁洁.当代德育基本理论探讨[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112.
[5]吕其庆.敬畏?信仰?道德——访伦理学家江万秀[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2(1):16
[6]叶飞.现代德育是否还需要传统经典[N]中国教育报,2011-05-31(6).
[7]兰德曼.哲学人类学[M]阎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247.
[8]罗素.中国问题[M].秦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170.
[9]刘欢.北京中小学德育课程融入传统文化元素[J].基础教育,2007(11):53.
[10]黄伟杰.基于经典阅读的教师职后教育模式[J].中国教育学刊,2012(3):75-78.
【陈苗苗,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博士后】
责任编辑/刘 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