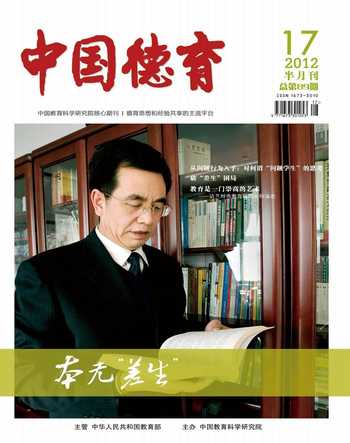破“差生”困局
2012-04-29钟启泉
摘要 素质教育虽然开展多年,但应试教育的影响还在。应试教育过于重视学生的考试成绩,使得“差生”批量产生。解决“差生”问题,必须全面贯彻素质教育要求,保障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权,革新教育观念,培养“淘气包”脑袋,培育儿童的“规范意识”。
关 键 词 差生;多元智能;儿童“前创造性”;规范意识
作者简介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球教育展望》杂志主编
应试教育重视的是数理逻辑智能的训练、开发与评价,使得众多儿童的潜能被忽视、被压抑、被封杀。可以说,应试教育是批量生产“差生”的温床。然而,数理逻辑智能并不是人类智能的全部,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智能组合。例如,建筑师及雕塑家的空间感(空间智能)较强,运动员和芭蕾舞演员的体力(肢体运作智能)较强,公关人员的人际智能较强,作家的内省智能较强,等等。
一、认清“差生”成因:
应试教育是批量生产“差生”的温床
素质教育已是我国教育发展的基本国策和既定方针。然而,一些人对于应试教育的本质及其弊端,仍然存在认识误区,以为学校教育就是传授现成的知识而已,以为学生的知识点积累得越多就越是“好学生”“好人才”。一些地方教育行政官员甚至明目张胆地提出“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有机结合”“理想的教育=素质教育+应试教育”。结果,“素质教育讲得热热闹闹,应试教育抓得扎扎实实”。应试教育大行其道,上上下下却偏偏忘却了基础教育学校的基本功能:“要向学生传递这样一种信息:学校教育不是通往上流社会的阶梯,而是通向智慧的道路。成功不能用金钱和权力来衡量,成功更意味着建立爱的关系,增长个人才干,享受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以及与其他生命和地球维系一种有意义的连接。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学校几乎被出卖了,这表现在对学生考试成绩的过度重视和对学校职业准备功能的无限要求。”[1]多年来,我国基础教育的功利主义倾向愈演愈烈,难道不值得我们好好反思吗?
美国哈佛大学加德纳教授在1983年提出了著名的“多元智能理论”,主张“每个儿童都是一个潜在的天才儿童,只是经常表现为不同的方式而已”。在他看来,以往对“智能”的界定过分狭窄,未能正确反映一个人的真实能力。他认为,人的智能应该是一个量度其解决问题能力的指标。据此,他在《心智的架构》中提出人类的智能至少可以分为七个范畴——语文智能、数理逻辑智能、空间智能、肢体运作智能、音乐智能、人际智能、内省智能。后来,他又陆续补充了“自然探索智能”“生存智能”,一共九种智能范畴。这个理论背后的潜台词是,学生的智能没有尊卑贵贱之分,区分的只是“每个人的智能类型是什么”。无论是哪一种类型,都是等价的。不能说数理化好的学生是“好学生”或是“英才儿童”,体育、艺术好的学生是“差生”或是“问题儿童”。应试教育重视的是数理逻辑智能的训练、开发与评价,使得众多儿童的潜能被忽视、被压抑、被封杀。可以说,应试教育是批量生产“差生”的温床。然而,数理逻辑智能并不是人类智能的全部,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智能组合。例如,建筑师及雕塑家的空间感(空间智能)较强,运动员和芭蕾舞演员的体力(肢体运作智能)较强,公关人员的人际智能较强,作家的内省智能较强,等等。况且,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需要有多种多样的人类智能支撑。可以说,“多元智能理论”为每一个学生树立自信、开发潜能,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是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的教育。在我国的教育舆论中年复一年鼓噪的所谓“高考状元”,或者花招百出所谓学校改革的“成功案例”,不过是赤裸裸的功利主义教育的真实写照罢了。与其说是教育的典型,毋宁说是“反教育”的典型。其实,应试教育语境下的“好生”未必是“好才”。君不见,2010年上海某名牌高中有一名“优等生”被推荐上北大,然而,他自以为“屈才”,闹情绪非上清华不可,结果未能如愿,跳楼自杀了。像这样的学生,目空一切,唯我独尊,冷酷无情,恣意妄为,称得上是“优等生”吗?不,应当说是名副其实的“差生”!平日里只不过凭他所谓“骄人的学业成绩”,得以“一俊遮百丑”罢了。这种人格被严重扭曲了的“优等生”,与那些相对更具“可逆性”的学习困难学生相比,孰优孰劣,不言自明。
二、解决“差生”策略:
抓住两个根本问题
(一)认识儿童的“前创造性”,培育“淘气包”脑袋
保障每一个儿童的基本人权——学习权,培养每一个儿童的创造性和实践能力,是新时代学校教育的诉求,也是衡量优质教育的根本标尺。只要这所学校、这个班级有一个儿童掉队,就不能说,这所学校、这个班级是优质的。换言之,每一个儿童都应当享受卓越的教育。这里的“卓越”,并非指谁跟谁比更杰出,而是指每一个儿童创造自己的最优、寻求最高境界意义上的卓越。“基于竞争的卓越性寻求,带来的是优越感与劣等感。与此相反,创造自己的最优,寻求最高境界的卓越性,带来的是教授者与学习者的审慎与谦恭。”[2]归根结底,学校教育事业是一种公共事业,教师的公共使命就是“为社会公正而教”。从这个意义上说,泛泛而谈教师必须具有师德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学会尊重每一个儿童、发现每一个儿童,真正树立起“大众主义”的教育信念,即“学校和教师的责任并不在于‘上好课。学校和教师的责任乃在于:实现每一位学生的学习权,提供学生挑战高水准学习的机会”[3]。我国中小学教师由于长期受凯洛夫教育学的影响,缺乏“儿童研究”的本领。然而,一个教师倘若不研究儿童,就像一个医生不研究病人一样,是荒唐可笑的。
可以想象,倘若我们的学校和教师缺乏必要的儿童学研究的专业准备,所谓“创新教育”只能是缘木求鱼。比如说,如何认识儿童的“前创造性”,就是任何一个教师回避不了的课题。事实上,界定“创造”存在两种不同的维度:个人的维度与社会的维度。倘若基于社会的维度,所创造的产品的质,当然是一个焦点。从这个维度出发,对照人类文化的历史,大凡超越了过去与现在的一切产品,在所有侧面经得起社会评价者,则被认为是“创造”。倘若基于个人的维度,创造的产品是不必“经得起社会评价”的,只要同其所属集体过去的产品相比,有某种程度的新颖性、新发现,就可以认为是具有创造性的。因此,它并不是像获诺贝尔奖那样推动社会变革的新发明、新发现,更不是什么划时代的思想与艺术,只要是对于其个人来说是独特的表现、独特的产品,就可以视为“创造”了。例如,儿童创作的舞蹈和自由画,技能的巧拙并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是否达到了某种自由表达的阶段。
确实,儿童的独创性观念和行为并不一定是带来文化和科学技术革新的创造性活动,但这种儿童的思考过程类似于创造过程。随着儿童的发展,或许会很快成为巨大的创造性活动。我们平日所谓的“儿童的创造性”应当是基于这种语境下的“创造性”,因此,亦可称为“前创造性”。只要社会文化环境适当,并且施以最好的教育,所有儿童都会表现出一定的“前创造性”。当然,由于他们的基础体验与学习不足,所以多少会有差异,但每一个儿童都会直面新的问题情境,解决新的问题。这就是说,儿童的日常生活是一种创造性活动,每一个儿童都具有创造性。当我们思考教育语境中的创造性问题的时候,必须设定如下前提:
(1)每一个儿童都拥有潜在的创造能力;
(2)儿童拥有的“前创造性”是可以通过学习发展起来的;
(3)发展儿童创造性的场所是每日每时的教育和教学;
(4)基于这种认识的教学过程,就是学校教育的本质性功能。
基于上述认识前提培育儿童创造性的教育实践,必然会确立起新的儿童观和新的教育方法。我国教育界往往把“差生”视为“淘气包”,弃之不顾。然而,外国学者却在大力倡导培养“淘气包”脑袋——SCAMPER,值得我们回味:S——有什么可替代(Substitued);C——有什么可链接(Combined);A——能否移作他用(Adapted);M——能否做出调整(Modified);P——能否变“一用”为“多用”(Put to other uses);E——能否除去什么(Eliminated);R——能否重组什么(Rearranged)。这样说来,热衷于应试教育的教师其实是在热衷于“反儿童”。在应试教育背景下被斥为“差生”(淘气包)的脑袋,正是新时代教育的理想目标之一。
(二)摒弃“拔尖”,从培育儿童的“规范意识”抓起
我国的基础教育,究竟应当从何抓起?从培育“拔尖人才”抓起,还是从培育儿童的“规范意识”抓起?这是关系到基础教育定位的问题。教育事业是一种人性化的事业,基础教育就是为儿童的人格建构与基础学力奠基、为儿童的终身学习与终身发展奠基的阶段。基础教育学校就是为每一个儿童的未来发展奠基的教育机构,绝不是什么“拔尖创新人才培育基地”。我们千万不能混淆了“精英主义”与“大众主义”的分野,也不能模糊了“基础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界线。21世纪是大众主义教育的世纪。在当今世界基础教育的地图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和地区还在张口闭口标榜精英主义教育的。这是因为,在知识社会的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靠培育一小撮所谓的“精英人才”,却把每一个国民核心素质的提升置之度外甚至对立起来,是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21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应当成为我国学校教育的基本准则。然而,应试教育同这个基本准则背道而驰,热衷“育分”却疏于“育人”。在我看来,特别是作为基础教育的中小学,首当其冲的教育课题是儿童的核心素养——规范意识——的形成。这是因为,我们生存的社会里存在种种的规则。在这些规则之中有一种被社会广泛接受和期待的规则,谓之“规范”。在这种规范中,存在着超越时代的任何社会和文化都需要遵守的规范——道德规范,和特定集团的人们相互交往的礼仪礼节之类的规范——习惯规范。这些规范通过日常的人际交往和生活,以及通过受教育者体验而得以内化,成为规范意识。儿童拥有规范意识是儿童人格成长不可或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理由有三:其一,习得规范意识的过程就是人格奠基的过程。儿童通过克制自己的冲动,学会周遭世界的规则。让儿童受到限制,是引导儿童走向现实的世界——每一个人不能为所欲为,我行我素。需要在自己的冲动与外界规则的对照、协调之中,养成能够区分自身的幻想与自己所处的现实世界的力量。在这种活动中明晰自身的轮廓,积蓄儿童把握自身内在矛盾的力量。其二,规范意识是作为同他者分享的尺度来发挥作用的。我们是在维护常识与规则之中相互关联的。一旦有“不守约束”“打扰他人”之类的不守规范的行为,往往是被社区排斥的。规范意识引导儿童走向关系性的世界。其三,规范意识是同理想与目标联系在一起的,为儿童明示了成长的方向。所谓“让儿童掌握规则”,无非就是培育儿童以符合外在的标准来制约自己的力量。由此看来,规范意识的形成是人的成长与社会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可以说,培育这种规范意识是素质教育的原点。[4]
作为中小学教师,需要认识支撑规范意识的要素。在以皮亚杰和柯尔伯格为代表的婴幼儿道德发展的古典研究范式中,道德是儿童对善恶行为的社会认知判断,以语言表征作为主要指标。在这种指标中,婴幼儿的能力是未熟的、自我中心水准的,只能对来自他者的有魅力的诱因与惩罚做出反应,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自我本位的“道德主义者”而已。应当说,这是对婴幼儿的过低评价。在晚近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从更广的框架——从“儿童是怎样调节自己与他者的需求、意图而得以社会化的”观点,来把握儿童的道德发展。就是说,他们不仅从认知侧面,还包括自我意识、气质与角色作用等社会、情绪侧面,来开展研究。规范意识的发展基础,在婴幼儿期急速发展起来。进入幼儿园后,角色能力也发展起来——在日积月累的集体生活中,规则的认识提高了,道德判断力、解读他者的立场、从他者的立场出发来思考也有了可能。有人指出儿童规范意识的形成要素是:同信赖的他者的爱意与信赖关系;理解规范,理解自己与规范相关的自我,从而理解他者的心理,并基于这种立场进行思考的角色获得的智力发展;超越、调整或解决源于自我需求、他者需求与规范冲突的矛盾与失败的自我控制力的发展。[4]
对于儿童的规范意识而言,重要的在于培育“内隐规范”。不过,如前所述,规范本身基本上是由儿童同周遭环境的关系所决定的。这种结构本身进一步加剧了学校教育课题的复杂性。解开这个难题的关键概念是“自律性”。“自律”在道德教育中往往是同“自制”同义的。然而,近年来在各个领域受到关注的“自律性”是指“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用自己的判断行动”。可以说,作为幼儿期的发展课题,就是这种“自律性”。
破“差生”局,别无选择,唯一的出路就是高扬素质教育的旗帜。
参考文献:
[1]诺丁斯.学会关心——教育的另一种形式[M].于天龙,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175.
[2]佐藤学.教师的挑战[M].钟启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38.
[3]佐藤学.学校的挑战[M].钟启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2.
[4]岩立京子.幼儿期规范意识的萌生[J].儿童心理,2012(1):14-18.
责任编辑/刘 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