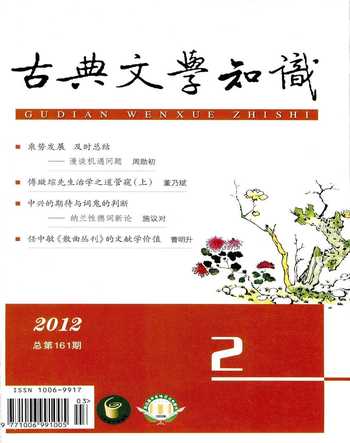历史上的同时同名现象
2012-04-29何剑平
何剑平
上人外人内天,不定不乱,舍法而渊泊,无心而云动,色空无碍,不物物也。默语无际,不言言也。故吾徒得神交焉。玄关大启,德海群泳。时雨既降,春物具美。序于诗者,人百其言。
少年不足言,识道年已长。事往安可悔,余生幸能养。誓从断荤血,不复婴世网。浮名寄缨佩,空性无羁鞅。夙从大导师,焚香此瞻仰。颓然居一室,覆载纷万象。高柳早莺啼,长廊春雨响。床下阮家屐,窗前筇竹杖。方将见身云,陋彼示天壤。一心在法要,愿以无生奖。
一
王维有《谒璇上人并序》,载在《王右丞集笺注》卷之三。璇上人是谁?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对象。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卷三于“璇上人”的笺注引《续高僧传》云:“元崇以开元末年,因从璇禅师谘受心要,日夜匪懈。璇公乃因授深法,与崇历上京,遂入终南,至白鹿,下蓝田。于辋川得右丞王公维之别业。”这段引文见于《宋高僧传》卷十七《唐金陵钟山元崇传》:“释元崇,俗姓王氏,……以开元末年,因从瓦官寺璇禅师谘受心要,日夜匪懈,无忘请益。璇公乃揣骨千里骏足可知,因授深法。……至德初,并谢绝人事,杖锡去郡,历于上京。……遂入终南,经卫藏,至白鹿,上蓝田。于辋川得右丞王公维之别业。松生石上,水流松下。王公焚香静室,与崇相遇,神交中断。”对照之下,赵氏的注文显然有误,陈铁民已有专文论及之(《考证古代作家生平事迹易犯的几种错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在此不赘。不过,这段注文至少表明:赵氏以为王维所交往的这位璇上人即是释元崇的老师——润州江宁县瓦官寺的璇禅师。陈铁民在汲取赵说的基础上又补充了这位璇禅师所属禅派的一条材料:《景德传灯录》卷四载“嵩山普寂法嗣”,其所出法嗣凡二十四人,中有“瓦官寺璇禅师”,二者当为一人。因此之故,陈铁民编此诗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其《王维年谱》云:“开元二十九年辛巳(七四一),四十一岁。春,自岭南北归,尝过润州江宁县瓦官寺,谒璇禅师。”(《王维集校注》第四册附录五,中华书局1997年版)其判断依据乃《宋高僧传》卷十七《元崇传》及《景德传灯录》卷四“嵩山普寂法嗣”谱系,但现在的问题是,王维此序并未明言己所谒之璇上人即瓦官寺璇禅师,也即是说王维在序中并未说明自己同瓦官寺璇禅师有关系,此其一。王维于开元二十九年春至瓦官寺谒璇禅师没有文献依据,此其二。从“少年不足言,识道年已长”等句看,此诗序似应作于其早年在洛阳时,而非四十一岁的年龄,此其三。由于以上疑问,就不能不让人重新考虑璇上人的身份及此诗序的系年问题。
二
在中国佛教史上存在着一种常见而不容忽略的现象:僧人同时同名。璇上人亦是如此。在唐开元年间,除了润州江宁县瓦官寺的璇禅师外,还有一位在开元二十四年(736)之前一直活动于洛阳的僧人道璇。他的师从背景和驻在地都极易引起我们的注意,并将他和王维序中的璇上人联系起来思考。关于道璇的详情介绍始见日本求法僧最澄《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并序》“达磨大师付法相承师师血脉谱”中有“大唐大光福寺道璇和上”之传记,今引与本文论述相关者如下:
天平宝字年中,正四位下太宰府大吉备朝臣真备纂云:大唐道璇和上,天平八岁,至自大唐。戒行绝伦,教诱不怠。至天平胜宝三岁,圣朝请为律师,俄而以疾退居比苏山寺。常自言曰:远寻圣人所以成圣者,必由持戒以次渐登。……自余行迹,具载碑文。其前序云:昔三藏菩提达磨,天竺东来至于汉地,传禅法于慧可,可传僧璨,璨传道信,信传弘忍,忍传神秀,秀传普寂。寂即我律师所事和上也。本在嵩山流传禅法,人众多归,故有敕请入东都,常在华严寺传法,故曰华严尊者。(《传教大师全集》第一,比叡山专修院编纂,大正十五年版)
吉备真备是日本奈良时代赴唐留学生,曾于717年至752年间两次随遣唐使团入唐学习。此传记乃多引仆射吉备真备所纂道璇行实录及道璇原始碑文材料,它至少向我们提供了以下重要信息:
一是在唐代有一名为道璇的僧人尝于天平八年(732),实正当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应日本国之请东渡日本传律。这在中日交流史上乃一引人注意之事件,在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宗性《日本高僧传要文抄第三》“高僧沙门释道璇传”、凝然《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师炼《元亨释书》卷一六《力游九》、卷二二《资治表三》等日本佛教史籍及交通史料中得到广泛记载。
二是从其行迹看,道璇乃一禅律结合之僧侣,即所谓“律藏细密、禅法玄深”。
三是道璇在赴日本传律之前,尝从北宗普寂受传禅法及华严教义。关于前者,《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卷上言及“禅宗”在中土兴起、弘传及东传之历史,说:“五祖弘忍之下有神秀禅师,是北宗始祖。普寂禅师承于神秀,寂禅师下有道璇禅师,日本天平八年丙子来朝,住大安寺,弘所习学禅法、律法。璇公以禅授与同寺行表和尚,行表授之最澄大德。”关于后者,《日本高僧传要文抄第三》“高僧沙门释道璇传”记道璇修行“依《华严净行品》”,又《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卷中说:“璇公赍华严宗章疏,始传日本。”师炼《元亨释书》卷十六《道璇传》引道璇告日本大安寺行表比丘语曰:“我师普寂……始在嵩山传唱禅法,道誉闻帝扆,诏入东都居华严禅苑,故世曰华严尊者。我从《华严》得,以付汝。”可见,道璇对日本佛教之禅法及华严学曾产生过重要影响。
那么道璇在赴日本之前居止何寺呢?《日本高僧传要文抄第三》“高僧沙门释道璇传”条对道璇身份介绍说:“释道璇者,唐许洲人也,住河南府福光寺。俗姓卫氏,卫灵公之后也。”按“福光寺”当作“福先寺”,盖传写之误。《唐会要》卷四十八“寺”条:“福先寺,游艺坊,武太后母杨氏宅。上元二年,立为太原寺。垂拱三年二月,改为魏国寺。天授二年,改为福先寺。”关于道璇的驻在地为福先寺还有以下材料为证,如《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卷下:“去天平五年癸酉敕兴福寺永叡禅师、大安寺普照大德入唐留学,并请传戒律之僧,先请东都大福先寺道璇大德令向日本,道璇年三十五,天平八年丙子,当唐开元二十四年丙子,随副使中臣朝臣名代之舶方来朝矣。”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日本[国]天平五年(733),岁次癸酉,沙门荣叡、普照等随遣唐大使丹墀真人广成,至唐国留学。……仍请东都大福[先]寺沙门道璇律师,附副使中臣朝臣名代之[舶]。先向本国去,拟为传戒者。”另有思托《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逸文:“其荣叡从开元二十年来至唐国,初至东京大福先寺,见僧道璇,便请具论心事。其僧道璇当即受请,先向日本相待。”综合以上所引材料,我们得知,这位道璇上人在开元二十四年赴日本传律之前,一直居止在洛阳福先寺。作为律师,道璇是北宗普寂之弟子,尝随普寂习传华严及禅法。在开元二十四年赴东瀛之前极有可能与王维交游往还,我们这样说,决不是故作戏论,而是因为王维在《谒璇上人并序》里无意间向我们透露了一条与道璇佛学修养密切相关的文本内证:“方将见身云,陋彼示天壤。”所谓“身云”,这一事典出于《华严经》及《度诸佛境界智光严经》、《佛华严入如来德智不思议境界经》卷下、《佛说如来兴显经》卷二、《佛说罗摩伽经》卷下,由智升《开元释教录》卷十一可知,后四经皆为华严本部之眷属经,其中《度诸佛境界智光严经》一卷与《佛华严入如来德智不思议境界经》等同本异译,《如来兴显经》四卷是《华严经如来性起品》及《十忍品》的异译,《罗摩伽经》三卷则是《华严经入法界品》的异译,这就向我们昭示:“身云”这一事典乃华严本部及眷属经所专有的一个佛学概念。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及陈铁民《王维集校注》为揭示作者所祖述的本始出处,皆于注文引华严本部以释“身云”,可谓颇具识见。因为无论是东晋佛驮跋陀罗译的六十卷本还是大唐武后朝实叉难陀译的八十卷本《华严经》,都在当时的知识阶层颇为风行。至于“身云”要义,实叉难陀译《华严经》卷五一《如来出现品》云:“如来应正等觉无上法王亦复如是,欲以正法教化众生,先布身云,弥覆法界,随其乐欲,为现不同。所谓:或为众生现生身云,或为众生现化身云,或为众生现力持身云,或为众生现色身云,或为众生现相好身云,或为众生现福德身云,或为众生现智慧身云,或为众生现诸力不可坏身云,或为众生现无畏身云,或为众生现法界身云。……如来以如是等无量身云,普覆十方一切世界。”相类的“身云”用例在《华严经》中随处可见,恐烦不述,其要旨都在强调菩萨为满足众生的各种需求,能在世间示现无量化身而教化之。在此,所谓“方将见身云”句实在是盛称璇上人具足不可思议的教化之力,远非《庄子·应帝王》中之壸子所能比拟。笔者认为,这一事典的引用是经过作者措思经营的,因为它用于称赞一位精通《华严经》的法匠极为切合,现在看来,这一人选只有东都大福先寺的律师道璇堪足当之。
三
前文所论即已判定王维所交往之璇上人是东都福先寺之道璇,且道璇在开元二十四年已东渡日本,则王维创作此诗序之时间也不当在开元末而宜在开元初。王维的行迹也为我们提供了与此判断极相助益的依据,此即王维在早年有隐居嵩山的经历及过访洛阳的多种机缘。盖在开元三年(715),王维十五岁时,即离家赴长安(《过秦皇墓》诗题下注:“时年十五。”),从此与其弟王缙为求仕进常往来于长安与洛阳两地,《旧唐书》本传所说“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可以为证。从其诗自身提供的线索看,王维至少在三个时期都有频繁在洛阳活动的经历。一是开元六年(718)以前,王维居长安时,曾与祖六隐于终南山,又尝共游洛阳,有两首诗为证:一是《哭祖六自虚》中云:“念昔同携手,风期不暂捐。南山俱隐逸,东洛类神仙。未省音容间,那堪生死迁。花时金谷饮,月夜竹林眠……”此处“东洛”自指洛阳,“东洛”句追忆自己与祖六在洛阳相友善的交谊,其中“金谷”、“竹林”皆河南洛阳人文圣迹。王维与祖六游访洛阳时间之长短虽不得而知,但题下原注曰:“时年十八。”这说明,此诗应作于开元初年。陈铁民《王维年谱》系此诗于开元六年,是。作于同时同地的还有《洛阳女儿行》,诗题下注语作“时年十八”。总之,在开元四、五年至七年这一期限之内,王维在长安,间至洛阳。
第二个时期,是开元十五年(727)至开元十六年(728)之间,王维二十八岁,尝居淇上,有《淇上即事田园》、《淇上送赵仙舟》等诗可证。淇水,今河南北部淇河。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六、《太平寰宇记》卷五六河北道五“卫州”条,河北道卫州管县有五:汲、新乡、卫、共城、黎阳。淇水源出共城县西沮洳山。而卫县西北十一里处有苏门山,相传为阮籍见孙登隐居长啸之所。《偶然作六首》其三更引人注目,并可与王维居淇上所作诗相印证,云:“日夕见太行,沉吟未能去。问君何以然,世网婴我故。小妹日成长,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几回欲奋飞,踟蹰复相顾。孙登长啸台,松竹有遗处。相去讵几许?故人在中路。爱染日已薄,禅寂日已固。忽乎吾将行,宁俟岁云暮?”这首诗至少叙述了三层意思:一是自己屡屡未能归隐乃缘于世网的牵挂(小妹、兄弟及家贫);二是作者居止地当距太行山及孙登长啸台遗迹不远。陈铁民断王维于是年为官淇上,可从;三是说明这段时间自己世俗之念日渐淡薄,而习禅日益精进(“爱染日已薄,禅寂日┮压獭保。┆
第三个时期是王维至东都任谏职前,大抵于开元二十二年(734)至二十三年(735)之间,尝隐居嵩山,有《归嵩山作》、《留别山中温古上人兄并示舍弟缙》、《过乘如禅师萧居士嵩丘兰若》诗可证。诗中提到的温古上人乃嵩岳沙门,开元十一年作为笔受人员参与过金刚智的译经(《续古今译经图记》、《开元释教录》卷九),并为沙门一行述记的《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义释》作序(安然《诸阿阇梨真言密教部类总录》卷上)。乘如禅师则颇善讲说,精研律部,尝住东都敬爱寺(《宋高僧传》卷一五《唐京兆安国寺乘如传》,圆照《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一载代宗朝《请置大兴善寺大德四十九员敕一首》中有“东都敬爱寺僧乘如”),这都意味着,隐居嵩山时期,王维曾广泛接触流行于京洛一带的北地佛教,与各派僧侣交往。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王维与道璇所属禅派北宗普寂一系的深切交往。因为在王维隐居嵩山、往来洛阳期间,以神秀及其弟子普寂、义福为代表的北宗禅正化流帝京河洛地区(宗密《禅源诸诠都序》卷上)。当时王维所栖止的嵩山周围诸寺亦皆被统摄于北宗禅法之下。据李邕《大照禅师碑》(《全唐文》卷二六二)及《嵩岳寺碑》(《文苑英华》卷八五八),普寂于长安年间(701—704),度编嵩山岳寺。神龙年中,神秀卒后,考功员外郎武平一奉宣唐中宗诏,敦劝普寂统领其徒众,宣扬教迹。开元十三年(725),普寂应诏住洛阳敬爱寺。逮至开元十五年,玄宗将幸长安,诏义福从驾,普寂留东都兴唐寺安置。开元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坐灭于兴唐寺。可见,自武后长安以还,普寂一直居止嵩山,在岳寺及东都敬爱寺、同德寺等处传法。王缙《大唐东京大敬爱寺故大德大证禅师碑并序》(《金石萃编》卷九五)亦自述其在登封(今河南登封)为官时尝承传北宗禅法的经过:“缙尝官登封,因学于大照(普寂),又与广德(普寂弟子)素为知友。”王维《留别山中温古上人兄并示舍弟缙》所谓“舍弟官崇高(汉县名,武帝置,唐时曰登封县),宗兄此削发”,亦印证了这段经历。所以从因缘机遇方面来看,在北宗禅大行北地这一重要时期,王维在开元二十四年前又频繁往来于传播衍绎北宗教义的化区——洛阳一带,完全可能有合情之理由与普寂的弟子——东都福先寺的道璇上人相接触。如此推测成立,则《谒璇上人并序》创作时间的下限只能在开元二十四年之前,而不是之后;创作地点自然不必在润州江宁县瓦官寺,而在洛阳。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