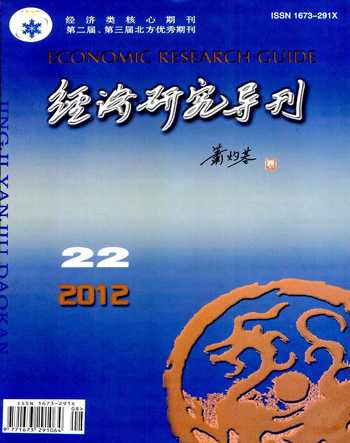方言背后的权力话语
2012-04-29孙继涛
孙继涛
摘要:语言是传递思想的有力工具,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特殊作用,它总能引起上层社会的重视进而对其加以干预。官方语言由此产生,与之相对的就是种类繁多的方言。在同一社会环境下,不同形式的语言形式代表着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角逐。通过比较方言和官话的差异,分别从文字、文学和文化三个层面揭示语言背后的权力之争。
关键词:言文分离;史官文化;大众文化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2-0228-03
秦朝建立之初,各地“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这为中央推行政令造成诸多不便,于是始皇帝特立小篆为官方文字。原本只是一支普通地方方言的秦小篆当时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一统天下的官方语言,其背后的政治推力不容忽视。“方言属于一个有明确界限的社会群体”,这个社会群体具有共同的感情和共同的目的,彼此间由一种无形的力量凝聚在一起。秦官话的推行实际是借助国家权威巩固原秦方言区政治地位而采取的一项措施,此举将其他地区的方言边缘化,将无数操持异语的“外国人”隔离在国家管理者的大门之外。换言之,官修文字其实是秦国贵族利益集团为了削减六国在中央的势力而发动的一场权力斗争。
萨丕尔说:“语言是纯粹人为的,非本能的……传达观念、情绪和欲望的方法。”所谓官方语言,只是当权派借助政治权威刻意选出来传话立传的文字代表而已。自秦而下朝代更替迭换,历朝统治者都要颁布一套自家的官话作为选拔人才的门槛,以保证国家的管理者与皇族同根同源。在维护皇权的统治中,语言发挥了筛选器的作用,轻而易举地将蛮夷异族隔离在正统之外。由于中国古代的政治中心主要集中在北方,久而久之官话趋于相近,竟形成了今天涵盖地区和人口最为广泛的北方方言区。
一、文字层面——言文分离
清代学者淩廷堪说:“上古圣王所以治民者,后世圣贤之所以教民者,一礼字而已。”在一贯注重礼教的传统社会,语言教育早已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一环,有雅俗文白之分。孔子曾极力推崇雅言,“诵诗、读书、执礼必正言其音”。雅言即当时的官方语言,它以黄河中游地区的方言为基础,早在周朝就已经被推广全国。夫子认为这种语言最适合表达“无邪”的思想,讲学著书无不倚重。于是中国社会出现了两种共存的语言形式:一种是由政府强力推行,教谕百姓,全国通用的官话;另一种是讲述家长里短,内容通俗,形式粗粝,掺杂着南腔北调的地方土语。前一种语言是颁布政令、编书修史的御用规范,被委以“载道”的重任,成为文人墨客附庸风雅、加官晋爵所必修的“文学语言”;而后一种则被划入“蛮音”“野语”之流,长期流行坊间不受官方重视,游离在正统文化之外。有政治势力撑腰的官方语言与草根出身的地方方言之间角力导致了书写(形)与说话(音)的长期分离。
书面官话和口头俗语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轨迹。尽管各朝各代的官方语言不同,但是从修辞的角度来看都属于诗的语言。因为诗的语言精悍凝练、喻事于物,所以一直以来深受权力士族的青睐,在王道衰落、礼仪废弛、国家异政的时代更是如此。“取可施于礼义”部分编纂而成的《诗经》寄托了孔子恢复周礼、匡正乱世的政治理想。诗的语言施于政事可以“言志”,施于人可以使百姓“温柔敦厚”,具有教化的作用,因而是古人进入权力王国的必修课。“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儒雅的官话被人为地赋予了“远行”的权力,影响力不断向下层社会渗透,成为读书人表达政治理想、占据政治优势的便捷工具。经过无数文人墨客的粉饰和加工,它在语言技巧方面已经颇为成熟,是现存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的主要载体,传递着几千年历史主流思想的声音。与官方语言相比,散布各地的方言就逊色很多,由于形式粗糙、受众有限,很少有人记录和研究,所以它们曾一度被忽视和遗忘。时至今日,不少俚语还停留在口头阶段,没有统一的书写形式,甚至有的发音还找不到相应的文字来匹配。
“言文分离”加剧了不同人群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反映出政治地位的差别对待。语言形式的差异剥夺相当一部分人享受政治权力的机会,目不识丁、满口粗语的底层劳动者被毫不留情地排除在“说话者”的行列之外,他们的声音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言文分离”还生硬地将人分为三六九等,同是从事语言活动,写和说的情形却大相径庭。修的一手好文章备受敬仰,被世人誉为“才子”或是“学士”,留名青史;而唱的一口好曲、说的一段好书,最终只能沦落艺妓之流,受人驱使,终难登大雅之堂。到了近代社会,随着民主意识的增强,一部分有识之士提倡开启民智,打破“言文分离”,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接踵而来。文字垄断成为了历史,诗的语言的政治特权被打破,更多的人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这场运动被后人视为“汉语的现代化,其功也许可比近代社会历史运动中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因为只有少数人掌握的书写、表意系统,被空前地大众化了,文化的神秘与特权色彩被抹去,民主的曙光已经初现”。
二、文学层面——雅俗之争
与希腊神话完整的谱系相比,中国的神话显得支离破碎,这与主导传统社会的官方文学不无关系。由于“子不语怪、力、乱、神”,荒诞的想法很难被载入由正统思想统治的典籍,千百年来散落民间,只能靠人们口口相传“非法”地延续至今。但另一方面,封建统治者为了给自己的凡人身份开脱又常常借助神话的力量,于是就有了三皇五帝的世袭家族史,“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白帝斩蛇之类天人合一的“合法”故事。在政治力量的干预下,中国神话分裂为上、下两个层次:“一个是以古史形式出现的体系神话的层次;另一个是被古史排斥在外的依然保持着原始面貌的独立神话的层次。前者堂而皇之地进入官修的史书,后者则零乱片段地保存于诸子散文、楚辞及《山海经》一类杂书里。”官书中的神话经过文史学家的改塑承继着深刻的政治寓意,被供奉在庙堂之上作为皇族神圣血统起源的佐证;而杂书的神话则流浪街头,仅供市井小人茶余饭后的消遣。两种神话迥然不同的下场反映出雅文学和俗文学的不同遭遇。
先说说雅文学,王国维认为“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按照他的说法,神话反映了原始人对客观现象的认识,与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体裁一样都是表现艺术美的“第一形式”。官史神话和民间神话都具有这种形式。但“第一形式”本身尚算不得美,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升华,加入“神”、“韵”、“气”、“味”之类的品质,形成所谓的“第二形式”,使美者愈增其美,而这是大多数民间神话所不能及的。王国维将“第二形式”的美命名为“古雅”——“古雅者,可谓之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也”。于是同样是神话,一为温厚,一为刻露,有雅俗之分,在美感上相差甚远。王国维的“古雅说”代表了传统文艺的美学倾向。
雅俗矛盾的背后是官话和方言权力话语的不平等。雅文学是上层社会的一贯腔调,长期占据着主流文学的位置。社会等级制度确立后,士成为了一个权力庞大的阶层,这个阶层选择先秦留下来的文学形式——诗作为共同话语,并将这种话语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侵占俗文学的发展空间,成为引导全社会的审美观。由于创作主体特殊的社会身份,他们的作品往往带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凌人之气,表达了个人的理想和抱负,反映主体人格,表现出国家管理者才具备的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社会责任意识。雅文学的创作在无形中被套上了政治的枷锁,以牺牲思想的自由为代价换取政治上的支持,它更像是权力的传话筒,充当了上层社会“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工具。
俗文学体现了地方方言在官方文学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为寻求话语权而进行的抗争。“用一种语言的形式和质料形成的文学,总带着它的模子的色彩和线。”俗文学用来自社会最基层的声音表达,随性而发,无所顾忌。语言虽然粗鄙但却鲜活,将情欲表现的淋漓尽致,如明清时代的吴歌《偷》所唱:“结识私情弗要慌,捉着子奸情奴自去当,拼得到官双膝馒头跪子从实说,咬钉嚼铁我偷郎。”歌者完全无视道学家宣扬的道德伦理,发出大逆不道的声音。可惜这种声音只能回荡在勾栏瓦肆下,根本无法进入主流的文学作品中。当雅文学的声调过于一致,日益变得僵硬的时候,或许俗文学更能代表那个时代的旋律,正如胡适所说:“我们不应向那‘古文史里去寻,应该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学里去寻。因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当世。”
三、文化层面——史官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角力
语言属于文化的范畴,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官方主导话语的漫长时期当中,权力因素不断地渗透和强化,文艺被当权派抬到一个很高的地位,为权力注释。“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原则注定这样的文字只是代权力言、代君主言的工具,最典型例子的莫过于官史。中国人一贯注重历史,对于一个民族本是件值得庆幸的事。可惜由于古代史官很少有人能够摆脱当时政治的影响,在修史时要么对敏感问题隐晦不言,要么言辞之间表现的过于殷勤,结果导致炮制出来的历史带有亲上层社会意志的倾向。正如梁启超所说:“二十四史,不过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英雄浪漫主义式的记载方式将少数人放到了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而芸芸众生只化作一连串的数字或代号充当了帝王家的陪衬。这种带有权力标记的文字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历史学家范文澜将这种文化称为“史官文化”。
“黄炎族掌文化的人叫做史”,可见最初的史是代替文化说话,是中央意志在文化领域的代言人。所谓史官文化,按照顾准先生的说法是“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这个定义划定了史官文化涉及的范围,也确立了其服务的对象。由于政治地位上的优势,正史文化观察世界的视角是自上而下的,试图利用自身的势力影响其他人,它常见的话语表达方式是一种无具体人称的说教——“它不以个人而始终以集团为单位,它始终代表集团说话”。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个人创作的自由大大受到了限制,难免会失去个体性。
在正史话语的统治下,我们会发现个别不和谐的杂音。它来自社会的底层,创造者是那些闲耍谋生的艺人,他们以仰视的目光观察着正史话语构建的世界,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因为他们的地位足够卑微,所以不必顾忌高深的政治学,有机会突破正史话语的禁忌,像上文提到的吴歌《偷》那样,可以解放情欲,放纵感官,自由地表达着感性的声音。因为他们不具备说教别人的资格,所以只能依靠别出心裁的叙述来吸引人的注意,在严肃的正史之外虚构了戏说、外传之类娱人娱己的文艺形式,不经意间促进了叙事美学的发展,其中值得一提的就是小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由口头文学发展而来的小说自诞生之初便带着草根性,它浅显易懂,注重表演效果,主动迎合普通听众的审美趣味,先后经过志怪、传奇、笔记话本、拟话本的发展,终于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顶峰,取代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诗的语言。
海德格尔说:“唯有言说使人成为作为人的生命存在。”借助小说的形式,每个人可以从自己的立场上相对自由地发表对世界的看法,民间的声音有机会突破史官话语的封锁传播开来,在传统文化之外形成一股新的势力。从叙事上看,小说是对说教式的史官文体的一种削弱和瓦解。它依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自由地编写故事内容,它虚构的情节可以将讲述者从沉重的政治使命中解放出来。小说家是“存在的探实者”,可以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情,比正史更为真实。
正史文体对以小说为代表的草根文学的态度是复杂的。最初诗道盛行,文人们对小说很是不屑。有人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庄子·外物》),还有人说小说虽然有趣,但“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论语·子张》),对于干大事的人来说,小说这种琐碎的文字实在是太不入流了。那个时代的小说家竭力隐藏自己的身份,深恐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斥。终于有一天,就是这不入流的“小道”写出了《金瓶梅》,引起了上层文化监察机构的重视,慌忙编罗“妖书”、“伪书”、“淫秽”等罪名进行打压,一大批作品被划入了打击的范围,连被今人视为四大名著的《西游记》、《红楼梦》也不为当时的官方文化所容。从此,草民出身的小说出现在官家的视野中,有一部分官史文化培养出的文人开始尝试用小说的形式进行创作,从坊间杂谈中精心选取孝义忠贞之类“健康”的素材加工成“第二形式”,返销到民间,试图将小说改造为宣扬正史文化的有益补充,却无意中为小说在原来娱乐的基础上又新增加了教化的功能。文人的介入推动了小说话语权的扩大,尤其在经历了近代白话文运动之后,诗的语言——这一史官文化的重要载体被完全抛弃,平民话语彻底取代了史官话语,成为左右文化发展方向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1]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99.
[2]殷实.语言和谐与价值和谐[J].读书,2012,(1).
[3]俞汝捷.仙鬼妖人:志怪传奇新论[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
[4]顾准文集[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7:147.
[5]敬文东.被委以重任的方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3.
[6]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56.
[责任编辑 王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