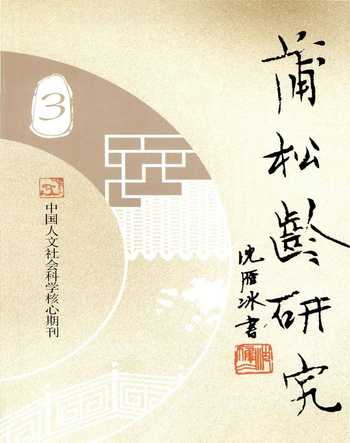唐五代小说中的鬼怪趣诗
2012-04-29徐婷育
徐婷育
摘要:唐五代小说中出现了大量鬼怪所作的趣诗,这些趣诗以文为戏,诙谐幽默,纯粹追求趣味性。本文把趣诗分为戏谑打趣、即席联句、自寓身世三类进行探讨,重点说明趣诗的特点和“趣”之所在。小说作者“好奇”的审美心理和文人的娱乐心态是这类趣诗出现的重要原因。与汉魏六朝小说相较,唐五代小说中的鬼怪趣诗表现出作者自觉追求诗歌和小说的娱乐功能的审美心理,强调了文学非功利的“审美”的本质特征,对于小说文体的独立具有重要作用,因而在小说史上具有了超出作品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鬼怪;趣诗;以文为戏
中图分类号:I207.41文献标识码:A
“唐三百年,文章鼎盛,独诗律与小说,称绝代之奇” ①,并称“绝代之奇”的诗歌与小说在唐五代具体的小说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完美的融合和表现。宋赵彦卫《云麓漫钞》曾评价唐人小说:“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诗笔”的运用是唐五代小说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唐五代小说的“诗笔”问题,学界前辈己作过精辟深入的研究,但是对于小说中“趣诗”的探讨则比较少,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重点探讨唐五代小说中鬼魂精怪所作的“趣”诗。
一、鬼怪趣诗类型
唐五代小说中,不但人能作诗,鬼魂精怪亦能作诗,精彩纷呈、蔚为大观的鬼怪小说中,各类形形色色的鬼怪逞意使才,妙语连珠,所作之诗不乏佳作。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一○《鬼》中说:“杂传记中,多录鬼神灵怪之词,哀调深情,不异畴昔。”明人杨升庵在《艺林伐山》卷一七中也说:“诗盛于唐,其作者往往托于传奇小说中神仙鬼怪以传于后,而其诗大有妙绝千古、一字千金者。”鬼怪能作诗,已是相当神奇有趣,而鬼怪所作的趣诗就更有趣了,这些趣诗大多为“趣”而趣,纯是一副游戏笔墨。《全唐诗》卷八百六十五和卷八百六十六收鬼诗两卷,卷八百六十七收怪诗一卷,这些诗多是从唐人小说中辑录出来的,《太平广记》中多有收录。今据笔者统计,全唐五代小说中直接穿插诗歌的作品共有271篇,含鬼怪所作诗歌的作品共有67篇,含鬼怪趣诗的作品共有16篇 ① 。鬼诗或是自叙身世凄凉、泉下寂寞之感;或是抒发盛衰变迁、生死兴亡之叹;或是和生者相和赋诗,寄托思念之情,趣诗相对比较少。《玄怪录·刘讽》(《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二十九)、《河东记·踏歌鬼》(《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四十六)、《宣世志·梁璟》(《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四十九)中的诗歌是鬼所作趣诗的代表。精怪小说中则出现了大量的趣诗,虎马牛鸡、秃帚破铛皆可为诗,妙趣横生。综观这些鬼怪趣诗,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戏谑打趣类
这类小说中的鬼怪往往活泼顽皮,聪明伶俐,不但不可怕,反而率真可喜,或是恣意歌唱,或是和作品的主人公戏谑谈咏,极富情趣,一派轻松活泼的氛围。如《玄怪录·刘讽》,夷陵空馆中的一众女鬼月夜相聚,饮酒行令,弹琴击筑,“谈谑歌咏,音词清婉”。《全唐诗》录其诗三篇,题为《空馆夜歌》。其一曰:“明月清风,良宵会同。星河易翻,欢娱不终。绿樽翠杓,为君斟酌。今夕不饮,何时欢乐。”其二曰:“杨柳杨柳,袅袅随风急。西楼美人春梦长,绣帘斜卷千条入。”其三曰:“玉户金缸,愿陪君王。邯郸宫中,金石丝簧。卫女秦娥,左右成行。纨缟缤纷,翠眉红妆。王欢顾盼,为王歌舞。愿得君欢,常无灾苦。”三篇皆为清词丽句,婉转有致,读来琅琅上口,具有浓厚的生活情趣,宛若人间良宵欢聚,谈笑风生,这些女郎虽为鬼,却殊无鬼气,相互调笑打趣,妙语连珠,所作诗歌也充满了轻松、明朗、乐观、幽默的情调。这几首趣诗曾得到大文豪苏轼和黄庭坚的高度评价,黄庭坚认为这些诗“当是鬼中曹子建所作”,而“东坡亦以为然”。同时苏东坡以为“邯郸宫中,金石丝簧”这两句“不唯人少能作,而知之者亦极难得耳”。① (P871)苏黄二公以鬼诗相互谈咏打趣,开怀大笑。
又如《河东记·踏歌鬼》:“长庆中,有人于河中舜城北鹳鹊楼下见二鬼,各长三丈许,青衫白袴,连臂踏歌曰:‘河水流溷溷,山头种荞麦。两个胡孙门底来,东家阿嫂决一百。言毕而没。”二鬼就像是邻家的顽皮小儿,用无赖天真的口吻,把臂共唱了一首清新欢快的民谣,语气活泼戏谑,诙谐幽默。
2、即席联句类
在这一类小说中,众鬼怪良夜相聚,把酒吟诗,根据一个规定的题目,即席联句,共同吟咏相同的事物或是抒发相似的感情。最有代表性的当推《宣世志·梁璟》。梁璟在商山夜宿时遇到三丈夫,分别为王步兵、萧中郎、诸葛长史。梁璟虽知其为鬼,但仍是与之饮酒联句,成诗两篇,《全唐诗》题为《秋月联句》和《天明联句》。《秋月联句》为:“秋月圆如镜(王步兵),秋风利似刀(萧中郎)。秋云轻比絮(梁璟),秋草细同毛(诸葛长史)。”《天明联句》为:“山树高高影(萧中郎),山花寂寂香(王步兵)。山天遥历历(诸葛长史),山水急汤汤(梁璟)。”这种联句颇有文人雅戏之风味,所作之诗并无多大意义,纯是一副游戏笔墨,考的是各人的急才和文采。不但联句本身给人带来趣味的享受,就连联句的过程也是妙趣横生,这集中表现在诸葛长史这个鬼身上:每当轮到他联句,他总是“沉吟”、“嘿然久之”,一副苦思不得、窘迫尴尬的样子跃然纸上,等到他好不容易想出一句,往往换来众人一阵大笑,笑曰“拙则拙矣,何乃迟乎”,就如文士相互打趣玩笑,欢乐幽默的气氛扑面而来。
3、自寓身世类
这一类趣诗最多,也最为普遍,在精怪小说中大量出现。精怪们往往用隐语、典故的方式自寓身世、暗示本相,这些诗其实就是诗谜,多经作者精心构思、巧妙经营,最可见出作者的才气和学识。这类诗也多有联句、即席赋诗的形式,但是和第二类诗不同,这类诗主要是由精怪吟诗暗示本相,而不是吟咏风物。如《玄怪录·元无有》(《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六十九),元无有在维扬郊野的空庄中遇到四人,相与谈咏联句,至天明,元无有发现堂中只有故杵、灯台、水桶、破铛,乃知四人即此四怪。《全唐诗》把此联句题为《维扬空庄四怪联句》:“齐纨鲁缟如霜雪,寥亮高声予所发(故杵)。嘉宾良会清夜时,煌煌灯烛我能持(灯台)。清冷之泉候朝汲,桑绠相牵常出入(水桶)。爨薪贮泉相煎熬,充他口腹我为劳(破铛)。”从四怪所吟之诗来看,这些诗均都符合它们各自的器物用途和特点,这四个器物怪的诗就是对自身准确传神的写照。《灵怪集·姚康城》(《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七十一)中的破铫子、破笛、秃黎穰箒所赋之诗也是相似的作品,如破笛所吟之诗:“当时得意气填心,一曲君前值万金。今日不如庭下竹,风来犹得学龙吟。”极为巧妙地暗示了自己“笛子”的本相,同时又有荣辱沉浮的感叹,但这不是诗的主旨,作者主要还是以文为戏,制造幽默趣味。
王洙的《东阳夜怪录》(《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九十)继承了这种构思,并且将其发扬得淋漓尽致。《东阳夜怪录》主要讲了秀才成自虚雪夜投宿渭南县东阳驿南佛舍,遇老病僧安智高(呼为高公,橐驼),又有前河阴转运巡官、试左骁卫胄曹参军卢倚马(呼为曹长,驴),桃林客、副轻骑将军朱中正(呼为朱八,牛),敬去文(犬)、奚锐金(鸡)四人偕来,相与诵说诗章。后苗介立(呼为苗十,猫)、胃藏瓠、藏立(刺猬)兄弟继来与谈。天明,自虚于舍内外见有橐驼、乌驴、老鸡、驳猫、二刺猬、牛、犬,方悟夜所遇者即此八怪。《东阳夜怪录》中一共穿插了诗歌十四首,其中五律一首,五绝四首,七绝九首。作者煞费苦心,巧妙布置,刻意展现自己的学识和才情,在八怪所作之诗中大量运用了典故、隐喻、双关等手法,从不同角度暗示精怪的本相,“至八怪诗咏谈论,亦皆借用典故,明其本相,所赋各诗直是诗谜耳。十数条注语颇能破其机关,唯犹未尽之。” ① (P414)如敬去文的咏雪诗:“爱此飘飖六出公,轻琼冷絮舞长空。当时正逐秦丞相,腾踯川原喜北风。”“当时正逐秦丞相”一句用了秦丞相李斯“东门黄犬”的典故:《史记·李斯列传》载李斯被杀前对其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此典故暗示敬去文是一条猎狗。又如朱中正诗:“乱鲁负虚名,游秦感宁生。候惊丞相喘,用识葛卢鸣。黍稷滋农兴,轩车乏道情。近来筋力退,一志在归耕。”“乱鲁负虚名”用了鲁国竖牛作乱的典故,《左传》载鲁国叔孙氏家臣竖牛作乱,被叔孙昭子诛杀。朱中正用此典暗示自己是牛,但是由于竖牛并非牛,所以这里说“负虚名”。“游秦感宁生”用的则是宁戚半夜饭牛的典故。“候惊丞相喘”用《汉书·丙吉传》中宣帝丞相丙吉出行见牛赶路吐舌喘气,从而预测到气候反常的典故。“用识葛卢鸣”,《左传》载介国国君葛卢懂牛语,从一头牛的鸣叫声中知道它曾得重用。“黍稷滋农兴”则暗示牛从事田间劳动。“一志在归耕”则隐喻牛回农村耕地 ② (P407-421)。这首诗几乎句句用典,虽不免有堆砌炫耀之嫌,但是从中确可见出作者的文才。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通过破解这一个个诗谜典故,获得一种浓厚的兴味和文趣。
这些诗关合动物自身的特点,用典精确,取喻奇辟,有机锋侧出之妙。同时,这些诗亦有寄托,微含寓意,表达对社会人生的感悟,但作者之意并不在此,更多地则是作者以诗为戏,以造文趣,“作者有意在鄙陋——精怪的原形——和高雅——精怪吟诗——之间的极不协调中制造滑稽感” ① (P80),其间的巨大反差所造成的诙谐嘲谑效果是十分强烈的,并且“通过精怪们谜语式的自喻诗来制造妙趣横生的效果” ① (P80),文章的趣味性也由此而生。同时,这些精怪所作之诗并无高妙的诗境和深远的诗味,也被用之以典实,借以嘲讽舞文弄墨、才能平庸的诗人,形成一种嘲谑调侃的效果,从而获得另外一种趣味。近代诗人樊增祥《樊山诗集·蒲州道中阅题壁诗戏书其后》云:“敬文苗立总能诗,涂遍蒲东及绛西。”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也讽刺文理不通的丁敦龄:“未识原文作底言语,想尚不及《东阳夜怪录》中敬去文、苗介立辈赋咏。” ② (P127)
除此之外,《宣室志·崔瑴》(《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七十)中的笔精诗、《玄怪录·滕庭俊》(《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七十四)中的苍蝇、秃帚二怪联句、《传奇·宁茵》(《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三十四)中的牛、虎二怪诗、《河东记·申屠澄》(《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二十九)中的虎妇诗、《宣室志·李员》(《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中的金缶魅诗等都是此类相似的作品,切合精怪自身特点,暗示本相,趣味横生。正如李剑国先生所说:“予谓《夜怪》诸作之妙不在言理而在言趣,令读者赏玩事趣、文趣耳。” ② (P416)
二、鬼怪趣诗出现的原因
1、小说作者“好奇”的审美心理
唐五代小说的作者普遍具有“好奇”的气质和审美心理。鬼魂和精怪的世界本就光怪陆离,众说纷纭,充满了想像力和吸引力,这给唐五代小说作者提供了天马行空般广阔的创作空间,而唐五代小说作者“好奇”的审美心理使得他们格外关注这片领域,在继承六朝小说成就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发扬和创新,充分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和才情,不但“蒐奇则极于山经十洲,语怪则逾于齐谐列异” ①,而且赋予这些鬼怪吟诗作赋的能力。鬼怪之事已是一奇,而鬼怪还能作诗,那就更是奇上加奇。当然,唐人小说中非人类的“诗人”,除了鬼怪,还有各种各样的神仙,但是神仙作诗,似乎还理所当然,因为神仙是世间凡人所崇拜敬奉的对象,得道成仙也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神仙自是无所不能,逍遥快活,欢聚赋诗当然可以理解。然而鬼怪也能作诗,则颇堪玩味,因为鬼怪自来为人所恐惧厌恶,是异类的象征,这些常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异类,居然也能出口成章,吟诗作赋,这本身就是一个奇特而充满了趣味的现象,充分展现了小说作者“作意好奇”的气质。
2、社会上普遍的娱乐风气和文人的娱乐心态
社会上普遍的娱乐风气和文人的娱乐心态也是鬼怪趣诗出现的重要原因。唐五代时社会上具有浓厚的娱乐风气,上至皇帝,下至布衣,常常相聚谈笑谐谑,赋诗取乐,唐五代笔记中有不少这样的记载,如刘餗的《隋唐嘉话》中的一则记载:
太宗宴近臣,戏以嘲谑。赵公无忌嘲欧阳率更曰:“耸髆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家麟阁上,画此一猕猴?”询应声云:“缩头连背暖,俒裆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团团。”帝改容曰:“欧阳询岂不畏皇后闻?”赵公,后之兄也。
皇帝和群臣也经常互相“戏以嘲谑”,可见当时娱乐风气之浓。
大文豪韩愈也是“以文为戏”的代表人物。韩愈著《毛颖传》,郑重其事地为一支毛笔立传,产生一种特殊的滑稽效果。对于韩愈“以文为戏”的行为,世人多加非议,而柳宗元读《毛颖传》后则为韩愈辩解道:“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圣人之所弃者。” ① 这种“以文为戏”的行为,正折射出了文人们轻松幽默、宽容开放的娱乐心态,正是这种娱乐的心态,使得小说作者自觉追求小说的娱乐功能,促使了鬼怪趣诗的出现。
三、鬼怪趣诗的意义
唐人鬼怪小说中的趣诗,除了“令读者赏玩事趣、文趣”之外,在小说史上具有其独特的意义。
1、自觉的小说创作意识
唐五代小说中的鬼怪趣诗是唐小说作者“作意好奇”(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六)的具体表现。唐人开始有自觉意识地创作小说,正如鲁迅所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际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 ② (P44)汉魏六朝的志怪小说作者很大程度还是秉着史官“秉笔直书”的精神,把这些鬼怪之事当作真实的历史进行记录,没有认识到小说的文学地位,而认为小说是“史官末事”(《隋书·经籍志》)。鲁迅先生曾指出,六朝的小说创作“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自叙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 ③ (P24)而到了唐五代,小说作者开始有意识地进行虚构,不再一味追求小说的真实性,甚至明确指出作品纯属虚构,如《元无有》中的主人公“元无有”和《东阳夜怪录》中主人公“成自虚”,这两个名字明确告诉读者小说所写都是虚无之事。小说中鬼怪们所作的趣诗、鬼怪和人相互调笑的幽默场景,自然也是作者刻意的虚构。鬼怪趣诗说明作者已经挣脱了小说“史官末事”的桎梏,开始自觉地、有意识地创作小说,为小说脱离“史”的地位、实现自身的文体独立作出了贡献。
2、非功利性的审美追求。
唐五代小说中的鬼怪趣诗,是对于文学“审美”本质的自觉追求。文学的本质在于审美,是一种无功利性的观照,从这一点上看,文学的娱乐功能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在我国古代传统的文学观念中,文学最大的功用是政教功能,“诗言志”、“文以载道”的儒家文学观一直被奉为圭臬,汉魏六朝的小说也努力实现这一以“教化”为主的功利目的,小说家虽然也有“游心寓目”(《搜神记》序)的观念,但主要还是为了“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 ① ,强调了其政治和伦理的意义。但是这些鬼怪趣诗却没有什么明确的思想含义,也没有明确的情感趋向,它们只是在表达一种情趣、一种文趣、一种奇趣,是纯粹地为了“趣”而“趣”。这些诗没有巨大的言志抒怀、载道教化的负担,只是以文为戏、相互赏玩而已,作者通过“玩文学”来表达一种闲适自在、轻松幽默的心态。“兴趣之所以在唐人小说中成为一宗主题,完全是小说创作进入自觉状态的结果,是唐人(一部分人)的非功利意识进入创作意识,从而把小说的审美性、娱乐性、赏玩性作为主要表现目的的结果”。② (P81)这种创作倾向是对文学娱乐功能的强调,是对文学功利化的一种大胆的疏离和反叛,是对文学本质属性的自觉追求,这类“趣”诗着眼于“审美”,凸显了小说“文学”的地位,使小说在文体独立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大步。
3、小说情感力量的增强。
鬼怪趣诗大大增强了小说的情感力量,为鬼怪小说注入了浓厚的“人情味”。鬼怪作为异类,不管是在时空还是心理上,都与人类有距离,且在传统观念中,鬼怪多伤人害人,令人厌惧憎恶,汉魏六朝志怪小说中的鬼怪,就绝大部分是人人得而诛之的怪物。如《细腰》(《搜神记》卷十八),写金、银、钱、杵四怪在宅中作怪,导致两户入住人家“衰老财散”、“举家病疾”,后被新主人何文设计问出原形,掘出金、银、钱,烧毁杵,最终“宅遂清宁”。同样是写器物所化的精怪,这四个怪物就不同于《元无有》中的故杵、灯台、水桶、破铛四怪,它们作怪害人,最终被主人公一一除去,不得善终。但是唐五代小说中的这些善作趣诗的鬼怪完全是另外一种面貌,极具“人情味”。鬼怪若是能吟诗作赋,那么与人就有了共同行为和共同语言,拉近了与人的距离;鬼怪不但能作诗,而且作的还是妙趣横生、轻松幽默的“趣”诗,使人赏心悦目,不忍释卷,那么,鬼怪与人的距离就又拉近了一层,鬼怪也就更具“人情味”。《刘讽》中聪明活泼的众女郎、《踏歌鬼》中把臂踏歌的顽皮二鬼,均是率然可喜、人情十足;《梁璟》中的良夜清会、《东阳夜怪录》的雪夜赋诗,绝似人间文士雅聚,欢饮赋诗的场景;《梁璟》中联句“又拙又迟”的诸葛长史,就是苦无文思、尴尬窘迫的文人写照;《东阳夜怪录》中的敬去文和苗介立争锋相对、互相讥讽的“言志”之作,活似世间某些不学无术、却爱自夸身世、爱慕虚荣的文人嘴脸。鬼怪们在吟诵这些趣诗的同时,已经具有了浓厚的“人情味”,就算暗示本相,也不忘卖弄学问、故弄玄虚。它们只是一群热爱生活的精灵,与人相谈相亲,殊无丝毫鬼气。鲁迅先生评论《聊斋志异》是“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 ① (P147),用在这里评论这些善作趣诗的鬼怪们,也很准确。小说中的这种情感力量大大增强了小说的审美性,摆脱了六朝志怪小说粗陋单一的状态。
综上所述,唐五代小说的鬼怪趣诗以文为戏,表达一种幽默轻松的趣味,自觉追求小说的娱乐功能和非功利的审美性,促进了小说文体的独立,在小说史上极具研究价值。
(责任编辑谭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