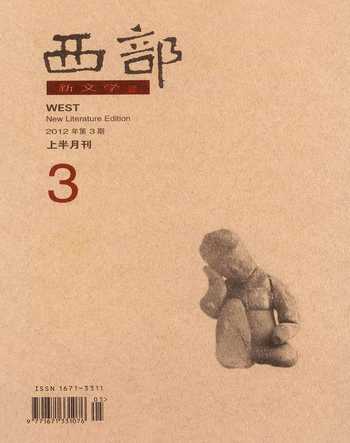误入省城的牦牛
2012-04-29郭发财
除非逃到这个世界当中,否则怎么会对这个世界感到高兴呢?
——弗兰茨·卡夫卡
1
夜黑如墨,零散的灯,像来路不明的子弹,把省城的夜空击出些大小不一的窟窿。卧铺客车一个急刹,刺耳地响动几声,摇晃晃地在下关长途汽车站停稳。司机回过头,说,省城到了,有急事的,赶紧下车办你的急事,不急的,可在车上躺着,继续睡觉,天亮了以后再走。
司机的言语,没有得到多少响应。这辆外埠开往省城的长途汽车,路上运行一天两夜,旅客一路颠簸,困倦之极。因此,车到省城下关汽车站,醒着的人不多,大部分,都还躺在狭窄肮脏的铺位迷迷糊糊地睡觉。
但是,我却是车上为数不多的清醒者之一。躺在上铺右边靠窗的位置,面向贴着几片黄胶带的玻璃窗,风从破裂的缝隙吹进,凉森森的,在车厢里,我不由得打了个寒噤。背对窗子侧卧,拧开不锈钢茶杯,我喝了口茶。苦涩清爽的凉意,在我无可名状的心里蠕动。在铺上,我伸开一路弯曲的肢体,旅途的劳累,因为省城的抵达轻松很多。
2
午夜开进省城的长途车,暴露在早晨八点多的红太阳里。睁开眼睛,车已空了。和我一路同行的旅客,宛如大风吹散的蚂蚁,来自外埠的男男女女,与我一路伴随的声音与形容,突然一个也没有了。我被吓了一跳。不过抬手看表,很快又镇静下来。出门在外,谁都无法保证头脑清醒,精神高度集中。偶尔迷糊,只要不会误时误事,对我也算不幸中的万幸。
我提着一个黑色密码箱,背着鼓鼓囊囊的迷彩背包,走到车门前,用力拉门,发现情况不妙,就是说,我乘坐的这辆外埠开往省城的长途汽车,不知什么时候车已上锁。要下车,只好等现在不知跑到哪个角落寻欢作乐的司机中途返回给我开门,否则,我只能待在车里。
但司机不可能在希望的时间赶回。我的省城之行,只有一天时间,许多事,我都必须当天办完。开门,开门,他妈的,快开门!额头急得出汗。我的愤怒可想而知。形象地说,它和这些年打了膨胀素的GDP一样,愤怒从脚到头,不停地往我头上直冲。但我的怒吼,终究只是徒劳。因为在长途汽车停在下关的众多外埠车辆中,我的吼叫,已被省城忽略,被下关车站的固有空间稀释。
点燃一支烟,我冷静下来。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我想出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车窗,跳窗而出……我就这样走人。我只能这样干。这是偶然中的必然,也是必然里的偶然。
我撕开玻璃窗上的黄胶带,将碎成几块的玻璃捧在手里,小心放在汽车过道。我将两件随身携带的行李抛出窗外。钻出没有玻璃的车窗。可我遇到了麻烦。
嘿!一个省城爷们腔说,嘿,我说,您干吗啦?悬在长途汽车的半空,我扭头一看,车下原来站了两个下关车站的警察。警察A拎着我的箱子和背包。警察B用一根粗硕的警棍顶住我的屁股。屁股凉嗖嗖的,快要拉稀。我只好引体向上,双手鸟爪般紧抠长途车的窗沿,冷汗淋漓,大口喘气。我双膝顶着车体,上不能上,下不能下。兄弟,让我……我哀求着说,让我下来再说,好吗?
警察B望了一眼警察A。警察A笑而不语,满意地点头。随后,我仰拉八叉,落在下关长途车站的水泥地上。两个警察带上我,来到车站东侧,进入一间大小适中的屋子。警察A示意我坐下,对我盘问;警察B拿来纸笔,开始记录。
3
姓名?
郭发财。
知道为什么把你请到这儿来?
知道。
那好,请如实交代问题,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等等!
为什么等?
你们误会我,像电视里的公安人员,把我的问题搞得有些复杂化了。
哦!你说,……我们不冤枉任何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好,我说,车到省城是早晨四点,天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见,时间当时太早,出站也办不成事,我就躺在卧铺,神鬼不知地睡了一觉。没想到,睡过头了。真的,我说的都是实话。天一亮,车上的旅客都走光了,司机不知我还在车上睡觉,锁了车门,我连一点察觉都没有。
那么,天亮以后,你就顺手牵羊,带上别人遗忘的东西跳窗逃走?
不是这样,别把我想得那样坏,这样说,是诛心之论。
诛心?你以为我们和你在网上泡论坛,诛心,这两个字,亏你说得出口!
你们的问话,和论坛有关?
没有。
两位,这些东西本来就是我的,我指着两件行李,愤怒地说,怎么偏被你们说成是别人遗忘的呢?
你有证据?
证据?
比如,能说明箱子和包里面,你都放了些什么东西,我们打开当场验证,假如里面的东西与你说的相符,你就可以赢得我们的信任。
我不一定完全做到。
怎么讲?
我只知道迷彩背包里的东西,因为这些都是我的,至于密码箱里放了些什么,我不好说。再说,我也不知箱子密码,如果当场查验,我们根本无法打开箱子。
很好!
什么很好?
嗯,郭什么来着?哦,对,郭发财,谢谢配合,你终于开始说实话了,这样很好。
4
警察A如释重负一笑。
警察B笔走龙蛇,在我对面的办公桌,唰唰地记录。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絮叨着,说,你……二位什么意思?
我们会让你明白。警察A说。
你们要干什么?
不是我们要干什么,而是你要干什么,郭发财先生,看你戴一副近视眼镜,大约也读过两天书,总该不会不见棺材不落泪吧?
刚才,我不是答应你们,和你们核对迷彩包里的东西吗?
但是,密码箱呢?警察A凑近我,小声说,老郭,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你如实告诉我,箱子究竟怎么回事?
我虽不知箱子的密码,但我照样无所谓地望着他的眼睛,说,可这并不能说明这个箱子不是我的。
那么,请告诉我们箱子的来历。
好,我说,掏出一盒烟,我气得手指哆嗦,取出一支,两位,我能抽支烟吗?
警察A看了警察B一眼,把一个硬纸杯从办公桌上拿过来,递到我手里。
谢谢!抽了两口烟,我对两位省城警察如实相告,我从外埠回老家探亲,临走时,领导交给我这个密码箱,让我在省城转车,务必夜里九点钟前把它送到黄寺的某某手里。箱子的密码,只有我们领导和黄寺的某某知道,你们和我谁想打开箱子,目前都不现实。
你做什么工作?
有时给领导写东西,有时跑腿办事。
请把身份证拿来,我们要看。
我没出示身份证。我将一个红色证件递给警察B。接过证件,他很意外,翻开合上,合上翻开地看了两次。他将证件信息逐一抄写在对我的问话记录上,然后递给警察A,警察A看了看证件上的照片,又看看我,走到我面前,将证件还我,说,老郭,请收好。
那么,黄寺的某某和你们领导是什么关系?他望着我,神色稍有缓和。
你们是啥关系,他们就是什么关系。
你不废话?
难道不是?
警察A伸出食指,将办公桌玻璃上的灰尘划出几道猫抓般的印子。他从裤兜里掏出纸巾,慢慢揩去手指的灰尘,双手撑着办公桌,冲动地面向我,他要突然站起,但做问话记录的警察,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坐下,面无表情地久久盯住我,像看一只蹿出外埠森林在等省城香蕉的猴子。
5
警察和我的对话出现短暂沉默。目光从两位省城警察身上离开,窗外的太阳白花花的。进站、出站的外埠车辆在下关长途站汇车。阳光落在车窗玻璃上,俨然我老家秋日田野里,随风晃动的待收棉花。阳光里,我睁不开眼,两个省城警察也有些不太适应。
他们同时交换一个眼神,同时将双臂抱在胸前,同时半仰在椅子上,同时眯缝着眼,同时从头到脚地看我许久,两位省城警察最终也没把我看出名堂。警察B合上刚才对我的问话记录。
老郭,就是说,警察A不甘心地说,真的不能打开箱子,让我们与你当场查验?
抱歉,我的目光对视着他,说,如果真的怀疑我是小偷,不如这样,两位请随我一起去某某办公室,等他打开箱子,我让你们与他当面查验,到时真相大白,我也落个清白,顺便把领导交待的差事办完。
那倒不必,某某办公室,不在我们责任范围之内,怎么可以随便去?
不能去某某办公室,就可以随便怀疑我?
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哪个意思?
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郭先生,希望你对我们的问话给予配合。
配合?可以!但是,你们配合我吗?我冲动地说,在省城,我只有一天停留时间,晚上九点,如果不把箱子送到黄寺某某手中,我向领导交不了差事小,回不了老家,事儿可就大过了天。
你家能有什么大事?
我母亲……快不行了!
老郭……那你……先走吧!
真让我走?
走吧。
我提上迷彩背包,拎着黑色密码箱,转身要走。但警察A拦住我,说,别介,老郭,请等一下。我深吸一口烟,走近两位警察的办公桌,将烟蒂掐灭在纸水杯里,我说,事情都已摆明,两位,还要让我签字画押?在下关长途车站警察办公室,由于长久抽烟,回答问话,我嘴唇已经干裂,我咧嘴对两位警察笑,唾液沾上嘴唇,却有某种隐隐的疼痛。
6
老郭,你别阴阳怪气,先在这儿老实待着,等我给某某办公室打完电话,他们知道你的来历,确实如你所言,并且知道箱子的来头,到时再走,也不迟。警察A瞪着我道。
请便,我让你同事看着,不袭警,也不逃匿。
屁股一歪,我坐上警察的办公桌,点了支烟,给警察B顺手扔了一支,烟落在地上,他捡起,看看,横放在鼻子下边,嗅嗅,他走向我,将烟送到我手里,客气地对我说,老郭谢谢,我以前抽,但现在,为了老婆打麻将的专项经费,我戒了。
望着玻璃那边——隔壁屋里打电话的警察A,我想,某某会理你们?心情很矛盾,既想某某办公室不理他,最好让他挨顿臭骂,碰一鼻子灰;又希望某某办公室,体察下情,告诉警察我要送交的箱子的来历,以便让我尽快脱离下关这是非之地。
打完电话,他走出,面无表情地说,郭发财先生,某某办公室的秘书和你通话,对不起的地方,你多担待。是吗?跳下桌子,拎起箱子,背好背包,我轻松地对他说,你们履行职责,我倒没有觉得。
可走进他刚才打电话的里屋,拿起电话,我却深感非常意外。因为受话器中,没有某某办公室秘书的声音,只有一串嘟嘟的忙音。忙音麻酥酥,如电击,不停地舔吻我的神经。怔了怔,我知道两个省城警察还在关注我,侧过脸,我就装出外埠某机构小吏拜见大领导时,特常见的热情、卑微和谨慎状,冲着空空无人的电话忙音大声喊话。
哦,不用,……真的不用麻烦,谢谢,……嗯,我弯腰,点着头,说,嗯,好的,请您转告某某,对,……嗯,……对,我马上打车过来。两位警察的眼睛在窗外迷惘地看我。告别下关车站,面向他们,我自我解嘲地笑。警察身后的墙壁白晃晃、亮堂堂的。墙上有只蟑螂,紧抓白色墙体。蟑螂害怕落地,自己摔死自己。我听见他们一个对另一个说,嘿,哥们儿,你瞧,他那一副得意的尊容!
7
黄寺大街的林荫小道,天空蓝莹莹的,间或飞着燕子和纸做的风筝。我感觉奇怪,林荫道两边,明明密布着树枝,但透过头顶茂密的树叶,我却能看见蓝如玻璃的辽阔天空。不过,燕子与风筝究竟是从哪个方向飞过来,又蹿上天的,对这些,我又一无所知。
提着密码箱,背着背包,嗡嗡地,我像一只无头苍蝇,顽固地寻找省城的目标。
在黄寺的人群和车辆中穿行,我在想省城的另一外埠——我乡下病重的母亲。我的嘴角噙着烟卷,面容带有外埠男人进入省城的惯常姿态。我神色淡漠,满怀心事。在我脸上,不时还有外人不易觉察的几丝焦虑。
我步履稳健,走得匆忙。但走出林荫小道的出口,我却迷路了。街上的出租车吃了鼠药的野狗般无声地疯跑。拦了几辆,司机一律拒载,不是说车没油了,就是说,哥们儿,你拦下一辆吧,这会儿我要回家吃饭。根据司机不愿拉我的情况判断,司机拒载的理由可谓简单,我要去的地方可能就在附近。因为区区九元的起步生意,精明牛逼的省城司机一般都不会做。
站在黄寺的十字街头,最终,只好放弃通过出租车把我带到目的地的念头。临上外埠开往省城的长途车前,领导到车站送我,握着我的手,交代任务的特殊性、必要性,之后曾经问我,到了黄寺,如果找不到某某办公室,你怎么办,我说好办,把地址告诉出租车司机,就是要找三条腿的老鼠洞,司机也会把我拉到目的地。可现在,我与某某办公室近在咫尺,省城的出租车司机却把我视为怪物。计划没有变化快,这教训——我受够了。
8
从地质研究所到双旗杆西,不远不近的一段,我却走得背上隐隐冒汗。我在小街停下,举目张望,对面街口一个手提鸟笼佩戴红袖标的省城大妈突然出现。大妈也在向我张望。见大妈迎面走来,我就快步上前问路。
小伙子,你跟我来,大妈爽快地说,你要去的地方,正好我也要去。走吧,我们同路。望着大妈胳膊上的红袖标,我似信非信,有些不好决断。年轻人,大妈放下鸟笼,抬起右手,指着左手的红袖标,说,我有这个,只管放心跟着我走,保你不会吃亏。
谢谢大妈。
别谢,出门在外,谁都有不方便的时候。
省城大妈在前,我在后边,默默紧随。我们在春天的黄寺大街行走。大妈的鸟笼里关有一只叫不上名的鸟儿。我纳闷,大爷的鸟笼,怎么提在省城大妈手上?当然,我也只是随便想,没有贸然问她。可大妈偏偏又是个很爱说话的热情大妈,对我尤其好奇,不停地问这问那。大妈的问题,有的我能回答,有的根本不能,我只能勉强支唔。
以前,你没来过黄寺?
没。
这次,走亲戚,还是看朋友?
都说不上,呵呵,又都沾边。
到省城,坐车要一天一夜,走赤北高速,还是从古北口直接过来?
两条线,嗯,都能走。
坐长途汽车来的?
不,我坐商务车。
商务车?
对,就那种价格便宜……运管部门钓鱼执法,特别喜爱的车子。
手提鸟笼的省城大妈把话问完。大妈,我们要去的某某办公室,离这到底还有多远?当我眼前出现一座过街天桥,望着大妈的背影,我才开始着急地问她。大妈转过身,说,小伙子,没多远,过了立交桥,径直往北再走一会儿,很快就能赶到。站在高我三级的天桥台阶,大妈脸上纷乱几丝被风吹乱的花白头发,但她只顾和我说话,没顾得上将头发理顺。头发纷乱的省城鸟笼大妈,在我眼里,有点像遥远得已被人忘记的刘胡兰。
9
跟随红袖标鸟笼大妈,来到一座青瓦红墙小院落,院落的朱红大门很好看,像少年时乡下老家的墙壁上,我抬头仰望多年的画儿。院落门口,左右各有一尊石狮。开出一条小缝的朱红门里,是条卵石小道,左串右连,花红叶绿,正在随意点缀着园子。
院里一把藤椅,半躺个头发花白的老头,老头戴着让我无法看见眼眸的墨镜,墨镜老者身边,毕恭毕敬守着一个和我年岁相差不多,也戴近视眼镜的年轻人。
年轻人给墨镜老者朗读报纸。藤椅上,墨镜老者仰望蓝天,鼻吸均匀,像是打着呼噜,已经睡着,又像风从鼻孔钻出他的眼眶因墨镜的阻隔发出的响动。年轻人却两手拉开,略微向前平举一份报纸,依然给墨镜老者读新闻。
读报青年见我和大妈进院,收住声音,后退一步,将刚读的报纸叠好,弯腰放在墨镜老者身边的茶几,又直起身,训练极有素地,双腿快速自然岔开,目无表情地,将两手背在身后,面向我和鸟笼大妈迎风跨立。
读报青年像电影、电视中人,秘书跟随首长、小弟跟随大哥的风采,不断在青瓦红墙院落飞扬。但读报青年服侍的墨镜老者,却一时无法让我将他与头脑中固有的首长形象挂钩,涉及到香堂、帮会的大佬模样,也让我不敢对他倒底是何身份给出结论。
10
先生醒醒,避开读报青年的瞩目,鸟笼大妈轻手轻脚地走近墨镜老者,轻拍他的肩膀,说,先生,你醒醒。嗨,老者颇不耐烦,嗨的声音,拖得很长,老者拨开大妈的手,说,眼睛都长瞎了,我哪儿是睡觉,网上关于卡扎菲的争论,各方言论十分活跃,我在听报纸,领会精神,判断各种观点的对错,刚才,好不容易才将老卡的军力部署理出头绪,结果,你猴急猴急地打岔,思路又被你给搞乱球了。
先生,先不说老卡,大妈有点委屈地说,是这样,外埠的客人已经到了。
这么快,有把握吗?
有。
人在哪?快让我看,这事得慎重,千万不能马虎。
来,过来,大妈退后一步,拉住我,说,过来,让先生好好看看。
看我?挣脱大妈的手,我有点发毛地说,你不是说,要带我到黄寺大街,去找某某办公室吗?
小伙子,别着急,大妈温暖粗糙的左手重新拉住我的右手说,小伙子,过来。大妈的手很有力,嘴唇嚅动着,我一大把年纪,不说假话,让先生看你,是对你好,我们不害你,来呵,别紧张,先生问你话,想好后你再诚实回答,没把握的千万不能乱说。
大妈的手心,像冰凉的水蛭用吸盘紧紧吸住我。望着大妈右手笼子中的鸟,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想到老家母亲的病,我虽忧心如焚,但一面对省城的人和事物,我只能干着急。事已至此,我也没有任何可以脱身的办法。水蛭的吸盘,从大妈的手心钻出,紧紧抓住我的头发,我被吊在半空,双腿乱蹬,我与省城地面的关系,已经越来越远。
11
我背着迷彩背包,提着黑色密码箱,带有警觉地向走向墨镜老者。老者如果真是某某办公室的,我就按领导交代把箱子直接给他,立马走人,赶往另外的外埠,回乡去看病中的母亲;墨镜老者假如与某某办公室无关,我就需要沉着应对,不能让人把我洗白,我还傻了吧唧地帮人家数钱。
有了心理准备,墨镜老者要看我,我就没有理由不让他看。
先生,谈什么?到省城,我只有一天时间,许多事必须在今天办完,我说,我母亲得了很重的病,我有事,你请快点,晚上九点,我要赶到西客站,坐夜车回家,时间晚了,我就无法见到我妈。我和墨镜老者说到病中的母亲,镜片背后,我的眼眶里有眼泪涌动。但在省城这座青瓦红墙小院落里,我却没有轻易流下。
年轻人,呵呵,别急,耽误不了多少时间。老者仍然仰望天空,在两片大墨镜下,嘴唇呱嗒着,说,年轻人,心急吃热豆腐,烫嘴,说真的,老者手腕轻抬,肥胖手指敲着躺椅扶手,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急着回家看老娘,呵呵,有娘时,我也这样,你的心情我理解,但你不要忘记任务,千万别急,我对你的情况了解不清,对我对你都没什么好处。
好吧,我不急……那么,请问先生有何指教?
指教?呵呵,屁的指教,随便聊。老者直起身,抓过躺椅边黑檀茶几上的红泥小壶嗞溜喝了一口,隔着两片墨镜的目光或集中或空洞地继续看我。大约过了三十多秒,墨镜老者对我说,年轻人,我们已经等你很久,但你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等你的作用和意义。
您是……某某?
现在,我是谁,并不重要。
那您……
我只问你,认识绫子不?
绫子……
哈哈哈,绫子是个姑娘,当然,你可以不这样叫,嗯,绫子嘛,就是你们叫的小姐,哦,不能叫小姐,嗯,叫美女吧?哈哈哈,老者仰天大笑,声音嘶哑,听着像宫廷影视剧里的太监,嗯,小姐、美女……哈哈哈,边笑,老者边抬起肥胖的带有黑色老年斑的双手,把刺猬状的花白头发往粗短肥腻的脖子上捋了又捋。
12
呵呵,我被墨镜老者的样子感染,无法控制自己,也跟着他笑。我说,真的先生,我不认识叫绫子的姑娘、小姐或美女,呵呵。
你不认识绫子?
不认识!
这就奇怪了去,昨晚绫子明明对我说,今天上午有个手提黑色密码箱的外埠青年要在大院门外的十字路口出现,他来省城见她可能迷路,我才让大妈事先等在路口,把绫子说的外埠青年从机关门外引到这来见她。
不可能吧?
怎么就不可能?
绝不可能!
好,那我问你,你是不是姓郭,叫郭发财?
你是……怎么知道的?
绫子亲口告诉我的。
绫子是谁,与你是什么关系?假如我的问题不算冒昧,还请先生……
这个……暂时你就不要多问,墨镜老者打断我的问话,说,到时你和绫子见了面,呵呵……不就什么都明白吗?墨镜老者的声音,听着虽恐怖,但说话的表情,还有年轻时代他对他老娘也曾像我一样记挂,这些倒也能够赢得我的认同。
13
我抬手看表,时间是上午十一点三十八分,距夜间九点去西客站,时间还有富余。为了揭开谜底,我决定在青瓦红墙院落滞留,拜访叫绫子的姑娘、小姐或者美女。既然,绫子对我的行踪如此了解,我也没有理由不去会她。
临来省城前,在外埠长途汽车站,领导交代我,到省城转车回老家前,务必把箱子带到某某办公室,由于任务特殊,我不能携带手机,省城下关车站出站,可直接往黄寺方向走,到时有人会与我接洽,带我到某某办公室去。至于接我的人是谁,领导要求我最好不要问,因为领导早就做了安排。
因此,除了对省城女人绫子的单纯好奇,服从领导安排,准备移交黑色密码箱,或许是个不好也不太坏的选择。但是,由于领导的任务交代得只能意会,无法言传,所以,白发墨镜老者与我谈到绫子与我认识与否,我不好根据臆断给出我与绫子认识的准确答案。
走近青瓦红墙小院的西厢房,大妈把鸟笼递给读报青年,捞起衣服下摆掏出一串钥匙,打开门,大妈后退一旁;墨镜老者跟在我的身后,说,郭发财同志,这里就是绫子的房间,她留下话,让你不要出门,请在她的房间等她。老者将手在我肩上摁了摁,示意我既来之则安之,但我转身看他,他又觉得有些不妥,不好意思地将手抽回。
请问,绫子到哪去了?站在省城女人绫子的房间,我问,除了让我等她,绫子就没留下别的什么话?郭兄,这些天,她忙,只吩咐郭兄一到就在她的房间等,别的好像什么也没有说。读报青年说,不过,郭兄,请你绝对放心,绫子既然这样说,在她方便的时候,或者下午下班以后,她就一定会尽快与你见面。
墨镜老者、读报青年对我点头示意,留下省城大妈,两人先走。不一会儿,红袖标鸟笼大妈,变戏法一样弄出两听八宝粥,说,小伙子,坐了一夜长途车,肚子饿了,先用这个垫巴着。可还没等我道谢,大妈就礼貌地关上门,提着估计她睡觉也会提着的鸟笼,风一样快速退出。
两听八宝粥,让我饥饿更加难耐。但我觉得那东西是两颗定时炸弹,一动,它就会立马爆炸。因此,我虽想吃,也没有轻易动它一个指头。我从迷彩背包里翻出两块面包,就着昨夜残留不多的剩茶,把我从外埠带进省城的面包吃掉。鸟笼大妈留下的八宝粥,哪怕它是天上的龙肉,为了黑色密码箱的安全交接,我不被蒙汗药弄翻,我的胃口也要坚决抗拒。
14
在省城女人绫子的闺房,我开始打量她的房间。她的房间陈设简单,除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几乎没有什么奢侈品。但绫子的房间布置简单,不等于她的房间因此就没妙龄女子的闺房气。绫子房间正中是日式榻榻米,绕墙而围的蓝花布缝满大小各异的口袋,里面插有开本不同的各类书籍;榻榻米的右侧,放置一盏小巧的软羊皮台灯,墙上挂有古色古香的铜镜,墙边置有原木打造的个性工作台等。绫子整个房间的陈设,都在向我展示女主人的格调与情趣。
不难看出,绫子是个带有波西米亚风格的文艺青年。这种女人,如果也会图财害命,我的外埠生活经验与艺术修养,则有可能坍塌殆尽。目光在绫子的房间,蛇一样继续流窜。我在心里琢磨,黑色密码箱的接手人,倒底是不是让我在她房间等她的绫子。
绫子多久回家?绫子是什么样子?绫子留的是长发还是短发?绫子的性格是温婉还是刁蛮?她与我单位的领导究竟是何关系?……关于绫子的各种猜想,本来就如乱麻,很难理出头绪,掺和我如蛇流窜的目光的搅和,她已让我倍感压力。
我踱到绫子的工作台前,在笔记本电脑的翻盖与键盘之间抽出一张A4纸,看到绫子让我等她的具体安排。一条小狗想咬自己的尾巴,急得团团乱转,基于绫子留下的A4纸,小狗终于放弃自己想咬自己尾巴的企图。我预感,绫子与戴红袖标鸟笼大妈不同,她会顺利把我带出省城的迷宫。
夜间九点,登上省城开往老家的夜行列车,于我,将不属于空想。
我靠墙而坐,迷彩背包、黑色密码箱放在随手可及的位置。但是,当我等得青瓦红墙院落上空落霞满天,根据A4纸的留言,理应下班回家的绫子却依然不见影形。绫子不但没有按时回家,鸟笼大妈、墨镜老者、读报青年也无一人露面。夜间九点赶车回到老家的计划,似乎正在落空。
我困得眼皮打架,饿得前胸贴后背。绫子在A4纸的留言中告诉我,饿了可吃大妈送来的东西,困了可在她的榻榻米上休息,无聊时,还可用她的笔记本电脑上网。为了我能顺利上网,在留言中,绫子告诉我,事先她已经将网络连接设置为开机自动连接。不过呆在她的房间里,除了靠墙而坐,我还是只能昏昏欲睡地靠墙而坐。
15
女主人不在,我不敢有超出常规的其他动作。快到晚上新闻联播开始时,绫子还是没回来。离开下关车站的警务室,红袖标鸟笼大妈、墨镜老者、读报青年与绫子A4纸上的留言和我要找的某某办公室,根据我的判断,彼此间都有现象与本质的必然联系。但是,当门外昂昂如同牛叫的新闻联播前奏音乐响起时,不祥的预感却让我在绫子的房间如坐针毡。绫子摧毁我的耐心,把我几乎推到崩溃的边缘。
在绫子的房间,我无法再待下去。早点回家,探望病中的母亲是其一。没将领导交代的事情办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但绫子的房间毕竟不是下关车站。在下关的外埠长途客车上,司机把我锁在车里,我可以搞掉车窗玻璃走人,但在绫子的房间,我的确不能这样干,就是想这样干,我也没有机会。因为除了已被红袖标鸟笼大妈锁上的房门,我四下寻找,绫子的房间并没可供逃匿的出口。也许绫子房间的窗子隐藏在绕墙而挂的蓝色花布背后,但缝满口袋,插满各种书刊的花布,又是个我如妄动就会垮塌的书架。因而,寻找窗子的企图,我只好放弃。
看来,我要离开绫子的房间,只有突破已被大妈锁上的房门。但在绫子房间的门外,如果鸟笼大妈、墨镜老者和读报青年举着棍棒等我,我贸然出去,一定会被他们打得头破血流。这种假设一旦成立,肯定会让人防不胜防。不过话说回来,本着事情已然,对绫子和青瓦红墙小院中人,我也不能全把他们当成坏人搁在心里揣摩。
早晨,下关车站的两位警察,因误会给我带来麻烦,他们在我身上犯过的错误,在省城女人绫子的房间,对绫子、红袖标鸟笼大妈、读报青年、墨镜老者我就不能重复。赫拉克利特说,人的一只脚不能同时踏入两条河流,两只脚不会踏入同一条河流,这话,是我困在省城女人绫子的房间终归不能贸然行动的一个阻力。
我该怎么办呢?地板上,两听八宝粥,出于安全的考虑,我可以不吃,榻榻米地铺,因我与绫子男女有别,我可以不睡,但绫子的笔记本电脑,既然她已留言许可我用,迫不得已,我也不能再有什么好自律,或者好客气的。我的想法是,用绫子的笔记本电脑上网,通过MSN,把我在省城遭遇的情况给领导进行汇报,如果领导在线,就等他下达更进一步的指示;不在,我就把我在青瓦红墙院落绫子房间里面临的困境告诉他,如果有个三长两短,领导决定采取其他补救措施,也好有个第一手信息参考。当然,我也可以写条微博复制给我的网络朋友,假如我遭遇不测,在指定的时间没与他们取得联系,朋友就可把我的最后信息公之于众。
我翻开绫子的笔记本电脑,坐在原木打造的工作台前,开机时间,大约用了四十多秒。果不其然,正如绫子事先在A4纸上所言,在她的房间里,不用网络连接密码,我也能够顺利上网。而且登录MSN后,领导的ID战狼123,果然像只虱子一样欢跳多时,他在网上早就给我说过了话。我在省城的经历,他已全部掌握。通过MSN,领导发来的信息有责备,也有谅解。当然,差事没给领导办好,省城的具体情节、细节,并非能以我的意志可以左右,光责备不谅解,并不符合他对部下的风格,对解决问题也没直接帮助。
16
我送你上车时,就让你脑壳醒豁点,当时你都答应得好好的。可结果呢?到省城你在下关车站,别人都下车,你不下,给我捅了娄子。两个警察问你话,你那样回答没错,能够看出你的水平和素质。但跟他们磨叨那么久,这就是你犯下的致命错误。这下可好,警方对你的问话记录,虽说你没签字,但人家根据你的证件信息,已把问讯记录传真到我办公室。
事情办成这样真丢人!这样说没有怪你之意。怪你也已于事无补。回过头想我也有错。早知事情如此不顺,还不如让你开车先到省城,事情办完后,再将车子开回你老家。有JPS定位仪给你带路,你总不会给我乱球闯吧!?
黄寺的某某办公室,现在也已给我来过电话。现在,他们不会和你正面接触。因此,鉴于你捅娄子和在省城的情况,我已会同朋友重新安排。你在绫子的房间,我希望,你能用她的电脑上网,及时看到我给你的留言。不过,你要记住:就是没事给我睡觉,你也老实待在原地最好不动!
记住,遇有特殊情况,也别再耍小聪明。砸坏汽车玻璃的糊涂事,在绫子房间,千万别再重演。凡事记住顺势而为即可!我安排好单位的工作,亲自开车到省城与你会合。晚上九点之前,咱们争取见面。约定时间内,如果我还没到,你就继续待在省城等我。误了回家看你母亲的时间,你可直接开车回家。
17
合上绫子的笔记本电脑,我看了下表,时间是晚上七点四十左右。我踱回墙角,重新靠墙坐下,回想领导给我的留言,内心可谓喜忧各半。喜的是,领导到省城与某某办公室亲自交割密码箱,我会省时、省事很多;忧的是,我没把领导交待的任务完成好,嘴上他虽不好明显责怪,但日后我还在他手下继续干活,日子将有不难想象的艰难。伴随饥饿、困乏、紧张、沮丧,在省城女人绫子的房间,靠在墙壁怀抱黑色密码箱,我既不心甘也不情愿地睡去。
我被鸟笼大妈弄醒时,省城黄寺的天空,在青瓦红墙院落已经黑透。大妈打开门叫醒我,发生了不该发生的意外。像上午拍打墨镜老者的肩膀那样,大妈蹲在我跟前,用胳膊戴红袖标的手拍我肩膀,引起我睡眠中保留的警惕对她的反弹。从不离手的鸟笼和大妈一道,被我一脚踹倒在绫子的房间。
哎呦,为啥要踢我这个老太婆?扶起鸟笼大妈,我将鸟笼捡起,重新递给她,说,大妈,我到省城出差,携带的东西很贵重,任务性质决定了外人不能轻易靠近我,刚才我睡觉,你惊扰我,才被我在梦里踢了一脚。对不住的地方,您老多担待。
哎呦,就算这样你也不能把我随便踢倒……大妈抱怨着,从光洁度可照人影的地板爬起,将鸟笼重新提在手里,说,小伙子,曹操在梦里可以杀人,你呢,睡觉也能踢人,哎呦。大妈站起来,不断地揉着屁股,随后脸上带着笑容说,早知你是属曹操的,我就该用根竹棍或者树梢儿把你叫醒才对是不?呵呵!
嗯嗯嗯!见大妈笑了,而且,还能和我开玩笑,我知道,刚才,大妈虽被我踹在绫子的房间,但从她的言语中,我却有理由深感庆幸,其实,她并没受到我所想象的伤害,否则,领导从我供职的单位赶到省城,我又会给他捅出新娄子。可我尽管暗自庆幸,但在红袖标鸟笼大妈面前,我还是装着她真的受了伤,并且我还很愧疚地说,大妈对不起,没有什么大事儿吧?有事儿,我可赔你医药费。
18
小伙子,别说医药费,我这老骨头,没那样金贵,我来,是要给你说正事,红袖标鸟笼大妈告诉我,说,绫子今晚有事,不回家,你们的会面需要另外约时间。大妈你说什么……其实,绫子不见我,从领导给我的留言中,我早猜出八九不离十,但在鸟笼大妈面前,我不想很轻松地便宜他们,我佯装心里压抑着巨大的失望与愤怒,说,她单位有事,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你说我该怎么办?
不行,你就再等她?
等她,说笑话吧你,到省城,我只有非常紧凑的一天,可是,根据你们的安排,我老老实实等绫子,结果现在你又说她不回来,这明明是把我当成猴子耍。
不是这样,绫子的确有事,她的单位今天通知她,上头开展“下转正”活动,有意增加了她的名额。
什么叫“下转正”?
下基层,转作风,正文风,这些就是“下转正”。
这么说,绫子在媒体工作?
这个,我不知道。她怎样让先生给我传话,我就怎样给你说。具体情况,只有先生和绫子本人才知道。
可是大妈,我母亲病得很重,今晚,我要赶去西客站。绫子不露面,箱子交不成。两件事,都被你们耽误了。
这个你放心,绫子知道你要回家看你老娘,相关情况她和你的领导会给你安排好。
19
红袖标鸟笼大妈提到绫子与外埠我单位的领导,这点让我很意外。看来,他们什么都已沟通,我只是个被排除在外的局外人。但在鸟笼大妈跟前,我不好把事情点破,或者说把这事情点破没有半点必要。我沉默着。看到两听八宝粥摆在原处,还是老样子没动,鸟笼大妈也许意识到,在绫子房间,我还没有吃过东西。也有可能,红袖标鸟笼大妈根据绫子的意图,料想我沮丧,怕我愤怒,她才提出由她陪我到青瓦红墙小院外边吃饭。
离开省城黄寺大街的青瓦红墙院落,我背着迷彩背包,提着黑色密码箱,叼着从不离口的烟卷儿,步履匆忙地走在前面;戴着红袖标,手提鸟笼的省城大妈几乎小跑,紧紧跟在我的后边。根据她的提议,离开绫子的房间,我们去找馆子吃饭。但墨镜老者、读报青年却没露面。他们没有如我所想,按照常理,陪同我与红袖标鸟笼大妈一起去吃。
在名叫薇薇老妈蹄花馆的小馆子,我和大妈坐下来点菜。饿了快一天,根据我肠胃的实际需要,本应找个菜品齐全的饭馆,好好吃喝,美美饱餐。但考虑到鸟笼大妈上了年纪,同她一起吃饭,作为晚辈,我该给她弄些软和易消化的东西。所以,生气归生气,沮丧归沮丧,走到薇薇老妈蹄花馆门前,我还是反客为主,邀请大妈与我坐下一起吃老妈蹄花。
服务员将一瓦盆蹄花上桌,大妈抄起筷子,吃得比我欢实。我喝了小半碗飘着几粒葱花的蹄花汤,对文火炖得烂若鼻涕的猪蹄实在没有多大兴趣。我又要了一碟油炸花生米,就着一杯枸杞散白慢慢吃喝。等待领导抵达省城,能在第一时间与我联络。大妈则坐在我的对面,吧唧吧唧,吱溜吱溜,把老妈蹄花吃得地动山摇。
我为鸟笼大妈选择蹄花馆的例子可以证明,在省城女人绫子的房间,我虽被墨镜老者、读报青年关了一天,但我的脑子还是没有被驴踢过,考虑问题还不致于完全报废。单位领导将我当局外人,如果基于我的脑子不够用,他才作出如此的考虑,那只能说明,那是他和他们的错误。
我将碟子里的花生米一粒两粒地数着吃,把杯中的散白酒偶尔沾沾嘴唇,不置可否地慢慢喝。为了黑色密码箱的绝对安全,我的目光在薇薇老妈蹄花馆里流窜。根据庄子的理论,或者可以说,我吃喝的是花生米,枸杞散白,也可以是放在餐桌下,被我双腿紧夹住,白白浪费一天时间,还没交接脱手的黑色密码箱。
嘿嘿!哥们儿,都听我说,薇薇老妈蹄花,在省城,真的有名。邻桌的光头男操着省城口音明显的普通话,给同桌壮实的络腮胡、肩背吉他的摇滚老炮介绍馆子的好处,光头男将朋友的杯子倒满酒,怪笑两声,一脸匪气地说,薇薇老妈蹄花,除了猪蹄炖得烂,沾水香,有名之处还在于,二十四小时营业从不打烊;黄寺这带的性工作者,晚上都喜欢来这吃宵夜,喝啤酒,各路寻欢客要找她们,只要来薇薇老妈蹄花馆,每个人都不会跑空,嘿嘿!
络腮胡、摇滚老炮没点头,也没回应光头男的情况介绍。我却可肯定他们对光头男的介绍听得认真,也有相当兴趣。将一粒花生米放进嘴里,抿了小半口色如黄尿的枸杞散酒,奇怪的是,我的味蕾发生故障,酒与花生突然没有半点味道。我将目光离开临桌的三位,摄像机似地对着蹄花馆的玻璃墙体,墙外、临街小矮桌四周,果然围有几名妖冶女子在吃东西,在喝啤酒,在旁若无人地闹玩。
20
玻璃墙外的马路牙子,与妖冶女子相隔不远的霓虹灯下,走来一个吹箫男子。男子穿着老式军装,腰系猪肝色的武装带,背上还插了个稻草人。我的麦克风耳朵可以听见,在省城春天的夜晚,军装男吹的是《笑傲江湖》。军装男把苍凉、自由、旷达的旋律用箫吹起,我的手指在餐桌合着他的节拍敲击,心里却随黄霑的名曲,嘴也不张地吼唱: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天知晓……在心里唱歌,符合我在省城遭遇的林林总总。
灯红酒绿的黄寺大街,在我的摄像机眼中本来就极陌生,经《笑傲江湖》这么一闹,瞬间就多出许多荒凉无人的况味。当然,内心的荒凉无人相当程度要归于我对吹箫男背上插着的草人的瞩目。稻草人真实而又虚幻,突兀却又融洽。它与黄寺的夜景浑然一体,使我坐在薇薇老妈蹄花馆,早将自己远离省城,置身世外。
令我非常不解的是,武装带里插着稻草人的军装吹箫男,把《笑傲江湖》吹响不久,邻桌的光头男、络腮胡、摇滚老炮仿佛得到某个秘密信号,像赴一个重要约会,光头男在吧台飞快地结完账,他们三个就快速冲出门去,钻进一辆草绿色的士,走得不留痕迹。更让我深感莫名的还有,鼓起腮帮吃得欢实的红袖标鸟笼大妈,听见军装男的《笑傲江湖》,她也迅速起立,也像得到某个神秘暗号,撇下我,独自飞叉叉地跑开。
一曲《笑傲江湖》,俨然一阵大风,吹了薇薇老妈蹄花馆的四名食客。当然,消失的人,只有我的摄像机眼睛才能看到。其他人,如玻璃墙外的性工作者,对此她们就没觉察。时间,已是晚间八点四十,距我到西客站赶车的计划越发急促。但我的引路人,红袖标鸟笼大妈却抛下我,连话也没留,就独自走开了。
21
领导迟迟不到,我被搞得毛焦火燎,又将再度现入坐立不安时,引路人红袖标大妈却提着鸟笼,带着两个警察,令我讶异地重新回到薇薇老妈蹄花馆。装有消音器的狙击枪射出的子弹击中要害。玻璃墙外,妖冶的性工作者如同皮影,霎时淡出我的摄像机眼睛。大厅内外,吆五喝六的客人如同泄气的皮球即刻瘫软,却将目光整齐地盯着我看。
在外埠某机构工作,我持有过硬证件,在省城,我又没干违法勾当,对警察,因此我有良好的自我免疫力。所以,大妈领着他们来到薇薇老妈蹄花馆,我依然心劲拳拳,有时间将大半杯枸杞散白一仰脖子喝光。不过,鸟笼大妈同两位警察混在一起,在心里,我还是难免咯噔。因为两位警察不是别人,他们正是早晨我在下关车站遭遇的两位警察。红袖标大妈与两位车站警察的意外出现,正好也是我面不改色心跳却要加速的主因。
警察A由鸟笼大妈领着,在吧台埋单;警察B走向我,微微地笑。我离开餐桌,背起迷彩背包,警察B见状,伸手要帮我提黑色密码箱,却被我出手捏住手腕,将箱子轻轻摁住夺回。老郭,大家是哥们儿,别见外啊你。他尴尬地说。我没吱声。两位下关车站的警察,早晨误会我,给我造成麻烦,现又在我眼里出现,他们的意图 ,一时半刻,我还没搞明白。但打他们一进蹄花馆,放弃连夜回家去看母亲的打算,这也是我内心清楚的不争的事实。他声称我是他哥们儿,对他,我却没有拿出哥们儿的信任,给他哪怕是种装装样子的反馈。
死猪不怕开水烫是我重新面见两位警察的心态。但我走出薇薇老妈蹄花馆,眼前却意外出现了一辆警车和外埠我单位的那台猎豹越野。看到单位的车,我双腿绵软。坐在地下,想站起来,力气已经不够。帮我买好单的警察A见状跟来,掏出一盒软中华,取出一支点燃,递给我,说,老郭,早晨真的是一误会,希望你别介意。
警察A轻言细语,与早晨在下关车站他对我的问话的语气判若两人。但我依然沉默,没有回话。抽着他的软中华,轻松与芳香,的确比我五元一盒的劣质烟卷受用。他拉起我,替我拍去屁股的泥灰,说,老郭,走吧,回家去看母亲,时间虽晚,愿望毕竟没有落空。望着两位警察、省城的红袖标鸟笼大妈,我将黑色密码箱放在三人中间,背对他们,我背着自己的迷彩背包,跟随灯影拉长的影子,在黄寺大街飞跑,目的只有一个——早些回家,去看乡下病得不轻的母亲。
责编:孙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