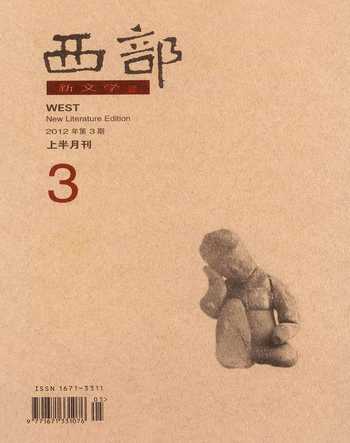对窗
2012-04-29凌明玉
我经常站在窗口,凝视着窗外。
不久之前,我才倚着自己的窗,看着对面旅馆。与旅馆二楼房间对望的是我的住屋。那里门窗大敞,电扇还在柜子上嗡嗡转动,好像主人只是暂时离开,随时都可能回到座位继续阅读摊开的书。
这里像荒废的孤立城楼,楼梯转角的绿色纱门“呀”一声发出低沉叹息,纱门兀自飘摇,像一张急欲言语的唇。我想转身往楼下奔去,噔噔噔噔,一阵笨拙声响令我收住慌乱的步子,回头一看,却什么也没有。
以为又重复了一次梦境。经常在梦中出现打不开的纱门,长长的走廊,阴暗的光线,一个女人的身影。
这不是梦境。此时,只能挥开这些缠绕的记忆。我知道,她在那里等我。
走上二楼,长廊出现,两旁是编排着号码的房间。我在左边第二间房门前停住,踟蹰一会儿,再度推翻预想的行动。
已经不能回头了,只能前进或停在原地。
拉开走廊靠阳台边上的玻璃窗,轨道拨拉拨拉的声响不顺畅地回荡于整个空间,稍微一使力,木窗的绿漆就被剥落一大块。
此时不会有人忽然从房间跑出来,附近有家汽车旅馆,游人大都在那里,休憩过宿。即使这样,女服务生还会在后面的窄巷刷洗脚踏垫,老板娘习惯在柜台打盹,当我被发现时,她们只会抬起宽松眼皮看一眼,想着,喔,是老镇长的孙子。
●
看着窗外继续吞吐烟圈,下意识摩挲着裤袋里的打火机。
下午有不太炎热的阳光,但天际浮泛着介乎阴晴之间的颜色,看起来有点悲伤。或许行动很快将被终结,或许我得回去。如果还留在自己的房间,我可能像家中的肥猫蜷在椅子上,摊开书打个呼噜沉沉睡去。
我可以一整天都盯着窗外。远方连绵的山脉,在天空写成蜿蜒虚线的鸽群,让灰暗的色泽填满整个视线。不要问我聚焦的是什么。经常在窗边站成一竖破折号,直楞楞的,在边陲小镇现在的时空,想起从前那个家。
一年前才从医院回到诞生之地,我已长成青年,小镇却静止在某个时间点,不曾改变。旅店、老街、爷爷故去后留下的低矮古屋。
摸着刚刚冒出的胡须,我的确在不停地成长并崩坏之中。站在长廊窗口已抽了两根烟,阳光从这格窗移往下一格,我还站在原地。
站上整个下午也不会有人发现吧。失去火车靠站的小镇,随着居民陆续迁徙也遗失繁华,空荡的车站立在寂寞的铁道旁,仅留下轨道交错,再也等不到旅人。
每天我注视着这条街,直到有一天,她走进画面。
但我不为所动。我想她是来欺骗我的视觉,从小到大,只要她的影像一出现,身体就会浮现出罪犯的气味,牵引着我跟她走。这也是她最让我羡慕的能力,丢弃一切的能力。
●
我的行动应该再敏捷一些。攀翻过矮墙,后门轻易打开了。刚才不愿由前门大摇大摆进来,但我居然又看见柜台女服务生,头一点一点地瞌睡。像一再出现的梦。是幼年回忆浮出意识呼应我的行为?因为她没有更老一些、更沧桑一点。那打盹的女服务生是此刻的幻影吧。
靠着窗遥望远山、街景、路人,小镇像个音乐盒,每天只固定走完上紧发条的那一圈旋律。
她出现在街道上了。从踏进小镇那一秒起,只要她一出门,空气即会凉滋滋的与风细语她的种种,都市来的女孩,挺着肚子嫁到这里,更无法苛责镇里老去的女人在背后议论揣测。
她穿着金色低跟凉鞋啪答啪答敲响小镇唯一的道路,手里挽着小菜篮哼着歌,每个人都看到她悠闲的模样。金色亮光在她脚下像栖着模糊的影子,正在舔着冰棒的小孩盯着她直看,冰棒掉到地上去了。
我也喜欢看她。看她在菜园拔菜,看她趴在地板上使劲擦地,看她在大雨将至时收衣服的慌张模样,看她讲电话说没两句就笑个不停。
曾经以为只要回到这里,破碎的心情就能痊愈,但只要我专注地想着她,她就来了。
啪啦、啪啦,她回来了。
不知道她是否看到我,是否注意到有人站在二楼看着她。她还穿着金色凉鞋,她在我家大门收住脚步,然后走了进去。
我将烟按在窗外的水泥墙上熄掉。我只能当我是第一次见她,虽然我已习惯追索她的身影。
●
“喂!大哥哥,你在这里做什么?”
一回头,忽然看见从右边房门走出一个皮肤黑黝的男孩。
“我在抽烟。”我没好气地吐出烟雾,“你又在这里做什么?”
“我来找一个人。”小男生说完后就走到走廊的另一格窗,直盯着窗外。“我住在对面。”小孩子回话很自然,但我才不信。
“小弟弟,赶紧回家啦,这里不好玩。”我一心只想把这讨厌的小孩驱离,我有更重要的事,不容许他人破坏。
小男孩并不理会我,他坚定而焦灼地看着对窗。对面的窗门“嗯”地一声被推开了。
“妈妈在打扫我的房间。哈哈……等一下她会丢掉我藏在床底下的那堆纸牌。”小男孩笑了。
啊,我居然没认出他!想到无法认出自己,一阵晕眩猛地敲击头部,像钻进地里的打桩机,频密有节奏地拆解意识。我恨透了被药物控制的身体,幻想和幻听又跑出来干预思绪,这代表在医院进行的治疗无效,回到乡下静养的想法无效,我的过去和未来都无效到底了。我捏紧口袋里的打火机,右手颤抖不停,手汗将塑胶外壳完全溽湿。
“大哥哥,我的玩具要被丢掉了。”小男孩靠近身旁,平静地说。我很羡慕他的单纯,他什么都不懂。
“丢掉。最后你也会被丢掉。”不由自主越来越小的声量。我不想让小男孩听见,让他就这样长大。
小男孩天真地望着我说:“大哥哥,妈妈要来了。”
对窗传来喧哗声,电话响起、老人高昂激愤的咒骂、圆形纸牌落雨一般飘扬在街上。小孩惊慌地躲在窗户后面盯着女人的身影,她带伤跑出了大门,一道好长好红的伤痕烙在小腿肚,老人抄着扁担跟在后头追出来。她跑进了旅社,在女服务生帮助下走入房间。过了不久,小孩急促地奔跑,跑下旅社一楼,噔噔噔噔。
●
一切情景都和往日相同。阴暗的光线,在那张床上,我曾被她紧紧拥抱啜泣。从她说话时习惯提高尾音的方式看的确是我一直找寻的那个人。听她和女服务生哭诉,以前同学打来电话被公公误解她与外人有染,丈夫在外地工作毫不知她所受的冤屈,孩子还小,该怎么办?今天被打成这样,镇上的人马上会对我指指点点,这个家要怎么待下去?
我走到窗边“刷”地一声拉开色彩俗丽的窗帘,屋里大亮起来。下午的小镇,依然静止不动,像失去画者的写生。木然的老建物,不再流动的空气,毫无生机地停顿在窗的框框里。
没想到会再走进这房间。床边有把粗藤编成的高背椅,我坐在高背椅上,缓缓摩挲嶙峋的藤节。总是不断设想这里的景致,如今果真与小时候探索过的空间无异。但,记忆中留影的人哪里去了?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对面房间喔。”小男孩熟悉屋外景致。
往前一望,看到对窗我书柜上的大同宝宝公仔还是站得歪歪的,有点安心地舒口气。我和她在这房间住了一晚。她离开之后,我回到家,然后开始趴在窗边看着对窗,等待窗帘被拉开等待灯亮起来,等待有人来。
这条街很窄,两栋房子也靠得近,有几次我以为看见了她移动的身影,若是她不开窗,我就呆望着灯暗下去。而旅人很少,我的想象却一直长大。直到我也离开家,发现世界上还有个人和她长得很像。
在这里出生,中学到校住宿,大学休学、住院,回到故乡的我,已变成邻人眼里的陌生人。一年前决定回老屋住,但爷爷留下的老屋不只旧,还到处漏水。
整修旧屋时和旅馆的女服务生商量,让我上楼来观看施工。我扒着长廊木窗眺望幼时住过的家,打着赤膊的工人翻开熏得漆黑的破碎瓦片随意往楼下一扔,屋顶露出一个个深黝的洞,他们又铺上一片片新瓦。
当时看着新鲜的赭红瓦片和凝黑的旧瓦错落而置,屋顶盖得细密严实,但总感觉以前和玩伴打棒球时球飞上屋瓦砸开的那个洞,始终掩盖不住。
●
“你想她吗?”我对身边的小男孩说。
他看着我,露出缺了两颗门牙的笑:“大哥哥,我知道你很爱妈妈。”
很久以前,我曾很喜欢一个女生,她笑起来很像我在思念的那个人。我忘不了。
看到她的第一眼,我以为那始终存在于母亲眉间的两道深刻皱纹,突然松开了。
“小时候住过我家对面的旅馆,在那里过了一夜,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我妈。”向她叙述旧日的自己,像在转述别人的人生。
那天晚上妈妈没有再回过家。趁着爷爷不注意,我偷偷跟着她背后奔进旅馆,我以为自己像侦探会发现什么。
在房门外,听到她恣意悲切的哭泣,我发现了妈妈的伤心,不像喜欢哼歌抱着我转圈圈的她,想到这里不禁蹲在走廊也哭了。号哭不停的我被她发现,她让我进去,搂着我睡了一晚。隔天一早,醒过来,她已不在。
“我以为她会回来看我,没想到一次也没有。早知道,我就继续跟踪她。”我和那女孩倾诉旧日的神情,一定非常哀伤,她抱着我,很久很久都不说话。我觉得自己很荒谬,怎能如此对待心爱的女孩。
她成为影子,附着在我的想象之中。
直到我将治疗失眠和头痛的药物搅拌着酒精吞下的那天,梦魇终于暂时离开。学校的心理辅导老师建议我接受治疗,住一阵子疗养院,和她的影子也结束了那种宰制的关系。
回到老家后,翻拨过的整片屋檐,却出现一股看不见的气味,像幽灵持续飘晃于整个老屋中,让我无处可逃。
●
天色暗了。路灯亮起来,我的家慢慢在夕阳中隐没。
“大哥哥,明天妈妈就会不见了。”小男孩蹲在窗下,路灯将他瘦小的身形描出一层浅浅的黑。
“嗯……”我听见自己哽咽的声音。
隔天发现妈妈走了。一直走到镇外的河堤边上的我,以为自己还是可以找到妈妈。但河水阻隔了方向,我不知在野外哭了多久,才被爷爷领回去。
“没关系,大哥哥,我明天一定可以找到妈妈。我很厉害,我是福尔摩斯哦。”小男孩忽然绽开笑颜,无邪地望着我,漆黑的眼睛很像妈妈。
我紧握着打火机,拇指轻轻拨动着打火的转轮。失去旧址,失去这栋建筑,我们在自己的窗口可以看得很远很远,再也没有阻碍。我想告诉小男孩,本来打算把这里放一把火烧个精光,以后我们就不用在往事和伤痛中反复奔波。
我关上房门,沿着长廊走下楼,老板娘趴在桌上睡觉,我从旅馆正门走出去,好像一切都不曾发生。
回到自己的家,攀着楼梯爬上二楼,感觉全身被放尽力气似的,明明我只是到了对面。走到书桌旁,书页被风吹乱,桌上用雕刻刀刻着深深凿痕,还有我填进的红墨水蓄满凹沟。
仿佛被遗忘的时光,那个遗忘我的人,我还可以在对窗找到她。
暮色里远方的山脚下,错落着砖瓦房舍,隐约有吐纳炊事的料理气味,小镇也要准备休息。当我的视线回到对面的窗口,小男孩向我挥挥手,他的嘴型说着,“再见了”。
(本文获台湾第五届宗教文学奖小说首奖)
凌明玉,生于台湾屏东县,现就读国立台北教育大学语文创作研究所。现任耕莘写作会专任导师,和平国际出版社绘本书系主编。曾获中央日报小说首奖及小小说奖、宗教文学奖小说首奖、联合文学巡回文艺营小说首奖等。主要作品有《爱情乌托邦》、《打开甜蜜口袋》、《不远的远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