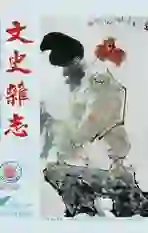子规夜半尤啼血 不信春风唤不回
2012-04-29徐志福
徐志福
在中国近代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队伍中,有一位文笔犀利的报刊宣传鼓动家。他的文章像投枪匕首,办的报刊像重磅炸弹,使清廷万分恐惧。朝廷曾告示天下:“以万金购其头颅。”甚至警告百姓:“有藏者比室株连,获主笔(雷任报刊主笔)则就地正法。”[1]其人便是著名的报界巨子、奇人雷铁崖。
辛亥革命的先行者之一
雷铁崖,原名昭性,1873年出生于四川富顺县,1905年东渡日本留学,同年8月由孙中山介绍,在东京加入同盟会,遂改名为铁崖,意欲从此将以雷霆之声唤起国人的觉醒。
雷铁崖是辛亥革命的先行者之一。他于1906年征得孙中山同意,与川人留日学生中的同盟会骨干邓絜、董修武等创办四川在国外出版的第一份革命刊物《鹃声》。他的创刊号《说鹃声》一文中说,欲借蜀国王杜宇失国而死,魂化杜鹃,声声啼血,冀唤起国人复国,公开打出同盟会政纲:“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报刊才出两期,就使清廷异常恐惧,惊呼:“此报若行,将乱中国”,立即严禁出版,下令缉拿主笔。1907年春,雷铁崖冒着被“就地正法”的危险,在东京将《鹃声》复刊,用“铁铮”笔名发表《中国已忘之命案说》,痛斥清朝政府的卖国罪行,坚决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专制政体,“恢复祖国,以建民主政体”。复刊一出,再遭封禁。他毫不畏惧,又与吴玉章等在原《鹃声》基础上创办《四川》。当《四川》又遭禁后,他不得不转战南洋和国内,继续以报刊做阵地,传播辛亥革命火种。他曾在马来西亚槟榔屿、新加坡与中国上海、北京等地创办或主持《远东闻见录》、《越报》、《光华日报》、《国民日报》、《民主报》等,用雷崖、啼红、啼红生、铁铮、龙言、龙等十余个笔名撰文宣传革命思想,或阐述辛亥革命宗旨、或揭露批判清廷残暴腐朽、或与改良派论战、或抨击康梁保皇立宪邪说、或歌颂武装起义和缅怀殉难烈士英雄业绩、或欢呼辛亥革命的伟大胜利,为建立共和高唱凯歌;同时批判党内无政府主义思潮,还在讨袁的二次革命中当急先锋,揭露其专制独裁的滔天罪行。雷铁崖的创作,贯穿了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是辛亥革命政纲的传声筒,故深得中山先生的赏识。
《警告全蜀》的振聋发聩
吴玉章于1908年1月5日在东京创办的杂志《四川》,是当时中国最进步和最革命的刊物之一,它的前身是《鹃声》。雷铁崖是它们事实上的主编和发行人,也是最有影响的撰稿人。在《四川》杂志1、2期上,连载了由雷铁崖执笔撰写的洋洋洒洒近两万字的长篇政论《警告全蜀》。
该文历数帝国主义侵华现象,揭露列强侵略本质及侵略政策和侵略手段,极陈中华大地已成英法日等列强瓜分的“中心点”,天府之国已成列强竞争的“大战场”,中国人民面临“枪下之血肉”的厄运。面对“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作者深感部分四川人的“麻木不仁”,找出其病根有三,即自私、依赖、推诿,并尖锐指出,若人不觉醒,以为四川有险可守、有恃无恐的话,其恶果是:“岂知所拥有广地将入他人之版图,所有公民将为他人之奴隶!”《警》文号召四川人要“各尽心力、合理图谋”,要“舍身国事、百折不回”地去拯救国家。《警告全蜀》的发表,使人想到两千多年前的成都才子,时任汉朝(武帝)中郎将的司马相如。其时,他奉命返蜀处理有关开通西南夷的急务,实现他变革的主张,却遭到成都守旧派耆宿的反对。后者上书认为朝廷此举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司马相如针对此写了《难蜀父老》一文,以诘难川人的口气批评“蜀不变服”、“巴不化俗”的顽固观点,指出闭关自守的危害,宣扬开通西南夷的历史价值。《难》文开创了四川人自我解剖的先河,是最早向盆地意识开火的檄文。两千多年后的雷铁崖继承了前人勇于自我反省的传统,向民族虐根性挑战。《警告全蜀》洋溢着作者的爱国爱乡情怀,对提高国人认识、提升革命精神,起到振聋发聩的积极作用。可以说,它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动员令和号召书。此后几年,海内外就雨后春笋般出现像《四川》这样勇于自我解剖的杂志,如《夏声》、《秦陇》、《晋乘》、《汉声》、《粤西》、《云南》、《河南》、《浙江潮》等,“无不本斯意以呼唤故乡社会”。可以肯定,这些杂志对宣传辛亥革命思想起到了星火燎原的作用。
1911年(辛亥)6月,四川发生了保路运动。它先于武昌起义,是引发辛亥革命的导火线。9月间,四川人民率先在荣县、成都等地发动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运动,以后又处死了四川总督赵尔丰、杀死了带领清军入川镇压的刽子手端方,击溃了清廷的新旧军队,其激烈的程度超过其他省份,所以孙中山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起义或者要迟一年半载。”雷铁崖时刻关心家乡的光复和反正。当保路运动初起时,他就预言:“铁路风潮实即满廷告终之导火线,而为革命成功之大转机。”当保路运动在西南如火如荼开展起来时,他赞扬四省之中“唯蜀人激烈最富后劲。”[2]当他得知四川民军竟占领了成都,杀了川督赵尔丰后,高兴得眉飞色舞,随即撰写《四川战局之观察》一文,刊登在他主编的《光华日报》(在槟榔屿发行)上。他连写了五个“祝!!!”字,赞扬四川人“雄飞进步”:“始而惊惶,继而痛苦,更继而罢市罢课,热潮愈高,众心愈奋,竟一举而诛锄清吏,占领全城,独立之旗飞扬锦里,自由之花开满蓉城。前之滑头者,今日竟断头而不顾……语曰:士别三日,便当刮目。”其为乡人突飞猛进而欢欣鼓舞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雷铁崖一生创作颇丰,单在《光华日报》(1910年12月2日创刊)主持报务的一年多,就日日撰文宣传革命。仅据《雷铁崖集》统计,这一阶段他所撰署名时评文章即达278篇之多,长篇连载64次,还写《喻培伦史略》出版。人们赞美他“一卷文章穿海外”,良无过誉之词。
忧国忧民的“啼鹃”情怀
雷铁崖既是激进的革命党人、叱咤风云的著名报人,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诗人。同时,他还是有名的书法家,“自幼工书法,名噪川中。”他早年与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及柳亚子等人关系密切,曾多次参加“南社”在西湖的一些重要活动,并积极投稿。《南社丛刊》第二、三、五、六、八、十一、十三、十六各集分别收入他的诗作数十首。在他主编的《光华日报》等报刊上也时有诗作见报。其一生百余首诗作,都以忧国忧民的“啼鹃”情怀,吟唱辛亥革命主题,呼唤国人觉醒,企盼祖国新生。他的诗作广为流传,博得“啼鹃诗人”美名。
1905年1月,他与川人熊克武、但懋辛、谢奉琦、黄树中等东渡日本时,在船上诗兴大发,激昂吟道:“乘风破浪上硫州,脱却胡装觉自由。回首神州肠欲断,汉家故业几时收?”放言他就是元末杨铁崖,一句“学得屠龙好身手,归来收拾旧山河”,代表了当时留学人员的心声。
1908年,雷铁崖在《四川》一、二期上发表的《警告全蜀》中有使人发聋振聩的诗句:“呜呼,云海苍茫,空作楚囚之泣;家山危殆,愿效杜宇之啼。侧身西望,握管怆然,不自知其言之长而心之戚也。”其赤子情怀跃然纸上。
1909年7月,雷铁崖执教于上海新公学校,除写“主张革命排满激烈”的文章外,还在课堂上公开向学生灌输民族革命思想,号召推翻清朝政府,被当局指名通缉,于是年秋化名潜逃杭州西湖白云庵为僧。白云庵得山方丈等僧人同情革命,见雷铁崖诗、字超俗,遂以上客相待,不以僧规约束。
雷铁崖不信佛,自然不是真出家。他一方面说皈依佛门,不作诗了;一方面又“身坐蒲团,心却荡游”:“忽刺秦皇响,忽斩楼兰首,忽悲乌江骓,忽饮黄龙酒;或击祖生揖,或撞亚父斗;或拗钟期情,或泣任昉后。”他坐着,有时还忽然浪曝般地唱起《满江红》来。白云禅院虽然幽静,却安置不了一颗忧国忧民的灵魂:“男儿不拯神州劫,辜负龙泉破壁鸣”,民主斗士的岗位应该在战场!他每晚睡不着,睡不着就写诗。他以声声唤醒国人的杜鹃自命:“杜鹃夜半声凄绝,不是愁人也泪流”;“竖尽星旗思拍马,招来蜀魂再啼鹃”;“杜宇啼红春欲泪,长弘化碧月留痕”;“一寸山河一寸泪,啼来红润碧花枝”;“五日悲愁游子梦,三更啼月蜀王魂”;“不用吾谋心莫死,西邻杜宇早同哀”;“鹃哀唐汉宵磷内,鬼哭炎黄碧血中”;“鹃因口瘁啼衔赤,烛为心伤泪堕红”,真是字字含泪,声声带血!
就在雷铁崖出家期间(1909年11月),浙江学生创办《越报》。他应邀任编辑,作发刊词。
翌年春,在党人的力促下,他结束僧人生活,返沪参与创办留美预备学校,为革命培养人才。雷脱去裳装起程,吟道:“金戈铁马文明血,荆棘铜驼祖国秋。谁遣骄儿横海窟,阿童持节下龙舟。”后胡汉民写信给他,说孙中山先生要他去南洋槟榔屿筹组《光华日报》,便于1910年秋,前往主持该报笔政,历时一年余。这是他一生中办报最有成就的时期。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震撼全球。雷铁崖情不自禁,立马写下一则《快言》:
大喜!!大喜!!革命成功!!
快哉!!快哉!!革命成功!!
革命党万岁!
新中华共和国万岁!
炎黄子孙万岁!万岁!!万万岁!!!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雷铁崖应孙中山之邀回国出任总统府秘书,他又强拉柳亚子也到总统府任职。当时总统府秘书班子中有一半以上是四川同盟会员,如吴玉章、黄复生、邓家产、李伯中、熊斐然、任鸿隽、任鸿年兄弟等,但文字上主要倚重雷铁崖。
任总统府秘书不到半月,他因与秘书长胡汉民意见相左,更为党人中对袁世凯的妥协态度及其投机者钻营夺利之举大为不满和失望,遂挂冠而去,离前自嘲道:
一笑飘然去,霜风透骨寒。八年革命党,半月秘书官。樱下竿吹暂,邯郸梦已残。西湖山色好,莫让老僧看。
这里的“樱下”、“邯郸”句,是针对民国开国后一些党人争权夺利而言。
其时,革命尚未成功,军阀却盗弄国柄。雷铁崖“深感国事日非,扰怀难释。在极度苦闷中,常歌哭无端,精神尽成病态”,于1920年5月8日忧郁而死,享年47岁。真是一代英才,天不假年,令人叹惋!他死后,各报以“革命先觉,功成不居,蒿目时艰,卒以忧死”[3]的醒目标题竞相报导。据说这16字是孙中山先生对雷铁崖的评语。
注释:
[1]《〈鹃声〉再兴发刊词》,收入《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第556页。
[2][3]引文皆出自《四川近代人物》,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0页。
作者: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