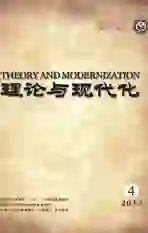“象”范畴的渗透与跨越
2012-04-29邓心强
邓心强
摘要:元范畴“象”自魏晋之后衍生出系列子范畴,并在相互交织与融合中走向扩展与弥漫,彼此渗透,进而形成梯级式的范畴群落,实现了世界、创作、文本和接受不同层面的跨越,最终成为涵盖整个文艺领域的核心母范畴,与“气”、“味”共同建构起中国古代文论的潜在体系。
关键词:象;渗透;跨越
中图分类号:I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4-0090-06
“象”是中国古代文论史上重要的元范畴之一,它从萌芽、产生到发展、演进,历时千年之久,并最终由哲学转入美学、文学领域,成为核心母范畴,并初步形成具有民族特征的具象思维方式,对后世艺术、文论、文艺批评等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文论元范畴后便开始走向成熟,拓展、衍生出系列子范畴,并在相互交织、渗透中组成一个庞大的范畴群落,关联并涉及到创作、文本和接受各个层面。甚至不少范畴同时跨越多个层面,具有很强的统摄力和涵盖性。随着创作实践和理论总结的并辔齐行,“象”范畴在发展演进过程中不仅衍生出系列子范畴,如物象、意象、气象、兴象、境象、心象等,尤其是由“虚象”所生发出的“境”范畴,又产生出虚境、实境、情境、清境、浊境、神境、空境、化境、写境以及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等系列子范畴,它们构成一个庞大的范畴群落,而且依“象”还催生了很多经典的文论概念、命题,如“立象以尽意”、“观物取象”、“情中景,景中情”等等,同时与“象”有关的象意识、象情感、象风格等也在唐宋以后更趋明显。[1]“象”的成熟与泛化使它和“气”、“味”共同支撑着传统文论的体系结构。
“象”的家族成员不断扩增,分布于世界、创作、文本和接受四大层面。同时作为母范畴,“象”还辐射到文艺不同层面,具有很强的统摄性,这使“象”范畴的涵盖面远远超过其他范畴。这里选取“意象”、“兴象”、“气象”、“境象”等若干重要范畴加以透视,以窥全豹。
一、跨越创作与作品层面:意象、兴象、气象
“意象”原本用来指艺术构思,后世被泛化指作品的“形象”。而“兴象”不仅指创作中因“兴”构“象”,而且也指作品情景交融的风格特征。“气象”不仅对主体的刚健气质提出了相应要求,同时也指作品或时代整体所具备的精神风貌。“象”的这三个重要子范畴都关乎创作和作品。
1.“意象”
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论构思过程时提出“意象”说,此后这一范畴便在中国文艺和美学中具有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从先秦《周易》、《庄子》论言意关系起,“意象”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这里无意去追根溯源,只就“意象”如何跨越创作构思和作品结构两大层面,稍作剖析。
刘勰谓:“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文心雕龙·神思》)可见,“意象”孕育于构思过程中,还没有形诸笔墨,尚处于使用语言符号来传达此前的心理这一营造阶段。刘勰以比喻形象地说明作家要根据艺术构思中形成的“意象”来动笔塑造艺象。因此,“意象”也可顾名思义理解为“意(念)中之象”,或如章学诚所说是“人心营构之象”。正是处于脑心的孕育和酝酿阶段,尚未成为栩栩如生的文本形象,没有被客观化和对象化,刘勰便将之置于《神思》篇中。而后人无视具体语境,几乎将“意象”等同于“形象”了,这是违背其初衷、有欠妥当的。
外界“物象”一旦变成“表象”进入作家脑海中以后,主体便自觉而充分地调动意念,并根据表情达意的需要来进行艺术构思,这时“表象”便被意念所调遣、浸染,深深打上了主体的情感印迹,绝不是单纯而机械的再现“映像”。如果把“意象”置于《神思》全篇,从刘勰论构思过程和功能来看,则此子范畴中的“意”绝不单纯指情感,同时也包含一定的“理”,是情与理交融的统一体。刘勰曾明确地说:
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文心雕龙·神思》)
此皆“思理之致”。并且他进一步概括说:“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可见,在构思中,始终“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意”便成为取象、构象的枢纽与统帅,这里尤其强调构思中主体的关键作用,以及应具备的相关素养。比如,“意象”中不仅饱含“理”,同时也深含“情”(“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而“意象”中的“象”也不是纯粹的客观物象,而是经作家情思浸染后的“象”,其间主体必须对物象进行选择、概括和提炼。故从刘勰论“意象”来看,这一范畴便是主观与客观的交融,是情与景的融合,是情与理的汇通。学界曾从心物交互作用、想象激发、情感参与以及拟容取心等四个方面,分析过“意象”范畴的形成过程,也剖析过“意象”主体性的多元表现,[2]读者可参看。这些都可看出“意象”如何在构思的过程中潜在地运作,都是从主体层面论及的,兹不赘述和展开。
此后众多批评家也都以“意象”来论构思。如司空图曰:“意象欲出,造化乃奇。”[3]王昌龄则云:“久用精思,未契意象。”[4]何景明说:“夫意象应曰合,意象离曰乖。”[5]李维桢云:“意象风神,立于眼前,而浮于言外,是宁尽法乎?”[6]
从最初含义来看,“意象”处于创作构思时主体之“心”与外界之物交融的阶段,反映出诗人取材构思时某种复杂而微妙的心理状态。然而一旦构思完成,主体借助艺术符号(艺象)把“意象”(心象)传达出来后,“意象”就成为作品的“形象”或可供欣赏的“艺象”。其生成过程恰似郑板桥《题画·竹》中所描述的,从“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再到“手中之竹”的过程,也就是从“物象”到“心象”再到“艺象”的过程。构思时主体移情渗理于“象”,实现心物交融,这“形象”便具有相应的品鉴美感,它要求读者接受时,必须通过形象去感受作家所要传达的“意”,领悟其中特定的情感与哲思,因为“意象”的形成是主体寄“意”于“象”中的过程,“象”不过是达意的载体,所谓言以尽象,得意忘象,“立象以尽意”是也。否则读者不能寻象会意,而作品的“美感”也必然大打折扣,得不到应有的激发与领略。由于“意象”为“人心之营构”,展示出主体的创造性与审美观,其组合方式多种多样,这就使“意象”含蓄不尽,比“形象”更具多义性,在接受中才能带给读者丰富的艺术享受。
诗人所写的是主观感受中的“象”,是“意中之象”,故“意象”范畴首先当归属构思层面。然而此范畴在使用中其内涵和外延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后世诗人和批评家也将之归入作品层面用来指“艺象”,近似于作品可视可睹的“形象”(显然它们是有差异和区别的,如上分析)。如明代胡应麟谓:“古诗之妙,专求意象。”[7]清代方东树评价孟郊诗曰:“意象孤峻”,[8]王廷相曰:“诗贵意象莹透,不喜事实粘着。”[9]近代康有为则谓:“《始兴王碑》,意象雄强,其源亦出卫氏。”[10]很显然,他们所论之“意象”是“心象”客观化和对象化后的艺术形态(即为符号化的“艺象”),这已超过了构思的范围,可视作“意象”的进一步引申和发挥,也可作为“象”之子范畴具有超强辐射性和涵盖力的见证。
2.“兴象”
上文从“文本”层面对“意向”的内涵进行了详细阐发。针对怎样创造出具有“兴象”之美的诗歌,殷璠提出了三条途径:情来、气来、神来。这同样可以看出“兴象”这一子范畴是兼容了主体和文本两大层面的,它融通了创作和作品两个领域。
就主体营造而言,殷璠认为诗歌不仅应当有“风骨”,而且应当具有“神来、气来、情来”之妙。“神来”,是指以神似为主,形神兼备;“气来”,是指具有生气盎然的特点;“情来”,是指作品中有充沛的强烈的感情,能够感染读者。并且构思要新颖、奇特、巧妙,具有自然的声律之美。他评论高适、岑参之诗莫不如此。从作品结构来看,“兴象”似乎要将物象的生动性、鲜明性与意蕴的抽象性、模糊性互相融合,从而形成一种情景交融的境界,它是一种内在的情感与外在的景物融合化一、圆融无碍的美学意象及其所具有的风格特征,它重在情感之抒发与意象之创造。这已具备后来“意境”论的萌芽。因此,就作品而言“兴象”反映了唐代诗歌创作在创造审美意象(具备自然精妙之特征)方面的艺术追求和评价尺度。
盛唐诗注重“兴象”创造的特点,后人也多有论述,都推崇作品中“象”的自然性。如清代翁方纲《石洲诗话》谓:“盖唐人之诗,但取兴象超妙。”又曰:“盛唐诸公之妙,自在气体醇厚,兴象超远。”都不仅看重作品中物象应具的特征,而且也看重主体依“兴”取“象”,这是“象”范畴发展至唐代随着文艺创作的繁荣、艺术实践的深入和理论术语的提升,而日趋走向成熟和泛化的重要表现。
3.“气象”
盛唐诗歌风貌可用“笔力雄壮,气象浑厚”八个字来概括。“气象”是指诗歌的艺术气概和整体风貌。这是指“盛唐诗歌给人以充实饱满,旺盛有力之感。元气内充,真力弥漫,使作品精彩动人,具有整体的生命意义而难以句摘。”严羽论诗便极力崇尚风骨之美。
“气”与“象”原本是两个独立的元范畴,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和渗透,进而组合成“气象”这一子范畴。“气”是充斥人体内作为生命本原的精气,是基于人内在生命活力或基于主体志气之上的风致和韵度。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率先提出“文气”说,并以之作为区分不同文章风貌的基本尺度。而关于“气象”与“象”之关联,前代刘熙载则指出:
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故诗无气象,则精神亦无所寓矣。[11]
显然,批评家将观物取象、以具象代表来写景物之“精神”作为具备“气象”之美的途径。在他看来,气象是精神的载体,脱离烟霞、草树等典型具象,则诗无气象,也无从传达出主体的内在思想感情。因此“以气象写精神的过程,也就是以上创造寓主观于客观、化抽象为具象的过程。”[12]
“气象”能够连用成词,离不开古人对“气”与“象”关系的深刻认识。如《礼记·乐记》就曾记载:“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后来北宋张载则进一步指出:“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正蒙·乾称》)并提出“然则象若非气,指何为象?”(《正蒙·神化》)可见,“象”因“气”生,主体之“气”——无论是生理的血气、气质还是心理的志气、精神世界——都会通过某种“象”体现出来,具体反映到文艺上,则尤其重视诗人主体如何抒发感情、创造意象,因气成文,则尤其强调空灵、飞动的感兴、情思之美,而这些都对诗人主体的创作个性、气质才华、情感思想等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都在创作层面对构象之主体作出了相应规定。
魏晋玄学家虽不均以“气”为生命本体,但他们多以“气”为连接生命主体与抽象精神的中介概念,从而只在“气”与其哲学本体论中的元概念蕴意一致时,才赋予“气”以本体意味。王弼提出了精气氤氲万物,使物、性、体、用如一。他提出万物、人事皆因“气”的聚合而完成情的交感与物的呈现:
任自然之气,致至柔之和,能若婴儿之无所欲乎?则物全而性得矣。
气无所不入,水无所不(出于)经。
故万物之生,吾知其主;虽有万形,冲气一焉。
精气氤氲(交感而生)使一切存在物趋向无为静朴的境界,这一境界因系本体所设定,故其目的与存在相统一,具备了观念超越的哲学品格;同时,“气”的本体自在地涵容了主体化的情、性成分,也使得人本情性得以宣张,使王弼的玄学成为人文色彩很浓的哲学美学。这也很明显地表明主体之气对“性”、“情”的赋予及在文艺作品中打下的深深的烙印。
“气”作为生命之气,在魏晋唐宋普遍使用。它包括由后天因素而形成的个性、气质、才华、思想、感情等生命精神世界,如“志气”、“意气”、“才气”、“气力”等大量见于文论著作中。单就《文心雕龙》而言,以“气”论文,就不胜枚举。典型如:
妙极生知,睿哲惟宰。精理为文,秀气成采。(《征圣》)
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明诗》)
匹夫庶妇,讴吟土风,诗官采言,乐盲被律,志感丝篁,气变金石。(《乐府》)
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乐府》)
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放怀寥廓,气实使[之]文。(《杂文》)
周振甫先生注:“放怀寥廓:即以凤凰翱翔自比。气实使文,气势在驾驭文辞。使之,唐写本之作文。”[13]笔者以为此处应为主体之气。又如:
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体性》)
志气盘桓,各含殊采。(《书记》)
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神思》)
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神思》)
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体性》)
这些都是从主体气质个性、才华情感角度出发,来论诗人如何创作出不同风貌的作品。
就文艺而言,正是因“气”成“象”,则“象”为“兴象”,描绘成具体形象和意象,作品自然呈现出雄浑、峥嵘的整体风貌,远非乏力无奇之作可与媲美,这种作品属超拔豪迈的凌云健笔,有感荡心灵且耐人寻味的艺术力量,读者接受起来自然以之作为佳作的评价标准。如:
秦、汉以前,其气浑然。迨乎司马迁、相如、董生、扬雄、刘向之徒,犹所谓杰然者也。至后汉、曹魏,气象萎尔。(李汉《昌黎先生集序》)
其以“气象”区分不同朝代的文风,显然关乎文章的神气与风貌。而宋代严羽则直接把“气象”当做对作品创作风貌的辨识标准。他将“气象”列为诗之五法之一,其《沧浪诗话》云:“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气象、曰格力、曰兴趣、曰音节。”在该著中他数次论及“气象”,明确将其看作时代特征和诗歌个性特征的融合,并以此作为区分不同时代、不同作家风格的标准。
而从文学接受来看,“气象”论要求诗歌形象完整,给人浑成之美。宋人论诗强调“气象欲其浑成”,不仅注重篇法,而且否定局部字句上的雕琢而忽视全诗整体意境的构成。严羽更是以浑然天成的汉魏古诗为楷模。其《沧浪诗话》曰:
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晋以还方有佳句,如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谢灵运“池塘生春草”之类,谢所以不及陶,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灵运之诗,已是彻尾对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
这里以“气象混沌”评定汉魏古诗与建安诗歌,是对那种浑然一体、具有整体之美的诗风的欣赏与推崇。其对谢灵运诗删削意见的看法,也是以“意象”是否游离、文章气脉是否贯通、全诗是否浑然一体为原则的。自宋代严羽之后批评界以“气象”论诗比比皆是。如元代陈绎曾《诗谱》谓:“古乐府浑然有大篇气象,六朝诸人语绝气不绝。”论辞求气,亦是以汉魏古诗为楷模。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则曰:“盛唐气象浑成”,[14]许学夷则说:“盛唐浑然活泼,而气象风格自在。”(《诗源辨体》)都是着眼于诗歌整体美而言的。不仅如此,气象论还要求诗作情理的表现含蓄蕴藉,具有沉厚之美,而所谓“沉厚指寓情理于形象,使诗意不浅不露,耐人寻味。”[12](38)姜夔曾曰:“气象欲其浑厚,其失也俗。”(《白石诗话》)可见,自宋以后谈论诗歌创作每每论及“气象”,则要求诗歌意象博大壮观,具有宏阔之美。
中国古代“气象”子范畴渗透到创作和作品两大层面,反映出古人重视“气”在作品中的贯通,认识到主体内在之“气”与外在之“象”的完美结合,“气”是“象”的生命与统帅,“象”是“气”的载体与展现,二者相得益彰,共同成为中国古代论诗的重要审美标准。
二、跨越作品与接受层面:“境象”与“意境”
1.“境象”
“境象”有时又简称“境”,或称“诗境”,它是“象”范畴在唐代的重要嬗变。这一子范畴的形成与“象外之象”极为密切。最初由王昌龄将“境”作为美学范畴使用,其《诗式》多处论及:
处身于境,视境于心。……了然境象,故得形似。
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
这里率先把“境”“象”对举或连用。并且他还把“境”分为物境、情境和意境三类。后来皎然提出“取境”说,刘禹锡提出“境生于象外”,都认为“象外”生发诗“境”,诗之“境象”也就由此萌生。
当然,文艺创作由最初“取象”到后来“取境”或“以象造境”,不惟唐代批评家的理论总结,南朝谢赫率先提出“取之象外”说,佛僧们的“象外”之谈等,也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诗歌“境象”的不懈追求。虽然“取境”说偏重于创作层面,然“境”之魅力何以领悟,诗歌的美感何以实现,这又必须依靠读者去想象和再创造。创作必须突破有限的、单一的、具体的“象”而追求一种无限的、整体的“象”(空间,即境象),这直接导引读者去感受“象外”的整个“虚空”,去领略“象”所暗示、象征出的无限意蕴。因为“境象”的营造是虚实的结合,这体现了艺术形象有限与无限的统一,艺术创造和艺术欣赏的统一。
中国古代艺术家历来都非常重视读者联想、想象在欣赏品鉴中的重要作用。这也可看作从读者接受层面论“象外”、“境象”。如况周颐云:
读词之法,取前人名句意境绝佳者,将此意境缔构于吾想望中。然后澄思渺虑,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吾性灵与相浃而俱化,乃真实为吾有而外物不能夺。[15]
其谓“想望”,“澄思”云云,即是指联想与想象,这是对接受者调动能动性去领悟诗美的强调。唯有读者寻“象”联想,展开思索,方可真正理解古人的“名句意境”。
诗僧皎然曾力举“诗境”的创造,不仅关乎创作也联系着作品接受。他认为“诗境”会超越文字表层意蕴,由“象”到“象外”,由“文”到“文外”,引发读者的不尽联想,从而产生“文外之旨”。其《诗式》中所谓“情在言外,旨冥句中”,“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等论述,均是对“诗境”特征的概括。这对读者品鉴诗歌有何功效呢?成功的诗境必然使读者在言、象、意三大层面中得象忘言,得意忘象,最终不睹文字,去品味文外之重旨与不尽之意趣。
2.“意境”
意境说是《诗经》以来中国抒情诗歌创作与欣赏的艺术审美经验长期积淀的产物,也是经过唐诗的繁荣而进一步确证的诗美规律,更是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影响诗艺及诗论的理论结晶。意境揭示的是抒情诗文的审美特征,是指客体之“境”与主体之“意”交融和合所产生的一种情景妙契、虚实相生、韵味不尽的艺术境界。
意境说的思想渊源可追溯至先秦时代的文化思想。先秦礼乐文化崇尚天人以和,儒家文化追求中和之美,老庄道家文化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此外,佛教文化对心理空间及境界的开拓,都为“意境”说的产生奠定了厚重的哲学基础,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
就唐代文化与文论的关系而论,先有初唐儒学家孔颖达将“境”范畴运用到文论中来,他在《礼记正义》中解《乐记》之“感物”说时讲:
物,外境也。言乐初所起,在于人心之感外境也。……心既由于外境而变……若外境痛苦,则其心哀,哀感在心,故其声必踧急而速杀也。
孔颖达反复宣讲的“外境”一语,指的即是客观的物象世界。
初唐时期的《诗格》,围绕诗歌的“景”、“情”、“理”之关系展开辨析,认为诗歌应该景意相兼、理景相惬,“诗不可一向把理,皆须入景语始清味”(《文镜秘府论十七势》),“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凡景语入理语,皆须相惬”。对诗歌情景关系的探讨,无疑是意境论的核心内容,因为艺术意境的创构,是使客观景物作为主观情思的象征。
王昌龄在《诗格》中已将“境”作为诗歌理论的重要概念并大量运用。他提出了“诗有三境”说,此“诗境”之构成分为三个层面:物境,指自然景物层面;情境,指主体情感层面;意境,指整首诗的深层意蕴层面。后人所谓意境,实则包括了此三境。并且他还将“意”与“境”二者统一起来谈诗文创作:“夫作文章,但多立意。……思若不来,即须放情却宽之,令境生。然后以境照之,思则便来,来即作文。如其境思不来,不可作也。”又说:“夫置意作诗,即须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这些观点既强调了客体之“境”在创作中的基础作用,又揭示了主体之“意”、“思”在创作中的主导地位。
王昌龄的意境论还明确了诗歌创作中“象”与“境”的关系,认为先须有“境”,然后构“象”,至“意”、“象”契合,才算完成。“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久用精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放安神思,心偶照境,率然而生。”(《诗格》)诗境的创造,关键在意、象契合,当久思不得时,不可力求,只有当“境”成熟于胸,“象”才会生生不穷。
可以说,王昌龄“诗有三境”论开唐宋“意境”论之先河。此后,以“境”论诗者代不乏人。李白、杜甫、殷璠、白居易等都曾运用“境”范畴来谈论诗作。刘禹锡《董氏武陵集纪》提出“境生于象外”的命题,丰富了意境说的理论内涵。他不仅阐明了“象”与“境”的关系,认为诗境是由表层之象与象外之意共同构成的整体意象,而且还从欣赏的角度揭示了诗境的特征,认为“象外”的艺术空白、不尽意蕴都是诗境的构成部分。此外,皎然“取境”、司空图“诗品”、严羽“兴趣”、“妙悟”等,均构成唐宋“意境”说的丰富内涵。
由上可见,“象”成为文论元范畴后从未停止发展和演进,其衍生出的系列子范畴,在交织、渗透中贯穿创作、文本和接受各个层面,并同时实现多个层面的跨越,显示出元范畴极强的统摄力和涵盖性,并最终辐射出系列范畴群落,与“气”、“味”等核心范畴共同撑起中国传统文论这棵“参天大树”。
参考文献:
[1]王振复主编.中国美学范畴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185.74.115.
[2] 朱恩彬,周波主编.中国古代文艺心理学[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286-291.303-310.
[3] 司空图.诗品·缜密[M].
[4] 司空图.与李空同论诗书[M].
[5] 何景明.唐音葵签[M].
[6] 李维桢.来使君诗序[A].大沁山房集(十九)[M].
[7] 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一[M].
[8]方东树.昭昧詹言[M].
[9]王廷相.来使君诗序[A].大沁山房集(十九)[M].
[10] 康有为.广义舟双楫[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11]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82.
[12]冯冠军.中国古代诗论中的“象”[D].新疆大学2001年硕士论文,2001.35.
[13]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49.
[14]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58.345.
[15] 况周颐.惠风词话·人间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9.
The Penetration and Crossover of "Image"
Deng Xinqiang
Abstract: Since the Wei and Jin Dynasty, the category of "image" generated many sub-categories, and they intertwined and fused with each other, then they extended and diffused. Since then, those categories formed a ladder-style category community and crossed different levels like the world, the creation, the text and the acceptation of literature. It covers the entire field of literature and art. Eventually, it becomes not only the core category, but also the parent category. It establishes the potential system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with the category of "pneuma" and "taste".
责任编辑:王之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