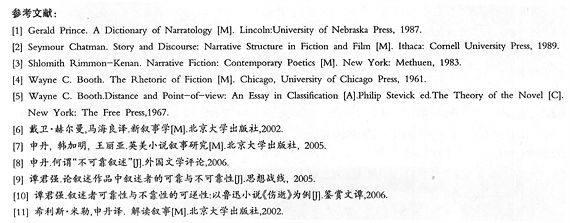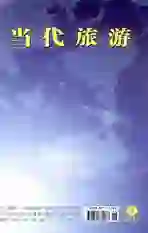浅议“叙事者的不可靠性”
2012-04-29刘春伶
刘春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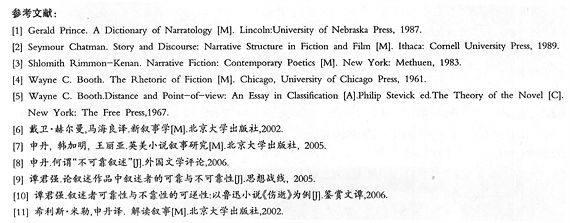
摘要:“叙事者的不可靠性”是西方叙事理论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别于传统批评的极端主义,鉴于以“作者为中心”的观点,试在作者塑造叙述者的语域范畴内,将其分为正面,中立和反面的叙述者。正面的叙述者建立在本我和超我之上,是自我的积极提升;中立的叙述者是最本真的自我。前两者均视为“可靠的叙述者”。反面的叙述者是反叛的自我,视为“不可靠的叙述者”。
关键词:不可靠的叙述者;隐含作者;修辞方法;认知方法
一、引言
在叙事学领域,叙事作品中的叙述者基于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内涵迥异,贯以不同标签的叙述者。按照叙事者是否参与故事可以分为同故事叙述者(homodiegetic narrator)和异故事叙述者(heterodiegetic narrator);根据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可靠的叙述者(reliable narrator)与不可靠的叙事者(unre-liable narrator)。
二、研究方法
一般来说,研究“叙述者的不可靠性”主要有两种方法:修辞方法和认知(建构)方法。
(一)修辞方法
修辞方法是布斯在其《小说修辞学》(1961)中首次提出的,追随者甚众。西方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布斯的学生和朋友,里蒙·凯南,查特曼,詹姆斯·费伦和玛丽·帕特里夏·玛汀等。国内的学者如申丹,谭君强等也比较推崇修辞修辞方法并在—定程度上发展了此理论。
1、创始人-韦恩·布斯
“传统批评强调作者的写作意图,学者们往往不遗余力地进行各种形式的史料考证,以发掘和把握作者意图。英美批评兴起之后,强调批评的客观性,将注意力从作者转向了作品本身,视作品为独立自足的文字艺术品,不考虑作者的写作意图和历史语境。”(申丹等,2005,225)在传统批评走向衰微,英美批评盛极之时,布斯应潮流而动,提出了“隐含作者”一轻作者,重文本。他(1967)认为,如果叙述者的言行与隐含作者的规范相背离,就是不可靠的。
作品以体验为基础,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生活的主体可以是作者本人,但更多的是芸芸众生。我并不赞成极端的以“作者为中心”或以“文本为中心”。同时,对于后者,所谓的隐含作者,不也是作者的影子吗?也就是说,“隐含作者”是逃不出作者的语域范畴的,与弗洛伊德的“自我”,“本我”,“超我”有契合之处。这一点在布斯对自己提出“隐含作者”这一概念的第四个原因中,尤其是所举的例子中可谓体现的淋漓尽致。
下面就是布斯在:2003年10月于哥伦布举行的“当代叙事理论”研讨会上所做的解释:“(1)他对当时学界追求小说中的所谓‘客观性(作者隐退)感到不满。(2)对学生将叙述者和作者相混淆的误读感到忧虑。布斯特别提到学生在读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的《麦田的守望者》时,完全与第一人称叙述者霍尔登·考尔菲尔德相认同,看不到作者对这位有严重弱点的叙述者的反讽。(3)对于批评家忽略修辞和伦理效果而感到的一种“道德上的”苦恼。这种苦恼有两个缘故:一是不少学者将小说视为艺术品,仅仅关注小说的审美效果;二是越来越多的学者片面强调读者反应,无视作者的意图,无视作者对读者的道德教育。(4)人们在写作或说话时,常常以不同的面貌或带着假面具出现,在文学创作中更是如此。布斯举了一个十分生动的例子:数十年前,他问索尔·贝娄(Saul BeHow)近来在干什么,贝娄回答说自己每天花四个小时修改一部将被命名为“赫尔索格”的小说。布斯追问贝娄究竟在修改什么,贝娄答道:“正在抹去我不喜欢的有关我的自我的那些部分。”(申丹等,2005,226)
另外,对于布斯所提到的例证-T·S·艾略特的《艾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在普鲁弗洛克的眼里,黄昏的天空就像是一个被麻醉的病人。笔者对他的解释,也持强烈的否定态度。“如果读者想知道真实的天气情况,那么这样的描述很显然是不可靠的。”(Wayne C.Booth,1961,175)
很明显,这段描写不是天气预报,只是起到奠定基调,烘托气氛的作用,并不在于如何精确的告知读者当天的温度,风级等。隐喻性的描述,难道不是更加形象地反衬了叙述者心情的沉重与无奈吗?而且,对隐含作者所传达的思想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怎么能被视为不可靠的叙述呢?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布斯的理论,难以自治,有含混之处。
2主要代表人物
里蒙·凯南也是根据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的规范,尤其是道德规范来区分可靠的叙述者和不可靠的叙述者的。他认为,不可靠的叙述者由于其道德价值规范与隐含作者的道德规范不相吻合,因此,这样的叙述者对作品所做的描述或评论使读者有理由感到怀疑。(Shlomith Rimmon-kenan,1983,101)查特曼也认为,隐含作者构筑着叙事作品的规范(一般的文化规约)(Seymour Chman,149)。
詹姆斯·费伦和玛丽·帕特里夏·玛汀进一步完善了这一理论。在他们合著的《威茅斯经验:同故事叙述、不可靠性、伦理与(人约黄昏时>》中对理论作出了三个重要的修正:(1)不管叙述者人物是谁,人物功能与叙述者功能都不可能总是密合无间的,因此我们不能总是根据叙述者的人物角色推断叙述者的可靠性或不可靠性;(2)不可靠性不仅发生在事实,事件和价值,判断轴上,而且发生在知识,感知轴上;(3)对这三条轴线上的不可靠性及其激发的读者活动的探讨,使我们区分出六种不同的类型: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和“不充分报道”;价值,判断轴上的“错误判断”和“不充分判断”;知识,感知轴上的“错误解读”和“不充分解读”。(马海良译,2002,35)
申丹在《何为“不可靠叙述”》中指出,费伦的研究忽略了第一人称叙述的回顾性质并以鲁迅的《伤逝》为例进行了分析。此外,谭君强也针对这一点,同样以鲁迅的《伤逝》为文本,提出了“叙述者可靠性与不可靠性的可逆性”,与申文的“回顾性”有异曲同工之处。串文认为“永久是这样的安宁和幸福”与两人爱情的悲剧性结局直接冲突,属不可靠叙述”。然而,按照布斯的理论,隐含作者与作者本人并不等同。作品中的涓生是作者没能实现的本我,自我,即超我形象。如此说来,应该不能将其简单地归为不可靠叙述吧?
(二)认知(建构)方法
认知(建构)方法既不考虑作者,又不考虑文本,主张以读者为中心。创始人是塔克雅克比,主要代表人物是A·纽宁。
1、创始人-塔克·雅克比
塔克·雅克比从修辞性方法的反面出发,在《论交流中的虚构叙事可靠性问题》及在2005表于《叙事理论指南》的一篇论文中阐释了自己的理论。“他将不可靠性可靠性界定为一种‘阅读假设或‘协调整合机制(integration mechanism),即当遇到文本中的问题(包括难以解释的细节或自相矛盾之处)时,读者会采用某
种阅读假设或协调机制来加以解决。雅克比系统地提出了以下五种阅读假设或协调机制,即“关于存在的机制,功能机制,文类原则,关于视角或不可靠性的原则,关于创作的机制。”(申丹,2006)
2、主要代表人物
另一位颇有影响的认知建构方法的代表人物是A·纽宁。他受雅克比的影响,聚焦于读者的阐释框架,断言“不可靠性与其说是叙述者的性格特征,不如说是读者的阐释策略”。他在199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对“隐含作者”这一概念进行了解构和重构,采用“总体结构”(the structural whole)~替代“隐含作者”。在A·纽宁看来,总体结构并非存在于作品之内,而是由读者建构的,若面对同一作品,不同读者很可能会建构出大相径庭的作品“总体结构”。在1999年发表的《不可靠,与什么相比?》一文中,A·纽宁对不可靠叙述重新界定如下:与查特曼和很多其他相信隐含作者的学者不同,我认为不可靠叙述的结构可用戏剧反讽或意识差异来解释。当出现不可靠叙述时,叙述者的意图和价值体系与读者的预知(foreknowledge)和规范之间的差异会产生戏剧反讽。对读者而言,叙述者话语的内部矛盾或者叙述者的视角与读者自己的看法之间的冲突意味着叙述者的不可靠。
也就是说,A·纽宁用读者的规范既替代了(隐含)作者的规范,也置换了文本的规范。尽管A·纽宁也是一再提到文本的规范与读者规范之间的交互作用,但既然在他的理论框架中,文本的总体结构是由读者决定的,那么文本规范就变成读者规范了。
三、结语
无论是以隐含作者的规范,文本规范,还是读者规范为标准来判别可靠的叙述者和不可靠的叙述者,都有所偏颇。然而,兼顾三者,包括思想动态的考究(如回顾性和可逆性),难以把握衡量的尺度。尽管差异是必然存在的,但是人们认知的是同—个世界。有别于传统批评的极端主义,鉴于以“作者为中心”的观点,在作者塑造叙述者的语域范畴内,泛化读者,可以将其分为正面,中立和反面的叙述者。正面的叙述者建立在本我和超我之上,是隐含作者在文本规范中,塑造的叙述者自我的积极提升和不断完善,是可靠的叙述者;中立的叙述者是最本真的自我,亦可视为可靠的叙述者。反面的叙述者是隐含作者超越道德,凌驾于文本情节的意外,塑造的反叛的自我,属不可靠的叙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