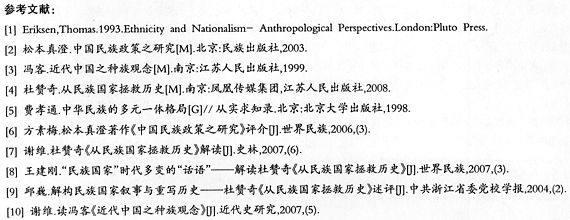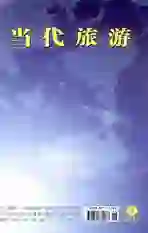叙事结构与民族观史
2012-04-29廖吉媚
廖吉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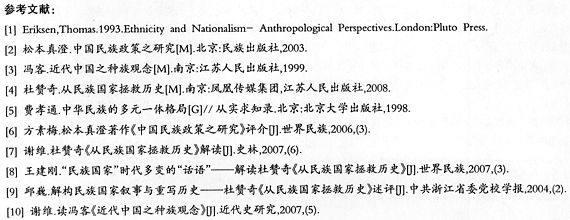
摘要:对历史的叙事结构不同,常常得出不同的历史。冯客通过对中国经典文献资料的考据,认为中国的“种族”观念自古就存在,并非西方独有。经过演变,“种族”以“家族”、“宗族”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之中。这些观念和文化概念成为近代中国革命民族主义的基础。而松本真澄书写近代中国的民族观念史时,认为政治对民族观念的形成至关重要。尤其是民族政策。通过大量考证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在一定意义上批判了冯客所谓的中国的民族的连续性和统一性。杜赞奇指出,线性历史所塑造的民族的连续性、统一性遇到复线历史书写时,变得虚假和压抑。
关键词:中国民族观;民族论;种族;民族
一、冯客的中国种族观念变化说
冯客(Frank Dik6tter)1961年生于荷兰。1990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作品主要包括《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1994年)等,其运用文化史研究中国近代史上诸多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重视。
笔者以他《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分析他关于中国民族观的理论。他分析有教养的社会阶层的作品,以线性时间为轴,分时期展示中国民族观的演变史。但他不打算探讨汉族的少数民族观念。他说:“尽管有许多在少数民族的虚构的野蛮起源之上的污蔑性评论,汉族的少数民族观念仍然被植入强调社会文化差别的种族中心主义的结构中。”所以,这项研究探讨精英如何构造一个关于身体上不连续的民族的学说——主要是西方人和非洲人,亦即外夷,而非内夷。
冯客认为中国自古就有“种族”观念,并非西方的专有。只不过它是以不同的面目出现的。作为文化的种族是历史文化背景,而作为类型的种族是1793年至1895年的产物,作为宗族的种族出现在1895年至1903年,作为民族的种族则是1903年到1915年上升为主流观念,在此之后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一段时间内,种族是作为种类的、种子的面目出现的。新中国成立之后,种族观念并非消失了,而是带有阶级的意味。冯客在本书前言中提到:“这项研究的分析性结构被集中在集团限定的概念上。集团是社会化地构造起来的实体,用来达到识别和组织的目的。集团采用的形式很大程度上具有暂时和无常的性格。”这与Thomas Hylland Eriksen的观点相似。“民族”观念的形成之初就是一种人群分类的指导思想。有了与自己不同的“外人”,才有“自己人”的观点。虽然区分自己与他者的界限总是模糊的。但以“种族”、“民族”为分类的标准却成为了现代性之后人群分类研究的主流。
为了论证他的观点,冯客参考了中国的古典文献,考证在这些古典文学诸如《五经》(《诗经》、《书经》、《礼经》、《易经》、《春秋》)中,是否出现了“种族”观念。他指出《礼经》(公元前三世纪)强调:“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冯客将这此称为一种文化优越性、政治唯我论:“受其文化优越性的假设支配的统治精英,根据一个标准来衡量外来的集团,凡是那些不能行‘诸夏之道的便被认作为‘夷狄。……在其《公羊》注中,何休(129-182)稍后在‘诸夏与‘夷狄之间做了区分。在‘太平时代(与西方的黄金时代相似的一个寓言性概念),野蛮人会流人并被改造;世界将变为一体。”
在论述“作为宗族的种族”时,冯客也从梁启超的文章中取料;并且分别展示了种族的战争、种族的连续性、种族起源、种族的灭绝、种族的分类、种族的分类等级、种族的边界、种族融合等,以说明这些现象都是因为种族有了“宗族”才有的特点才致于此。他将中国的民族观演变史,上溯至公元前三世纪。冯客的理论仍是在国家层面的,重点讨论的皆为正统经典文书史料。
二、松本真澄的民族政策研究中的中国民族观演变史
日本学者松本真澄(Matsumoto Marika),女,1957年出世,主要从事亚洲、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民族政策和回族研究。出版著作有《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近现代中国国民统合原理与伊斯兰改革派的政治方面诸关系的历史研究文集》等。
松本真澄关于中国民族政策的理论是研究中国民族政策的海外学者不可忽视的经典。她在《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中得到清晰的展示近代中国的民族观念史。松本真澄旨“在探讨现存的重要的中国‘民族观是如何诞生的,怎样被解释的,同时又被赋予怎样的意义,并对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进行分析。本书是以解读‘民族这一关键词语为纵线,透视20世纪的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的一种尝试。”本书以线性时间为主轴,展示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思想和民族观的发展过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思想以及民族政策为研究重点。展示了丰富的民族政策史料。
近代中国深陷严重的内忧外患,为避免沦为各帝国的囊中物。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将种族、宗族观念与西方的国民、民族国家理论相结合,试图改造近代中国。然而清朝领土范围内,除了汉民族,还有满、蒙、回、藏族等人口众多且“汉化”程度不高的族群,和众多的于汉族差异不大却仍是异族的南方少数族群。日本侵略者利用汉族与众多少数族群的差异,策划和挑拨民族间的关系,以达到全面侵略的目的。为了团结内部,抗击外敌,政治精英的“民族”观一直在做改变。
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中说到:“……‘民族是什么,应该是什么以及‘中国、‘中国人指的是什么,应该是什么,理应同时问津。……由孙文提出的这个课题,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也同样必须面对。因为使边境殖民如何参加到新国家中的问题是其国家的根本,具体而言,是关系到加入国际性的国民国家(nation state)体系时,中国国家的主权领域所具有的正统性的大问题。”
松本真澄与冯客不同,她论述的历史仅是清末至1945年这一时期。为了解读中国的民族、民族主义,作者用别的概念置换中国思想家和为政者以及日语、汉语共通的、中国、日本的研究者称之为“民族”的人类集团,并对其进行重新的解释。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重视人类的认同感(identity)的ethnieity论的方法论。在本书中,“民族”这个族群意义的词都不用中文,而代之以英文单词ethnics,ethnieity,这样的确便于读者辨清众多关于“民族”的概念。
松本真澄主张“复合认同感(identity)是ethnicity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一个人会有几个identity,随着环境、状况的变化,这些认同感是以各种复合化、重叠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松本真澄的理论就是探讨“民族”观与政治的关系。她认为梁启超的“民族”概念既承认领土内所有人是一个民族,但仍是汉族为中心的。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不仅是对内的,还是对外的。毛泽东的“民族国家”是“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他的民族论。还带着马克思的阶级内涵的。
松本真澄本书的最大贡献在于,她重视少数民族的民族观发展与政治的关系。而这也使得她的论述有时矛盾,因为她的角度不够明晰,有时同情少数民族,以少数民族精英的论述为
出发点去论述;而有时又以汉族精英的论述为出发点,认为正是这些汉族学术精英、政治精英的民族论凝聚了“中华民族主义”。
三、杜赞奇的复线历史所展示的线性民族观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历史学家、汉学家,印度裔,早年就学于印度,后去美国求学。其《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曾先后荣获1989年度的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其第二本专著为《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2008年)(另有译本译为《从国族中拯救历史:质疑现代中国叙事》,中译本2003年面世。)
杜赞奇在《从国族中拯救历史》中主张在进化史中,历史运动完全被看成是前因产生后果的过程,而不是过去与现在之间复杂的交易过程(transaction)。通过把对进化史的批评与民族主义的研究结合起来,我们便有可能析解历史与民族之间的深层的、执着的和(正如我们要论证的那样)具有压抑性的联系。
杜赞奇在本书中展示了近代中国的民族观的形成。他对近代中国的民族观的历史考查更多展现意识形态,尤其是意识形态是如何构建中国的民族观的。精英知识分子或政治人物线性叙述地构建了民族历史,但线性历史创造出来的“民族”是经过过滤的,有很多意义是失散了的,还有一些仍隐藏在民间的。杜赞奇指出线性下的民族历史是压抑的。他认为:“历史叙述结构与历史表述摄取了并隐匿了与其世界观不相适应的错综复杂的历史现实。”
杜赞奇对此理论的论证最精彩的莫过于辛亥时期的革命家如何从民间秘密会党摄取浪漫叙述结构,并将之融入一种全球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民族主义话语系统。秘密会社是“义”为名集合了自己的会员,会员的来源不仅有上层知识分子、政治人物、还有底层流民、车夫、工人等等。秘密会社的“义”来自传统理念。杜赞奇如是说:“民族缝合的进程始自革命党人说服秘密会党相信,共和是儒家思想,因此,他们应该参加。……在此过程中,会党的种族观念被从其复杂的精神特点中提炼出来,提炼环绕着儒家的文化主义以及反帝思想,并在视民族纯洁为全球性民族生存竞争中必不可少的社会达尔文的框架内进行。此外,孙中山又增加了下述观念:会党是幼稚的。不能独立采取革命行动,革命的政治对他们来说是外来的东西。最后,随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过时,革命党人本身的种族话题逐渐小视,革命的种族主义被归之于仍然沉默的秘密会党。”
杜赞奇从复线历史的角度揭示了民间“反满”思想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历史关系,他这样说到:“我已经清楚地揭示了(民族主义者及其他人提出的)基本观点,即:历史的连续性只有通过共和主义者才得以重新发现,辛亥革命完成率领秘密会党民族主义者的使命。……这样看来,话语吞没了历史。”在展示线性历史叙述所掩盖的扩散与差异时,用的“封建”的意义和功能的转变使得与历史的彻底决裂成为可能。
线性的历史创造了有连续的“民族”实体,并为政治的合法性赢得了话语权。但杜赞奇还是批判了正统的民族历史把民族说成是一个同一的、在时间中不断演化的民族主体,为本是有争议的、偶然的民族建构一种虚假的统一性。至少在复线的历史,证实了这样的虚假统一性。
四、总结
如果说冯客只考虑汉人社会的民族观念演变史,无意去了解汉人对少数民族的观念史,也无意去了解少数民族对汉人的观念史。松本真澄补充了这方面的空白,她在考查国共两党的民族政策时,挖掘了少数民族的民族观念。少数民族在政党的民族政策下能动地斡旋。这两种理论观点,用杜赞奇的观点来解释,前者是在以线性的方式构建了统一性的民族;而后者则通过复线的历史叙述,展现了正统历史之外的复杂历史细节,那些细节恰好反映了线性历史的压抑。这正是松本真澄将少数民族对国家民族政策的反应纳入到中国的民族观念史时,字里行间流露出矛盾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