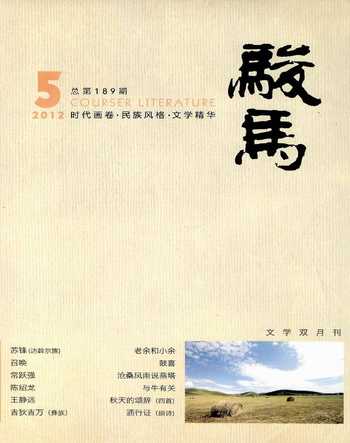与牛有关
2012-04-29陈绍龙
陈绍龙
一
放牛是必须的。秋李郢人个个都是放牛娃出身。
雨润,风轻,雾薄,草绿,秧也绿。放牛最好。
“打角”是不需要真的打角的,只是在牛角上拍一下,或者,在牛身上拍一下,有时你根本就不用去拍它,牛便把头低下来了,把牛角低下来了。你脚一抬,踩上牛角,一手薅牛鬃,一手扶牛角,待你站稳,牛头一扬,便把你送上去了。你只消走两步便到牛背了。心有灵犀,人与牛之间的契合沟通不是一天养成的。
“打角”就是踩牛角上牛背。
穿蓑,戴笠,虽说笨重,但气息好,有味。这身行头与田头、水边相搭,合宜的很。“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钓鱼的朝水边一站,成诗成画,美了千年。只是我总觉得柳宗元有点不靠谱,下雪天一人去到江边钓鱼?再说了,你钓鱼那身打扮干吗,哪有冬天穿蓑衣的。后来我才知道,是他被贬永州心情不好。穿蓑戴笠到江边钓鱼,哪里是真钓鱼,他是到江边散散心的。
蓑不离笠,笠不离蓑。两者相配,不只是防雨周全,也好看,好比穿西装要打领带一样。雨小,水滴便在蓑草上积聚着,积聚着,每个蓑草尖上都有一个小水滴。我一身珠光宝气,好像一抖能发出“哗哗哗”的声响。我们不去抖它,让它兀自滴落。一抖还不全洒了呀。笠上的小雨滴我们也不理它。它倒是耐不住性子了,齐齐地爬在笠沿边上,向我张望,个个都有好奇的样子,哪知后面的雨水也跟着凑这份热闹,一推搡,笠沿边的小水滴便失足落下了。
雨大了才好。雨滴在笠上滴滴答答的响。雨矢如箭。笠和蓑衣是挡矢的铠甲。这会儿我并不忙着打角上牛。我得好好和雨斗上几个回合。斗雨。站在雨地里,无所畏惧的样子,马步,“哈哈哈”,嘴里同期声, 左拳打在右手掌里,然后,右拳再打在左手掌里,全身一抖动,身上的每根草叶都像是鳄鱼身上的鳞片一样,它一抖动,周边的水便跟着哆嗦。雨便跟着落了一地。雨败。有时,我还会一个急转身,雨便飞也似的叫我抛得很远,像是重重地都跌了跟头。我有莫名的征服感。
我们如田埂上的巴根草一样,雨日里有精神,神鼻竖眼的,不泛困。坐也有累的时候,我们便站在牛背上,直直的。白鹭也会站在牛背上,它与我对峙一会,一展翅,我有一丁点的动静,白鹭便呼拉拉地又飞走了。我有点失落。我要是站着不动,白鹭也便站着不动,偶有在牛背上迈动步子的,或是低头,寻牛身上的牛虱。估计白鹭把我当成稻草人了。我要真是稻草人就好了。我要真是稻草人白鹭或许就会一直站在牛背上的。
饿牛不下田。露水草养牛。牛背下方与肋骨处有个三角区。我们会依据这个三角区的凹凸程度来判断牛吃的是全饱还是半饱。“半口草”自然不好。我们得耐着性子让牛吃饱。
雨大,渐冷的时候,我们便蛰伏在牛背不动了,听雨响。牛是嘶嘶拉拉地忙着吃草。牛胃“咕咕咕”不停地蠕动。牛背很热。裸露的双腿贴着牛肚子,我感到很暖和。我过分贪恋这雨日的温暖,恰恰成了错。不出两天,我的腿上长满了牛疥。牛疥如红豆,红肿,奇痒,挠也无用。牛疥好了腿上也会留下细小的黑痂。我的腿上满是黑痂,像是脸上被放大了的雀斑。其实,秋李郢人谁的腿上没有“雀斑”呢。因为,秋李郢人个个都放过牛,秋李郢人个个都是放牛娃出身。
二
我看过动画片电影《牧笛》。片子不长,印象很深。牧童把笛吹奏,笛声悠扬,意境顿开,幻想无限。情境在笛声中渐次展示开来,一幅幅画面很美,都像李可染笔下的水墨,挺中国的。
满湖的稻,满湖的绿,因其满,因其多,田野一时却单调起来。有笛声响当然好,一如这张硕大的绿荷上,滚动着一串串露珠。牧笛声在田野上灵动无比。
真的有笛。秋李郢的孩子个个都有一支属于自己的笛子。笛音悠长、高亢、辽阔、宽广,也能奏出欢快华丽的舞曲和婉转优美的小调。笛音旋律优美。笛横,头歪着,范儿便显出来了。
《公社喜开丰收镰》《扬鞭催马运粮忙》都是我们吹奏的保留曲目。《喜洋洋》喜庆,手指忙得欢。这曲我吹的要次点,吹出来没有“喜洋洋”的味,我吹的便少。秋公社吹得好,只要他听过的歌曲,知道调子,手指便能跟着调子走,曲调出。你哼什么调,他便能吹什么曲。他吹《百鸟朝凤》的时候,因其惟妙惟肖,能引来鸟与他共鸣。杜鹃叫,斑鸠唱。神了。
我们常“斗笛”。站在牛背,比谁吹的曲多。有比音高的,还有比不换气,把一个音一直吹下去,比一口气吹的时间长的。我们个个都把脸憋成了紫猪肝色。谁都不服输。败下阵来的是我。其他人也败。秋公社胜。
牛埋头吃草便是。我们站在牛背上,牛绳踩在脚下。牛尾巴鞭子一样在牛屁股周围抽打着牛虻,一刻也不闲着。牛虻嗡嗡响,极烦。牛虻像苍蝇,只是比苍蝇强壮。它有软毛,头大,半球形,或略带三角形。复眼很大,口器利,喜欢叮牛的创口。牛尾巴抽打的半径有限,有时,牛也会用角猛地一触,或是抖动一下皮肤,驱赶牛虻。
那天我正和另一条田埂上放牛的秋公社吹《喜洋洋》斗笛呢,并不知牛已站在稻田边的水沟里吃草。估计是牛被牛虻叮得实在难忍,它竟然也不通知一声,“扑通”一声打起汪来,把整个身子埋进了水里。牛虻是跑了,我却成了落汤鸡。哪里还“喜洋洋”起来,不斗自败,叫秋公社笑昏了。
放牛又不是天天把笛子别在腰上的。我们就地取材,去拔臭莆叶。掐两片,寸余,放嘴上,能当笛子吹。豆荚也行。豌豆荚最好,其他苕子荚什么的也能吹出调子。要是实在没有合适的“乐器”,我们掐两片草叶也成。多数的时候我们什么也不用,吹口哨。口哨响,心情好,多半牛已吃饱了,我们吹着口哨回家了。
“荷把锄头在肩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喔喔喔喔他们唱,还有一支短笛隐约在吹响”。校园歌曲很田园,这情景我们觉得很熟。一天劳动结束了,跟我们一同回家的,还有荷锄而归的村民。
三
“它横竖不说一句话,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它把头沉重地垂下!”想起臧克家《老马》的诗。马活脱得很,昂首奋蹄的,牛才木讷呢,不说话;要是说这首诗是写牛的,怕也好。
我是叫“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的句子震住的。
背负在牛身上的东西真的太多。
穿牛鼻注定是一次痛苦的洗礼。牛犊小,撒欢,在老牛旁跑前跑后的,不出两年,它是要做事的呀。穿牛鼻子是给牛行的“成牛礼”。我是没有亲眼看过给牛穿鼻子的过程的。庄重、神秘,近乎绝情。这种绝决果断的行事方式没有半点犹豫。我们见不得血,见不得牛充满泪花的眼神。我们听不得牛“哞哞”的呻吟。三四个壮男,抱着牛头,抱着牛角,将牛绳牢牢地缚在树上,将拇指粗的木棒从鼻肉硬生生地穿过。那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呀。那是怎样的一个场面呀。牛注定是要挣扎的,牛注定是要撒野的。牛注定是要在原地狂跳的呀。一地蹄印。一地鼻血。一地唾液。一地哀鸣。
穿过牛鼻子的小木棒叫牛鼻枸子。牛鼻枸子,木制,一头有鸡蛋大小的圆形头座,一头有系牛绳的凹槽,中间穿牛鼻子的梁较细。
穿破牛鼻,装上牛鼻枸子,人们便把牛绳拴在那棵树上了。走人。
牛第一天不吃东西。牛第二天或许也不吃东西。牛叫牵住了鼻子,牛叫牵住了牛绳。牛绳系在了树上。牛围绕那棵树转。四周的蹄印形成了凹槽,深深的凹槽。尘土飞扬。牛尘土满面。牛眼角的泪痕很是浑浊。浊痕两道,与鼻血混和在一起。
两天,两天之后,牛便乖了。牛绳牵在主人手里。牛没有了犟脾气,牛不再撒欢。牛乖乖地跟着牛绳走。牛乖乖地跟着主人走。牛乖了一生。
牛是最重要的“稻具”,其实,加负在牛身上的道具也很多。
首先得有轭。
轭是架在牛肩胛处的曲木。牛轭“人”字形,两边有弧度。牛轭两边有榫眼,榫眼上系有镰刀柄粗的牛耕绳。“人”字开口小,牛用力前挣,轭只能“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了。牛背负压力越大,牛轭往肉里扣得就越深。
那天我看深圳街头《拓荒牛》雕塑,多好,牛前胛隆起,肌肉一坨一坨的,蹄弯曲,斧凿一样,刀刀见力。看后又觉得好笑,轭呢!不负轭,怎么拓荒,哪有它满身充满锐气的肌肉。也许轭不好看,叫雕塑家给省了。省了倒也罢。要是人们不知道牛的这种情状肩上是要有一副轭的,那就不是不真实这么简单了。
牛身上背负了什么,牛耕绳知道。
牛耕田的多。耕田时把牛耕绳系在犁上便行。平整土地或是破垡的时候要耙田,耙田得用耙,耙田时便把牛耕绳拴在耙上了。场上打谷时,牛耕绳上系碌碡,拉车时,牛耕绳上系牛车。秋李郢有了手扶拖拉机的时候,乡路泥泞,手扶拖拉机常陷泥里。人们也把牛牵来用牛耕绳拉。秋李郢手扶拖拉机里就备有牛耕绳,好比现在人车里都有备胎一样。有一次我看赵本山演的一部小品,县领导的小轿车陷泥里了,乡民们拉轿车的也是用牛。
负轭在背,一生,牛就没有解套的时候。
四
我第一次闹着要去放牛的时候我妈是经过思想斗争的。去,还是不去,是个问题。
我妈担心的很多。我妈问我会不会叫牛“打角”。我说会。我妈问我上坡时如何。我说薅牛鬃。我妈问我下坡的时候如何。我说拽牛尾巴。我妈又问我有岔道了怎么办。我说拽牛绳。回答正确。面试通过了,我妈还不放心。我妈担心是有道理的。我还小,我只有八岁。她更怕我从牛背上掉下来,摔下山去。要不是我一再坚持,加之秋公社力挺我“不碍事的”,估计我妈还会犹豫不决。
我不是去给队里放牛。我们是给山上畜牧场放牛的。畜牧场在山上,离秋李郢有七八里路,不算远。秧季,春耕春种,用牛的多,周围生产队都到畜牧场借牛用,一时畜牧场放牛人少了。畜牧场人放出话来,哪个队借牛,哪个队就要派人来放牛。条件是供午饭,白米饭,不限量,放开肚皮,紧吃紧添。
这话是畜牧场场长说的,肯定算数。是白米饭呀!
我这样闹我妈是冲着那白米饭去的。
饥春,青黄不接,上面下发救济粮也不会有我家的。有饭吃是美差,何况是纯的白米干饭,何况这干饭紧吃。
秋公社极说白米饭的香。秋公社每年都去畜牧场放牛的。秋公社放牛归来会证实中午果然吃了鼓鼓一肚子米饭。都傍晚了,他的肚子都还叫米饭撑得圆圆的。队长会很高兴地叫秋公社把褂子掀起来,露出圆肚皮。队长会用中指去弹秋公社的肚皮。弹一下,还贴着肚皮听一下。弹时肚皮会发出“嘭、嘭、嘭”的响声,弹几下响几下。弹一下,秋公社会笑一下。秋公社护痒。
“熟了,熟了!”
队长说秋公社的肚子是西瓜。
我们都会在队长弹响指的时候,跟着去凑热闹,也把小指伸过去,学着队长的样子,去弹秋公社的“西瓜”。我们羡慕得很。
我并不知道我妈那里并不是最后一关,决定我去不去放牛的还是队长说了算。后来我知道了,要放牛的人家的孩子不少,去几个孩子放牛是看队里借多少牛的。队长给落选的孩子和孩子的家长说好话,答应下次一定让去放牛的。轮到我妈向队长求情时队长并不爽快,推说我年龄小,不放心。我妈说出什么事不找队里。我妈向队长下了保证书。
哪知队长依旧犹豫。
我妈感叹了。近乎哀求队长了:“去让孩子吃一顿饱饭吧。”
估计是这句话打动队长了。最终我胜出。我成了放牛娃一员。
我欢呼雀跃的情形不述。
乐极生悲,我妈说她那天央求队长让我去放牛差点酿成了她一生的错。
我上山的时候我妈终究不放心,午饭不知何时吃,怕我饿着,给我塞了一块玉米面饼。其实近晌的时候我肚子真的饿了。我只是想忍忍吧。忍忍有干饭呢,有纯米饭呢。我就这么美美地想着。气温渐高。不知什么时候,我竟然不知不觉地爬在牛背上睡着了。
午饭,畜牧场人说少了一头牛!有人带话给队长,队长急了,问是谁家的孩子没回。一问是我。队长抱怨我妈的不是。我妈没再理论,只是急得直哭,显然没有了方寸。队长就派人上山去寻。午后,我没回。傍晚,我没回,眼看太阳要下山了,我妈已哭不出声了。
也不知是太阳晒的,还是我饿的。总之我是什么也不知道了,在牛背上睡得很沉。根本不知道去拽牛绳,随牛跑。哪知牛跑到一个山洼子里去了,一时人根本看不到。近黑队上人寻到我时我才睁开眼看到我妈。我饿坏了,再去摸我妈塞给我的手帕,哪还有玉米面饼的影子。一顿米饭没吃到,差点出了大事。
五
鲁迅说,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要搁秋李郢,他们会说,这话说在点子上了。
说在点子上就是说在要害上了,说出了它的本质。牛索取的少。这话是表扬牛的,赞美牛有无私奉献的精神。
牛吃鲜草的时候是自己吃的。牛舌头在地上一划拉,卷在口中,拢住,牙一咬,那地上一周的草就是它的了。忙里偷闲往胃里填草,秧季了,牛就没有闲下来的时候。好像牛就没有时间慢慢把草嚼碎似的。它哪里是吃草,它只是把草咬过以后放在肚子里,放在胃里,等它耕地的时候才吃,等它睡觉的时候再把胃里的草倒出来,反刍。
我敢说,牛没少打那满田秧苗的主意。秧苗那可是丰美的草呀。秧田边上的那排秧也有短了的时候,还不是叫牛偷吃了的么。牛自从拴上了牛鼻枸子之后,自从有了牛绳拉它的枸子之后,牛便知道了好坏似的,它在田埂边吃草,却少去动那挨在嘴边的秧苗了。坐怀不乱,这要何等的定力呢。
想想有点残酷,甚至残暴,人在活生生的肉上穿了根木棒,用绳子强拉硬拽,那是肉呀,牛一定是疼坏了。牛鼻枸子像是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牛稍有想法的时候,嘴还没靠近秧苗呢,这紧箍咒有人就开始念了,放牛的就开始抖绳了。拼命地抖绳。那牛还不明白么,牛疼呀。
一个秧季,一个稻季,牛除了偷吃短过田埂边的那排鲜美的秧苗之后,牛没吃过庄稼。稻季过后,入冬了,人们把稻子脱了粒,留给牛的是干稻草。干稻草我们也叫它“牛草”。
牛草,加水,这是牛冬天里的全部饮食。
冬天,牛进屋,进牛房。牛房也成了人的好去处。牛房暖和。人们在牛房里开会,在牛房里学习《毛主席语录》。我们待在牛房里是有条件的,看牛的李老二要我们做两件事:给牛喂草、拉牛到沟里喝水。他嚷,抱草去!我们知道,哪头牛的牛槽里没牛草了。我们便屁颠屁颠地去草堆上扯干稻草,放到空了的牛槽里。他又嚷,给二牯子饮牛去!我们便知道把二牯子拉出去喝水了。“二牯子”是牛的名字。
每头牛都有名字。像“独眼”“断角”什么的都是公牛名。公牛好斗,独眼断角都是公牛斗后落下的残疾,李老二便由此给牛取了名,倒也不觉得对牛有什么不敬之处。公牛叫“疤瘌”的多。“二疤瘌”、“三疤瘌”什么的。疤瘌自然也是公牛斗后留下的创口。“二牯子”是母牛,母牛叫“牯子”,李老二也叫它“二小姐”的。还有“三小姐”“四小姐”的。母牛不好斗,身上自然没有残疾。给母牛起名字李老二都是按出生年月排行的。当年李老二的牛房里有“七仙女”,就是有七头母牛。有人跟李老二开玩笑,你闺房里有七仙女呀,李老二倒一时不好意思起来,有时,也跟着发噱。
喝凉水,吃稻草,一个冬天下来,牛骨瘦如柴,毛也尽褪,像是只有一层牛皮披在了身上,走路也没有精神。看样,牛草并没有多少营养。牛如此模样,李老二自然也心疼,他只是说,春天来了就好了,秧季里草肥水美,牛会来膘的。
一个冬天,我们都跟着李老二一起,盼望春天,盼望秧季的到来。
(责任编辑 王冬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