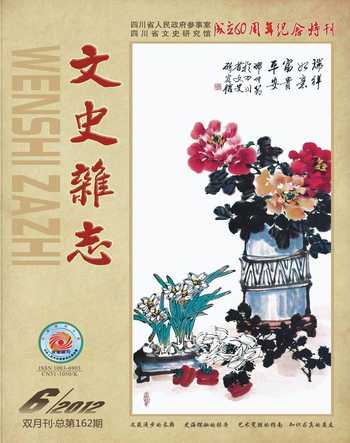创新的魅力 学术的分量
2012-04-29晓强
晓强
2011年7月,巴蜀书社出版了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何崝先生的力著——《中国文字起源研究》。何崝先生于1947年7月出生于成都,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就学期间师从著名古文字学家、《古文字诂林》主编李圃先生),赓即以古文字学的非凡造诣被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徐中舒先生纳入门下做助手,在四川大学古文字研究室参加了由徐中舒任主编的《甲骨文字典》的编纂,对古文字研究颇有建树。他还在先秦史领域、书画篆刻及诗词歌赋创作方面表现出极高的见识或才能,是中国文字学会会员、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不过,比较起来,他最为学界看重的才识则在古文字领域。这部以探索中国文字起源为的彀的《中国文字起源研究》,其写作时间长达9年,加上前期的准备工作,则长达十几二十年之久,可谓他的呕心沥血之作,最能反映其在古文字方面的精深功力与治学水平。正如孟世凯先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郭沫若主编之《甲骨文合集》主要编纂者之一)在该书序言所指出的,该书的撰写、出版,实非一日之寒。这是缘于“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一、要对考古资料熟知。因几十年来伴随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文化遗存和出土器物上发现许多刻划符号或图形,是文字的源头。二、要有甲骨文功底。能直接使用甲骨文资料,因为商代甲骨文是处于我国汉文字承上启下的时段,否则很难说得清楚。他完全具备了这两方面的功力”[1]。
下面,笔者从三方面着眼,谈谈对何崝先生《中国文字起源研究》的初步认识。
具有穿透力的理论:文字生成机制说
过去,学界将“中国文字的起源”与“中国最早的文字”这两个问题大多混为一谈,“谈文字的形成,似乎主要着眼于符号本身的演变”,“对所谓的‘最早的文字、‘较原始的文字、‘完整的文字体系等概念并未加以严格的界定,因而他们所谈论的文字形成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2]。何崝先生认为,“文字的起源问题不能只谈‘最早的文字,还应包括与文字有关的‘最初因素”,“文字起源问题就要研究这些‘最初因素如何经过几个阶段发展为最初的文字体系”。[3]鉴于此,何崝先生在本书里提出“文字生成机制”理论(或称“文字生成机制说”), 用以指导中国文字起源研究,用以探索并回答中国文字是如何从“最初因素”一步步进化为“最初的文字体系”——商文字(甲骨文)的。
何崝先生提出的“文字生成机制”大致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图画和符号的出现;第二阶段,巫师文字(主要用于人神交流)的形成;第三阶段,通行文字(用于人际普遍交流)的形成。何崝先生特别指出,由巫师文字发展成通行文字,必须具备较大规模贸易这一基本条件。这也是形成通行文字的原动力。它包括拥有相当发达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以及畜力和车辆之类的运输手段,还要有优越的地理条件,有多个文明同时并起,以利于达成较大规模的贸易。[4]
何崝先生运用他的这个创新理论,阐明了苏美尔楔形文字与古埃及象形文字在距今四五千年的时期得以最终发展成较为成熟的通行文字的科学性。何崝先生以主要篇幅冷静、客观地考察、分析了中国文字的早期状况,认为直至距今三千年左右的殷墟时期,才“初步形成了通行文字——殷墟文字”[5];因为殷墟时期由巫师文字发展成通行文字的包括贸易在内的各种条件方才成熟。而此前在中华大地上发现的、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刻划符号、中经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字符号(虽是文字,却属于巫师文字),再到夏代所谓“简单文字”、“原始文字”、甚至包括早、中商时期的文字符号(均属于巫师文字),由于缺乏具有较大规模的贸易作为原动力,所以都不是通行文字。何崝先生还指出,殷墟时期商文字(中原文字)体系尽管已形成,但其文字尚处于通行文字的初期;至周代,中原文字体系才成长为比较成熟的通行文字,使之得以逐渐传播到南方,通行于整个古代中国。其间的关键推动力,乃是周代比商代更为发达的贸易。[6]
何崝先生以贸易为核心的“文字生成机制说”,在数百年来关于中国文字起源问题的层层迷雾疑云的交错纠缠中,像一把清亮锋颖的利剑独辟蹊径,立时将中国文字起源的探索引向一条崭新的路径。其为中国文字起源研究所作的重大贡献,是显而易见的。李圃先生因此欣喜地说:
何崝君在中国文字起源研究中所提出的具有理论穿透力的中国文字生成机制原动力说,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理论上的创新,往往是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一把钥匙。[7]
坚实的结论:中国文字起源于中国本土
苏美尔楔形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与中国汉字并称为人类最古老的三大文字。但是,在20世经80年代以前,特别是在甲骨文大量出土(1936年春至1937年6月)之前,西方学者多认为中国汉字来源于前两种文字。如19世纪末伦敦大学教授拉克佩里《中国上古文明西源论》,1899年日本白河次郎、国府种德《支那文明史》,1913年英国传教士鲍尔《中国人与苏美尔人》等书,都认为中国文明、包括中国文字都传自苏美尔—巴比伦。17世纪中叶耶稣会士柯切尔《埃及之谜》与《中国礼俗记》、1667年德国祈尔歇《中国图说》、1716年法国尤埃《古代商业与航海史》、1758年法国德经《中国人为埃及殖民说》、1933年日本板津七郎《埃汉文字同源考》则认为中国文明源自埃及,文字亦传自埃及。到了1952年,美国学者I·J·Geib又著文认为中国文字可能源自印度河文明。20世纪初叶,包括中国文字在内的中国文明西来说在中国学者(如丁谦、蒋智由、章太炎、刘师培、黄节)那里也颇有市场。直至2005年,苏三在《历史也疯狂》(金城出版社)一书里仍坚持中国文字来源于古埃及象形文字。对于西方学者而言,之所以有上述怪论出现,从骨子里看,乃是“西方中心论”在作崇。20世纪初丁谦、章太炎等学者对中国文明西来说的“赞同”,则出于清末的反满情绪,属于“带有政治色彩的学术观点”。至于进入21世纪后苏三等个别学者的立场,则不好揣摩了,或者至少可以说是缺乏民族自信心吧?
中国文字是否独立发生、发展并自成体系,事关中国文明亦是否独立发生、发展并自成体系的重大问题。归根结底,这是一个事关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尊严问题、文化自信力问题。许多中国学者实际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峻性。如李济先生(1896—1979)在《考古琐谈·试论中国文化的原始》里已将“(中国)文字的开始”归于“尚难断定来源者”。他“在地下材料还不够充分的条件下提出这样的看法,是一种审慎的态度”[8]。
作为一名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浓郁氛围里成长、成才的中国文化学者,何崝先生自觉地担负起为中国文字寻找母体或本原的光荣使命。他运用他发明的“文字生成机制说”,不仅为中国文字的起源勾勒出一个从刻划遗迹、文字符号到通行文字的清晰轨迹,而且还将其置于世界文明起源、人类文字起源的坐标系及古代世界贸易往来的大背景下予以对比、观照,从而将中国文字的出生本末有根有据、有理有力地清楚地展现出来。他在《中国文字起源研究》里写道:第一,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现的距今7330年至6900年的蚌埠双墩文化(属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大量文字,“已经具有较高符号化程度”。它们比两河流域的乌鲁克(在今伊拉克境内)“古朴字”(属巫师文字,为苏美尔楔形字前身)和古埃及图形文字(属巫师文字,为古埃及象形文字前身)要早一千多年。这也就是说,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巫师文字的形成比两河流域与古埃及的巫师文字的形成要早得多,而且其发达程度也比后两者更高。第二,双墩文化的文字孕育出生成汉字的一些必要因素(象形、指事、会意以及组成文句)的雏形。“仅就这一点看,也可以认为汉字是独立形成于本土的一种文字”,“决非从域外传入”。[9]第三,“印度河文明与古代中国相同相似的文字符号中大部分可以相信是从古代中国传入的”[10]。在殷墟文字之前不曾在中国本土出现,而只见于印度河文明区域的这些文字,实际上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文字”[11]。
何崝先生最终理直气壮地坚定地宣称:“中国文字的的确确起源于中国本土。”[12]
这样的结论,是何崝先生经过大量细致的爬罗剔抉与严谨的科学求证,经过长期焚膏继晷的苦行僧般的艰苦努力得出的,而且得到李济先生过世后30年间出土的丰富的地下材料及考古学成果在广度与深度上的坚强支持,是足可以告慰长眠于地下的像李济先生一样的老一辈学者了。孟世凯先生对何崝先生所做的艰辛工作感喟道:
凭着一个人的精力运用大量的考古资料和甲骨文、铜器铭文等古文字资料,写成这本对中国文字起源全面探索之巨著,我认为是对中国古文字学界、古史学界做了一件有功德之事。[13]
理性的声音:巴蜀文字仍是巫师文字
何崝先生还运用其首创的“文字生成机制说”,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川渝学者的一个重大问题:所谓巴蜀文字是否是先秦时期通行于巴蜀大地的成熟文字。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过去30年间,川渝学者主要分出三派——
一、巴族文字还处于象形文字的最初阶段。此说以徐中舒先生为代表,邓少琴先生亦表赞同。徐中舒先生在《论巴蜀文化·巴蜀文化初论》中认为,巴蜀地区发现的巴族铜器上的两种象形文字,尚“停留在比较原始的阶段,即文字与绘画还不能有显著的区别”;而象形文字必须发展到形声字(象形兼具声符的文字),才能够完成文字的功能。现存的么些(纳西)象形文字——么些文字虽“也有形旁注音的字,但还没有发展到最完备的阶段”。徐中舒还指出,巴文与现存的么些象形文字和汉字,在文字构成的条例上,“具有一定的共同基础,最初还有可能是同出一源的。但是它们的分枝,应当是远在殷商以前”。徐中舒特别指出:“现在的甲骨文,已经具备了完整的六书条例(按:徐中舒在该书其他段落里说明道:‘其实六书中只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造字的根本原则,其余如转注、假借是属于文字训诂的范围),这应是甲骨文在分枝以后单独发展的结果,就是现存的么些象形文字,也还没达到这个阶段。”徐中舒还说:“巴文虽已有合体字,如手和花蒂形,可能这还是会意字的开始。它有没有形声字,我们现在还不能肯定的作答。”[14]
二、巴蜀文字完全脱离了原始的象形阶段。童恩正先生在《古代的巴蜀》一书里指出:1.所谓巴文字,应目为巴蜀文字。2.巴蜀文字是方块字,有偏旁结构(但与汉字有别),“完全脱离了原始的象形阶段”,“与汉字一样,应属于表意文字的范围”。3.从商代到周代,中原文字也在巴蜀境内流行。4.巴蜀文字之外,还有巴蜀符号,两者是不同的(如郫县出土的战国铜戈上并列的符号与文字),不能笼统地称为巴蜀文字。[15]李学勤先生在《论新都出土的蜀国青铜器》一文里也提出(据1960年《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巴蜀文字有两类,一类是符号,另一类是“似汉字而又非汉字者”。李学勤将前者称为巴蜀文字甲,后者则叫巴蜀文字乙,称“巴蜀文字乙是一种文字,研究者是公认的”[16]。
三、巴蜀文字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此说以段渝先生《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为代表。段渝先生承接童恩正先生、李学勤先生的观点而以发展,将巴蜀文字分作方块表意文字与符号象形文字两系,称其可上溯至商代中叶,至春秋战国时期而大量使用,为当时巴蜀境内并行不悖的两大系列文字。其中巴蜀方块字是比较成熟的文字,“它以象形为基础,发展出了指事、会意形体结构,其水平接近于商周甲骨文和金文;而巴蜀符号象形文字也已开始了由表形文字向表意文字的过渡”。段渝还特别指出:“目前所见的巴蜀方块字和巴蜀符号,均发源于川西平原蜀地。所谓巴蜀文字和巴蜀符号,从其起源看,其实是蜀的方块字和符号”;而川东巴人所使用的文字和符号,其实是向蜀借用过来的。段渝先生的观点,均迥异于徐中舒先生所论。此外,段渝也跟童恩正先生一样,认为“巴蜀在使用自己的文字时,也使用中原文字”。[17]
关于巴蜀文字的论争,其实早在汉晋时期就开始了。扬雄的《蜀王本纪》说:“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严可均辑《全汉文》卷五十三)这就是说古蜀人并没有文字。徐中舒、邓少琴二先生是赞同其说的,将巴蜀两地发现的战国铜器铭文统统视为“巴文”或“巴人使用的象形文字”。而常璩则反对这种说法,认为古蜀国具有悠久文化传统,担任殷太史的彭祖就是蜀人;蜀地如果没有“书学”(典籍、文字)和“文学”(学校)传统,是不会推拥出这种人才来的。(参见《华阳国志》卷十二《序志》)对此,蒙文通先生是大体赞同的。
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关于巴蜀文字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巴族、蜀族的文字是否原始或成熟的问题上,而主要的衡量标准,则是汉代人提出的“六书”条例。上举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便基本遵循这些条例而做是非判断,最终导致出自说自话而莫衷一是。何崝先生显然看到这种弊端。他在《中国文字起源研究》里能跳出过往窠臼而别开天地,依恃的仍是“文字生成机制说”这一法宝。
何崝先生首先承认,在以商、周文字为代表的中原文字逐渐发展成通行文字时,南方地区也在形成覆盖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包括巴蜀文字在内的南方文字。它是与中原文字并立的一种文字体系。而商周时期,中原文字在南方虽有传播,但终究属于零星态势。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吴、楚把中原文字传播到南方之前。
何崝先生接着说,在南方,东部经济较为强势,其文化也因之强势,并由东向西传播。西渐的文化自然包括文字,主要是今两湖地区土著扬越人的A、B、C三种文字(其渊源于良渚文化、吴城文化的文字符号)。迄今发现的战国时期的巴蜀文字不是由早期的巴蜀文字符号(如三星堆遗址、十二桥遗址发现的文字符号)发展成的,而是由扬越文化、扬越文字传播影响所致。(取代杜宇建立开明王朝的鳖灵是扬越人;巴蜀文字的A、B、C三类与扬越人的三种文字相似,但扬越人文字年代早于巴蜀文字,故可认为巴蜀文字主要渊源于扬越文字。)
何崝先生最后指出,战国中晚期,尽管“巴蜀文字已处于向通行文字发展的临界点上”,但“似仍属于巫师文字阶段,还未发展为通行文字”。由于巴蜀地区周边文化过于强大(其时中原地区和楚国都普遍使用中原文字),使得巴蜀文字难以发育为通行文字。巴蜀文字是南方文字发展的最后阶段(或即古越族文字体系的最后阶段),“其发展程度高于此前阶段的其他南方文字。巴蜀文字尚且未能发展为通行文字。其他南方文字就只能是属于巫师文字了。”[18]
何崝先生运用“文字生成机制说”而提出的关于巴蜀文字主要并非土生土长,而是渊源于扬越文字的观点,关于巴蜀文字尚未达到通行文字的高度(属于巫师文字的末期)的观点,或许会令一些热爱巴蜀文化者、痴迷于巴蜀文字者丧气或不快,却到底是真相,是大实话;因为它们委实具有丰富的考古资料的坚强支持,合乎辩证原理,合乎历史逻辑。李圃先生之所以认为何崝先生的《中国文字起源研究》是“为学界奉献了一部难得的历史文化考古的创新之作”[19],乃基于作者所展示的不迷信权威,不囿于成说,崇尚真理,独立思考的品质和脚踏实地,心无旁骛,孜孜矻矻,上下求索的精神。正是有了这种品质、这种精神,方显出该书宏大的视野、深刻的内涵、创新的魅力与学术的分量而令人肃然。
我国第一部甲骨学辞典的独立编撰者孟世凯先生说:
甲骨学是古代史、考古学、古文字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不仅专业性强,内容争议也较多。甲骨文虽是汉文字,但它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成体系、能完整表意的古文字。“殷墟”出土的也是距今三千年前商王朝的实用汉字。因此,甲骨学不是普及性的学科。[20]
何崝先生的这部《中国文字起源研究》却主要以甲骨文为研究对象(兼及金文与其他古文字、刻划符号)。目前学界对甲骨文单字的考释,尚“未超过五千零几十字(含合文)的一半,许多考释过的字仍然是见仁见智”[21]。在此情况下,还要对中国古文字追根溯源,展开全面研究,其困难度、艰辛度是可想而知的了。但是,何崝先生在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及学术责任心的驱使下,不仅成功地完成了对中国文字起源课题的攻坚战,而还将主要以甲骨文、金文架构起的中国古文字的高雅堂奥和悦地敞开来与一般文化人、一般文史爱好者共享,殊为难得。其论证充分而不烦,条理清晰而谨严,文笔平实而流畅,面貌淳厚而近人;虽是长达89万字的煌煌巨著,读来并不觉累,而收益则可谓车载斗量,不可胜数。
注释
[1][13] 何崝:《中国文字起源研究》之《孟世凯先生序》第4页、第5页,第8页,巴蜀书社2011年版。
[2][3] [4][5][6][8][9][10][11][12][18] 何崝:《中国文字起源研究》第1029页、第1030页,第1029页,第1030页,第1041页,第1044页、第1045页,第1027页、第1028页,第248、第249页,第562、第563页,第584页,第1028页,第1022页、第1051页,巴蜀书社2011年版。
[7][19] 何崝:《中国文字起源研究》之《李圃先生序》第3页,第3页,巴蜀书社2011年版。
[14]徐中舒:《论巴蜀文化》第45页—4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5]童恩正:《古代的巴蜀》第131页—13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6]李学勤:《论新都出土的蜀国青铜器》,徐中舒主编《巴蜀考古论文集》第196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17]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第269—273页,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20][21]孟世凯:《甲骨学辞典》之《自序》第3页,第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作者单位: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