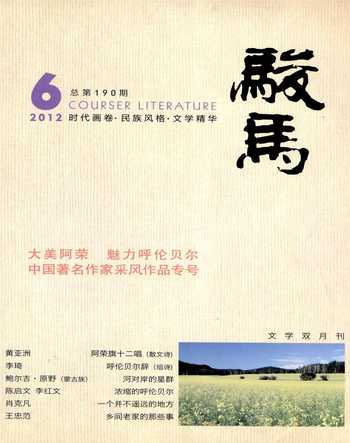故乡的榆钱儿
2012-04-29孔祥胜
孔祥胜
五月的北国,和风拂面,冰雪消融,兴安杜鹃悄悄开满了山岗。
天空刚下了一场春雨,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的春的气息;榆树在枝头孕育了暗红的花苞后,就展开了久违的新绿——一串串晶莹的榆钱儿,在风中摇曳。
我凝望着枝头那一串串新绿,不由得又想起了故乡的榆钱儿。我的故乡在日照,原属临沂地区。那大概是1976年清明节前后,房前屋后的一株株榆树就迫不及待地绽放了新绿,把春天的希望带到了人间。
那时我们全家刚从山上搬下来,新建的四间瓦房,在生产队是最漂亮的。我虽然还小,但依稀记得那时家家都采榆钱儿充饥。
“阳春三月麦苗鲜,童子携筐摘榆钱”,这诗里说的就是采榆钱儿的情景吧。老家的榆树大多长得弯弯曲曲,老枝横斜的样子。每当采榆钱儿时,一群穿着破破烂烂衣服的孩子就三五成群,挎着竹筐、夹着布袋,一边打闹着,一边说笑着,全然不解当时大人们的阴郁心情。
男孩子爬到树上,把袋子搭在树枝上,或把筐挂在树枝上、夹在树杈间,开始捋摘榆钱儿。女孩子则站在树下,仰着脸望着树上的猴子们,不停地叮嘱要小心,别掉下来。但掉下来也是常有的事,不过那时的孩子都很皮实,摔不坏。
爬树最担心的是磨裤子,费鞋子。我们常常甩掉鞋,脱了布衫,赤着脚,光着膀子爬树。大孩子手脚并用,一会儿就爬上去了,而我只能用双臂搂住树干,把自己紧贴在树上,然后一点一点地往上挪。下树就更难,一不小心就从树上滑下来,把肚皮都蹭白了,但那时没有人在乎。
在树上先捋一把最嫩的榆钱儿放在嘴里嚼着,自己先吃个够,然后再往筐里、袋子里装。
母亲将榆钱儿摘掉蒂,筛干净,用清水淘洗两遍,然后均匀地铺在帘子上,再在上面撒些豆面,放到锅里蒸。
我们围着锅台,眼睛盯着从锅沿冒出的丝丝热气。等揭开锅,就迫不及待地把蒸熟的榆钱儿饭塞进嘴里,粘粘的,滑滑的,还有一股清香味。
后来榆树都被捋光了,就只能偷偷地去剥榆树皮。
大人用石头先在树根部砸开一个口子,蹲下去用双手抓住翘起的树皮,然后猛挺起腰用力往起扽,一張树皮就这样剥了下来——那时我不知道树被剥了皮是会死掉的,然而大人肯定是知道的。
我们趁天黑把树皮藏在僻静的地方凉干,用石头砸成小块,再用石磨磨碎,就可以做着吃了。
1977年10月,我们全家搬到了阿荣旗,一个在当时看来虽然偏远但可以不挨饿的地方。
虽然有的多是饥饿和贫穷,但那时并不缺乏快乐。我慢慢地咀嚼着那段时光,总想从中品出点别的什么滋味,每次也总能有不一样的感受。记得有人曾经说过:经历就是最好的财富,我将终生受用并将永远珍藏这份宝贵的财富。
2006年6月,我回了一趟老家,参加小妹的婚礼。老家的变化是巨大的,我已经很难再找到童年的旧迹了。
小妹带我回到老屋前,我记忆中的漂亮的房子已经变得破旧矮小,与周围非常不相应,已远不是记忆中的模样了。
我沿着记忆中的小路,寻找着记忆中的榆树。它们有的已经老去,有的因为建房被砍掉了,只有靠近河边的一株还顽强地生长着,倔强地向四周伸展着虬枝。
我抚摸着被岁月环绕成的粗壮树干,感慨万千:当年爬树的孩子如今已经长大成人,当年扎着围裙做榆钱饭的母亲也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唯有这株榆树还依然挺立,见证着这些年来身边发生的巨大变化和人世沧桑。
树虽无言,但我仿佛听到了它急速的心跳声和对往昔的低喃。
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人们早已不再剥榆树皮了,吃榆钱儿也变成了一种时尚,城里人很前卫地享受着这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我不知道过来人是否还会记得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孩子们是否听说过父辈们的这些故事,但榆树始终都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榆钱儿始终都是我们最难忘的患难之交。
(责任编辑 晋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