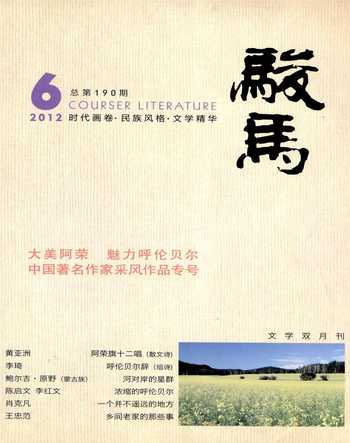河对岸的星群
2012-04-29鲍尔吉·原野
鲍尔吉·原野
蒙古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在大陆出版“原野文库”等43种散文集、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在台湾出版《现代文学典藏——鲍尔吉·原野散文集》等2种散文集,为德国独逸学院驻访作家。作品收入大学、高中、初中、小学课本以及试卷。曾获《人民文学》杂志散文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文汇报》笔会奖,内蒙古文艺特殊贡献奖及金质奖章等。
花朵从露水里醒来
早晨从库伦沟林场的招待所醒来,感觉像花朵从露水中醒来。后窗连着山坡,茂密、修长的青草上面长满了野花。花朵好像刚看完戏,还在睁大眼睛回忆剧情。前窗的对面垛着伐下时间不长的红松,鳞片还是新鲜的,松脂的香气整夜在我的房间中萦绕。梦境仿佛镶嵌了琥珀。
出门跑步,山坡传来群鸟的喧腾。我几乎不想跑了,想钻进山里把藏在暗处的小鸟一只只揪出来,看是什么样的鸟在唱这些歌。人的眼睛没什么能耐,见到的只有松树,见不到鸟。这里的空气比刚开瓶的香槟气味还香。人在城里呆久了,连街道垃圾都辨不出臭味,鼻子来在这里像一只刚刚被救活的狗。没想到,大地上竟有这么多种香气,让人晕眩,好像香味挤跑了血液里的氧。香味在脑子里冲撞,人走起路来跌跌撞撞。我有些舍不得大口呼吸,这么好的空气用来跑步呼吸都糟践了,应该慢步走小口吸气,跑步浪费香味。
水泥大道笔直通向远方,没有车过,好像白修了。水泥上稻草袋子的花纹依稀可辨,真没怎么过车。跑吧,在这里跑步是专场,周围一个人都没有,只有天空上的白云和藏在树里看不清的鸟。皇帝跑步也不过如此待遇——我对自己说——虽然没听说哪个皇帝跑步。正在想,忽见路边房顶站着三四个砌砖的人,他们停下手里的工作,看我跑步。他们的脸像砖一样烂红,身上彩色的半袖衫已被晒褪了色。我看他们,他们不好意思了,低头砌砖,弯腰时偷眼觑我。
跑出三公里,路边彩旗招摇。一块横幅写到“欢迎来到××庄园”。我从彩旗的夹道跑进去找这个庄园,跑了两公里也没见什么狗屁庄园并想像好多人拐进来找不到这个庄园而折返,庄园因此破产了。当然,真正上这个庄园吃与宿的人,都是开车人而非跑步人。因此,他们还是破不了产。两公里的夹道彩旗证明他们活得很好,至少有流动资金买几百面彩旗在风里飘。
回到大道上,慢慢地跑,心情好,想唱歌并感到会唱的歌太少。在这么好的环境里,一气唱一百首歌一点不为多事,把歌唱草原的、歌唱河水的、歌唱爱情的、歌唱母亲的、歌唱友谊的歌唱一遍,才跟周围景色配套,当然还应该歌唱瓦匠、彩旗和松树。作曲家为什么不谱歌唱瓦匠的曲呢?他们住的房子难道不是瓦匠搞的吗?我愉快地胡思乱想。左边草原出现牛群,三四十头,像红色、黑色的石头堆在薄雾里。牛群后面是一片桦树。桦树长在平地而不是山上,它们仿佛只愿意跟修长的青草长在一起。白桦林那么密,像挽着裙子的姑娘们相互拥挤。白桦树纤细秀美,有的两、三株长在一起。它们叶子碧绿,比涮火锅的青菜还要绿,衬出树干的皎白静美。人进白桦林里更应该唱歌了,不一定非唱俄罗斯歌,唱哽咽的日本歌也行。
桦树林边上有小河,流在呼伦贝尔人称之为“沟塘子”的里面。小河四五尺宽,青草作岸,草长二尺高,仿佛是河的伪装衣,不让别人发现这有一条静静的河。阿荣旗的伟大——但愿我使用伟大这个词不会让人惊讶——是由于这里没开矿,没破坏草原。它的土地上流淌着成百上千条小河,藏在深深的草丛里。多么好的植被才涵养出这么多条小河?熙熙攘攘的小河证明这里山深林密,草长莺飞,小鸟和白云在此安居乐业。拨开草丛,见到了河水,河水因为没见过人而害羞,扯过天上的云影遮挡面容。探身看,河里游着土黄色的小鲫鱼,水底有未腐烂的蓝莓果和红色的山丁子。小河是遮着绿色面纱的闺女,她们在草丛下奔跑,去了不知名的远方。站起身远望,大草原似一片无接缝的绿毡,见不到小河的踪影。
在这样的地方跑不了步,跑步大师来到这里也要走走停停。眼前美景太多,把工夫全耽误了。人跑着跑着,心已飞向远处。我不止一次跑下公路,看白桦林,看小河,看草叶上的露水。甚至出现幻觉,想跑到堆在天边的矮矮的云彩垛里瞧瞧。想不到,完好保护自然环境,世间竟有说不尽的美景,这里即使不算仙地,也算一个人一生很难遇到的奇境。
这里的森林比匈牙利更多
库伦沟林场的场部在一个小镇上,十几户人家,也许叫小村更合适。房屋的红瓦被露水浸过,一片鲜洁,好像洗干净的红砚台,等人用毛笔去试墨。各家的木板栅栏被雨水浇得黝黑,上面环绕嫩绿的牵牛花枝蔓,点缀蓝和粉色的花朵。你看久了,发现栅栏里有一条狗正以疑惑的眼神看你,并使劲嗅你带来的外来者的气味。
我去买牙膏,现在是早上五点钟,不知小卖店开门否。走过去,水泥路两边用石头砌的排水沟長满野草,而没有常见的垃圾。飞鸟从头顶飞过去,变成黑点。在阿荣旗的早上,眼前常常出现这样鸟的黑点。也有小鸟迎面飞过来,由高向低,同伴说我们处于气流的下坡。这时传来断断续续的手风琴声,总是拉开头两句就停,这不是哪一家放音乐,而是有人拉琴。
琴拉的是乌克兰歌曲《德涅伯尔》,开头两句像这首曲子。可是,在呼伦贝尔草原的阿荣旗的林场,有人用手风琴拉乌克兰歌曲?我生活在所谓大城市,也未曾在街上听到从窗口飘出的琴声,原来有过小孩练习钢琴声,现在没了。夏日窗口飘出的只有打麻将的码牌声。我从一片被小葱和小白菜间隔开的土路走过去,进入小卖店,琴声忽然响起来,一个老汉像母鸡展翅那样对着我拉手风琴,他红脸膛,坐在一只用水果箱子改制的简易椅子上。“花城百花开,花开哎朋友来……”他边拉边唱,欢迎我。等他拉完四小节,我低声,卖弄地对他说:作曲秦咏诚。
哎哟!他站起来,身高有1米85。你还知道秦咏诚呢?他欣喜并惊讶,从柜台边上拖出另一只水果箱子改制的椅子,快坐。
我说,知道秦咏诚有啥可哎哟的,你能拉德涅伯尔更哎哟啊。
没啥,他开始拉这台破旧的鹦鹉牌手风琴,风箱有的地方漏风了,键子和簧片的接触也有间离,声音忽轻忽重。
“拉,多咪,拉——咪,来多,多西——”这架破手风琴的乐音让他心醉,甚至合上了眼睛。我跟着旋律小声唱:“——在黑云后面徜徉,林中的枭鹰……”不幸,我忘词了。
还拉啥?他眼瞅着屋顶思索,他老婆不好意思地看他,仿佛他快出丑了。皮亚佐拉?他问我。
我竖起大拇指,皮亚佐拉,这是意大利的炫技派作曲大师。他拉了一段,额上像蛐蛐须子的长眉毛上下跳动,但我没听过这首作品。
他摘下手风琴,脱外套,身上剩一件千疮百孔的白背心,上印七个字:我为边疆修大渠。
拉什么?他问。
查尔达什会吗?
嗨,他拉起查尔达什,蒙蒂作曲。这首曲子的前身是匈牙利人的民间舞曲。他拉的真好,慢板和快板的节奏都准确(民间音乐人常常篡改节奏)。
他拉过一遍后,又拉了一遍,一共拉了三遍。这位民间手风琴演奏家的小卖部里摆着镰刀,驭马用的皮套包子,刷绿漆的铁犁,一捆铁锹杠。水果罐头最多,摆了两排。他老婆一直站着听,她前额的皱纹把眼睛压小了,头发花白,手背暴露凸出静脉,女农民就是这样子。她频繁地眨眼,仿佛沿着她丈夫的乐曲走到了匈牙利,正在辨识那里的森林和道路。
匈牙利的森林有库伦沟林场多吗?这里长着一片又一片樟子松。樟子松一年只长一小点,路边这些粗壮的樟子松不知已经长了多少年,像一队队披墨绿斗篷的军士。这些军士漫步在阿荣旗的原野,成千上万。空气中,除了查尔达什,还有屋外传来的布谷鸟的单调的鸣叫。屋外菜畦子开着白花,像落下了成群的蝴蝶。
我听完乐曲,躬身致意,告辞了。我觉得意外听到这么多乐曲,已经偏得了,再呆下去就打扰他们了。走在街上,背后传来《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文革歌曲,男中音马国光当年演唱。对我而言,我爱这阿荣旗的早晨,寂静中有人拉手风琴。快到住地,我想起我是买牙膏的,但我不再返回小卖店了,下站再买,让这个记忆在脑海里保留着唯一性吧。
大熊星座在河里洗澡
阿荣旗境内河流多,眼前这条是阿伦河。夜色下,岸边茂密的树林像披着黑色斗篷的巨人睡着了,阿伦河水猫腰从他们鼻子底下流过。夜色如毯子盖在河岸的草地上,盖住了不知多少野花。
早上,我来到河边的时候,草地被野花占领了。天刚亮,野花已精神抖擞站在那里,披一身露水,好像一宿没合眼,等一个盛典。太阳每天升起来都是盛典,新鲜光亮,野花知道,人不知道。花朵以细细的身子支着陈鲁豫那么大的脑袋,它们的面庞比人类肉质的脸更纯洁。花的面孔不讲五官讲瓣,三瓣、四瓣、五瓣的花脸都比肉好看,像能旋转。花的表情只有一种:笑。花朵除了在雨里哭泣之外,其余的时光都在笑,笑弯了腰。真不明白花到底在笑什么。晨光射入草地,被雾阻挡,景象朦胧。花朵从斜坡的草地上跑向河边,仿佛去梳洗。蓝的花、白的花、黄的花高出青草,凝视河面微颤的波光。河水在早上蜿蜒流远,天边的山峦不是青山,而是玫瑰山。树尖在白雾里冒一点头,如波涛里的礁石。大地苏醒了,四处沾满湿漉漉的露水。
眼下是夜里10点钟,阿伦河发出白天听不到的响声,似咕噜噜滚东西,又像嘻嘻哈哈偷笑。山峦和树丛被夜藏进包裹里,活动的物体只有河流。河如不流,水面嵌满星星。星星趴在水面的时候特别怕被打扰,一片被风吹落的树叶或鱼儿翻身都会拆碎星星。水流淌,星星在水里被捣成了星星酱,波浪上隐约只剩一层白光。
这时,对岸燃起篝火,火光照亮了一棵老树。它必定是榆树,鄂温克人和满族人都崇拜榆树,老榆通灵。不一会儿,鄂温克人围拢老榆树跳舞,歌声隐隐约约地传过来。头几天,我们在那吉镇参加广场篝火晚会,转圈跳舞的有好几百人。鄂温克人单纯,无论老幼,都如纯洁的儿童,他们尊崇大自然,信仰舍沃克神、铁神和奥卓尔神。他们在篝火上扔一些马鹿和犴的油脂,冒出的香味会让舍沃克神高兴。萨满法师敲鼓,舍沃克神也高兴。猎人们趁舍沃克神高兴,把灰松鼠——最好是尾巴带白尖的灰松鼠皮——在火上抖几抖,神会赏赐给他们更多的松鼠。
歌声越来越大,夹杂鼓声。篝火边上跳舞的鄂温克人的袍子被火光映照得十分鲜艳。我沿着河往那边走。走了几百步,被柳树挡住路。鄂温克人脸庞清晰,被火照成红铜色,舍沃克神看到会更高兴。河流在我眼前静止不流,也许停下脚步看歌舞,也许水深无澜。大颗的星星浮在河面,仿佛来自对岸。星星优雅地泡在水里,我替它们说凉快太凉快了。星群当中应该有大熊星座。鄂温克人敬畏熊,他们管公熊叫爷爷,母熊叫奶奶。现在大熊星座的爷爷奶奶们在河里洗澡,鄂温克人在篝火边上跳舞,河水一动不动。灰松鼠在树林里偷窥,把白尖尾巴藏在树叶里。
大自然从来没停下过脚步
寂静统治着山林和草原。早上,曦光而非太阳本身从东山洒过来,被山腰的一缕雾隔离,如罩金纱。金光到来之前,长满樟子松的山峰被横绕的雾截成两段深绿,中间是不移动也不消散的白雾。没有汽车,水泥公路显出宽阔笔直,越来越窄地消失在高处。
寂静啊,黑黝黝的樟子松一群一群地站在浅绿的、带一些明黄的草地上。有几头牛吃草,穿雨衣的牧牛人身子一动不动,转动脖子看我跑步。我挥挥手,他立刻低下头,羞涩。四周没有声音,万物好像都在用形态和色彩对话。山丘浑圆深绿长满松树,草原平坦带有娇嫩绿色,林场的红砖房顶砌着灰色的高烟囱,公路的路基两侧堆着青色的碎石。蓝天全体瓦蓝,没有灰云尘霾。在这里,万物互相注视,它们彼此打量了好多年。而电线杆子始终站在公路的北侧,始终是这样。脚下的水泥路面清晰地印着一排动物足迹,有婴儿拳头那么大。那是水泥未干的某个夜里某个动物留下的,它不知什么叫水泥,更想不到它的行踪可以永远放在这里展览。我觉得公路就应该这样,水泥刚浇筑的时候,让猫狗、母鸡、猴子和驴在上面走一走,显出生气,证明这地方不光有人,还有其他动物。土地不光属于人,还属于所有生物。再凶残的动物也不会出卖土地。地是卖的吗?地不是人和动物刚学习走路时走的地方和他(它)们死后掩埋的地方吗?怎么能像黑奴一样被卖来卖去呢?这些话,说给动物听,动物也听不懂。
山腰那条轻纱的白雾,已经降落到山脚下,更薄了,好像一条棉胎被灌木丛刮烂了。太阳升达山巅,大地现出庄严。白桦树干染上金红色。它们刚還像拥来挤去的少女,现在像一队谛听唱诗的男童,面对上帝,神色虔诚。
阳光如万道金蛇从草叶下面爬向远方。这种金里透红的绿,如上天把珍贵的颜料不小心泼在这里,这么纯而鲜艳,让人不敢上去踩一脚。上帝就这么慷慨,每天都把万丈金光洒下来,第二天还洒,毫无吝惜。在森林和草地才能看到这样的金光。对浑浊的城市,太阳只给了一些光,而没有金光,因为那里没有森林和草地。人喜欢讲条件,其实万物都讲条件。人让地倒楣,地让天倒楣,天让人倒楣,反之亦然。人损地,或地损人是一个循环。这些年,人不明白老天爷为什么常常发脾气,降暴雨乃至造出冰冻灾害。这正像老天爷不明白人为什么在大地建造太多的水坝、水库,开矿和砍伐森林。两方面都不明白,没建立对话机制,人过分了天就过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并不是谁管谁,法是顺从尊崇,是循环。顺天则昌,逆天则亡。那些柔软的小草,清澈的小溪和可怜的动物的背后都有一个大力量为它们撑腰,它叫道。
来阿荣旗林地草原,最深的印象是静,正如最多的色彩是绿。草太深了,一尺多高,把小河汊子都藏了起来,听不到什么机器车辆的轰鸣,也没有大到高音喇叭小到MP3的噪音。草站在那里,树站在那里,山不曾移动,让人觉得这是一幅静态的画。
然而,大自然发生过一切事,生生息息,却像什么都没发生。太阳出来之后,露水消失了,草在风里前仰后合,弄出有深有浅的旋涡。水泥路上,一只大甲虫自负地向前爬。我看它,它站下来,好像要跟我比一比。我比不过它,我背上没有孔雀绿的荧光壳,没有精致的六足。小鸟低飞下来,钻进草里不见了踪影。林中突然飞出一群鸟,在空中打旋尖锐啼鸣。桦树叶还在风里抖动,像女人在风中扯紧领口。大自然从来没停止过脚步,它的语言不是声音是生命。
(责任编辑 高颖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