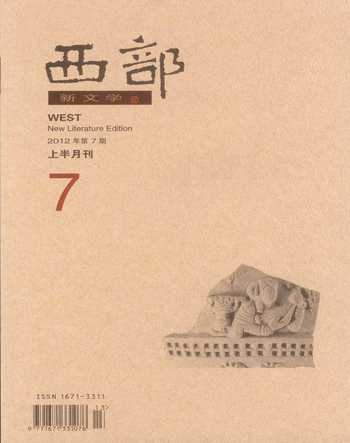托马斯·温茨洛瓦诗选
2012-04-29高兴
高兴
一首有关记忆的诗
你在等待那离去的人们?进入
他们离去的深处。墙壁背弃了
他们,如同照片,铅笔,钟表
和灵魂,雨和报应,沙和雪,
还有松针,征服死亡的胜利。
此刻,谁是谁非早已难以说清,
当你数点所有这些分离时,
你漫无目的的总数自内爆炸,
分裂成各种声音,激烈搏斗。
这些事物停驻:刀画出的圆圈,
书架上的尘土,盘子上的污迹,
如此充裕的自由、诗句和虚妄,
如此匮乏的可以信赖的命运。
两个声音同样留下。它们触摸
城市温暖但又令人不安的体积。
他们被赋予一滴记忆。
那是你的。它不属于任何人。
它在随意奔走,挥动着羽翼,
天生盲目,就像被抛出巢的
燕子。而你所有的古典主义,
那所玩笑和庆典学校,又值几何?
就这样,时间同我们所有人分离,
被判死刑,披巾般飘扬
飘进楼梯、走廊和屋子,
落在裂缝上,它,目中无人,
在来来往往的时间中间,蔓延。
致一位年长的诗人
雪,融化在阳台上。磨损的丝料下,电光
在墙上投下影子。他们中,一位触摸了一下
雕像——其他人,抵达相反的方向,
试图将身子探出窗外。“瞧——两行好诗。”
就是这将我们聚到一起。而对于其余,
我们的目光不同:墙垣边哭泣的柳树,
红石露台,
夏日沙滩水沫边缘。是的,在我内心,我
发现了你对韵律的尊重,对放逐形式的
内容的怀疑。
可我同样记得:我们之间的距离在怎样
持续地增大,虽然我们围着寒冷的公园
走了一圈又一圈,虽然我们坐在
纳罗奇湖边的草地上,抬起头,望着云朵
绘制的破碎的地图如何在天空舒展和瓦解。
而这一切,我多么希望自己已不再记得。
那并不容易。在我将近十五岁时,
我觉察出你的弱点,有些你也想剔除,
另一些却令你自豪。正因如此,
我学会了呼吸阿尔卑斯山上稀薄的空气,
学会了坐在卡车后面旅行,学会了在雨中
划火柴,学会了煮劣质咖啡,也学会了
自省——
所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确保我们的
声音和笔迹不会相同。然而,你却比我
懂得更多:
关于边境哨所那边的疆土,关于地平线一般
标明我们的行动的世纪;兴许,甚至关于
死亡(你们一代
离得更近)和选择了
你我的语言。关于音节,句式,重音。
直到今天,我还听见你说:“遥远吗?
一定是的:遥远。”
仿佛人类的拯救依赖于它。然而,那时,
兴许,正是如此。
你会一遍又一遍重复:“当我不在人世的
时候……”可你并不相信。
像所有人一样,你害怕消失。像其他人
一样,你期望
书籍起码能为你确保一个二流的
永恒。兴许,你意识到,即便书籍也会
背叛你——
可为时已晚。你没有反对过你的时代。
“一个遵守交通规则的驾驶员,你怎么能
指责他呢?”当然,有些日子,你会突然
从意识中唤醒。有些友人
还在铁丝网背后。你曾帮助过他们中的
一些人——你说他们
并不记得你的善举。你像你的同时代人
一样生活过,
兴许,更加言行一致——因此,我想轻轻
地启动嘴唇,
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在你离去时没有说的话:
主啊,愿他们安息。愿他们再也没有噩梦。
愿永恒的光照耀他们。犹如矿井中的灯盏。
这些日子,你很少出现在我的梦中,
可有时,你却会。我们俩都在赶往火车站,
踉跄着,奔跑着,来晚了。我站在月台上,
火车
随时都会开动。我必须找到你,
可我明白我找不到你——你耽搁在什么地方了,手提箱沉重,
通道犹如迷宫,太多的台阶。然而,只要我
跟从你那脚步的回音,你那不稳定的呼吸,
你那胸口的疼痛(我有时同样会感到),
你就依然活着。
不管我多么使劲地想要抵制,你的动作
在我身上延续着。你那抑扬顿挫的声音
在我陌生的演讲中重新响起。在你渐渐
萎缩的时刻,
我也变得越来越小。总有一天,我会在
车站醒来,
看见你。悬挂于车厢后面的灯盏
将会晃动,火车将会开动,提速——可
我们却依然站着,
谁也不看谁,疏远,却又相似。
乌祖彼斯*
在欧椴树的喧嚣下,在石头堤坝的
前方,在一条似台伯河的激流旁,
我喝着杰尔彼酒,同两位老人坐在
一道。暮色中,酒杯的叮当,烟雾。
我们从未谋面。我只认识他们的父辈。
一代又一代。录音机在啭鸣,发出
吱吱的响声。两位对话者渴望了解
我曾经考虑过的问题:苦难和仁慈
是否还有意义;丢弃规则,艺术是否
还能生存。我与他们相同。天意却
给了我奇怪的命运:这,自然并无
什么优势。我明白邪恶永不会灭亡,
可人们起码得有所行动,力争消除
盲目。而诗歌显然比梦幻更富有意义。
夏季时光,我常常在拂晓之前醒来,
毫无畏惧地感觉到,时间正在悄悄
临近,那一刻,其他人将继承词典,
连同云,废墟,盐和面包。而自由,
那宝贵的自由,是我将要获得的全部。
*维尔纽斯附近地区,在立陶宛语中有“对岸”的意思,1997年这一地区宣布成为独立共和国。
忒修斯离开雅典
一位老人,在城门旁的沙地上坐下。
雅典比克里特岛,更早地迎来黄昏。
渐渐浓厚的影子,在临死挣扎中,贴紧
那酷似弥诺陶洛斯的脚,它的内脏
已被青铜剖开。那野兽是一名戴着皇冠的
妓女和一头公牛生下的后代。它专饮
童男童女的血来保持旺盛的精力。迷宫中
处处都是它抛撒的污物。最后,被剑击中,
它才一命呜呼。有人认为,那公牛是波塞冬
众多外形的一种,据此,人们推断,那是
两兄弟在搏斗,因为凶猛的海神同样是
胜者的生父。在花岗岩洞里,当迷宫
在百般曲折中展开,就像一根烧焦他的
棕榈树的线头,我们的英雄忽然意识到
这一点。
所有那些他杀死的生命,包括野兽,
都是兄弟。
老年凝聚起空间,松脂般将它牢牢地粘合。
外面,远处,他看见山丘,原先陡峭,如今
已被时间磨平。他曾路过那里,从特洛曾
到那座闻名遐迩的城市,那座本该属于
他的城市。
像坦塔罗斯(他的一个祖先)一样,他也渴望
整个宇宙:橄榄园,月桂树,
葡萄园和人群,大理石块形成的
阴郁而又荒凉的峭壁,四面体的
未完成的围墙粗劣的神殿,红发福波斯
在深蓝色的大海上空驾驭的辉煌的双轮
战车。
美女的身子,透过半透明的衣裳,隐隐闪现,
那私处的软毛听从他的触摸……
醒来时,他沉重的眼帘粘在了一起。
他踏上那最长的小径,欢欣鼓舞,一路
清理着
那片被诅咒的土地,那片狼和蛇的后裔的
土地。
他们也是他的兄弟,普罗克汝斯忒斯也是。
老年,听上去很怪,仿佛普罗克汝忒斯的
睡床。
命运不再能掌控你,可它却又超过
你渐渐衰弱的力量。怪梦重现,比记忆
更加生动,常常,生发出极度的苦痛。
有人正离开宫殿,一去不复返。
听不见脚步声。瑟瑟作响的大披肩。是
菲德拉王后?她拥抱着黑色的沮丧之光。
是她的姐姐?一个狂怒的神已将她霸占。
还是珀尔塞福涅?他曾降临她的王国,
可满眼所见尽是芦苇和潮虫,蛞蝓和蜗牛,
湿滑的地下斜坡和四处游荡的灵魂。
虽然影子难以相互辨认,可也许
有一天,在他们中间,他将看见菲德拉
和他那被马蹄碾碎头颅的儿子。
萨拉米斯附近,一叶孤帆在同风搏斗。
众神在掷骰子,而凡人却必须满足于
悔恨,宽宥,理解的愿望。
他同苦涩的命运达成了协议。他装饰
城市,祭奠死者,迎候
异国盲眼的国王。他命令点燃
泛雅典娜节的火炬。即便在他死去时,
新的神殿、纪念碑和花园也将拔地而起。
可他们
也会消亡。他不时地听见一个
声音,比上帝的声音还要响亮,那声音宣布:
“你已鞠躬尽瘁。”在雅典城门旁歇息的时刻,
他渐渐领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
那必然发生的一切终将逝去,用不了多久,
里刻墨狄斯将把他推下悬崖,正如先前
他对斯基隆所做的那样。
奥蒙德码头
——献给谢默斯·希尼
海雾,在都柏林上空的四月聚拢,
打湿砖头、花岗岩、乌黑的汽车
薄膜。退潮后的河床满是泥沙,将一片
裸露的浩瀚置放于桥下,空空荡荡,如
一只张开的手掌。这座泥泞的岛屿经历过
饥荒,纷争。二十年前就像利菲河一样浅,
可现在,黎明时分,当它在卡车的呻吟中
醒来时,河水又一次达到或超过了
高水位线。一只海鸥,哀鸣着飞入
货栈之间的裂缝。人行道破裂,潮湿。
塔楼旁,河湾借助雨滴、树枝、时间
在喃喃低语。但并非我们教会了它言辞。
青铜和黄金。楼梯陡直,面包发苦,
可报酬支撑着。码头角上,你看见
那著名的塞壬栖息地,人山人海,一位移民
诗人正为他在酒吧里的双重影像干杯。
全都一样。褐色的北方沼泽地;蓝色的
爱奥尼亚海岸,人们已倦于朝它划船。
皱裂的旧地图,如喀耳刻之床,正在扩展:
无家的欧洲用一条粗糙的床单将自己掩盖。
侍女图
有九到十一个人物,包括
小矮人,侍女,那面幽暗、敏锐的
镜子中的影像。还有那位尚未
开始作画的画家——四百年后,
那幅画还在耐心地躲避着我们的
目光。傅科假设画家正在
画我们。不过,更确切地说,模特、
观者和画家兴许全都是一个原型的
片段。比任何时候都更充沛的
光穿过窗口(并且,就像在天堂
那样,它的善行照耀着
所有的不完美)。而那道无形的凝视,
停留于所有的凝视汇集之处,
画笔会教我们如何将它保存。
六节诗
大约六点时分,冰雪之路
突然转向北方。防滑链,捆绑于轮胎,
在路上咯咯作响。一种不中听的钢铁的回声,
仿佛湖面,闪出一个倒影。
失重的三月雪,承受着伤痛,
依然试图覆盖那被毁的森林。
静止的森林,木筏般裂开,
目光蹒跚。路,多层自我复制的雪,
和一连串单调的白桦
令它沮丧。雾霭中,井的杠杆
升起,反射出那座空房子。
而其余的一切,都是回声
和凝结的空气。漫无目的、无家可归的
回声,并不存在的回声,轰隆隆穿越森林。
变得脏兮兮的石墨镜子,反射出
过度的黑暗。我们被赋予一条路
和在天空诞生、在天空成熟、在天空被
放逐的铁链:
那无形的,却吞噬一切的雪。
在雪的凝视下,年老的春天倒下,
听觉被多面的回声撕裂。
一丝盲目的思绪,像堤坝,奋力
挣脱铁链,渗入森林。
这里,汽油无济于事,白色的路,
那块展开倒影的空地,同样如此。
不成样子的宇宙倾泻着自己的倒影。
一颗颤栗的星,那片冲动的雪
围困原野,为路武装起自己。
倒影,影子,复制品,回声
再次充满重重跌倒的阿登森林;
它们的变化形成那唯一的铁链。
我们会被你的铁链锤打吗?
所有事物和元素升起,反射出
我自己。我将抛弃这座阴郁的森林,
那里,雪为树披上斗篷,守护着它们,
词语托付给一种无益的回声,
一切的一切临近尾声。兴许,路
本身就是铁链。我没有获准得到进入
森林的路。大地已被雪麻木。
我们是能照出影像的敌人。你的艺术,
一个回音。
虽然那井深不见底,又陡峭危险
写首诗,谈谈与鸟儿的对话。
——摘自一封信
虽然那井深不见底,又陡峭危险,
金黄鹂,芦苇,人,星辰
还是有勇气窥望辉煌的深处——
被难以预料的关系统一的深处。
时常,一面探测棱镜折射一道光,
看起来全都一样。
依照歌鸫那银铃般的诡辩,
真理和尘土,它们又有什么区别?
黎明之前,当夏天临近尾声,
当穹顶四散,世界轰然倒塌,
那同一股隐秘而无形的力将你击中,
让你,一把脆弱的里拉,突然发出声响。
纪念一位诗人。变奏
在彼得堡,我们会重新聚在一起
——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
你可否返回那曾经的应许之地,
返回城市的骨骼、倒影和痕迹?
一场暴风雨扫除了海军军部,
几何图形的色彩渐渐变成阴郁,
浮上表面。
切断
电流,一道影子从冰的光谱中
升起,锈迹斑斑的蒸汽机,犹如幽灵,
在伊泽梅洛夫大街中上升,显现。
一样的有轨电车,一样的褴褛衣衫……
沥青路,让碎纸片飘浮
在它的上方,而十九世纪的寒冷
湮灭了火车和车站。
悲恸的天空
将自身关闭。数十年化为雾霭,
阴沉的城市掠过,就像风暴漂流,
动作总在重复,恰似一份礼物,
可死者中不会站起一个人。
他隐身于二月的早晨,
围绕着罗马,缓慢地,朝着北方,
进入另一片空间,选取一个韵律
接近雪的时刻。
他被召唤到此刻已冻结的母狼之穴,
精神病院,肮脏的监狱,
黑色的、熟悉的彼得堡,不久前
从某人的言语中升起的彼得堡。
不是和谐,也非尺度,一旦遭到压制,
便会回归生活,也非爆裂声,也非
壁炉内的味道,时间已完全将它点燃;
然而,还是有永恒的、壁炉般的焦点
和眼睛,绘图命运,其本质
就在于幸运的巧合,
抑或就是那既非暂时之物
也非本土之物的会合和持续。
没有影像,只有一道裂口在已知物中,
一座岛,发展成潮流的泡沫,
找不到的天堂,它的替代品
在活生生的语言中上升。在云的
阵雨中,在漂浮的船首上方,
鸽子们绕着大圈飞翔,并不打算
去区分阿勒山和任何平凡的
鲜花盛开的山丘。
时辰已到。离开这海岸吧。我们将上船。
谎言已经耗尽,石头已经裂开,
只留下一个见证:艺术,
将光带入寒冬深处的夜晚。
被祝福的草木战胜冰,
河口在夜晚找到了海湾,
而一个词,毫无意义,如光,
回荡着,几乎同样毫无意义,如死。
阿喀琉斯之盾
——给约瑟夫·布罗茨基
我言说,只是为了能在神经的
屏幕上,在生动的色调中,如你那样,
看到石头小教堂附近的栅栏,
倒干净的烟灰缸边上的钥匙。
你说得没错:全都和这里一样。
甚至包括那想象的容积。
一样的距离,抵达海洋,
在夜晚倾听
我们的海洋。在叶子屋顶下,
那些沉重的灯在照耀时,多么相似。
乐声中不同的节奏
意味着危险要多于将我们
分开的苦涩的浪。退入空间,
你变成一名陌生者,就像米提亚人
和希腊人。我们留在这艘船上,仅仅为了
遇见耻辱——
因为这不安全,即便对于一只老鼠也不安全。
打量一下它吧:这根本不是一艘船,
而是闪耀的顶棚,灾难,墙,
日期,一切都在过快地重现——
总之,是成熟的时代。它的监护
渗入骨髓,它的空间,
每天都在制造更多的垃圾,将模糊那目光,
如果,在边境旁
(沉思的土地,等候笔直的雨),
庄严的声音拱门,几乎在这意外的
夏季遭到摧毁,不再升起,
却呈现给我们兴许同灵魂相符的
神圣的锁链——
它们会污辱、限定、提高形式,
因为我们的重重天空,我们的坚实的土地
仅仅是声音。
愿你平安。愿我和你平安。
让黑暗存在吧。让瞬间跌倒。
透过密集的浩瀚,透过层层睡眠,
我劈开你的词语,通读一遍。
城市消失。只有一副
白色的盾,替代自然,重于
非存在。我们的时代将当着它的面
被消耗殆尽
(要是力量和时间并不如此吝啬,那该多
好!)
就像在水中。或者,确切地说,
就像在虚无中。巨浪击打,
扫除生活情景。窗子
在黑色广场上闪着光亮。梦里,
炎热的空气缓缓地过滤着玻璃。
远处,塔楼那边,尖叫声响起
一辆摩托,让时间
从我身上滚过。不时地,人们在黑暗中
可以看见:你看见一只钟在摇曳,
你看见一段无边无际的间歇在磨损,
而这时,基础在默默地回答。
受到重创的大门在颤栗,绷紧,
拱门向邻居发出信号,
而灵魂和大陆,在呼吸的夜晚中,
彼此召唤。
脏兮兮的雾紧贴着码头上的帆船。
潮湿的岸变得温暖,还有云和蒸汽。
你看见塞莫皮莱,以及你见过的特洛
伊——
你已得到一副盾。你是一块岩石。
柱子,挺立在坚韧之上,
将闪耀的金属插入风,
虽然它离僵硬或虚假
并不遥远。
把所有的命运交托给我们,
你走进回忆的高原。
但每一时刻,都以片段加倍增长,
而成双成对的光,成为我们的伴侣,
在一个渐渐缩小的圆圈里。
低潮。沙滩缀满闪烁的水坑。
空荡荡的海岸上,那只眼睛依然
无法区分石头和舵。
闪出一缕微笑,站定
闪出一缕微笑,站定,然后打道回府——
窗外,黑暗试图掠夺视力,
可那音节,在我的舌上复活,
依然会祝福,并替代这一年中最漫长的夜。
闪出一缕微笑,因为我们远远分离,隔着
平原、冰湖,风雪,密不透光,
窗帘,仿佛侵入你大脑的睡意,
还有黑黝黝的火车,从陶格夫匹尔斯到卢加。
厨房里有冰凉的泉水,出口处已经干涸,
几张椅子四处散放着,就像稀疏的森林。
我也已坠入梦乡,而这幢房子的意义只是
一个邮政地址,一张带有调音指孔的唱片。
我也已坠入梦乡;仿佛从桌上
抓起电话筒。逗留会导致毁灭,
因为,剩下你我相伴,醒来时,我能
听见自己在另一头,当我停止敲击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