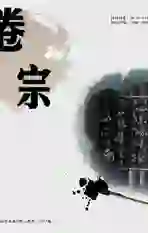人格的“如果—那么”理论:重要他人与关系自我
2012-04-24张艳
张艳
摘要:关系自我:一种人际关系的社会认知理论,以移情的社会认知加工理论为基础。
在普遍的社会知觉中,重要他人的重要性,以IF–THEN的人格模型为基础,提出人格的认知情感系统(cognitive-affective system)理论:概念化情境(reconceptualizing situation)、气质、动力和人格结构中的稳定特征以及他们的早期经历,以证明自我原本就是人际关系的。
由于我们已经显示对重要他人的心理表征是由特定情形下即时启动线索所激活的,而这种激活又影响了人们所体验的、所表达的自我和人格的特性,所以这一过程将IF–THEN法拓展至人际关系的动力水平。
除此以外,我们的模型还将社会认知和学习理论以及心理动力思想相整合,引入到人格的概念化领域,人格概念化强调情境的重要性。
1.引言
通常人们认为一个人很容易被视为一个拥有整体特质的人,这些特质不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Mischel认为这一假设掩饰了人格的复杂性。他认为人格具有复杂性:跨情景的稳定性与不一致性。
个体的行为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原因:内部状态、心理表征和理解这些一系列内部因素通过情景引起行为的变化。(Mischel, 1973, 1977)in situ(情景研究)研究已有所证明。
in situ——通过改变个体生活中的情景,引发个体对特殊情景的理解和其中的特殊行为来研究认知情感理论及方法。预测和改变人类行为的本质就是情景中的刺激,这些刺激能喚起特殊的行为,引发个体情景与行为间的特殊共变。
人格的认知情感系统模型是一种IF–THEN理论,即IF指(给与个体的)一个情景或一个具有启动线索的背景,THEN指反应(包括心理体验与可观察到的行为)。
我们通过呈现移情和关系自我的社会认知模型,重点强调IF–THEN框架。研究关注对重要他人的心理表征,以及检验了无论这些心理表征是否被激活,它们是如何影响时时刻刻的反应的。当情景中的启动线索激活了一个重要他人表征时,那个人所展示的那些线索将被理解为和那个重要他人一样。
当情景起作用时,表征被激活。事实上,重要他人表征具有一个相对更高的可及性激活基线水平。也就是说当情景中的线索不足以唤起对重要他人的表征是,表征仍然被激活。(Andersen,Glassman, Chen, & Cole, 1995; Chen, Andersen, & Hinkley, 1999;Higgins, 1990).
除了这些情感因素,相对动机对重要他人的表征也受自我的影响。结合可及性与重要他人表征的使用,情景中的线索说明了自我体验中多变性。
关系自我与移情模型是以对精神分析中的移情概念(Freud,1958, 1963; Sullivan, 1953)的检验为基础,作为社会认知中的概念(Andersen & Chen, 2002; Andersen & Glassman, 1996; Chen& Andersen, 1999),是之与经典的人格理论相关,同时也提共了一个将认知情感系统模型与心理动力学思想相结合的方法。
2.移情与关系自我
在移情中,当一个新来的人在一些小地方与一个重要他人相似时,将激活此时对重要他人的表征。这些相似处包括这个新来的人的人格特征如兴趣、习惯、信念、交往方式、快速表达或一些生理表现。当重要他人的表征被激活时,表征也倾向于被应用到这个新人身上,这表现在人际交往知觉中的情感转换和反应。(Andersen & Baum, 1994; Andersen & Cole, 1990).与重要他人相关的线索与储存在记忆中的有关重要他人的记忆相结合并影响着与新来成员的人理解和反应。
简言之,对于新来的这个人,我们除了对他的一些真实了解外,大部分关于重要他人的表征的其他方面随后都被假定对这个新人也是真的。这也是移情的估计成分。当一个新人与一个被认为积极的、可爱的重要他人相似时,这个新人被给与积极的评估。(e.g.,Andersen & Baum, 1994; Andersen & Cole, 1990; Andersen et al.,1995; Chen et al., 1999).移情过程也是一种潜在的、没有意识的。(see Andersen, Reznik, & Glassman,2005).
个体与重要他人的关系最终成为了重要他人和自我表征的一种记忆上的联系(Andersen & Chen, 2002).我们关系自我的模型关注的是重要他人的表征是如何与体验他人的自我相联系的,以及自我是如何间接地在重要他人激活(被线索激活)的基础上被激活的。
间接地引起自我-他人表征并不需要重要他人本人出现,任何与重要他人有关的线索都可以激活表征,然后间接地激活记忆中与重要他人相联结的自我形式。在这一过程中,自我就变成了与重要他人相关的自我。而且,重要他人关系的一部分:动机和目标也能激活对新人反应——自我暴露。当重要他人的表征要被激活时,预先了解一个重要他人所接受的和所厌恶的内容同样能阻止这样的激活。
3.学术背景
3.1历史根源:心理分析中的移情概念
移情在精神分析和精神分析理论中是一个中心概念。(Freud,1958)移情最初被定义为心理分析中病人在分析师的帮助下重新体验无意识的性心理愿望以及早期童年冲突。(Freud, 1958, 1963; see also Andersen & Glassman,1996).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的性本能是移情的力量来源,并承认移情能够发生在治疗以外的情景,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致性。
我们的研究更直接的受沙利文的“并行失调” parataxic distortion(转移性曲解)影响,沙利文的移情中,自我的人格化(与心理表征相连)和重要他人的人格化通过精神动力(“dynamisms”)相连(联结自我和重要他人的关系)。(Sullivan, 1953).人格化和精神动力形成于与重要他人的交往活动的体验中,而非纯粹的本能。因此,沙利文的模型与我们所关注的重要他人的表征更为相似,这一表征与记忆中的自我相连,并且当表征被唤起是影响着人们的知觉和行为。
沙利文抛弃了弗洛伊德性本能的假设,认为人们有其他基本需求:满足、保持与他人联系等等。他认为,并行失调很大程度上是受与重要他人交往中所产生的动机的影响,因为人格化和动能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些需要时如何被满足或不被满足。沙利文的动机概念与我们相一致,甚至我们所提出的人类基本需求在某种程度上走得更远。(Andersen & Chen, 2002; Andersenet al., 1997).沙利文认为移情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发生。
沙利文的人际关系模型与客观关系投射理论(object relations theory)有很多相似,前者更关注人际交往行为与一个人如何被对待这一现实,后者更加关注性驱力和幻想。客观关系投射理论假定某些与重要他人的心理表征相似的事物——外部世界的客体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渐渐内化。在投射识别中,这些客体被投射到其他事物。客观关系投射法大部分关注的是治疗中的移情,但也为否认日常中移情的存在。
另一个相关模型就是依恋理论,假设人们的思维、记忆、信念、期望、情感、自我的行为等都受到与重要他人交往的影响,并形成一个内部的工作模型,这个模型被用来处理后来与朋友、配偶、孩子的关系。(Bowlby, 1973).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早期关系将影响后来的关系。
早期的移情是理论的而非经验的,很少得到科学心理学的赞同。定义多变。我们采用的一般定义:对当前个体不适当的感受、驱力、天都、幻想、防御,这是一种源于对重要他人早期童年经历的反复的,取代性反应。
3.2人格的认知及认知行为理论
对移情概念另一方面的考虑就是凱利的人格建构理论。在这一模型中,人们将他们周围的世界以具有特异反应性的形容词法分为自己和他人,这种建构式每个人理解、决策和行动的媒介。凯利认为,重要他人是个人建构形式的中心,因为每个人都形成了一些以形容词为基础的建构模式,其功能就是定义特殊的重要他人之间或与自我之间有何相似又有何不同。Mischel的社会认知学习概念重建(cognitive social learning reconceptualization)假设个人的这种建构与认知是一体的。Mischel的模型通过明确定义这种建构发展了凯利的理论,如要求定义基本社会学习机制。在Mischel模型中,情景刺激激发了个人建构、期望、编码策略和自我调节我们的移情与关系自我模型是以凯利的人格建构理论和Mischel后来的认知情感加工系统为基础。同时我们的模型还结合了心理分析、行为主义、认知行为学,虽然在本质上是一种认知模型,但它仍依靠基本学习加工和心理动力学思想将自我和重要他人相连,并将动机和情感引入特殊情形。
3.3以人格原型为心理表征
米歇尔的人格原型理论也影响了移情范式的发展。早期研究利用一种记忆再认范式发现,人格原型可以被用在新人所给信息以外。重要的是,特质能影响人们在理解他人时的潜在人格假设。研究发现,以形容词标记的表征被视为一个人的特殊特征或某类人,而用名词标记的表征被试为人格整体,并且前者没有后者那么丰富、那么就有独特性,很少被用于加工。
这些证据引出了假设:重要他人的表征应该是那些在记忆中具有丰富表征且具有独特性的表征,这为刺激编码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这一效应通过使用各种控制条件已经不断被重复。研究也检验了各种各样的关于移情的情感、动机和行为方面的假设。(e.g., Andersen & Baum, 1994; Andersen,Reznik, & Manzella, 1996; Andersen et al., 1995; Baum & Andersen,1999; Berenson & Andersen, 2006; Berk & Andersen, 2000, 2008;Chen et al., 1999; Glassman & Andersen, 1999a, 1999b; Reznik &Andersen, 2007).
3.4气质与人的独特性
使得个体具有独特性如CAP中的人格识别标志,已经是人格概念化得焦点,(Allport,1937; Kelly, 1955; see alsoHiggins, 1990)。这也就是说在对个体进行理解是出了一般规律外,特殊规律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的研究中,即使激活表征并将之运用于新人这一加工过程是普遍的,但每个重要他人的表征都是独特的。(Andersen & Chen, 2002).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采用特殊——一般规律研究法。
4.移情和关系自我加工的证据
4.1 程序开端
移情研究通常是两部分范式。
首先,用包括等量的积极项和消极项(每项含2-6个词)的自我生成的句子对重要他人进行命名和和描述,然后对这些项目进行等级排序。其中有些特征是对重要他人的典型描述,如喜欢,厌恶,兴趣,信念等等。然后将这些项目与一些无关项目混合,并在随后的实验中使用。
被试随机被分配,并了解一个新人,这个人要么符合所被试所列出的重要他人的特征,要么不符合。在实验组中,新人和重要他人有些相似,而在控制组中,新人与其他被试的重要他人相似。这样,在实验组中,被试会产生移情,而在对照组中不会。
4.2移情与记忆
最初的移情研究主要是要检验一个已被激活的重要他人表征是如何在记忆中被反映。例如在记忆再认范式中,被试参与一项关于新人的填空游戏,要求使用他们以前的知识。(adapted from Cantor & Mischel, 1977).我们的研究用重要让人表征来表明。也就是说,当知道一个新人与一个重要他人有些相似,人们就可能推断这个新人也就有重要他人的其他特征。
这一效应甚至发生在当人际交往刺激在潜意识情况下存在时。(Glassman & Andersen, 1999a)加工并不要求个体对唤起移情的刺激产生意识。也不需要人们的努力,是不受控制的。如自动的(see Andersen, Moskowitz, Blair, & Nosek, 2007),能够持续一段时间,至少一周(Glassman & Andersen, 1999b).这说明了移情是一种非常普遍而非人为化的效应,能影响对自我在无意识情况下对他人的印象。
由于这些发现,很多潜在的实验人工化都已经被排除,如有人质疑被试自我生成的特征是否能解释这一效应。(Greenwald & Banaji, 1989).当自我产生刺激词时,可能导致对这些词记忆的增强。由于实验组中的被试所面对的特征本身就是由他们自己生成的,当表征是重要他人时,移情和记忆效应相对于其他表征就要强。(e.g., Andersen et al., 1995; Glassman& Andersen, 1999a).
无论表征的效价如何,即,在个体眼中无论重要他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一效应都会出现。(e.g., Andersen & Baum, 1994; Andersen et al., 1996; Hinkley & Andersen, 1996).无论是自我差异的类别(如,是否受父母虐待,近两周内是否抑郁),无论个体差异(特殊情感、动机反应)这种效应都会出现。(Reznik & Andersen, 2007).
4.3 估计与面部情感
当重要他人的表征被激活,对重要他人的整个估计也被激活了。这就好像是“图式启动效应” (Fiske & Pavelchak, 1986).如果人们遇到的这个新人与一个积极的重要他人相似,人们就会对新人做出积极的估计比与消极重要他人相似更积极的估计。(Andersen & Baum, 1994; Andersen et al., 1996;Berk & Andersen, 2000).
事实上,当重要他人被认为是积极时,应该存在着一种直接积极情感反应,并有证据支持。当一个新人与一个积极的重要他人相似时,这时会在面部表达中唤起更多的积极情感。当一个新人与积极或消极重要他人相似时,直接面部表达反应了对重要他人的的整个情感,并对新人进行再体验。这种相对的直接反应可能会反映移情中的自动评估。(Bargh et al., 1996)
4.4期望
通过研究表明,对重要他人是一种认可的期望还是一种拒绝的期望也会在移情中被激活,并通过移情反应在新人身上。当重要他人是积极的,与之相似的新人就可能会更期待被接受而非拒绝。(Andersen et al., 1996; Berk & Andersen,2000).
4.5交往行为
与重要他人的交往习惯在移情中被激活并在对待新人时有所表现,事实上,这是唤起了一种自我实现预言——行为证实。新人将会渐渐变成他所期望的那样。而有实验表明,人们并非由于有意产生期待行为,这种效应是在无意识情况下产生的。
4.6动机和目标
与重要他人相连的动机和目标是与表征一同被储存在记忆中,因此当重要他人的表征被激活时,与之相连的动机和目标也被激活与应用。例如,在移情中,新人与积极的重要他人相似时,人们将产生更多与新人接近的动机,并在情感上更加开放与更加愿意袒露自己。而当新人与消极的重要他人相似时,人们会避免这样的亲昵。(Andersenet al., 1996; Berk & Andersen, 2000).
另外,当一个令人喜欢的重要他人老是拒绝你的要求,情感目标将得不到满足,关于这一关系的事实将毫无疑问被储存起来。(Berk & Andersen,2008).因此,当这样一个重要他人在移情中被激活时,积极情感将被破坏,取而代之的是疏远的动机。事实上,当新人与不能满足个体情感动机的重要他人相似时,人们会对新人产生更多的敌意。但是,当这种重要他人是个体的亲属时,在移情中所表现的敌意越多,人们对新人表现出的却是更多的接受和喜欢。这是由于亲属关系较为稳定,不易被破坏。人们会在移情中继续的寻求与重要他人有关的未能实现的目标。但这种情况仅存于亲属关系。
有证据证明,当重要他人表征被激活,各种目标(不仅仅是情感目标)都被激活。前研究表明,如果要完成的目标与重要他人相连,那么启动一个重要他人的表征会影响行为的直接目标。(Fitzsimons & Bargh,2003; Shah, 2003a, 2003b).
4.7 与他人关系中的自我
事实上,个体的对自我的意识也会在移情中改变,变得与重要他人所体验的自我相一致。和每一个重要他人相处,自我都有一个不同的版本,这取决于关系的情境。例如,一个人可能很温和的和她母亲谈话,并表现的助人为乐;但在对其他伙伴时,她有表现的具有攻击性,并追求领导地位。人们不断变换着自我的形式,这与米歇尔的IF–THEN理论相一致。(Mischel & Shoda, 1995).当重要他人的表征被激活时,不同自我被激活(Andersen& Chen, 2002).
因此,关系自我在何时被激活取决于情景以及情景中的新人是否与重要他人相一致。如果相关的启动线索偶然与新人相连,那么重要他人的表征将被激活,与重要他人相连的自我将在此时变成一种可操作的自我概念。
4.7 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
在移情中,通过重要他人表征被潜在激发,不仅有效的自我概念会发生变化,而且自我调节也会被唤起。有这样的情况,当存在大量影响有效自我概念的负性重要他人特征时,处境将是破坏性的,人们将会产生自我防御、补偿性反应,作为对伤害的应答。(Greenberg & Pyszczynski, 1985; Steele, 1988; Taylor & Brown,1988)当与令人讨厌的自我形象相连的重要他人的表征在移情中被激活时,自我调节将会出现。(Hinkley &Andersen, 1996; Reznik & Andersen, 2005).在移情中,大量的负性关系自我将给有效的自我概念带来更多的积极特征,这些积极特征虽然不是关系自我的一部分,但事实上它们保护着自我意象(self-image)免受伤害。(Hinkley& Andersen, 1996; Reznik & Andersen, 2005).
而且,人们保护的不仅是移情中的自我免受伤害,还保护着某些环境下的重要他人。这种他人保护性调节(other-protective regulation)可能出現是因为有利于人们相信他们的重要基本上是好的,可爱的,而不是他们有很多缺点。因此人们在心理上将重要他人的缺点转换为巧合、令人着迷的癖好,甚至是优点(e.g.,Murray & Holmes, 1993).如果个体为了保存关系,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并得到很好的联系,那么这将可能最终自动在移情时出现。
有数据显示,在先前提到过的,移情中产生的自动面部情绪倾向于反应出对重要他人的整个情感。除此外,当被试面对一个具有重要他人负性特征的新人时,他们直接的面部表情可能变得比他们遇见积极特征时更为积极。(Andersen et al., 1996).因此,面部表情所展示的情绪似乎将特征的负性效力转化为了正性,并同时对重要他人表现出完全的积极情感。这一证据显示,自我调节出现在个体遇到拥有重要他人负性特征的新人时。这种自我调节可能能被延伸至当新人具有重要他人的负性行为或负性情绪方面。
4.8.1 以往重要他人的虐待及情绪
自我调节出现在个体遇到拥有重要他人负性特征的新人时。特别是这一线索与重要他人虐待行为有关,重要他人曾经在身体或心理上虐待过个体,个体将对这个重要他人产生负性情绪并唤起自我调节,以防止不良后果。有研究已经验证,童年时受过父母虐待的个体在移情中是如何反应的。
事实上除了在移情中产生直接的面部表情外,被虐待的个体还会表现出负性的感觉。当新人表现出与曾经虐待过他的父母相似时,个体可能会对新人产生不信任、期望被其拒绝并对其冷漠,并报告出更显著的负性情绪。然而,当额外信息被呈现——新人正在生气时,个体在移情中又会比参照组产生更多的积极情感,尽管存在被虐待情形。这一线索显示,受虐待的个体所产生的正性情绪不会比没有受虐待的个体少。如果新人与一个具有虐待性他人相似时产生这样的保护他人调节是很不明智的。也就是说,这有可能会开启另一扇虐待之门。而被试所表现出的较少的负性情绪在很多虐待研究文献中成为“情感麻木”。
4.8.2 情感中的自我标准和自我差异
另一种思考自我调节和移情的方法来自两方面的思考:个体是如何达不到重要他人所持有的标准,个体是如何体验这种来自重要他人的自我差异,以及伴随这种差异的情感弱点。在研究中,最初的目标是确定潜在的重要他人表征的激活是否激活了重要他人对个体所持有的标准以及个体真是的自我感受,这种感受通常是不同的,如自我差异、当与重要他人交往时的自我调节的焦点。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hopes about the self)或义务自我(obligations of the self)间的差异都可能促成低落情绪(基于现实与理想的差异激活)或激动情绪(基于现实和义务差异的激活)。
另外,当移情中新人的线索直接唤起了父母的标准(当新人强调他对朋友最大的希望)时,这也将启动标准的调节功能。也就是说,理想标准(如希望)与推广焦点或者与一个有效作用于潜在的收获的焦点相连,而责任标准与一阻碍焦点、避免伤害的警戒相连。调整警戒会加重激动情绪,而调整期望会推翻或减少低落情绪,与调整效应相反。在移情条件下有来自父母期望的现实理想差异的个体遇到一个唤起父母理想的线索,就会表现出一种对低落情绪的调整,而相似的线索发生在具有现实规则差异的个体身上时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激动情绪的降低。
5.未来方向
这些移情中的复杂可能性反应为人格概念化的IF-THEN关系提供了证据,也为进一步解释人类行为和人格的未来研究提供了方向。首先,重要他人就不仅仅是积极和消极之分,而是由满意水平和矛盾意象所组成,这些矛盾意象暗示了当重要他人表征被激活时个体所体验到的,这值得继续检验,并将研究延伸至重要他人所持有的标准的激活,以及重要他人的过往虐待性行为在操作中的矛盾性。个体可能爱重要他人,但他却与大量的痛苦情绪相连。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移情中的情感以及情感调节。我们也有必要研究个体是如何阻止和推翻移情过程,个体自我调节的能力。
6.结论
总的来说,我们关于自我与人格的整合模型在米歇尔的关系自我中已经有所见,他们的研究已显示出对行为中的跨情景可变性的观察以及对人们基于认知情感加工系统中的稳定性和人格标志研究。(Metcalfe & Mischel, 1999;Mischel & Shoda, 1995).我们的研究发现重要他人能被线索激活,反映出情景与个人反应在此刻的紧密联系,包括情感、期望以及对自我的体验。我们假设重要他人的心理表征被激活这一过程,间接地激活了与重要他人相连的自我,并反应出一种稳定的情感行为。同时,我们也假定被试在反应中的反应形式对于特定的人和关系来说是独特的,甚至是稳定的。以此,在任何时候所经验的自我和人格都与可及的重要他人相连。IF-THEN形式中,IF你与某个与重要他人相似的人交往,THEN你就会变成与重要他人交往的那个你。这一加工过程甚至出现在个人主义文化中。
总的来说,我们的研究揭示了重要他人对人格的理解的中心地位,特别是以情感、期望、行为和各种形式的自我。我们将心理学各个不同领域有关人格的研究结合起来,包括一个人的历史,当前情形,以揭示个体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