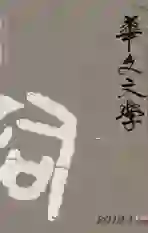“少年的我”的残酷青春记忆
2012-04-24钱虹
钱虹
摘要:近年来,美籍华人女作家严歌苓在国内是越来越“走红”了。但人们关注得较多的.往往是她那些“虚构”型文本,如《扶桑》、《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等。本文则选取《灰舞鞋》等有关“文革”题材的“穗子的故事”系列小说,从作品与作者生活经历的重合度、小说的“自传”色彩、时代的印象写真、残酷的青春记忆等方面,做了较为深入的解读与剖析,并以此凸显严歌苓有关“文革”题材小说的“印象派”版本的价值。
关键词:严歌苓;小说;“文革”题材;青春记忆;“禁欲”悖论
中图分类号:10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2)1-0064-06
近年来,美籍华人女作家严歌苓在国内是越来越“走红”了。在文坛上,她的小说接连出版,还屡屡斩获各种奖项(有关她的作品获奖名录,可参见收入《海那边》集中笔者辑录的《严歌苓获奖作品一览(1987~2010)》。去年5月在南昌举行的“中国小说节”上,她又凭借《小姨多鹤》获得了由中国小说学会的评委们投票选举的长篇小说奖。作为一位在海外从事华文写作的作家,连她本人都感到自己不再被“边缘化”了。不仅如此,在影视界,她也成了国内众多大腕导演眼中的编剧“红人”:她参与编剧的《梅兰芳》由陈凯歌执导拍竣,在海内外公映后获得了“华表奖”的诸多奖项。眼下,根据其小说《金陵十三钗》改编的同名电影由张艺谋执导,即将拍摄完成。此外,根据她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小姨多鹤》、《幸福来敲门》(原名《继母》)以及由她操刀改编自父亲萧马原著的40集电视剧《铁梨花》,也分别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并且取得了收视率与观众口碑双赢。可以说,严歌苓的社会影响力是越来越强了。然而,人们对她的作品关注度较高的,往往是她那些“虚构”与“想象”色彩较为浓厚的作品,如《扶桑》、《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金陵十三钗》等,而那些以“文革”为题材的“穗子的故事”系列小说,如《白蝶标本》、《老人鱼》、《梨花疫》、《拖鞋大队》等等,则较少有人重视,这多少有些令人遗憾。
不久前,江苏某出版社编辑发来手机短信,诚邀笔者在编选了严歌苓的《也是亚当也是夏娃》、《金陵十三钗》和《海那边》三部作品集之后,再编选一本严歌苓的小说集《灰舞鞋》,并允诺会尽快出版。《灰舞鞋》的电影版权已由导演姜文购买。或许,姜文在改编自山西老作家马烽原著的《让子弹飞》获得了2011年初票房大捷(据百度统计票房达7.24亿元)之余,说不定哪天他也能把《灰舞鞋》改编成一部既叫好又卖座的电影出来。然而,笔者对当下影视圈“娱乐至死”及“全民狂欢”的泛滥倾向却不无一丝忧虑。笔者以为像《灰舞鞋》这样的作品,以及严歌苓其他“穗子的故事”系列小说,绝不宜加些噱头噱脑的东西变成纯娱乐化的怪胎。有人曾称之为“一部颇有历史感的中国本土特色‘少女维特之烦恼”,而笔者觉得它更像是留存一个女孩儿在亲身经历从少女到青年成长过程中真切、严肃而又荒诞甚至不无残酷的青春忏悔录。它让你读后知道什么叫做沉重。《灰舞鞋》等作品,虽然写的是当年军队文工团一群少男少女舞蹈演员的生活故事,但它决非载歌载舞或是欢蹦乱跳的舞台狂欢,它镌刻着一个非正常的悲剧时代的深深烙印,承载着一段青春期的幼稚、纯真、狂热、骚动却又无比沉重辛酸的初恋情怀。这样的记忆与烙印虽然难堪甚至蒙受羞耻却是刻骨铭心、难以释怀的。这些作品,是成长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整整一代过早告别纯真的青少年的共同感怀与集体记忆。正如严歌苓在《士兵与狗》这篇小说收入某集后的附言中写的那样:“我的少年时期在军中度过,曾拥有过爱犬颗勒,它在我们的欺凌作弄式的爱抚下长大,度完它短短的一生。它不能控裁它的生死,我们也不能控裁我们的青春。在它和我们分别时,我们感到那样无力和无助。写下这个故事,我希望纪念我们的爱犬,也纪念我们那群迥异于全世界青少年的成长经历。”可见,那段岁月中的人与事、人与动物的关系都有一种特别的存在意义与历史印记。不仅作者难以忘却,读者也不能无动于衷。
严歌苓写于不同时期的“文革”题材的作品,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其中最长的《灰舞鞋》有5万余言;而最短的《馋丫头小婵》仅2000多字。这些长短不一的叙事作品,构成了一部以“文革”为题材的青春主题小说。自1976年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革”十年动乱时期结束,至今已经整整35年了。“文革”十年动乱对于中国当代历史和中华民族所带来的灾难性恶果,哲学家、史学家、社会学家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宏观地或是实证地对此作出了理性阐述或是深入探究。早在30多年前,文学家就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大量作品.揭示了烙在人们肉体上、心灵上的累累疤痕,反思“文革”爆发的历史积淀。深受其害的巴金老人则以“说真话”的文学方式,不仅写下了百余篇充满“我控诉”以及忏悔意识的“随想录”,而且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警示人们要记住并且警惕人兽难分的荒唐历史的重演。
生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严歌苓,其青春时代恰恰遭遇了那场父母受辱、亲人分离、少年失学、斯文扫地的灾难岁月,这对于其少女时代的成长无疑留下了不幸与缺憾。然而事物总有两面性,对于后来的作家而言,却反过来或许并非坏事。因为“文学是人学”。文学从本质上说是描写人及其情感、灵魂和精神世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积累人生阅历与洞悉世态人情,尤其是形形色色、面目迥异的“人”,往往是小说家最好的启蒙老师。严歌苓后来承认,使她写出《扶桑》那样的作品的初衷,就是为了以“足够的层面和角度,来旁证、反证‘人这门学问,‘人这个自古至今最大的悬疑。”她小小年纪,就经历了今天不少在温室中长大的乖男娇女们无法想象的严酷人生,见识了别人或许几辈子都难以接触到的幸与不幸的各色人等:有外表粗鲁却心存温情的,如《老人鱼》中的外公、《老囚》中的姥爷、《梨花疫》中的余老头;有相貌不俗却行事荒唐的,如《扮演者》中的“后勤部”(沈编导)与钱克;也有表面正派却内心龌龊的,如《灰舞鞋》中的团支书王鲁生、《少尉之死》中的司务长王有泉;还有明里示弱暗里逞强的,如《奇才》中的毕奇、《耗子》中的黄小玫等等。这些处于乱世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性格与精神状态的人物,显然给作者提供了反观、认识和表现“文革”那段历史的活生生的载体。
这些长长短短的小说,虽然描写的事件不一,人物各异,但其中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目击者或叙事人——“穗子”,并以这个稚嫩的小姑娘的眼睛作为观察视角,以其或朦胧或清晰的亲身感受和成长经历作为叙事脉络,来贯穿那个灾难岁月里所发生的一个个令人唏嘘的男女老少的悲剧故事。所以,“穗子的故事”,其实就是小姑娘穗子观察世界的“印象记”。与严歌苓的其他一些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不同的是,这些中短篇故事,在某种程度上,与作者的个人经历具有一定的重
合度.如:父亲的作家身份,他在“文革”中遭批斗侮辱,继而押往别处接受劳动惩罚父母感情不合,“文革”爆发却使他们相互依凭;女儿自幼寄养在祖辈家并渐渐长大,12岁被部队文工团选中而参军;8年军区文工团的舞蹈生涯,……并且作者是带着忧伤与忏悔的笔致来追忆这段苦涩而残酷的青春历程的,可以说,它比严歌苓后来的几部名气很响的中长篇小说(比如《扶桑》,比如《金陵十三钗》等),更具有一种“自传”色彩与“在场”的亲历感。与严歌苓曾获第16届台湾“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首奖的《扶桑》不同,它不是靠从移民博物馆发掘史料而后加以艺术想象,来塑造百多年前飘洋过海的一个中国妓女在新大陆半神半人的传奇形象;也不像被张艺谋一眼相中拍成电影的《金陵十三钗》那样,从南京大屠杀的悲情历史的史实中,寻觅出向屠城侵略者复仇的一群卖笑女子最后慷慨赴死而令人肃然起敬的画面定格,而是聚焦于“文革”动乱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让那段亲历并留存于记忆深处的黑门“底片”,原汁原味地在历史与人生的画册中曝光。那年月本身就是一篇篇时空倒错的荒诞派小说,一幅幅混沌不清的印象派画卷,因此,它似乎不需要挖空心思的“想象”,无关乎殚精竭虑的“虚构”,每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过来人,或许都会在“穗子的故事”系列中找到自己当年的小小剪影,虽然幼稚、单纯、无助、无奈、丑陋不堪甚至野蛮十足,但却真实可信、棱角分明。因为那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影像。
需要说明的是,“穗子”其实只是“穗子的故事”系列贯穿其中的一个人物,她在作品中主要担当的,要么是叙事者(讲她的亲人或旁人的故事,这时常用第一人称“我”的限知叙事视角);要么是女主人公(讲的是自己的成长故事,往往用了第三人称“她”的全知叙事视角,如《灰舞鞋》等)这两类角色,所以,“穗子”并不等同于作者。严歌苓曾这样谈过自己与“穗子”的关系:
“我和书中主人公穗子的关系,很像成年的我和童年、少年的我在梦中的关系。看着故事中的穗子执迷不悟地去恋爱,现实里的我明知她的下场不妙,但爱莫能助。看着童年的穗子抛弃老外公,和“拖鞋大队”的女孩们一块儿背叛耿荻,伤害小顾,面对人心向恶的社会和时代,她和她年幼的伙伴们以恶报恶,以恶报善,成年的我只能旁观。
穗子是不是我的少年版本呢?当然不是。穗子是“少年的我”的印象派版本。其中的故事并不都是穗子的经历,而是她对那个时代的印象,包括道听途说的故事给她形成的印象。比如《梨花疫》中的男女角,都真实存在过,但他们的浪漫故事,却是在保姆们、主妇们的闲言碎语中完整起来的,我写这两个人物时,只有对男主角的形象和性格的清晰印象,对他传奇背景的记忆。根据他的性格和背景,我找出这个爱情故事的逻辑,把当年人们猥亵娱乐式的闲话,拼接成穗子的版本。
可以说,“穗子的故事”系列当之无愧地构成了一部呈现“文革记忆”的“印象派版本”。虽然它无意于全面呈现“文革”爆发的惊心动魄的灾难场景,也无意于精心展示那场十年动乱留存在人们身体上、心灵上的累累伤痕。严歌苓承认,自己“总想给读者讲一个好听的故事”,但“又总是瞧不起仅仅讲好听故事的作者”,因为那仅仅使她“想起文学的最初级形态:说唱文学。我总是希望我所讲的好听的故事不只是现象;所有现象都能成为读者探向其本质的窗口。”如果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些“文革记忆”的小说给人的阅读感受的话,那就是——“沉痛”,痛彻骨髓的那种痛。这种痛楚引导着我们去“探向其本质的窗口”。那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带给中国大地与华夏民族的最大劫难,其本质要害莫过于:家不成家、人不像人,即中国人最为看重的人伦天性乃至血统渊源的遽然崩裂、尊卑秩序及其伦理观念的轰然倒塌。人,在一夜之间或变成了牛鬼,或变成了禽兽。作者以自己在“文革”十年动乱期间的成长经历及其生活环境中的人与事作为基本脉络,以春秋笔法反映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民族大灾难、文化大劫难在砸烂人的信仰和灵魂、推翻伦理与亲情方面的残暴及罪孽:父执叔辈身上的累累伤痕与人格屈辱是那样触目惊心:《我不是精灵》中的画家韩凌,他画画的手被打残、牙被杵掉、顶着“半青半白的阴阳头”、被发配到采石场去搬石头;祖辈的“历史清白”决定他们能否安度晚年的资格与权利:《老人鱼》中原本战功赫赫的老英雄,一夜之间竟被诬为“一个手上沾满红军鲜血的白匪”,不但被造反派停发了“残废津贴”,连本与外公相依为命的外孙女穗子也被急于“划清界限”的母亲趁机带走,她竟把自己的养父说成是“历史不清不白的一个不相干老头”。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悲哀在于:黑白颠倒、身心饥饿、学业荒废、个性压抑,以及道德沦丧与人性扭曲,成为“穗子”这一代青少年的启蒙教科书与人生启示录。这一切,构成了伴随“穗子”这代人从童年跨入青少年时期乃至影响其一生的魔障与梦魇。《老人鱼》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外婆去世不久,外面发生大事了。人们一夜之间翻了脸,清早就闻到穗子父母的家里,把穗子爸拖走了。之后穗子妈每天用她的皮包装来一些东西,到外公的后院去烧。烧的是照片、纸、书。有一些她实在下不去手烧的,就搁在一边。穗子知道,那是父亲的一些书稿或剧本稿子,还都是未完成的。”
母亲焚书的纸灰像黑灰色的蝴蝶扶摇飞上天空,遮住了太阳与光明。天地变成了暗淡无光的洪荒世界,人在蒙昧的世界中远离了文明、礼貌、尊严、同情与关爱,人格尊严被肆意践踏,甚至人伦天性也顷刻瓦解。“文革”颠覆了人的世界里应有的法则、伦理、道德、是非、秩序与公信力,无法无天的世界变得极其单调,人的存在似乎只剩下了动物的本能:争斗与撕咬。于是,原本的高贵者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人人都可以踏上一只脚,肆意凌辱他(她)的身体与灵魂,叫其永世不得翻身。严歌苓确信:“谁都弄不清自己的人格中容纳了多少未知的素质——秘密的素质,不到特定环境它不会苏醒,一跃而现于人的行为表层。正因为人在非常环境中会有层出不穷的意外行为,而所有行为都折射出人格最深处不可看透的秘密,我们才需要小说。”“文革”正是这样一个“折射出人格最深处不可看透的秘密”的非常环境。《白蝶标本》中那位戏剧名角儿朱衣锦被戴高帽子批斗示众,她不甘受其辱而吞服安眠药自杀,被送到医院抢救,竟让她光着身体一丝不挂地躺在过道里,成了众多“看客”围观的“裸体模特儿”,直到她的身子被盖上一条薄薄的白布单,“就像大幕关上了,观众散戏一样,周围的人缩缩颈子,松松眼皮,咂咂嘴巴,慢慢走开了。”只有年幼无知的小女孩穗子懂得羞耻,好不容易讨来一床棉被为朱阿姨身体遮羞并守护在她身边。可每当小穗子上厕所回来,“朱阿姨的身子总是给晾在那里”。半夜里小穗子睡眼惺忪地看到有个电工故意将香烟头掉落在朱衣锦的被子上,先是装出慌手乱脚的样子去拍打被子,“用手在朱阿姨身上扑上扑下”;继而干
脆抓起棉被来抖个不停:
“他眼睛一落在朱阿姨的身体上,手就僵住了。这个又瘦又白的身体天天都在缩小、干掉,两条甩水袖的胳膊开始发皱了,胸脯又薄又扁,一根鲜艳刺眼的桔黄色橡皮管不知从哪儿绕上来。电工动也不动。只有脖子上的大橄榄核在乱动。不知他认为朱阿姨的身体是太难看,还是太好看了。朱阿姨是一只白蝴蝶标本,没死就给钉在了这里.谁想怎么看就怎么看。她不防护自己,在你眼前展览她慢慢死掉的过程。她过去的多姿都没了,过去的飞舞都停止了……”
在窥视女性胴体的一双双不怀好意的猥亵目光里,“折射出人格最深处不可看透的秘密”:人的本性中最丑恶的“窥阴欲”,打着“革命”“专政”的旗号,达到了平日里隐藏在欲念深处的意淫满足。鲁迅先生曾经深恶痛绝的“看客”们,把活生生的朱衣锦钉在了“白蝴蝶标本”的展览厅里。如同黑暗的中世纪“禁欲”时代的“文革”毒瘤,“一跃而现于人的行为表层”。这里,人的尊严、人的隐私、人的高贵已经荡然无存。
人道、人伦、人性被兽性替代了,人的存在意义便只剩下了性本初的两件事:饮食和男女。先说饮食。《老人鱼》、《黑影》、《馋丫头小婵》等多部小说中都写到了当时人们的饥饿感,比如,押往外地接受劳动惩罚干苦力活的穗子爸,“世界对于父亲,就剩下个吃。穗子当然不知道冬天对父亲的那群人,确实只剩个吃,因为整个空白的严冬,就是个巨大的胃口,填什么进去都无法缩小它的空间,都填不掉那大漠般的饥饿。”不仅是像身为作家的穗子爸、才华横溢的画家韩凌等“专政对象”因肚子饿无法保持人的起码尊严,就连寄养在战功赫赫的外公家里被视为掌上明珠的小穗子,由于“食品的匮乏在这一冬恶化”,也只能靠外公的残废军人证,“一月多吃二两白糖、半斤菜油、一斤肉”;好不容易买到了轻易难以露面的小橘子,因其来之不易更显珍贵:“外公把小而青的橘子吊在天花板上,每天取一个出来,发给穗子,这样穗子每天的幸福时光就是酸得她打哆嗦的橘子。”读着叫人心酸落泪。顶着“馋丫头”坏名声的小婵,可没有小穗子那样拥有“残废军人证”的外公,只有一个一穷二白的“姥姥”。她12岁了,长在“文革尾巴上,搞不清怎么就消逝了肉、蛋、糖。没了这三样,粮耗得特快。春天大人们就揉我们出门撸榆钱打槐花去。小婵成把地将槐花掬进嘴,翅出老远的唇边都是泥污指痕。”为了能让同样饥饿难捱的姥姥能吃上一口肉,小婵用自己刚发育的身体跟在建筑工地上干活的板刷头做了交易,换回来一块吊在家门屋檐下的腊肉,“就用了这个简单法子,让姥姥好好饱了一度。”那年月,丰衣足食成了遥不可及的无望的梦呓。
可怕的远不止是人们身体上的饥饿,精神上的空虚与饥渴、心灵上的苍白与无聊更为可怕,它会使人变成忘恩负义的白眼狼、你死我活的乌眼鸡。《拖鞋大队》、《小顾艳传》等,更像是一部记录穗子那一代喝着“狼奶”长大的少年劣迹的成长手册,他们本身是受害者,背过身去却又成了加害别人的施暴者。如《拖鞋大队》中那一群因“文革”爆发而失学、饱受歧视的缺少教养、知识与文化的落难少女,整天游手好闲、无聊至极的她们,竟然“合谋”向真心帮过她们的好朋友耿蔌下了毒手。当她们狞笑着,围上来,七手八脚撕开她的学生蓝男式衣裤,只是为了亲眼看一眼她的女性器官以满足内心的饥渴感,令人不寒而栗。这篇小说写出了以恶向善、以怨报德的丑恶人性的一面,即使是些未成年的孩子,内心深处也多少有着或许她们并不自觉的“窥私欲”的恶性肿瘤基因。与此异曲同工的,还有在《小顾艳传》中那群把凹字形大楼楼顶当作游戏乐土的无人管教的孩子们:“他们最享受的娱乐是在天黑之后爬上平台的水泥护栏,观看每个窗子里上映的戏剧。平台护栏高一米六,只有两个巴掌的宽度,爬卜去再悬着两腿坐在四层楼高的天井边沿上,必得足够野蛮,足够亡命。当然,上映的戏剧都是极短的片断,有时只是惊鸿一瞥。将它们连缀成连续剧,还得靠想像、推理。最主要的,要靠幕后的跟踪考察。”
这群以“窥视”别人的秘密取乐开心的劣迹斑斑的孩子,在该求学的时候没书可念;在该学好的年龄学不了好,他们过早地介入了成人世界的尔虞我诈,成了一群“足够野蛮,足够亡命”的狼崽子,连许多成人都不是他们的对手。那位“文革”中因丈夫遭难、一心求助于军代表帮忙的小顾阿姨,不就成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木偶?他们和小顾阿姨本该是同病相怜的“天涯沦落人”啊!人们不禁要问:这群“足够野蛮,足够亡命”的狼崽子长大了又该怎么办呢?!
人之为人,除了物质的需求、精神的满足以外,还需要情感上的彼此慰藉、相互依靠,尤其是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这就涉及到两性关系。“文革”时期的“禁欲”思潮(至少在公众场合人们是不敢谈情说爱的),使很多人普遍患上了情感饥饿症。《灰舞鞋》中那位性情古怪却又洞悉一切的提琴手申敏华,就凭其眼力“看出小穗子是永远处于情感饥饿中的一类人。她的言行举动,都是为一份感情,抽象或具体,无所谓。”12岁参军后的穗子,她穿上了当时人人举目仰羡的草绿色军装,成了一名军区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她的脚上整天绑着一双灰扑扑的舞鞋,身体和情感也在练功房内不停地旋转中发育丰满起来。15岁的她由于一场执迷不悟的初恋,引发了“文工团有史以来的男女作风大案”,受到了最严明无情的军纪处分。被勒令当众朗读“悔过书”的少女,成了“狼性”未泯的人群中的一只孤零零的鸿雁,遭逢羞辱,倍感孤独。表面看来,《灰舞鞋》讲述的是偷偷谈恋爱的穗子,因尚属未成年人而触犯了军队的纪律条令而受到军纪处分和责罚,致使一场刻骨铭心的初恋夭折的情感悲剧,犹如一则光荣与梦想、爱情与人生、个性与自由的青春忏悔录。然而,它的更深层的哲学意蕴在于,揭示了那个时代“禁欲”的表象后面所粘附在“男女”(两性)关系中的一个荒谬的悖论:书写“肉麻”情书的,实际与情欲无染。小穗子写了几十封表达痴情暗恋的情书,可她并不懂男女“那件事”,无论好阿姨式的曾教导员如何苦口婆心地暗示诱导她都不明白;而偷看别人情书、日记的,倒是“虚虚实实地谈婚论嫁”!高爱逾分队长正如她名字的谐音“爱欲”。其理由也如同她对邵冬骏的挑逗那样,既霸道无理而又冠冕堂皇:“一个排级干部跟一个连级干部,慢说接个吻,就是明天扯结婚证.看哪个敢不腾房子给我们。”两个女人爱上同一个男人,无论他们的身份、军衔是否有明显区别,其实都存在着高尚与低俗、光明与阴暗、纯真与狎昵、美丽与平庸的精神境界的天壤之别,也与他们是否是军人的特殊职业无关。
严歌苓说:“人的多变,反复无常是小说的魅力所在”;“我总在寻找这个‘特定环境,以给我的人物充分的表演空间。”草绿色,曾是“文革”时期最时髦、最荣耀的流行色与时尚风向标,草绿色的军营也曾经成为少男少女们无比羡慕的一方圣地。这里也是严歌苓笔下的“人物充分的表演空
间”。《灰舞鞋》,打破了人们关于军营是严明纪律治辖下偃旗息鼓、一派平静的“避风港”的迷信与神话。这里,也有权势的淫威,人性的丑陋;也有是非的颠倒,青春的迷茫。在服从军纪条令的借口下,对于人的情感的压抑、人格尊严的侮辱、个性自由的制约,反而更加肆无忌惮。15岁的穗子正值青春期,那身草绿色的军装无法包裹一颗春心萌动、坠入情网的少女的心,她每天一封情书或一首情诗向既是救命恩人也是初恋情人倾诉她的爱情。青春心理学认为:青春期是“人生的第二次诞生”,心理学家戈特甚至称之为“疾风怒涛的时期”。当个体进入青春期以后,随着性意识的逐渐成熟,“就引起了与性意识有关的多种多样的内心情感体验,并在个体心理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时候他们逐渐开始产生一种追求异性的需要,逐渐地由一种模模糊糊、捉摸不定、短暂的‘感觉和‘激情乃至‘幻想,进入到恋爱阶段。”可以说,世界上再严厉无情的军纪条令也无法威慑、阻止青年男女的相互吸引与爱情勃发。《士兵与狗》中的鼓手小周与提琴手赵蓓夜间不顾一切地偷吃禁果,证明了军人也是有着七情六欲的凡人,何况是处于热恋中的一对有情人。问题是,当时的他们得不到正确的引导和善意的疏解。于是,赵蓓很快“非常复员”被送回老家,一对鸳鸯被拆散;而穗子虽在乔副司令力挽狂澜下勉强保住了军籍,但她的遭遇和打击其实比赵蓓更惨:心爱的恋人另择高枝,自己受到“观察留用”的处分。更令她难堪的惩罚是:犹如美国作家霍桑笔下那位19世纪因通奸而烙上醒目的红色A字标记的海丝特·白兰那样,穗子的那些纯属个人隐私的热烈情书,粘着众人的唾沫星子四处扩散,成为公众的无聊谈资与娱乐调料;她被迫站在类似军事法庭的批斗会现场,当众大声朗读自己的“悔过书”;之后成了谁都可以差遣她干这干那的“杂务兵”。更可怕与悲哀的是,“从她朗读了悔过书后,她失去了大笑的能力”,战友们像躲瘟疫一样回避她、孤立她,“驱逐对这只雁是致命的羞辱。”青春期因为初恋而经受这样的羞辱和难堪,一般人能忍受得了吗?虽然,穗子做到了。当然,她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此失去了人的纯真和热情,她再也没有了爱的能力与被爱的幸福。刘越赠与她的定情之物,在受到拒绝后被扔出了墙外。那一代人的纯真爱情,失落了,再也找不回来。
因此,《灰舞鞋》确是一篇“通向一个个深不可测的人格的秘密”的“悔过”与“改过”的爱情忏悔录,一出沉重而又哀痛地追忆似水年华的纯真青春祭。它比任何青春心理学和爱情教科书都要真实可信、鞭辟入里得多。它不能,更不该被遗忘。今天的年轻人,应该读一读《灰舞鞋》,永远记住曾经有一段让一个初恋的女孩胸前烙上红字以示羞辱和惩戒的难忘历史。但愿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责任编辑:黄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