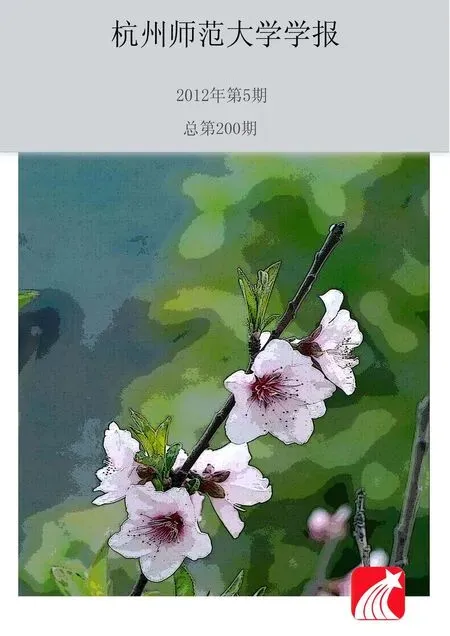开启中国思想史上的法学知识轴心时代
2012-04-14魏敦友
魏敦友
(广西大学 法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法学研究
开启中国思想史上的法学知识轴心时代
魏敦友
(广西大学 法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随着中国历史逐步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法治时代。与此同时,中国思想也将迎来它的现代形态,进到一个全新的知识时代——法学时代。从中国思想发展的长程视角看,法学时代是自秦汉以来继经学时代、理学时代的又一个新的知识轴心时代。正如经学知识、理学知识各自支配了上千年的中国历史一样,法学知识必将成为支配中国历史新的千年的话语范型。
新道统论;经学时代;理学时代;法学时代;正当性类型
如果从中国思想史的长程视域来看中国学术的现代发展,也许会发现,法学知识对于中国学术而言乃是一种全新的知识类型,在中国传统学术的格局里基本上找不到它的位置,也无法理解它。这意味着,法学乃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产物。的确,中国法学乃是应中国法治时代的到来之运而生成的全新的知识类型,同时它也将创造性地建构起这个法治新时代。所以从根本上说,中国法学乃是中国现代性的产物,当然它同时也建构着中国的现代性。但是另一方面,必须郑重指出,中国法学尚处在它的萌茁期,它对自己生成的正当性、知识的内在逻辑以及根本使命还缺乏通透的认知与自觉意识,因此,中国法学目前尚无力筹划、建构起自身的知识体系,当然也无力对中国的法治实践之基本取向作出严肃认真的反思。
中国法学要想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法治新时代,就必须从当前普遍弥漫于中国法学界的一种犬儒主义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真正开始思考与中国法学内在关联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真正开始对中国法学之生成的正当性、知识的内在逻辑以及根本使命进行深刻反思。本文对此进行初步思考,依次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中国法学的现状如何?第二,中国法学的性质是什么?第三,中国法学与中国文化的重构之间是何种关系?
一
在当代中国,随着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逐步展开与深入,法学越来越从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边缘地带向中心地带转移,逐渐成为一门“显学”。法学知识越来越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的建构性力量。甚至可以认为,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这一几乎是静悄悄完成的知识重心转移是中国现代思想中颇为意味深长的“思想事件”。然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中国法学界乃至于中国思想界尚无人(似乎也无兴趣)对这一发生于现代中国思想场域中的极其深刻的“思想事件”进行诠释;而不对这一“思想事件”进行深刻的反思,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现代中国的思想核心——从中国思想之数千年长程的历史视野看,中国思想史上也许正在迎来一个法学知识的时代。当然,中国思想史是否可能存在或开启一个法学知识的全新时代,这是需要我们仔细论证的思想事业。不过就当下而言,我认为,由于缺乏必要的思想坐标,在当代中国思想界,人们对法学这种知识的理解,要么是盲目的,要么是肤浅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批判地清理中国学人对法学的理解必然伴随中国学人建构中国法学的始终,因为只有深入地批判性地思考中国学人对法学的理解,才能克服中国法学的盲目性,超越中国法学的肤浅性。
一方面,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当代中国法学学者普遍存在的理解中国法学的盲目性。比如,著名学者何勤华先生在世纪之交推出了他的皇皇巨著《中国法学史》。他十分感慨中国的学者们早已在20世纪初就分别写出了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乃至中国伦理学史,却十分遗憾地没能写出中国法学史,并认为这或许是法学被人们视为“幼稚”的原因之一。[1](《序》)何先生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实现了中国学者写出中国法学史的宏愿。在他看来,法学这种知识正如文学、哲学乃至伦理学一样,在中国其实是古已有之的。因此,中国法学史的写出与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乃至中国伦理学史的写出一样是合乎中国思想的逻辑的。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法学在中国就古已有之的观念在我看来却存在着一个“时代错位的幻觉”,它将现代的法学知识观投射到古代的知识场域中去,将古代的知识经过现代法学这面透视镜加以观照并淘洗,似乎中国古代也存在着法学知识,于是建构起中国古代的法学知识。然而这样一来,知识的古今之别就被掩盖起来了,其结果必然是既误解了中国古代的“法学知识”,也对法学知识的这种现代性品格缺乏自我意识。这种在当下中国法学界几乎占据主流的观念危害极大,因为它看不到法学这种知识类型的时代品格,无法洞见现代中国法学乃是一种全新的知识类型,是中国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一个思想建构。
另一方面,必须深刻反思法学知识的正当性根据。在当下中国法学界,人们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认识,即法学知识乃是一门客观的具有中立性的科学,因此不管它产生于何处,产生于何时,只要它产生出来了,就是全人类必然普遍共享的知识系统。正是在这种法学知识观的支配之下,源自西欧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学知识获得了大规模进入中国的正当性理据。必须承认,西方法学知识在进入中国的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了中国的社会现实,为中国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助力;但是必须同时看到,西方法学知识在为中国提供新的秩序的同时也给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有法而无治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困局所在。虽然不能将其完全归罪于西方法学的传入,但不可否认,西方法学对这种现象也应负相当的责任。因为西方法学的深刻影响,使得中国人失却了思考“关于中国人究竟应该生活在何种性质的社会秩序之中这个重大的问题”[2]的能力。一直到今天,还是有许许多多的中国法学家们意识不到法学的中国品性,意识不到中国现代法学从根本上讲乃是一场文化重构(不是复兴)运动。如果我们意识不到中国现代法学是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历史土壤之上的一个知识建构,那么我们对法学知识的理解就永远只是肤浅的。如果任由这种肤浅的法学知识观继续泛滥,那么中国法学就不可能获致自己的正当性理据,其结果就只能是满足于吸食西方学人的余唾并以此津津乐道了。诚如是,则中国现代法学必然是镜花水月了。
因此,中国法学虽然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近30年来,它已成为中国现代知识系谱与蓝图中的“显学”,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中国法学依然是盲目的与肤浅的,中华学人必须扬弃这种盲目性与肤浅性,在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厚基础之上,有意识地进行法学知识的建构,真正有能力开启中国思想史上的法学时代。
二
再回到何勤华先生的问题上来。何先生的感慨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甚至于我们将它命名为现代中国法学的“何勤华感慨”也未尝不可,关键是寻绎其中的思想逻辑,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现代法学的生成,意义十分重大。
从表面上看,中国法学史的写出可以视之为19世纪、20世纪甚至21世纪中国“知识引进运动”的一部分。然而,当我们进入中国思想的深层,问题也许会发生一个巨大的转换,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正在从“中国法学史为什么要等到在20世纪末才被人们写出来”转换为“中国法学史为什么要等到20世纪才开始写”。这是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问题,前一个问题缺乏对现代中国法学的自觉意识,而后者正是以现代中国法学的自觉意识为前提。前一个问题是面向过去的,而后一个问题却是朝向未来的。
这同时也意味着,现代中国法学的性质至今晦暗不明。我认为,要真正理解现代中国法学,必须寻找到中国思想的参照坐标。只有在中国自身思想的参照坐标之中,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现代法学思想生成的内在逻辑。而对中国思想的追寻,切忌简单化地使用西方概念来切割套用。如钱穆先生所言:“今天中国人的大缺点,就在把自己本身的社会实相撇开不谈,而专门滥用西洋几个空名词套上,硬拼硬凑,硬要中国来做别人家文化的殖民地。我们希望中国文化还要自觉地站起来,那么中国才有新希望。”[3]
当我们摆脱西方概念的羁绊,真正进入中国思想的历史长程后,就会发现,中国思想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已走过了它的若干个阶段。我结合钱穆、冯友兰及余英时等人的研究成果,从知识论上将中国思想划分为四个阶段,依次为子学阶段、经学阶段、理学阶段及法学阶段。我认为中国思想在当下正处在理学阶段的末端,而正在全面进入一个以法学知识为轴心的新阶段。
思想之所以为思想,其根本要义乃在于它能为人类的生存秩序提供正当性根据,而能为人们所承认、所接受的具有正当性根据的思想则成为基本的思想范式,具有权威性。思想的权威性来自思想自身的内在力量,而当一种思想的内在力量丧失掉后,它必然就为另一种思想所取代,于是我们发现人类历史上在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思想相继踵起。以此思路来观察,中国思想史上存在着三种正当性类型,依次是经典为正当类型、自然为正当类型及自主为正当类型。获致中国思想中的这三种正当性类型,我深受金观涛先生的启发。金观涛先生在研究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时,深刻地洞见到一种非道德的正当性,这种非道德的正当性正是一种自主正当性,只有它,才能成为权利的根据。金观涛先生指出:“我们将权利界定为非道德的正当性。为什么可以这样讲?所谓权利强调的是自主性,而道德除了将自主性归在可欲性和德性之自由名下外,强调向善的意志。向善意志的结构同自主性的结构完全不同。例如,当人们把自由平等视为人的权利,是注重每个个人的独立自主,并不涉及这些行为应不应该。权利主张人的自主性具有非道德的合理性,即并不要求在自主性的名义下人的行为都是好的、向善的;只要这些行为不损害他人利益(或公共规则),人就有权做这些事,权利就保证了它们的正当性。”[4](P.332-333)这种自主为正当的正当性类型最终将法律与道德严格区分开来,于是,“法律并不是道德,也不来源于道德”[4](P.384)。这意味着,中国现代思想正是从道德的裂变中逐步产生出来的。从道德到法律,这是当下中国社会制度之中最重要的变化,相应的,中国思想则正在从理学走向法学。理学是以道德为中心的知识类型,法学是以法律为中心的知识类型,前者以自然为正当,后者则以自主为正当。更进一步,当我们向上回溯中国思想时,很长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将理学视为经学的一个类型,如冯友兰就认为子学时代结束之后一直到晚清民国时代都是经学时代,这种观点看不到宋明理学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知识类型,正如余英时所指出的,“理学并不能简单地分入经学的范畴”[5](P.102)。经学与理学相比,其正当性根据又是另一种类型,我将它命名为经典为正当的知识类型。
经典为正当、自然为正当及自主为正当乃是中国思想相继而起的三种正当性根据,它们分别对应着中国经学、中国理学及中国法学。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如果说经典为正当是以经典为中心的,其内在理据是以圣贤为崇拜对象的,它以圣贤之是非为是非;那么自然为正当是以道德为中心的,其内在理据是以事理为崇拜对象的,它以事理之是非为是非;而自主为正当是以法律为中心的,其内在理据则是以意志为崇拜对象的,它是以自我之是非为是非的。如此,则经典来自圣贤,道德出自事理,而法律根源于自我的意志。这是一个逐步由外向内的过程。
从这一知识图像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思想从中古到近古以及进入现代的内在逻辑。这个逻辑与西方的逻辑是迥然有别的。余英时指出:“西方的现代是脱离宗教,中国的现代是脱离道德。”[5](P.204)强调人的自我意志之自主为正当,这是中国文化脱离道德进入现代的基本要义,它与西方通过脱离宗教进入现代是根本不一样的。另一方面,虽然进入现代的路径不同,但中西方在法律根源于人的自我意志自主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这意味着现代中国法学的建立既有国内向度,也有国际向度,因此中国法学就不仅仅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的意义,它不仅会对中国人的现代生活秩序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必然对中国已经进入的当今人类世界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
要实现这样的愿景,需要现代中国法学从西方概念中解放出来,真正恢复中国文化的自主性。应该说,今天提出中国文化的自主性问题也是与现代中国法学之自主为正当这一新的正当性类型相应合的。当然,欲证成中国文化的自主性问题,其先决条件乃是对中国文化有一深刻的认识。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了人类历史文化之轴心时代的观念。这种观念为审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多年来广受讨论。在他看来,世界上几个大的古老文明如印度、希腊、以色列及中国等几乎在同一个时代也就是在大约公元前800年前后完成了所谓“哲学的突破”,形成了支配后世数千年的基本思想观念与思想范型。就我们今天所浸润的中西文化而言,如果说西方是来源于希腊的理念论传统,那么中国则根据于源远流长的道论传统。道论传统是中国先秦子学时代的重大贡献。虽然人们今天往往以儒家为正宗,但当时的各家各派无不以道论为旨归,道论思维因此成为支配中华文明内在精神的构成性力量,明道、行道成为此后数千年中华文明不变的主体性思想。中华文明之所以为中华文明,其内在根据就在于道论思维。从比较文化史的观点看,中国的道论思维与古希腊的理念思维相比,有其世俗性、历史性、整体性及圆道性的特点。它特别强调人类的生活秩序之正当性根据只能在人世间寻找,只能从历史中吸取,必须整体通观,而且,人类秩序不可能是绝对稳定的,它必然在循环往复中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这种道论思维形成了一种中国文化历史之道统观,当我们运用这种道统观来看待中国数千年的知识进展,可以获得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正是受到中国文化之道论类型的启发,我在2005年前后提出了所谓“新道统论”的构想,旨在通过对中国文化之道统论的阐发,辨明中国法学的基本思想方位,促使中国法学达到它的文化自觉,从而完成中国法学的知识建构。很显然,我的这种设想并不局限于雅斯贝尔斯之文化初期的轴心时代论述,而是将此后文化上的重大发展也视为新的知识轴心时代,如中国思想上的经学时代、理学时代乃至我认定的下一个法学时代。我的这种设想很快受到了国内一些学者的批评,如福建著名学者吴励生先生、复旦大学孙国东博士。不过我认为他们对我的批评基本上是出于一种误解。这种误解来自于对道统论的狭隘理解。对道统论的狭隘理解可以远溯到唐代韩愈,一直到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韩愈是道统一词的发明人,但是他对道统的理解一开始就是狭隘的。他将道统理解为一线单传的,甚至是可以断裂的。这种理解对宋明理学影响极大,所以宋明理学也主张一线单传的道统观。钱穆先生认为韩愈(包括宋明理学及牟宗三)所理解的道统乃是主观的道统,称之为“主观的单传孤立的易断的道统观”。[6](P.348)钱先生针对此一狭隘的道统观而提出另一种所谓真道统观。他说:“若真道统则须从历史文化大传统言,当知此一整个文化大传统即是道统。如此说来,则比较客观,而且决不能只是一线单传,亦不能说它老有中断之虞。”[6](P.348)的确,当我们从后一种道统观来审视中国文化历史,则有何等从容气象!道统就是全部中国历史文化,道统并不在中国历史文化之外。
汉代董仲舒曾经说过:“道之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7]近世以来,人们普遍地误解了董仲舒之意,将他的条件句读成了一个断定句,因此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将他视为传统社会的卫道士。其实董仲舒的意思很清楚,只有在天不变的情况之下,道是不可变的,然而,一旦天发生了变化,道自然就会发生变化。没有不变之天,因此也不可能有不变之道。作为学者,其学问之职志正在于明天之变化,阐道之精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同钱穆先生的如下说法:“学问主要目的,正在于明道行道。而道亦可以变,可以进。”[6](P.466)根据这种天道变迁观来理解中国长程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历史的内在变化。如果说先秦奠定了中国文化的道论基础,那么秦汉时代则是中国历史之一大变,中国人因此而建立起了经学知识体系。唐宋时代是中国历史之又一大变,中国人因此建立起了理学体系。而我进而预言,当下中国历史面临着更新一巨变,中国人将在这次巨变之中最终建立起新的法学知识体系。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梁启超先生在20世纪初的感喟之言了:“今日非发明法律之学,不足以自存矣。”[8]也许今天我们完全有信心可以告慰先贤了,因为我们今天正处在建构中国现代法学的门槛上,中国现代法学将经过它的萌茁期而进入酝酿期。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学术思想虽然在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形态,但它们永远自觉地受制于道论思维的支配,因此无论是中古的中国经学,还是近古的中国理学,乃至今天的现代中国法学,必然都是在道论的延长线上的学术体系。所以,从中国文化重构的意义上看,当下中国现代法学的知识体系的创建意义极其重大。甚至于可以这样说,中国现代法学知识体系的创建与中国文化的当代重构乃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事。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思想史上正在迎来一个法学知识的新的轴心时代。
[1]何勤华.中国法学史:第一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
[2]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64.
[3]钱穆.中国历史精神[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63.
[4]金观涛.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5]陈致.余英时访谈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2.
[6]钱穆.新亚遗铎[M].北京:三联书店,2007.
[7]班固.汉书[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800.
[8]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3.94.
OpeningupanAxicalAgeofLegalKnowledgeinChineseIntellectualHistory
WEI Dun-you
(Law School,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China)
With China’s historical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gradually taking shape, China is entering a brand new age of rule of law. At the same time, Chinese thought will welcome its modern expression, entering a brand new age of knowledge——the age of legal science. From a long term point of view of development, this age of legal science is a new axical age of knowledge on the continuum of the age of classics and the age of Neo-Confucianism since Qin and Han dynasties. Just as the knowledge of classics and the knowledge of Neo-Confucianism dominated Chinese history for a millennium respectively, the knowledge of legal science is going to become the discourse paradigm that will dominate Chinese history for the new millennium.
New Confucian Orthodoxy; age of classics; age of Neo-Confucianism; age of legal science; types of legitimacy
2012-08-20
魏敦友(1965-),男,湖北仙桃人,哲学博士,广西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法哲学研究。
D920.0
A
1674-2338(2012)05-0108-05
(责任编辑:沈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