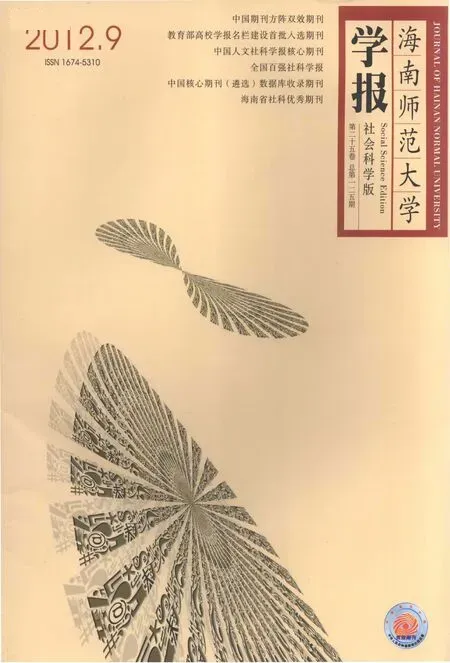宝塚歌剧团与模糊的性别主张
2012-04-13邹慕晨
邹慕晨
(武汉大学艺术学系,湖北 武汉430070)
导言
隶属于日本阪急电铁集团的宝塚歌剧团成立于1914年,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全部以女性演员出演的宝塚歌剧团分为花、月、雪、星、宙五个剧组,至今共上演剧目达2,600部,年均演出达1,500场,已成为日本国宝级的演艺团体。从阪急集团2010年年报看,宝塚歌剧团所创造的利润占集团总收益的14.4%,位列集团所有产业之第三位,仅次于作为支柱产业的公共交通(29.4%)和房地产(23%)。①见阪急阪神股份公司2010年年报,http://holdings.hankyu-hanshin.co.jp/ir/library/annual reports/data/ar2010j.pdf。并且在近年世界经济和日本经济持续走低的窘境下,宝塚歌剧团依然保持着效益上涨的良好势头,创造了国际演艺界的奇迹。
一 宝塚生长的社会土壤
日本,社会物质文明高度发达,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却是一个男女极其不平等的国度,女性不论在升学、就业还是家庭生活中都明显处于男性话语权的掌控和压迫之下。根据日本总务厅统计局的调查,虽然平成以来,日本女性参加工作的比例较之以往已有大幅提高,但她们中的大多数只能在收入很少的第三产业参与社会劳动,即便与男性从事同样的工作,其工资也只相当于男性的85%,这还是20岁至24岁这个年龄段的数据。随着年龄的增长,日本男性的工资水平会一直平稳上升,例如45岁至49岁这个年龄段,他们的平均工资为1,800日元/小时,而女性仅为850日元/小时,仅占男性工资的47%。但是从数据上,我们发现日本女性日益高涨的劳动热情,女性参加工作的比例正以每年2.6%的速度稳步增长,大大超过男性每年1.26%的增长速度。在日本的派遣社员这种劳务制度下,有60%的员工都是女性,从工作领域上看,也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到工程技术行业,而不仅仅停留在简单的办公室劳务或者服务行业。然而令人扼腕的是,即便在同样的领域从事同样的工作,女性所获得的晋升机遇是完全不能与男性相比的。工龄同为30年的男女职工中,晋升为系长、课长和部长的比例,分别为男:9%、15%、5%;女:7%、5%、0%。
但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却是另一番景象。根据日本文部省的学校基本调查显示,1970年女性的大学入学率仅仅只有17.7%,其中还包括11.2%的短期进修,但在1988年之后女性的大学入学率几乎翻了一番,与男性大学入学率基本持平,此后一直保持这个比例直到现在。[1]
越来越多的女性渴望受到高等教育并投身社会劳动,实际上已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技术工种和高科技行业。但在受同等教育、工作热情也日益高涨的同时,日本社会却没有给予她们同等的待遇,她们获取的工资收入和晋升机会却依然远远落后于男性。我们不能不说,日本虽然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但是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依然根深蒂固。然而有趣的是根据日本总理府的调查,对于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职业男性赞同的比例高达51.7%,职业女性反对的比例也同样高达47%,从这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女性要求经济独立,提高社会地位的心愿是很迫切的。①参见日本首相官邸发布的《男女共同参画白皮书》,http://www.gender.go.jp/whitepaper/h24/zentai/html/zuhyo/index.html。
宝塚歌剧团应日本女性觉醒和自立的需求而诞生和发展,既满足了女性社会的需求,同时又丰富和发展了日本戏剧。
二 女性博弈的名利场
作为少女歌剧,宝塚歌剧团的存在为日本女性实现个人价值提供了一个排他性的舞台,也当之无愧地承载了女性们对理想和梦想的演绎、对希望和未来的憧憬。在日本或许再也没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让那些有天赋、多才艺的女性们凭借自身奋斗实现理想,并能站在一个公司(宝塚歌剧团实际上就是个公司)的最顶端,受到无数人的景仰和赞美。在现实社会中得不到自我展示机会的女性们在这里却是自己的主人,她们保持姣好的容姿,在歌舞戏等专业方面刻苦钻研,她们不必再与男性竞争,而是凭借自己的才艺实现自身价值。宝塚歌剧团的主演明星制度是一项专门为女性开辟的晋升通道,在宝塚这个名利场上,女性们也是要竭力博弈、一生悬命才能成为胜利者的,从这个角度上看,宝塚同时也实现了女性们参与社会竞争,试炼生存能力的夙愿。
每年,宝塚音乐学校都会招收大约四十名新学员,这个音乐学校的招生考试,其竞争的激烈程度让人难以想象,平均下来淘汰率是30比1。[2]日本有一句话说:东有东大,西有宝塚——讲的就是日本最难考的两个学校,即东京大学和宝塚音乐学校。女性们想要站在宝塚舞台的愿望之强烈,由此可见一斑。但并不是进入宝塚就意味着获得了成功,正像前文所描述到的一样,即便每一个人都怀着明星梦加入宝塚,但能够成为主演明星的人却只有10个,更多的演员,终其在宝塚的数十年生涯,也仅能作为一个舞台陪衬或背景而存在,她们不曾在这个华丽的舞台上有过独唱,甚至连面容也不可能被人记住。所以主演明星制度是很残酷的,它只把所有的荣耀和光环给站在舞台正中间的那个人,就算是男二号和男三号,在各种待遇上都会与头牌明星有很大的差别。每年公演超过1,500场,可见宝塚演员们所面临的劳动强度、心理和生理压力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
日本社会虽未赋予女性与男性实现自我价值的同等机会,但却也让她们回避了激烈的社会竞争。反观宝塚,给予机会的同时也要求生徒们承担相应的压力,但每年依然有无数的少女渴望站上宝塚的舞台,只因那是一个承认她们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立身于世的平台。宝塚让女性在舞台上创造奇迹,在这里女性被尊重,不因为她们是某人的母亲,某人的女儿或者某人的妻子,而是作为享有独立自主权的、大写的人。
宝塚的戏剧也好,歌舞也好,所有角色全由女性扮演。在这个舞台上,女演员们可以实现征服世界、载誉历史的宏图伟业,她们可以和男人们一样冲锋陷阵,和男人们一样驰骋商场,和男人们一样参与政治,这在她们的现实生活中是永远做不到的,而在舞台上她们做到了——她们扮演过肯尼迪,扮演过麦克阿瑟,扮演过海明威和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还扮演过内尔森和拿破仑。可以说,正是通过宝塚的舞台,女性才象征性地站在了社会的前沿。
女性主义学说认为,普世的男性话语权下女性被认为是不完整的人,《圣经》中夏娃是由亚当的一根肋骨做成的;社会的属性是男性的,男性从未把女性当作同类,女性永远是人类及社会中的“他者”,因为社会的运转是遵照着男性制定的规则来进行的,这样的观念在其他众多国度或大有逆转、或大为改善,但在日本社会至今依然不能乐观:在这样的社会里,女性必须服从于男性,成为他们的附属品,她们大多因为自己的社会属性,比如血缘关系、婚姻关系等等而获得男性的尊重,而不是因为自己的独立人格。作为女儿、妻子、母亲所获得的权利,并不等于一个性别所获得的权利。
那么和男性的平等该从什么方面来实现呢?就是通过劳动创造社会价值。作为女儿、妻子、母亲固然也能创造价值,但是对于社会性的生产来说,她们的劳动还仅仅是局限在家庭的范围内。宝塚歌剧团的生徒们正是在社会生产活动的层面上实现了自我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她们还战胜了男性——宝塚的票房一向是跑赢大市的。
一般情况下,由于女演员的身份比较特殊,所以有人会提出,女演员的价值实现也是通过男性的话语权来实现的;又由于女演员所生产的产品需要男性来消费,所以处于“被看”地位上的女演员依然是这种二元关系中的“他者”。但是宝塚太特殊了,宝塚的观众们基本都是女性,就算最乐观的估计,男性观众的比例也不会超过8%,每年一度通过网络进行的宝塚爱好者普查,得出的结果甚至没有超过5%。①参见《宝塚フアン白书2011》,http:/navi.moo.jp/event/xmas2011/hakusya/frame.htm。女性生产,女性消费,宝塚创造了一个完全以女性的需求和女性的活动来维系的“国家”。
从观众角度来看,宝塚也是她们实现梦想的地方。平日里作为家庭主妇或者派遣员工的女性们,只有坐在宝塚的观众席中才能获得和男人们一样征服世界的快感。舞台上那些浪漫唯美的爱情、惊心动魄的战争竟然是和自己一样的女人们经历的,这一点让她们获得了心理的慰藉。
三 性别模糊的代言人
宝塚舞台上所有扮演男役的女性,台上台下都会努力去模仿男性,锤炼自己的男性气质,身穿黑色燕尾服的男役们是令观众神魂颠倒的魔器。但是另一方面,宝塚的男役们又带有很多非男性化甚至是消解男性气质的特征,比如舞台上男性们的形象温文尔雅,颀长俊美,他们经常身穿着华丽的缎子面料做成的西装,歌舞表演中有的演出服缀满亮片、水钻和羽毛,即便是军人角色,军装上也经常装饰着华丽的蕾丝,精致的刺绣等等,更不用说男役们也画着大浓妆,假睫毛,蓝眼影,根本就是女演员化妆的方式。宝塚的男役从外形上来看,与娘役最大的差别可能就在于身高、肩宽和发型了,但是刨去这些和刻意压低的声音,其实宝塚男役的性别特征很模糊,既非女性也非男性,更像是青春发育期之前的少年。[3]
这种被消解的性别特征使得宝塚的男役没有同龄女性的对抗性,也没有同龄男性的侵略性。一般来说,女性对于和自己同龄或者稍微年轻的同性会产生很微妙的防卫心理。因为在这个男性主导的世界里,所有同龄女性都互为竞争对手,正像巴尔扎克在《离婚生物学》一书中所讲到的:女人的命运和唯一的荣耀是赢得男人的心。而作为这个男性世界里共同的“他者”,女性们所面临的都是“被挑选”的命运,而至于是挑选你,还是挑选她,这里面就蕴藏着永难和解的矛盾或曰战争了。所以女观众们对于宝塚男役们是没有防备心理的,她们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对于这个世界的“男性争夺战”她们不会参与,原因是作为演员的她们在退团之前不能结婚。从另一方面来讲,宝塚的男役们也不会让女性们产生被奴役或者被侵犯的恐惧感,因为男役们身上没有让她们产生这种感觉的特征,她们没有随时会挥舞起来打人的粗壮的手臂,她们没有龇牙咧嘴动辄破口大骂的满脸横肉,更没有将女性们硬生生从甜美的少女时代拽进生硬粗俗的成年人世界的男性生殖器官。
从成年女性及其心理上来看,她们永远保留着对于少女时代的憧憬。她们留在蒙昧世界的时间相对来说要更长些,而男性可能到了青春期,父母就会有意识将他们塑造为成年男性,并且告诉他,不可以再哭泣,也不能再撒娇,因为成人世界有它独有的行事准则。亲吻和爱抚是女孩子的特权,父母也依然会让她依偎,给她抚慰;女性发现自己的眼泪和撒娇仍然拥有和小时候一样的功效,使父母心软或者让情人屈服等等。那时候的她们,对于男性的幻想,停留在童话里的王子层面上,他优雅高贵,温柔绅士,从来不会让女人伤心失望。她幻想着用一场童话般的盛大婚礼来宣布她在某一时刻忽然变成一个成年人——某人的妻子。但事实是成年的男性世界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男性世界里她是个完全的他者,一夜之间她跨入了成年人的世界,却没有想到婚姻和家庭距离童话世界竟然如此之遥远。
不过,宝塚歌剧团的男役们再造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男役的形象温文尔雅,体贴周到,英俊潇洒,多情又忠诚,就像她们情窦初开时梦里见到的白马王子一样。舞台上的他们从开满玫瑰的花园款款走来,带着迷人的香气,穿着绫罗绸缎,装饰着珠宝和羽毛,剑眉星目,唇红齿白,说着“永远爱你,忠于你,你是他的全部,没有你他就活不下去,你是他的世界里唯一重要的、值得守护的人”这样的甜言蜜语。
当年韩剧《冬季恋歌》在日本热播的时候,日本的杂志曾经做过一个专题,讲述裴勇俊在日本大热的现象,标题是《冬季恋歌引发离婚狂潮,宝塚不会》。对于现实存在的男人,女性们看了之后会有比较的,裴勇俊是如假包换的男人,“他对恋人多么多情而忠诚啊,为什么你不能”?当日本妻子们这样问自己的丈夫时,于是矛盾就产生了,于是离婚狂潮掀起了。但看宝塚歌剧的女人们却不会拿男役们去和自己的配偶做比较,因为她们切实地知道,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性别,没有可比性,现实中也没有穿着缀满蕾丝花边燕尾服的男人。
多好啊,宝塚!一切看上去都那么完美。宝塚舞台上的女人们,宝塚观众席里的女人们,似乎都从这里得到了莫大的满足感,在表演的情境中实现了女性的独立和自尊。但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如果深入到宝塚歌剧团的内部去看一看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性别模糊的代言团体,但它所代言的并不是女性的诉求。
四 男性掌控的女性群体
如果深入到内部去看一看,其实宝塚歌剧团依然是一个按照男性规则运行的小社会。
我们看到,宝塚的管理者全部都是男性,虽然近年来也有三位女性加入到理事会,但都是以演员的身份加入的,仅这三位女性也不可能改变宝塚作为一个男性掌控公司的根本性质。宝塚的演出计划、路线方针、人事变革等都是男性意志下的产物。在团的所有生徒,于森严的等级制度之下服从的并不是制度本身,而是服从于统治地位的男权。在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这本书里有一段对于女演员的描述,放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她们的身体不属于她们自己,制片商在决定着她们的发色,她们的体重,她们的体型,她们的类型,决定她们所扮演的角色。她什么新的东西也没创造,一般她们并不负责提出计划,宁可说她们是男人手中的工具。”[4]644
宝塚整个团体都是男人手中的工具,利用这个工具,男性实现了征服世界,征服女性的最高理想。宝塚成立之初,其创始人小林一三就为它定下了“清、正、美”的三字团训,尽管这三个字被解释为清纯、正直、美丽,但这不过是男性们对于女性居高临下的一种要求。在日本,作为二元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一方,男性对于女性有着天生的控制欲,如果女性变得和男性一样,矫健、聪明又样样能干,那么男人们就会怒斥她们不守安分,企图抢走男人的工作、事业和成就感,不管是女政治家、女律师、女作家,还是女军人、女运动员,都被男人们视为人类社会的异端。“世界上三种人,男人,女人,女博士。”这本是句玩笑话,但是却很深刻地反映出了日本男性对于变得强大的女性有多么反感甚至害怕,他们希望,女性永远是二元关系中的被动者、附属者,而非竞争者。
那么日本男性心目中理想的女性是怎样的呢?宝塚团训“清、正、美”三个字回答了这个问题。清纯正直美丽,这是多么令人赞赏的女性气质。何谓清纯?就是不复杂,不成熟,易于掌控;何谓正直?就是认同男性定下的社会行为准则,并且按照这个准则约束自己;何谓美丽?除了容颜娇美,还必须心灵唯美,既让男人赏心悦目,又能装点世界,并且能让她所依附的男性有面子。这里面没有提到女性的智力,女性的福祉,女性自身的重要性,而全部都是男性们心里理想的女性形象。波伏娃说,所谓女性气质,就是显得软弱、无用和温顺,任何自我表现都会削弱她的女性气质和魅力。在这样的信条下,宝塚生徒们在管理层心目中的价值与其说是通过塑造自己健全的人格来获取,不如说是根据男性们的理想去塑造自己而求得。
宝塚还有另一点从未明说,但却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准则,那就是“男役中心制”。宝塚歌剧团不论是台上的演出还是台下的诸多社会活动,都是以男役为中心的。上演的剧作,永远都是男人戏,娘役只起到陪衬的作用,而日本社会对于宝塚的印象,也被“男役”一词所代表了。举几个例子,1996年,宝塚歌剧团从德国引进了音乐剧《伊丽莎白》的版权,将其搬上宝塚的舞台,在德语版、还有后来的法语版、匈牙利语版中,都是以女主人公伊丽莎白为第一主角的,但是到了宝塚,第一主角变成了男性角色Der Tod,这部戏成为宝塚平成以来的代表作和最卖座的剧目。宝塚版的《飘》,主人公不是斯嘉丽,而是白瑞德;宝塚版的《阿依达》,主角不是阿依达,而是拉达梅斯;宝塚版的《卡门》,主角也不是卡门,而是何塞。宝塚所有的戏,都是围绕男役去写的,歌颂的是男人,关照的是男人,体现的也是男性的意志。在外部活动中,也是男役们全盘占领的格局,虽然都是女性,但由于她们中的一部分扮演的是男性,因而就比另一部分占有更多的优势和社会资源。这不能不说是男性意志在宝塚的体现。
五 隐含男权观念的本质
为什么,宝塚会走上这样一条体现着男性意志的道路?因为男性们能从改造事物中获得巨大的快感,他们热衷于让事物浸透着他的意志。塑造女性的形象,植入男权观念的本质,女性就像是他们手中的一块泥,被动地任他加工,任他塑造。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还讲到这样一句话:“在资产阶级社会,女人必须起的一个作用就是要有优雅的风度;她的美丽,魅力,智力和典雅都是她丈夫财富的明显外在标志。女性不仅满足了男性的社会虚荣心,它还是一种更深层自尊的根源,丈夫不仅在性爱方面,而且在道德与智力方面‘造就’了他的妻子。他教育她,加记号于她,在她身上打上他的烙印。[4]205
宝塚的剧作传达着这样一种隐含的信息:去臣服于男性吧,那才是你们与生俱来的归宿。你们不需要很辛苦,自然会有一位骑士将你们从苦难的深渊中解救出来。你所要做的,就是维持自己的美貌和优雅的风度,而不至于让他面对你的身体时倒了胃口。
从这种角度上来说,宝塚的女演员们不是不结婚,而是嫁给个男性这个性别。她们扮演着男性们需要的各种角色,有时候是母亲,抚慰他的伤口;有时候是妻子,带着炽烈忠贞的爱情投入他的怀抱。宝塚男役的养成时间非常漫长,通常都需要十几年,其中还会有各个不同的阶段,比如初舞台时期,新人公演时期,作为年轻明星的时期等等,这些生徒在宝塚剧团十几年的磨练和成长,会经历很多感同身受的喜怒哀乐,所以对于那些从这个生徒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她的观众们来说,这个过程与母亲养育孩子并无二致。一个母亲将自己青春的十几年都献给了孩子,当孩子独立而去,从自己的生活中生生脱离,这种巨大的空洞感被宝塚生徒们填补了。在宝塚生徒们的身上,年迈的母亲们再一次找回了年轻时的感觉。生徒们需要呵护,生徒们需要鼓励,生徒们需要有人关注着她们的成长,正像那些母亲的孩子们曾经需要的那样,而观众给了生徒们以足够的呵护、鼓励和关注。
生育职能之于女性,是一种排他性的选择。女人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如何将她的生育职能与生产职能协调起来,然而这种协调有时候又是非常困难的,选择了其一就无法兼顾其二。而男性话语权下的社会,将生育职能放在生产职能之上,因为社会要延续,女人就必须为社会提供孩子,女人也就必须成为某人的妻子,某人的母亲。宝塚歌剧团一直在做的,就是鼓励女性在生育职能和生产职能之间选择前者而非后者。从宝塚所上演的剧目中也能很清楚的看到这一点——1992年雪组公演《忠臣藏》,反映的是一群武士为自己的主公报仇的故事,武士们的妻子唱着“这就是武士的道路,男人的道路”来送丈夫们踏上复仇之路;1974年初演、迄今已经上演超过二千场的《凡尔赛玫瑰》FM篇,讲述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法王路易十六的皇后玛丽·安东瓦内特和情人菲尔逊的故事,在玛丽被愤怒的民众送上断头台之前,菲尔逊曾前往劫狱,但是玛丽不愿意跟他走,宁愿受死,当时她说的是:“请让我有尊严地死去,作为法兰西的皇后,两个孩子的母亲,有尊严地死去。”作为一个女性,为了男性而舍弃生命去实现的封建忠义观,她们应该完全理解并且支持;而她们自身所诉求的尊严是作为某人的妻子、某人的母亲死去,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活下去,女性生命价值之低下由此可见一斑。但是女性角色的类型也有例外,同样是《凡尔赛玫瑰》的另一位主要角色,奥斯卡就是一位女性,从小被当作男孩子养大,最后成为一名杰出的女军人,战死在攻占巴士底狱的战场上。这是一个非常丰满立体的角色,只可惜,在宝塚舞台上也是由男役来扮演的,而且与其说是一个很高尚的女性形象,不如说是一个很完美的人的形象,无关乎性别。
结语
运用女性观众们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男性们成功地将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的价值观念输入到了女性的意识中。在本文的行文过程中,笔者发现,如果用文化学的视角来观察宝塚歌剧团,我们就会发现,这同时也是一个在文化血统的归属上不甚清晰的表演团体,东方和西方的基因在她的血液中混合着、共生着,使得其绽放出变化万端而无法分辨的复杂风采,关于这一点,笔者拟撰文另述。
宝塚歌剧团,是一个混合着层层矛盾和冲突的文化现象。她既是日本女性们在男女不平等社会中可以实现自我价值的地方,更是男性们手中的一个工具,用来怀柔,用来洗脑,用来向女性灌输畸形的价值观。歌舞着的女性和观看着的女性,她们中间有着一条十分狭窄但是无限深刻的沟,你可以说,台上的人们实现了台下人们的梦想,你也可以说,台上的人们误导了台下的人们。这种矛盾,大概日本社会存在一天,就一天不会改变。
宝塚歌剧团已经出现了女性理事、女性编剧、女性导演,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正像《凡尔赛玫瑰》中奥斯卡所说的那样,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新世界会展现在我们眼前。
宝塚歌剧团将去向何方,让我们拭目以待。
[1]郭士征.浅析日本女性劳动力市场的现状和问题[J].现代日本经济,1991(01):23.
[2]〔日〕川崎賢子.宝塚というユートピア[M].东京:東京岩波書店,2005:3.
[3]〔日〕河竹登志夫.戏剧舞台上的日本美学观[M].丛春林,译.北京:中国戏剧学院出版社,1999.
[4]〔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