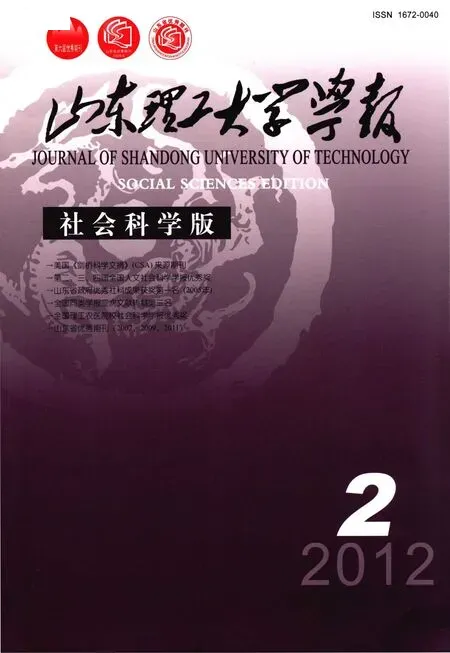论五四文学作品中的死亡—再生原型
2012-04-12陈强
陈强
(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淄博255049)
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求新求变的时代,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启蒙的时代,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中西方文化碰撞的时代。在这个打破黑暗、渴望光明的时代,涌现出了一大批思想上的激进者,涌现出了“摩罗诗人”般的思想的先觉者。他们率先觉醒,高举着科学、民主两面大旗,带着“重估一切价值”的批判精神,用自己的行为来打破这许久的黑暗,试图唤醒世人的觉醒。但殊不知,面临着尘封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先觉者”的行为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先觉者与愚昧者”之间的鸿沟难以逾越,先觉者痛苦万分,孤独、彷徨、疯狂成为他们的主情绪,“狂人”、“疯子”等字眼一时间成为了他们的代名词。但是,面对这个万恶的旧社会,“破旧布新”成为五四时代的主要任务。因历史进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变革的深层要求,五四文学也必然会对此做出“现代性”的回应。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狂人”、“疯子”、“零余者”、“孤独者”等摩罗式人物的大量出现,正是最直接的反映。
那么,是否这一系列新形象的出现仅仅是时代情绪或心态的反映呢?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其中必然也蕴藏着民族的深层文化内涵。
一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1]1文学是具有时代性的,与其产生的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不可否认,真正表现出时代特点、社会现实、个人体验的文学作品必然与人类或某一民族长期积淀下来的诸如人生、生命、审美、死亡、复活、焦虑、恐惧等永恒问题相遇。相遇的方式一方面可以体现在作品的情节上,如《凤凰涅槃》就是通过“凤凰”集木自焚后再生的情节与复活问题相遇的;另一方面也可以体现在作品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上,如《一生》,就是通过对“伊”的塑造来探寻永恒的生命问题。与历史永恒问题的相遇,必然会使文学作品中的意象与人类历史中经久不衰的某些“原型”相叠合,如海洋是生命的原型,洪水是灾难的原型,等等。
西方著名现代美学家、文学理论家荣格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理论,即远古人类在生活中形成的、世代相传的,并使现代人与原始祖先相联系的深层的心理体现,是无意识的深层。在“集体无意识”中必然隐藏着众多的“原始意象”即“原型”。原型是人类童年时代生存状况的模糊底片,代表着生命存在最基本的需要和最原始的欲望。这些“原始意象”世代遗传下来,存在于人类的无意识深处,潜藏着巨大的生命力量,能够帮助人类经久不衰地生存下去。这些已经形成了的生命意象,它们是最难消解的。五四之所以发生,是根源于历史变革的内在要求,或者说面对亡国灭种社会状况而产生的长久的文化焦虑和危机意识。传统文化虽也有一定的有价值的部分,但是从整体上与西方先进的现代文化进行对话时明显处于弱势,业已失去了生命力,迫切需要再创造。这一种文化焦虑正是长期存在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它的无意识深处正与最为久远的那种永恒的生命忧患意识相遇,并深藏着原始意象——死亡再生原型。当然,破旧布新的社会现实也必然会激活、唤醒这种原型。
然而这“原型”在日常生活中是看不见的,多存在于民族神话、传说、风俗中。荣格就很重视神话,他认为,如果“失掉了神话,无论在哪里,即使在文明社会中,也总是一场道德灾难”。[2]125在“五四”这个破旧出新的年代,面临着大变革大转折时代的召唤,作为对这一时代呼应的文学作品,通过对某些神话进行改写这一途径,表现着对这个时代独有的感触,如《凤凰涅槃》、《女神之再生》等。《女神之再生》是《女神》诗集中的一篇经典作品,就是郭沫若利用了“共工与颛顼争帝,怒而触不周山”以及“女娲补天”的神话故事尽情地渲染对旧世界的诅咒和对“美的中国”的渴望。在诗中,补天的神女们说:“我们尽他破坏不用再补天了!”她们“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而且创造的这个太阳“要照彻天内的世界,天外的世界”。这首诗歌,在神女们决定不再补天前,对这一争斗进行了大胆的诅咒,她们眼前的世界是“不和谐”,是“罪恶的交鸣”,是“喧嚷的声音”……在这场争斗中,“五色天球要被震破”,“太阳只在空中睡眠”……毫无生气。面对这种争斗,女神们断然做出了自己的抉择,那就是告别以补天为己任的过去的自己,决定不再补天,而是用自己的努力去创造一个新的太阳。女神们采取了与过去告别的方式,用自己的行为来反抗这个旧世界,以获得新生、获得再生。“女神的再生”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她在女娲开拓的优美世界中,音乐响彻、花开月圆,生命自由自在,循环往复。虽然太阳还在远方,但是希望也在前方,新的世界也很快到来。郭沫若的《女神之再生》充分体现了作者对破旧出新的歌颂,同时也象征着中华民族对光明的渴望。任由“破了的天体”破去,象征着旧世界的离去;创造一个“新的太阳”,象征着新世界的来临。可以说,从女神这个死亡再生原型里,几代人学会了从痛苦中看到欢乐、从绝望中看到希望、从黑暗中看到光明,所谓“绝望之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二
原型往往是经过历史的沉淀而深藏于人类内心深处或者是无意识深处的,在正常情况下很难显现,只有在某种特定条件下才会被激发出来,如梦境、妄想,等等。在五四这个特殊情况下,作者们往往运用“梦幻”等方式抒发自己的感慨,表现自己的思想。梦幻的破碎性、虚幻性、片段性给书写带来了无限的可能,也为日常看来荒谬的事件、话语等赢得了表现的空间。鲁迅的许多作品就将“梦”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段,《死火》、《狗的驳诘》、《失掉的好地狱》、《死后》、《墓碣文》、《颓败线的颤动》、《立论》等均以“我梦见”开篇。这几篇作品均出自散文诗集《野草》。在五四退潮期,作者面对着“《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的严酷现状,不禁抒发些许感慨才结集成了《野草》。在这个时期,鲁迅的内心十分痛苦,他迫切需要表达内心的痛楚、对未来的希望、对前行者的尊敬等,于是便选用了“梦”的书写方式。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在那个年代虽然是一种“策略性”的选择,但是,“梦”的出现从集体无意识理论出发也有其更深层的原因。王乾坤分析荣格的理论时提出“人类内心的、固有的因素和先验模式,可以随时同新的个性感性材料相结合,生成新的艺术体验”。[3]339正是借助于“梦”这种表达方式,鲁迅才能够借助于梦境或者是虚幻的景象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的认识和感慨,才能够更深入地剖析内心的彷徨、痛苦与无奈。在这里,一系列看似荒诞的事情或者人物突然间变得符合常规,“坟中坐起的死尸”、“死后坐起的我”、“永远前行的过客”等等意象也成为了“圣甲虫”这一原型在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再生。
“死亡”从表面上看是代表着生命体征的结束,代表着生命的幻灭,是一种悲剧情愫,令人生畏。但是真正令人生畏的不是肉体的幻灭,而是精神的死亡。“死亡”的表层下实际上隐藏着巨大的能量,那是一种精神的再度升华,那是对现实更加清醒的认识,那是一种思想的觉醒。《过客》中那个永远前行的过客,虽然不知前方到底是哪里,但是他依然前行,跟随着先觉者的呼唤向着目标奋进,也许某天过客会死去,但是他的精神永远存在;《死火》中难逃死亡命运的冻火,宁肯牺牲掉自己的生命,依然为我走出山谷提供光明;《死后》中已经死去的我当看见“一闪的火花”,“于是坐了起来”,复活成功……。鲁迅曾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说,《野草》中的作品“多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它们在绝处逢生,这就预示着在绝望中深蕴着希望,在黑暗中孕育着光明。
三
实际上从五四时期的某些作家的创作看,也是贯穿着死亡再生原型的,如郁达夫、许地山,等等。郁达夫早期小说的代表作《沉沦》通过对主人公“迷狂”的行为和变态心理的描写,凸显其内心的痛苦,最终无法救赎而走向毁灭。可是后来郁达夫从日本回国后,创作倾向就发生了转向。在《春风沉醉的晚上》中作者塑造了两个新人的形象:一是陈二妹,一是作家“我”。这个“我”已经不同于《沉沦》中的零余者,而是逐渐摆脱了“自卑”心理,走向新生。这一时期的创作就不同于前期的作品,而重在写再生的主题。许地山的创作也印证了这一现象,前期《命命鸟》中的敏明和加陵由于爱情受阻而双双走入绿绮湖。他们只会把希望寄托于虚幻的来世,并不曾想过要坚决反抗,反代之以消极的轻生。许地山随后创作的现实主义小说《春桃》一改前期创作中的宗教色彩,塑造了一个坚强、独立、自强的女性形象。春桃即使生活十分艰苦,但从未想过死,还是一直坚信“苦也得想法子活”。这些作家前后期创作主题的不同恰是应了死亡再生的原型要求。
四
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还模塑了一系列的“理想人物”,他们身上同样埋藏着死亡再生原型。弗洛伊德曾经说过,“幻想的动力是未被满足的愿望,每一个幻想都是一个愿望的满足,都是一次对令人不能满足的现实的校正”。[4]32每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都会不时地创造着幻想,正如“夜有所梦”一样,每个人也是光天化日下的梦幻者,编织自己的“白日梦”,作家也不例外,他们往往在创作时无意识地表现出他们的“白日梦”。五四时代就出现了一些在“白日梦”状态下进行书写的作家,如蒋光慈、冰心、王统照等。而这些作品也同样含有死亡再生原型,都在宣称旧世界或旧我之死亡,呼唤新世界或新我之诞生。1925年,蒋光慈的诗集《新梦》出版。《新梦》表现了作者渴望“极乐国”——共产共享的共产社会到来的美好愿望。但推翻旧有社会,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一带有理想化、浪漫化色彩的“新梦”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只能是作家的幻想而已。此外,冰心、王统照等宣扬抽象的“爱”和“美”的哲学,主张用“爱”和“美”来解决世间一切问题,这无疑是带有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的。《超人》中这样描述其主人公:“何彬是一个冷心肠的青年,从来没有人看见他和人有什么交往”。但就是这样一个“冷”人,却在禄儿感激自己而送来一篮子金黄色的花和一封信后,就毅然被禄儿身上的“爱”所启迪,得到了感化,树立起了对生活的信心。同样在王统照的《微笑》中,一个女犯人的“微笑”竟然感化了一个小偷,使他走上了新生,成为了一名工人。虽然,这些作品都带有浪漫色彩,只是作家的“善良愿望、美妙幻想和感时愤世情绪的一种真诚的倾吐”,[5]533但是不可否认,作家在这些作品的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抛弃旧我、渴望新生的憧憬正是与死亡再生原型相吻合的,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集体无意识”的再次呈现。
五
一部作品本身会显示出两种成分,“最近的诱发场合和旧时的记忆”。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现实的强烈经验会唤起作家对早年经验(通常是童年时代的经验)的记忆。”[4]36这种直接经验或回忆会直接影响到作家的创作,死亡再生原型同样出现在从这种角度进行创作的五四文学作品中。鲁迅的童年记忆是酸苦的,他的童年回忆和现实经验使他更加深刻地洞察了世人的真面目和封建伦理道德对国民的毒害。因此,“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成为他创作的重要目的。如祥林嫂(《祝福》)和孔乙己(《孔乙己》)就是被封建制度毒害的典型,他们虽然都死去了,但决不是自然的死亡,他们是被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压死的。他们的死亡从更深意义上讲,是意味着封建制度、封建思想的灭亡。换一角度讲,也正体现了人们呼唤新思想、新社会到来的急迫心情,更预示着另一种新制度的建立。这正好与作者渴望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愿望相融,触动了深藏在人类心中的渴望再生的“集体无意识”。
综上所述,在五四这个“大变革、大破坏”的特殊年代,死亡—再生原型的频现有其必然性。作者们力图借用这一原型来激发人们思想深处的集体无意识,来表现对旧世界的憎恶和对新世界的渴望,而这些正应合了五四时代先觉者的要求。“死亡只是代表了暂时的恶,它定时发生,但肯定有新的生命的诞生来取而代之。生命和死亡的正常周期是一种健康的周期”。[6]236我们应从中学会冲破“死亡”的黑暗,在死亡中寻求再生,在黑暗中寻求光明,最终实现瑰丽的凤凰涅槃。
[1]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瑞士]荣格.集体无意识和原型[A].文艺理论译丛(第1辑)[C].马士沂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3.
[3]王乾坤.鲁迅的生命哲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4][奥地利]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美文选[M].张唤民,陈伟奇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87.
[5]朱德发.中国五四文学史[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
[6][美]古尔灵,等.文学批评方法手册[M].姚锦清,等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