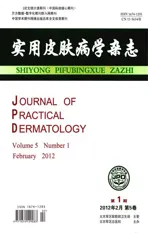关注抗组胺药治疗慢性荨麻疹应用的策略
2012-04-12宋志强
郝 飞,钟 华,宋志强
以往的研究认为抗组胺药物通过拮抗H1受体来阻断组胺与受体结合,从而影响变态反应发生的过程,是治疗慢性荨麻疹的基本药物。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抗组胺药不仅可以阻断组胺的结合通路,还可通过其他机制发挥更广泛的药理作用,为临床用药策略提供新的选择方案。目前临床上对抗组胺药物的选择及其使用方法较为混乱,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合理用药的现象。为此,本文就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1 抗组胺药作用机制研究是临床用药策略变化的依据
传统上讲,抗组胺药通过竞争性地与H1受体结合,从而阻断组胺引发的生物学效应,是抗组胺药发挥抗变态反应作用的经典机制。受体竞争性结合机制对药物提出以下3点要求:①受体亲和力高;②高选择性作用于H1受体;③与受体结合后药物解离速度缓慢。近年来研究发现,第二代抗组胺药不仅有抗组胺作用,而且可通过多种机制起到非特异的抗炎作用,包括抑制肥大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释放递质、对炎症细胞游走和激活的抑制和影响内皮细胞黏附分子的表达等[1]。 抗组胺药发挥抗炎症作用机制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途径实现:①非H1受体依赖性,即通过药物与膜离子相互作用(drug-membrane ionic interactions),抑制跨膜钙流出道活性和cAMP产生,稳定肥大细胞和嗜碱粒细胞膜,从而减少细胞内炎症介质的释放;②H1受体依赖性,即通过抗组胺药与H1受体结合,通过细胞内一系列G蛋白偶联反应影响NF-κB活性,从而减少细胞内炎症因子的产生。应该指出,不同抗组胺药在体内外实验中均具有抗炎症作用,但这种作用究竟有何临床意义仍值得进一步研究,尤其是在治疗剂量下如何较好发挥抗炎症作用。开发明确具有抗炎症作用的抗组胺药是今后研制的方向[2]。
研究认为,H1受体存在两种不同的活化状态即激活和非激活状态。正常情况下两者处于动态平衡之中,可以相互转化。组胺可以使活化型受体稳定,而抗组胺药使非活化型受体稳定。这一理论改变了抗组胺药典的通过拮抗组胺与受体结合而发挥药理作用的原理,而是作为反激动剂,可以在组胺缺乏的情况下实施对组胺受体活性的抑制[3]。
基于药理特性的差别,可将抗组胺药分为:①第一代抗组胺药或镇静类抗组胺药。上世纪40年代进入临床,以中枢镇静作用显著为特征,代表性药物有苯海拉明、氯苯拉敏、羟嗪、曲普利啶、氯马斯丁、异丙嗪等;②第二代抗组胺药,也称非镇静抗组胺药,其中枢镇静作用较第一代明显减弱,代表性药物有氯雷他定、西替利嗪、咪唑斯汀等。③第三代抗组胺药或新一代抗组胺药,其界定有一定的争议。有人提出以此类药物无中枢镇静作用为标志,也有认为以有明确抗炎作用为标志;此类药物多为第二代抗组胺药活性代谢物,代表性药物有地氯雷他定、非索非那定、左西替利嗪等。
2 抗组胺药物应用策略需要更新
慢性荨麻疹患者目前的治疗现状仍然是以控制组胺释放所致的一系列反应为主。因此,抗组胺药成为治疗的基本措施。按照抗组胺药竞争性与H1受体结合的理论,第二代抗组胺药物因其与H1受体亲和力高和选择性强,且在有效拮抗H1受体的同时对其他受体亲和力小,从而避免了第一代抗组胺药物的某些不良反应。同时,每日口服一次,即可以维持24小时疗效,患者依从性也明显提高。因此,第二代抗组胺药成为荨麻疹治疗的第一选择。
同样是第二代抗组胺药物,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别。西替利嗪仍有不同程度的镇静作用,尤其是增加剂量情况下更容易出现;阿伐斯丁因半衰期短,需每日2~3次服用,影响患者依从性;咪唑斯汀有明确的抗5脂氧合酶作用,通过拮抗白三烯代谢而兼有独特的抗炎症特性[4],但咪唑斯汀、氯雷他定需要经肝脏药物代谢酶(CYP450)代谢,需注意潜在的药物相互作用和心脏毒性(主要是Q-T间期延长),且严重肝功能异常患者需慎用。
当第二代抗组胺药物治疗无效时,欧洲荨麻疹指南中明确提出:增加剂量为优先选择;欧洲变态反应协会和英国变态反应和临床免疫协会也共同主张:对治疗无效病例增加药物剂量是优先考虑的治疗策略[6]。治疗无效的原因可能是抗组胺药物不能全面阻断肥大细胞活化后的3个事件,即脱颗粒、炎症因子合成和释放以及前列腺素代谢等[5]。有研究发现,抗组胺药物治疗无效的病例,其组织中以多形核细胞浸润为主,血中除存在组胺外,还表现有白三烯、前列腺素、细胞因子等多种炎症介质不同程度的升高。因此,抗组胺药物要想提高疗效,应更加关注于其抗炎症作用;而增加抗组胺药物的剂量,可达到这一目的。增加剂量的前提是保证治疗的安全性,并得到患者的知情。临床推荐地氯雷他定、氯雷他定和西替利嗪为选择增加剂量的药物。加量无效的患者可以采取联合治疗。严重且治疗抵抗的患者可以短期(3~7天)使用皮质类固醇激素,要慎用并防止药物的副作用。
单纯第二代抗组胺治疗无效时,第一代抗组胺药物应该成为联合治疗的首选。应客观评价第一代的抗组胺药在控制荨麻疹中的作用,尤其是疗效上并不比第二代差[6]。第一代抗组胺药物具有更广泛的药理作用,包括抗肾上腺素能、抗5羟色胺、抗嗜碱性粒细胞脱颗粒以及针对H4受体的作用(H4受体与瘙痒等关系密切),是发挥控制荨麻疹症状发作的重要基础。任何抗组胺药物的镇静等副作用与皮质类固醇激素、雷公藤多甙、环孢素等相比是很轻的,可以被患者接受。研究发现抗H1和H2药物抗组胺药物联合使用,主要是通过相互竞争性依赖肝脏药物代谢酶CYP3A4,从而提高抗组胺药物血中的水平,提高疗效,并非通过协同拮抗H1和H2受体而起作用。因此不依赖肝脏代谢抗组胺药物如左西替利嗪、地氯雷他定、非索非拉定等,与第一代抗组胺药联用显然无法有效提高临床疗效[4]。
为切实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减少停药后复发,抗组胺治疗有效后的维持治疗是关键。维持治疗的理论基础是抗组胺药可以作为反激动剂持久影响组胺受体的活化状态。激动剂和反激动剂理论引入对抗组胺药药理作用的解释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尤其是使用抗组胺药治疗慢性荨麻疹完全控制症状后仍需进一步使用一段时间维持治疗,以进一步降低组胺受体活化状态,防止因立即停药而引起疾病的反复。维持多长时间并没有临床大样本量的证据支持,通常主张一般荨麻疹患者需维持3~4个月,特殊情况下如物理性荨麻疹和伴有自体血清试验(ASST)阳性的患者需要延长到6个月或更长的时间,这在英国变态反应和临床免疫协会指南中有明确的建议[7]。应该指出,抗组胺药特别是第二代抗组胺药的安全性是可以得到保障的,长期服用对人体的不良反应是可以耐受的。
3 儿童和特殊生理条件下的合理使用
原则上,妊娠期间尽量避免使用抗组胺药物。临床观察发现,大多数慢性荨麻疹患者在孕期症状可以减轻或消失。但如果症状发作,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必须采取治疗。选择抗组胺时,应该告知患者目前无绝对安全可靠的药物,在权衡利弊情况下选择相对安全可靠的药物。有研究发现,数千例孕妇,包括在妊娠前三个月接受抗组胺治疗的几百例患者,接受氯苯他敏和氯雷他定治疗,表明其致畸率并没有增加;较大剂量的羟嗪和氯雷他定均可以在动物中致畸,因此主张西替利嗪、地氯雷他定、氯雷他定和羟嗪均不宜用于妊娠期[7,8]。研究还发现,大多数抗组胺药物可以分泌到乳汁中。比较而言,西替利嗪、氯雷他定、地氯雷他定在乳汁中分泌水平较低,哺乳期妇女推荐上述药物,并尽可能使用较低的剂量。有报道,氯苯拉敏可以降低婴儿食欲和引起嗜睡等副作用,应避免使用。
目前,非镇静作用的H1受体拮抗剂药物仍然是儿童荨麻疹治疗的一线选择。不同的药物其年龄限制和使用剂量有显著的差别,但多数抗组胺药物处方规定应使用在12岁以上患者。西替利嗪、地氯雷他定、左西替利嗪和氯雷他定都有小儿用的糖浆制剂。1岁以下的儿童仅可以使用氯苯他敏和羟嗪。但近期新的治疗手册提出:地氯雷他定、非索非那定可以用于6个月以上的儿童[8,9]。同样,在治疗无效的患儿中,可以增加剂量、联合镇静(晚上使用)和非镇静(白天使用)抗组胺药物治疗。在此基础上,可以试用H2受体拮抗剂和白三烯受体拮抗剂,后者可以在6个月以上的儿童中使用。
[1]郝飞, 叶庆佾. 第二代抗组胺药临床应用中的若干问题 [J]. 临床皮肤科杂志, 2003, 32(5):300-303.
[2]Jaurgui I, Ferrer M, Montoro J, et al. Antihistamines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urticaria [J]. J Invest Allergol Clin Immunol,2007, 17(suppl2):45-52.
[3]Estelle F, Simons R. Advances in H1-antihistamines [J]. N Engl J Med, 2004, 351(21):2203-2217.
[4]Greaves MW, Tan KT. Chronic urticaria: recent advances [J].Clin Rev Allergy Immunol, 2007, 33(1-2):134-143.
[5]钟华, 郝飞. 慢性荨麻疹的病理生理与临床 [J]. 中华皮肤科杂志, 2007, 40(10):652-654.
[6]Kapan AP. What the first 10,000 patients with chronic urticaria have taught me: a personal journey [J]. J Allergy Clin Immunol,2009, 123(3):713-717.
[7]PowellRJ, Du-Toit GL, Siddique N, et al. BSACI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chronic urticaria and angio-oedema [J]. Clin Exp Allergy, 2007, 37(5):631-650.
[8]郝飞, 钟华. 慢性荨麻疹发病机制和治疗策略的思考 [J]. 中华皮肤科杂志, 2010, 43(1):2-5
[9]Criado PR, Criado RFJ, Maruta CW, et al. Histamine, histamine receptors and antihistamines: new concepts [J]. An Bras Dermatol, 2010, 85(2):195-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