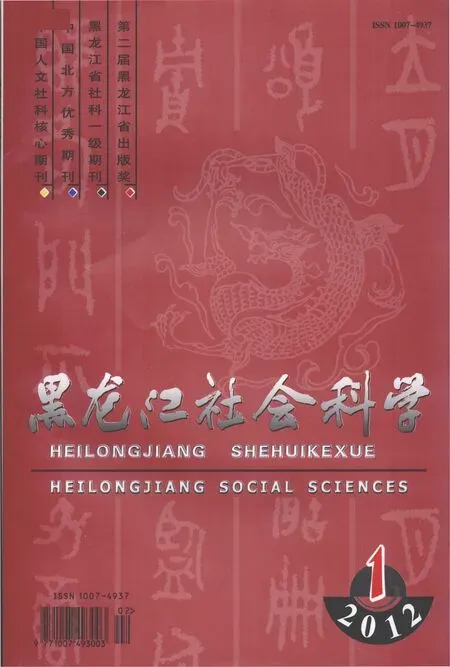后危机时期货币政策研究
——基于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启示
2012-04-12章曦
章 曦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100872)
后危机时期货币政策研究
——基于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启示
章 曦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100872)
源于西方货币理论的货币政策,必然出现只注重流通中的货币而忽视经济实体运行的理论异化。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认为商品流通决定货币流通,货币供给内生于经济实体运行,货币政策一定要建立在对实体经济调节的基础上,没有商品流通领域的结构调整,仅仅依靠宏观调控不可能解决经济中的顽疾。金融危机以来的中国货币政策实际效果表明,只关注流通领域的货币政策是有缺陷的,这也是马克思货币理论对现代货币政策的启示。
货币政策;商品流通;货币流通;马克思货币理论
自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以来,为了防止经济无可救药地陷入类似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全球各国无不采取扩大政府开支、向经济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的刺激性经济政策。危机似乎暂时度过,但随后却出现了严重的欧洲债务危机和世界范围的大通胀。当下,各国治理通胀的方法主要是紧缩政府开支和减少货币供给。从中国来看,自2010年上半年有通胀苗头算起至2011年8月底,央行频繁使用货币政策调控经济,货币政策收紧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是通胀猛于虎,紧缩性货币政策收效甚微。这是由于西方货币理论缺乏科学微观基础,从而导致其所提出的货币政策出现异化。对比和重新审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货币理论,对我们认识货币的本质和有效使用货币政策和反通胀政策大有裨益。
一、主流西方货币理论的一般缺陷
古典西方经济学对于总供给和总需求、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等都有非常精巧的描述,现代主流西方经济学更是建立在精致、复杂的数学推导和计量实证分析的基础上。但是,货币理论似乎长期游离于主流分析框架之外,通常所规定的弹性、供求决定价格的逻辑在货币世界里全都行不通了,取而代之的是货币层次的讨论、货币流通速度、货币量和实物量的对比等等,难怪开创宏观经济学的凯恩斯惊呼:“当讨论所谓货币与物价时,我们恍若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1]
西方经济学对货币的认识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马歇尔、瓦尔拉斯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他们认为货币不过是方便交易的一种工具,是覆盖在实物经济上的一层面纱,即“货币面纱观”;另一种是以魏克塞尔、凯恩斯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货币对于经济生活的影响不仅仅是交易媒介,货币对投资、资本转移的影响也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行,同时开创了现代货币分析的先河[2]。前者固执地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说,只有实实在在的产品才是真正的财富,并提出了货币数量和物价水平同方向变化的传统货币数量论。而后者以凯恩斯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为代表,坚信虽然货币运行有其独特的规律,但是货币量的波动一定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因为货币是财富的象征,社会个体财富的变化一定会影响微观个体的决策,从而对经济产生一系列的影响。
西方经济学关于货币和实体经济关系的争论,源于对货币本质认识的不同,是缺乏科学微观基础的必然结果。西方经济学认为货币就是国家法定规定用于支付的物品,这相当于说,一个东西之所以是货币,是因为我们规定它是货币。实际上,西方经济学直接回避了对货币究竟是什么东西的探讨,直接通过货币的功能“用于支付”来定义货币,这显然是一种取巧。弗里德曼甚至说:“它(货币)是一个有待于我们去发明的还不确定的科学的构成物,就像物理学中的‘长度’或‘温度’或‘力’一样。”当然这并不是说,不知道一个东西为何物的时候就没办法进行研究,比如企业内部长久以来被认为是一个“黑箱子”,但对于企业理论的研究从未停止过。然而要成为一门科学体系,内在运作机制是一定要弄清楚的,否则在实际操纵层面上永远是依照经验而不是规则。这也是导致现实中各国货币政策异化的重要原因。
二、马克思货币理论与货币供给的内生性
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在《资本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都有体现。马克思认为物品属于不同的所有者,为了生产和生活需要进行交换,表现彼此的交换价值,这是简单的物物交换。之后有一种商品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表现所有其他商品的价值,它自身则表现为交换价值,这种商品就是货币的原始形态。货币产生以后,任何私人劳动想要得到社会的承认就必须转化成货币,任何转化成货币的劳动都自动成为社会劳动,这是市场规律。因为个人的产品和劳动一旦和货币相交换,就加入到全社会的分工体系当中。在马克思看来,货币至少肩负了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储藏职能、世界货币的职能。货币在不同职能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担任流通职能的货币可以被储藏起来,而储藏货币因为交易的需要也可以被投入流通,即是说认识货币必须从“完整的货币形态”上来理解。反观西方经济学则是从货币的流通职能来肤浅地理解货币,然后再从这种片面的理解中推导出其他的职能。西方经济学至今仍然对货币流通层次中的M0、M1、M2(经济中的货币量)等概念争论不休,这也恰恰证明从流通角度定义货币必然要面临一些现实问题。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认为金属货币凝结了人类劳动,本身具有价值,但是当金属独立为货币并担当货币的基本职能后,它与后来的信用货币——纸币是没有差异的。“一般价值形式”到“货币形式”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变化,“麻布”和“金”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马克思认为货币的流通是货币职能的表面现象,不应当过分看重,“货币流通,作为整个生产过程的最表面的……和最抽象的形式,本身是毫无内容的”[3],货币的所有职能一定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
西方经济学的货币政策只关注货币的流通职能,调节的重点也是经济体中流通货币量的多少,这显然是选错了研究对象。反之,马克思认为货币流通是依附于商品流通的,“有多少商品从生产者那里出去,就有多少货币回到生产者手里”[4],“商品流通的性质本身造成了相反的假象……虽然货币运动只是商品流通的表现,但看起来商品流通反而只是货币运动的结果”[5]。也就是说,经济中货币的流通量由商品的流通量决定,因此研究的货币流通必然要建立在对商品流通研究的基础上。现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政府和经济学家意识到,经济中的货币量和通货膨胀并没有显著关系,短期内不宜采取单纯控制货币量的政策来控制通货膨胀[6]。即便如此,西方主流经济学还是确信货币供给是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工具。而马克思则认为,因为期票、汇票等商业信用形式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货币的作用,所以货币金融市场越发达,货币的供给与物价水平和商品的供给越没有关系。
三、货币政策理论的异化
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于货币本质认识的不同,不仅导致他们对经济运行中货币量认识的不同,而且使他们所提出的货币政策建议也必然出现异化。
现代西方经济学已经认识到货币供给有很强的内生性,流通中的货币层次对通胀的影响越来越复杂,但是基于薄弱微观基础的政策理论依然模糊。而西方货币政策理论则侧重研究货币数量与商品价格的关系、价格传导机制、货币需求的决定因素等内容[7]。以美国联邦储备局为例,一般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大都根据可得的主要经济指标,例如前几个月的CPI、PMI、失业率等数据作出相机抉择,而经济中的货币量(M0、M1、M2)依然是重要的参考指标,所谓的给经济下一个锚。但是,经济数据都是有滞后性的,即便采用最先进的计量方法进行预测也会出现困难。因为理性预期的存在,一项政策的颁布会改变个人、企业等微观个体的预期,并产生难以预料的行为结果,而关于预期的理论又是当今经济学研究最薄弱的环节。现实似乎也说明,这样的货币政策是有问题的。格林斯潘掌管美联储期间曾经依据经济数据相机决策的方法,将利率调上调下十多次,看似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一个“大平稳”时期,直到这次金融危机以后,人们才意识到在平静的数据下面是经济实体的惊涛骇浪。西方经济学在货币理论方面放弃了对于经济内在规律的研究,只是依据表面现象来被动地调节经济,与其说这是中央银行的无奈之举,不如说是因为西方货币理论缺乏科学微观基础所致。只调节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是对货币其他职能的忽视,而这样的简化是不符合基本逻辑的。
在马克思看来,货币同时肩负了价值尺度、储藏功能等多项职能,由于职能的改变,货币可以随时进入或者退出流通,所以西方经济学家从流动性出发去控制货币运动的想法是幼稚且徒劳的。事实上,在生产高涨的时候,货币被信用大量取代,社会只需要很少的货币量就可以保证交易的进行;而到了危机时刻,经济微观个体又会突然增加对货币的需求,一切商品都要求在此刻变现,货币由此变得“匮乏”起来;但危机过后经济复苏,货币又显得“过多了”。如果政府在危机时刻,违背经济规律增发货币,增加政府购买,强制地使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必然会染上“停滞增长”的怪病,治标不治本。“认为流通手段不足造成了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的缓慢或停滞,也是一种错觉”[8]。研究表明,一国的宏观调控应当专注于改善经济体制,专注于理顺经济中微观个体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调节经济中货币量的多少。近期的通货膨胀也说明,长期的、大规模的货币供给,在明显增大社会需求能力的同时,并不会产生相应有效的社会供给。
四、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货币政策效果分析
为了分析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货币量和物价水平的关系,本文选用MO层次的同比货币量增加率作为流通中货币量的指标,选用同比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作为物价水平的指标。研究发现,M0基本保持在月增长率10% ~15%左右,虽然2010年初和2011年初有过异常的偏离,但是随后恢复到平均增长水平;相比之下,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表示的物价指数变化则剧烈得多,大体上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并经历了持续9个月的通货紧缩。一方面是货币供给量的基本稳定;另一方面是经济的大起大落,货币政策似乎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以这段通货紧缩为分界点,分前后两个阶段进行重点分析。
第一阶段,伴随经济增速的快速下滑,物价水平骤降。自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兄弟投资公司破产起,直至金融危机达到高潮。中国人民银行配合中央政府4万亿的财政支出,开始频繁使用利率手段、公开市场业务,包括有极大乘数效应的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试图在国内经济受到外界经济冲击之前,尽可能地抵消经济衰退的影响。这一阶段的货币政策是“适度宽松”的,有不少学者认为是“极度宽松”甚至是“过度宽松”。从事后的数据上看,数量调控的货币政策似乎达到了“效果”,M0在这一阶段是平稳的,基本保持平均每月10%的增长。但是,货币量的稳定并没有带来经济的稳健,中国的物价指数从2008年9月的最高点开始持续下降,不到半年时间竟然出现了负值,到2009年7月经济到达谷底,当月CPI相比上年负增长了1.8%。在这一阶段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效果似乎并不显著,经济下滑的势头也非常明显。
第二阶段,主要表现为物价水平的不断上涨。此次危机源于大洋的另一端,中国的实体经济并没有出现大的问题,进出口的影响也很快被央行飞速的印钞机所掩盖,但是危机过后货币忽然显得“过多了”,CPI在2009年11月由负转正后,持续上升,通货膨胀的苗头已经显现。这时,央行确信通胀即将到来非得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不可。从流通中的货币量看,除2010年1月即货币政策转向的当期有所下降外,货币量基本保持稳定。但是,与货币量的稳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物价指数的持续飙升,到2010年年末接近5%的CPI月增长率,表明通胀也是毋庸置疑地来了。其中,受到美国自2010年11月开始的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2)的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新兴经济体面临着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威胁。随后,2011年1月由于银行信贷量的集中释放,流通中的货币量猛增了近一半。隔月央行再次使用货币政策工具,双双提高了银行体系的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并用央票进行了大量对冲。效果明显,2011年2月流通中的货币量恢复了10%左右的增长。这一阶段与货币量供应相对平稳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物价指数走出了近年来少见的持续上升态势,2011年7月份CPI更是达到了惊人的6.5%。M0的基本稳定可以证明货币政策的“成绩”,但是物价指数似乎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从始至终都处在明显的上升通道。所以从调节经济的角度看,这一阶段反通胀的货币政策是不成功的,不但没有抑制物价的上涨,反而有可能影响市场经济正常的价格机制,也会造成公众对更高通货膨胀水平的预期。
可见,从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现实来看,无论在面临经济下滑风险还是经济过热风险时,调控流通中货币量的货币政策的效果都不显著。这说明现代西方货币理论从流通领域去调控货币、稳定经济的做法并不理想,也不能通过实践的检验。
实际上,通货膨胀不仅仅是货币问题,也不能简单地依靠回收货币来解决。西方经济学认为物价上涨的直接原因一定是货币超发,既然货币发多了,那么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给出的“良方”就是收回多发的货币。马克思认为,因为货币供给内生性的特点,由交易需要所产生出来的货币一旦进入经济运行中,就不会有内在的规律将其反作用回去,就像泼出去的水一样难以收回。如果不顾经济规律,用人为手段回笼货币,必然使经济中的失衡情况越发严重。更为糟糕的是,由于随意增加或减少货币的供给,通过利率这个杠杆,实际投资的货币需求不易得到满足,宏观经济的整体调控有可能陷入两难:若政府担心经济下滑,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将鼓励证券和资本市场的投机,带来物价上涨和经济泡沫的可能;反之,若政府认为经济过热,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减少经济中的货币量,因为利率的上升银行收紧信贷量,实业界首先会受到影响,资金链紧张,投资信心下降,高利率产生的结果是投资服从于投机。在现实中,因为之前的金融危机和生产成本的上升,大量的民营资本退出实业界,多出来的货币量会被虚拟经济和证券市场的“大吸收器”所吸收,进入资本市场进行跟风炒作。这也是近一段中国资本市场涨势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根本原因。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由于短期货币量的持续增加,一方面并没有使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只是在原来消费结构上的累加,刺激了经济的波动;另一方面也没有使增加的资本找到更好的产业流向,大部分还是进入资本市场,而资本市场是不创造价值的。要解决经济中的通货膨胀问题不能仅仅关注经济中的货币量,马克思认为货币流通应当内生于商品流通,通货膨胀必须从生产环节着手解决,而政府则应着力理顺货币供给的市场机制。中国的货币供给机制中有很多非市场的因素,例如特有的结汇制度、地方政府的“供地融资”冲动、商业银行的利率扭曲等。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就要以市场自发的调节为基础,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的目的是为了修补市场的不足,而不是用来扭曲市场的。
可见,缺乏微观基础、只针对货币流通职能进行调节的西方货币理论治标不治本,在复杂的结构性问题面前,货币政策不仅不能达到稳定经济的目的,反而可能扭曲价格、利率等经济杠杆。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经济规律是不能背离的。货币政策要建立在对实体经济调节的基础上,没有商品流通领域的结构调整,仅仅依靠宏观调控不能解决经济中的顽疾。此次金融危机后的国内价格水平的大幅波动,货币只是表象,企图用调节货币量来消除危机是不可能一劳永逸的,我们应当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给市场发挥基础调节作用以必要的时间和空间。
[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252 -253.
[2]赵准.探究货币——马克货币理论研究[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0:6 -4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94.
[4]资本论: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80.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35.
[6]陈彦斌,唐诗磊,李杜.货币供应量能预测中国的通货膨胀吗? [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2).
[7]王聪.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货币数量理论比较研究[J〛.经济纵横,2010,(9).
[8]资本论: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41.
F820.3
A
1007-4937(2012)01-0093-04
2011-10-09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麦金农‘中国之谜’成因研究”(11XNH062)
章曦(1985-),男,陕西西安人,博士研究生,从事货币政策与金融体制改革研究。
〔责任编辑:陈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