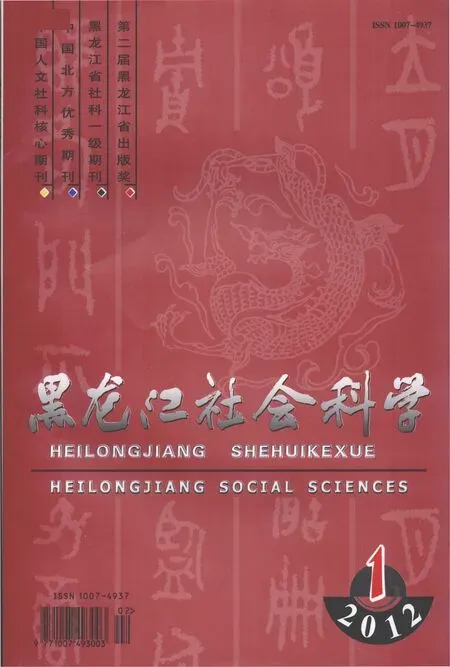马克思论意识形态与自由的精神生产之关系
2012-04-12黄力之
黄力之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a.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b.哲学教研部,上海200233)
马克思论意识形态与自由的精神生产之关系
黄力之a,b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a.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b.哲学教研部,上海200233)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把个人意识发展史、人类意识发展史和意识形态三者统一为一门学问,对意识形态学说有着积极影响。马克思于1842年创立德文“意识形态”概念,但同时通过对书报检查制度的批判,张扬了人的个体精神生产的自由本性,而不是定位于意识形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强调的不再是自由的精神生产,而是被控制着的意识形态生产。到《资本论》时期,马克思对精神生产内部有了深化的认识,开始对精神生产作出内部区分:一部分是直接反映阶级意志的意识形态,即“意识形态阶层构成的上层建筑”,另一部分则是更能反映精神自由特征的精神生产,即“最高的精神生产”。弄清楚马克思思想的内在构成,有助于发展真正自由的社会主义文化。
马克思;意识形态;自由的精神生产
通常的理解是,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思想、观念形态、精神世界都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不过,本文认为还应该有进一步的宽松化理解,就是说,还存在自由的精神生产范畴。
一、黑格尔关于人类精神生产过程与结构的基本思路
关于人的精神世界,黑格尔于1805年冬至1806年10月撰写了《精神现象学》,描述了个人意识到达绝对知识的历程,如何从最初的感性知识向科学发展,即形成哲学知识。黑格尔揭示了意识的两个方面:认识本身即主体方面和认识对象即客体方面。这两个方面的对立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显现为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意识在从它与对象的最初的直接的对立起到主客绝对同一的绝对知识止的运动过程中,经历了意识与对象关系的一切形式,产生了一系列的意识形态。可以说,《精神现象学》把个人意识发展史、人类意识发展史和意识形态三者统一为一门学问。
当然,黑格尔实际上并没有在《精神现象学》中使用德文的“意识形态”概念,只使用了法文“意识形态”一词,用于介绍并批判以特拉西为代表的观念学(意识形态)。所谓“把个人意识发展史、人类意识发展史和意识形态三者统一为一门学问”,只是从意识形态的实质来说的。
黑格尔在这里早于马克思揭示了意识形态现象的存在。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提出了“教化”和“异化”理论,对后来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创立具有直接的启迪意义。
黑格尔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教化是自然存在的异化。”即个体在伦理实体中的存在是直接的自然存在,而在法权状态下,个体就必须通过教化,扬弃自己的直接的自然存在取得现实的存在,即成为用社会意识形态构建的人。
教化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即一种群体意识,其前提是对个体进行思想工作,让个体接受,“国家权力……只有当它获得了现实的服从,它才是现实的权力,而它之所以得到这种服从,乃是通过自我意识判断出它就是本质实在,并且也通过自我存在对它作出了自由的牺牲。这种行动的结果,即将本质实在和自我消融在一起的行动,是产生了一个双重的现实,一是自我成为了真正的现实,二是国家权力的权威被接受为现实。”[1]必须注意这一说法,“通过自我存在对它作出了自由的牺牲”,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意味着公共思想的控制和统一,意味着个体精神活动的消失,如黑氏所说:教化乃是实体的观念、思想构成和普遍性向着现实的实在之直接的转化……。因此,个体教化自身的过程直接就是个体性作为普遍的客观存在的发展;这就是说,它是现实世界的发展。……教化显然就是自我意识在它原初的性格和才能的力量所许可的范围内尽量把自己变得符合于现实。因为个体的力量在于将自身变得符合于实体,即将它从自己的自身中外化出来,并从而将自身建立为客观存在着的实体。所以,个体的教化和它自己的现实性,即是使实体自身得以实现的过程。”[1]773
尽管个体精神生活在意识形态的过程中遭到了解构,但黑格尔并不认为可以忽视个体精神生活的意义。他认为,“一般精神既构成了个人的实体,同时也因此显现在个体之外,又提供给个人的实体以无机的自然。然而,从普遍精神作为一般精神实体的角度来看,文化的意义仅仅在于这个实体赋予自身以它自己的自我意识,使得它自己的内在的过程得以发生,并在自身中得以反映自身。”[2]他还说,“这样一来,意识就以意识形态的系统作为介乎普遍精神和它的个别性或感性意识的中项,作为精神生命有序地自我规定的整体,而这个中项发现它的客观存在的表现就是世界历史。”[3]461-463
由于个体的精神生活本质上是自由自在的,而非控制型的,但意识形态会不断地对个体施以影响,这样,至少在文明社会,人的精神生活过程体现出双重性,即自由的精神生产和意识形态生产的统一,就是说,“个体是自在地和自为地存在着的。……这样,对立就在个体自身内产生了;它就具有了这种双重性,即它既是意识的一种过程或一种运动,它又是一种具有现象特征之固定的现实性存在,一种在个体中而又直接属于个体自身的现实性存在。这个存在,既然是特定的个体的‘身体’,也就是个体的原初的源泉,或者说在制造个体的过程中,它是无所作为的。但是由于个体同时又只是它自己制造的东西,所以它的身体也就是由它自己所产生出来的关于它自身一种的‘表示’或表达式,也是一种符号或暗示,既是一种符号,那就不再是一种纯粹直接的事实,而只是个体借以显示其原初本性的东西。”[3]479-481
在此基础上,黑格尔区分出不同层次的精神世界,“第一个世界,是由它的分散着的特定存在,以及对它自身的个别确定性所构成的广阔王国……第二个世界含有类型,并且是自在存在的王国,或者说是与上述个别确定性相对立的本质真理性的王国。然而,第三个世界是功利世界,在这里,有用性就是真理性,真理性也就是自身确定性。信仰的真理性王国,缺乏具体现实性的原则,或者说,缺乏这个个别的自我确定性。但是具体现实性,或者说,这个个人的自我确定性,则又缺乏自在存在。”[1]925显然,这就是一个由自由的精神生产到一般的知识生产,再到意识形态生产的过程。
对黑格尔的这个庞大体系,恩格斯评价道:精神现象学也可以叫做同精神胚胎学和精神古生物学类似的学问,是对个人意识各个发展阶段的阐述,这些阶段可以看做人类意识在历史上所经过的各个阶段的缩影。”[4]这一评价告诉我们,关于黑格尔的理论,应该注意到对个体意识与人类意识的辩证区分,个体的精神生产与人类的精神生产有着发展的联系,但不可等同,个体的精神生产永远有着个体的特性。应该说,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直接影响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就是说,马克思一开始就注意到,精神生产一方面是个体的行为,另一方面是群体的行为,两者之间存在联系与区别。
二、青年马克思的自由精神生产理念
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异常的密切关系,但是实际上马克思并不拥有对这个概念的专利,法国哲学家、政治家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1754—1836)是第一个把“意识形态”概念引入思想史的人。材料表明,青年马克思十分熟悉法国意识形态学派包括特拉西的思想。早在1837年3月2日,马克思的父亲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曾建议马克思以滑铁卢战役为题材写一部戏剧[5]。马克思的父亲信中提到的是“意识形态”的法语词Idéologie,并且提到了拿破仑与意识形态学家的关系。马克思本人在1844年移居巴黎期间,已开始研读特拉西的《意识形态原理》一书,尤其是该书的第四篇和第五篇“论意志及其作用”。
1842年对思想史是有重大意义的,马克思在这一年创立了德文“意识形态”概念,就是说,“意识形态”不再是一个特定的法文概念,而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哲学概念。在《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一书中,英国学者柏拉威尔引用了法国当代哲学家亨利·勒斐伏尔《马克思的社会学》(企鹅出版社1972年版)一书的研究,指出“意识形态”这个术语从孔狄亚克和特拉西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个发展过程,并明确指出马克思于1842年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这个术语。柏拉威尔写道:“马克思在那篇林木盗窃的文章里,首次提出一个很快在他的思想里起中心作用的概念——‘意识形态’的概念。关于那些为维护林木占有者的权利而要求私人自由意志的人,马克思讽刺地写道:‘我们究竟应如何来了解这一突转急变的意识形态呢?要知道,我们在思想方面所遇见的只是些拿破仑的追随者。’”[6]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已经开始把法律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某些人类群体在思想上的合法性欺骗,形成虚假的社会意识,从而揭露了资产阶级法律的欺骗性。
但是,颇为有趣的是,就在1842年,马克思写了两篇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他通过对书报检查制度的批判,张扬的是人的个体精神生产的自由本性,而不是定位于一种意识形态。他说:“把书报检查制度看做我们优秀的新闻出版业的基础,这是多么不合逻辑的奇谈怪论!”实际上,“德国的精神发展并不是由于书报检查制度,而是由于违背了这种制度。当新闻出版业在书报检查的条件下枯萎凋谢、艰难度日时,这种情况却被援引来作为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论据,其实它只能否证新闻出版的不自由。”[7]150
马克思揭示出:“书报检查不得阻挠对真理的探讨,在这里有了更具体的规定:这就是严肃和谦逊的探讨。这两个规定要求探讨注意的不是内容,而无宁说是内容以外的某种东西。这些规定一开始就使探讨脱离了真理,并硬要它把注意力转移到某个莫名其妙的第三者身上。可是,如果探讨老是去注意这个由法律赋予挑剔权的第三者,难道它不是会忽视真理吗?难道真理探讨者的首要义务不就是直奔真理,而不要东张西望吗?假如我必须记住用指定的形式来谈论事物,难道我不是会忘记谈论事物本身吗?”
显然,马克思认为对精神生产是不能设定方式的,关键是追求真理的那种态度,设定方式只能限制人们对真理的追求。更重要的是,设定方式在实质上违背了精神生产的主体性,即个人的精神显示,从而扼杀了文化表现的多样性。
马克思明确地指出:“‘风格如其人。’可是实际情形怎样呢?法律允许我写作,但是不允许我用自己的风格去写,我只能用另一种风格去写!我有权利表露自己的精神面貌,但是首先必须使这种面貌具有一种指定的表情!
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的人,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豪放不羁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一片灰色就是这种自由所许可的唯一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适的表现;精神只准穿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花丛中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精神的实质始终就是真理本身,而你们要把什么东西变成精神的实质呢?谦逊。歌德说过,只有怯懦者才是谦逊的,你们想把精神变成这样的怯懦者吗?”[7]111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影响,“绝对自由的这个未分裂的实体,跻身于世界的王座,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有效地制衡它。”[1]931任何个体本质上都会追求自由的精神表达,人的个性有多少丰富性,精神生产的风格和成果就会有多少丰富性。即使在意识形态影响个体的过程中,这种精神生产的个性也会不同程度地存在,特别在审美文化的生产中,自由的精神生产性质就更具强烈性。
三、失去“独立性外观”的意识形态
到了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强调的不再是自由的精神生产,而是被控制着的意识形态生产。从表面上看,思想观念是人们自己自由创造的,但由于人本身是“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的,人们的观念形态也是受制约的。但是,分工的发展又使意识有了相对独立性,“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但是,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7]82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意识形态模式的精髓——“意识形态”意味着思想观念不是绝对独立的,而是受经济生活制约的。马克思的经典表述是:“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7]66“没有政治史、法律史、科学史等等,艺术史、宗教史等等。”[7]73“关于一个阶级内的这种意识形态划分:职业由于分工而独立化;每个人都认为他的手艺是真的。……关系在法律学,政治学中——在意识中——成为概念;因为他们没有超越这些关系,所以这些关系的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也成为固定概念。”[7]134-135
由于意识形态意味着社会生活中话语的真实性并不取决于本身,而是话语述说者的利益动机,这样,意识形态往往成为阶级话语的代名词,由此形成了意识形态的权力特征——意识形态不在乎自己的正确性,因为一定的统治权力需要它,马克思对这一特征作了如下经典式的描述:“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7]98-99
基于意识形态的控制性特征,阿尔都塞说:“意识形态把个体转变为主体。”“人本质上是一个意识形态动物。”[8]即意识形态通过教育等途径进入个体,使个体成了一个有见解能行动的主体。然而,真正的主体却是意识形态,因为它始终支配着人的观念。即使这样,也必须注意到马克思关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意识形态存在某种分裂的思想:“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在统治阶级中间表现出来,因此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玄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做主要的谋生之道,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并且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这个阶级的积极成员,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在这一阶级内部,这种分裂甚至可以发展成为这两部分人之间的某种程度的对立和敌视,但是一旦发生任何实际冲突,即当阶级本身受到威胁的时候,当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好像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而且好像拥有与这一阶级的权力不同的权力这种假象也趋于消失的时候,这种对立和敌视便会自行消失。”[7]99
这里是指,在统治阶级内部,作为实践家的人们和作为思想家的人们尽管在阶级利益上是一致的,但“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思想家可能会对实践家的行为表示不满或批判。这实际上就是思想的相对独立性表现。不能不认为,马克思在这里实际上又承认了作为个体的人,他在进行精神生产时,依然存在独立自由的追求,意识形态不可能消灭一切精神生产的自主性。
四、对自由精神生产的再度肯定
总体上看,自1845—1846年提出意识形态观以后,马克思关于自由的精神生产的说法越来越罕见。但是,到后来的《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对精神生产内部有了深化的认识,从而开始将意识形态与精神生产作出区分。
马克思指出了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关系的如下层次:“(1)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各种职能是互为前提的;(2)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对立,使得由各个意识形态阶层构成的上层建筑成为必要,这些阶层的活动不管是好是坏,因为是必要的,所以是好的;(3)一切职能都是为资本家服务,都为了资本家‘好’;(4)连最高的精神生产,也只是由于被描绘为、被错误地解释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才得到承认,在资产者眼中才成为可以原谅的。”[9]348
这里,马克思对精神生产内部进行了再次划分:一部分是直接反映阶级意志的意识形态,所以才有“意识形态阶层构成的上层建筑”这一判断,另一部分则是更能反映精神自由特征的精神生产,即“最高的精神生产”。
马克思对自由精神生产的肯定基于研究的方法论原则,他说:“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这样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9]346
关于精神生产的具体历史形态,马克思以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为例来加以说明。马克思提出了“斯密对牧师的憎恨”这个命题,他引用了亚当·斯密的话,说明在资产阶级还没有把整个社会、国家等等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时,只把教士、律师、医生、文人、演员、丑角、音乐家、歌唱家、舞蹈家等等视为社会的公仆,靠别人劳动的一部分产品生活,不生产任何价值。马克思评价道:
“国家、教会等等,只有在它们是管理和处理生产的资产者的共同利益的委员会这个情况下,才是正当的……这种观点具有历史的意义,一方面,它同古典古代的见解形成尖锐的对立,在古典古代,物质生产劳动带有奴隶制的烙印,这种劳动被看做仅仅是有闲的市民的立足基石;另一方面,它又同由于中世纪瓦解而产生的专制君主国或贵族君主立宪国的见解形成尖锐的对立。”[9]346
“一旦资产阶级占领了地盘,一方面自己掌握国家,一方面又同以前掌握国家的人妥协;一旦资产阶级把意识形态阶层看做自己的亲骨肉,到处按照自己的本性把他们改造成为自己的伙计;一旦资产阶级自己不再作为生产劳动的代表来同这些人对立,而真正的生产工人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并且同样说它是靠别的人的勤劳来生活的;一旦资产阶级有了足够的教养,不是一心一意从事生产,而是也想从事‘有教养的’消费;一旦连精神劳动本身也越来越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一旦发生了这些情况,事情就反过来了。这时资产阶级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力求‘在经济学上’证明它从前批判过的东西是合理的。”[9]364
马克思在这里明确划分了精神生产的两个层次:意识形态层次——“把意识形态阶层看作自己的亲骨肉”,自由精神层次——“也想从事‘有教养的’消费”,显然,“有教养的”消费,就是指宗教、艺术、哲学等精神生活。精神生产的精神文化价值就在资本主义历史形态中得到了确认。
关于资本主义时期不同精神生产的意义,柏拉威尔的分析更为细致。他对马克思所说“既理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也理解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进行了文本学分析,认为:马克思在这里实际上是指认审美文化的特殊性——自由性,他说,“这种论点是站得住脚的,即使我们必须承认,对这—段话的理解是有分歧的。马克思本人没有看到它的付印,而他的手迹又是这样模糊,后来的编辑者读做‘自由的精神生产’(freie geistige Produktion)的一句话也可以读做‘精细的精神生产’(feine geistige Produktion)。但是,不论读做什么,原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隐含地把文学与意识形态等同起来,而现在却把‘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同不管是‘自由的’还是‘精细的’方式作出区分,这是一个可喜的纠正。”[6]424
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体研究中,我们还可以看出,自由的精神生产是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一种克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指出,“这种经济关系——资本家和工人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两极所具有的性质——随着劳动越来越丧失一切技艺的性质,也就发展得越来越纯粹,越来越符合概念;劳动的特殊技巧越来越成为某种抽象的、无差别的东西,而劳动越来越成为纯粹抽象的活动,纯粹机械的,因而是无差别的、同劳动的特殊形式漠不相干的活动;单纯形式的活动,同样可以说是单纯物质的活动,同形式无关的一般意义上的活动。”[10]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的特征就是艺术属性的丧失,而作为精神生产的艺术性的创造是其他一切劳动都热烈向往的一种劳动,只有在这种劳动中个人才能体现和发展他的一切潜力。
柏拉威尔对马克思的自由精神生产的文化价值有一个更高的评价,他说:“马克思要说明的总的论点仍然是够清楚的。一个真正诗人的劳动能够保持——至少在密尔顿时代——不异化,只要他不计较市场价值。这样一个诗人出于他的心灵深处的要求,只写他非写不可的东西,而让别人去把他写的诗变成生产利润的商品。因此,他预示了一个‘自由王国’”[6]424的可能性,这就是《资本论》第三卷中的一段话:
“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11]所谓“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那就是精神生产。社会主义文化应该首先是这样的一种精神生产,以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商业文化。
[1][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3)[M].王诚,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1)[M].王诚,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45.
[3][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2)[M].王诚,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72.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45.
[6][英]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M].梅绍武,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下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475.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5.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28.
B1
A
1007-4937(2012)01-0008-05
2011-10-20
黄力之(1964-),男,湖南湘乡人,主任,教授,从事文化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姜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