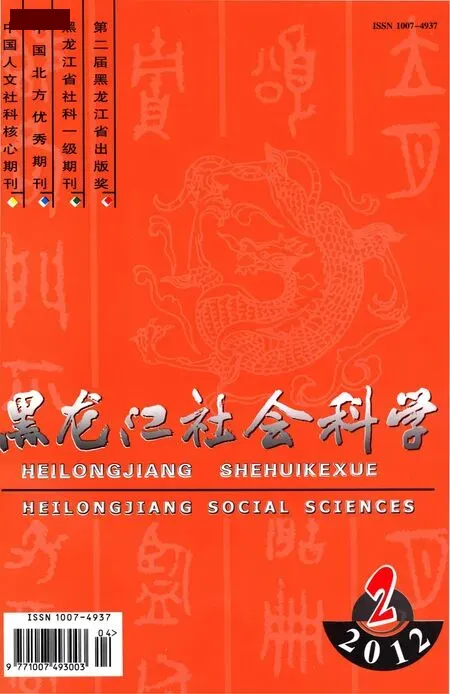当代多数主义民主理论探源
2012-04-12李鹏
李 鹏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广州510053)
当代多数主义民主理论探源
李 鹏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广州510053)
在人类社会中,有关民主理论的争论与民主的实践历史一样久远,古典民主与现代民主的争论占据了当代民主理论的核心领域。阿伦·李普哈特在梳理民主观念发展流变历程的过程中,发现民主的古今之争过多地集中在民主究竟应当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这个问题上,人为地夸大了古典民主和现代民主之间的隔阂,忽视了从古至今大凡主流的民主论者均把民主等同于多数人的统治,只不过古典民主的多数统治是多数人直接统治,而现代民主中则是通过“代议”这种方式来代表多数人的统治。由此,一种新的民主类型学,即“多数主义民主”把古典民主和现代民主又一次连接到了一起,重构了人们思考和研究民主的方式,并在民主观念史和民主类型学研究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
民主;古典民主;现代民主;多数统治;多数主义民主
随着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变迁,无数智士贤达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对民主的阐释以及围绕民主而展开的争论可谓浩如烟海,见证了民主思想的源远流长。然而,民主概念的诞生却并未统一人类有关民主政体的认识。伴随着民主实践的变迁,有关民主的思想也是莫衷一是、变动不居。进入20世纪以来,有关民主的思想和流派更是层出不穷。这一方面说明了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民主思想史与民主实践一样久远;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历史与现实的涤荡中一些人醉心于民主的过去,主张民主的理论和实践都必须与其本来面目相一致,而另一些人则依据变化了的现实对民主的理论和实践不断进行调整。对此,当代著名的民主思想史家乔·萨托利曾直言:我们当下正处在一个“民主观混乱的年代”[1]3。
然而,考察近代以来民主思想的发展和演化则不难发现,围绕着民主概念,即民主之所指而产生的理论流派之争涉及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有关古典民主和现代民主的问题,即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问题。而当代多数主义民主理论从民主的基本概念出发,在梳理民主观念发展变革的过程中却发现尽管民主经历了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但是不论是古典直接民主的拥护者,还是现代间接民主的支持者,他们均主张民主是多数人的统治。1999年,当代著名的比较政治学家、民主理论家阿伦·李普哈特在分析民主观念史的基础上把这种民主的多数统治论统称为“多数主义民主”,以区别于那些以分权、协商、共识为核心的民主类型,在比较政治学界和民主理论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古典民主理论及其批评者:从希罗多德到贡斯当
一般认为,克里斯蒂尼在公元前508年至公元前507年左右为雅典人建立了民主体制,从而开启了西方乃至整个世界民主政体的源头[2]。不久,古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创造了民主概念,用以指称克里斯蒂尼创立的民主体制。就现有的文献来看,《历史》一书成为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民主”概念第一次被刊载并被解释的人类民主思想的发端。在希罗多德那里,古希腊文的民主“Δημοκρατíα”是由人民“demos”和权力“kratos”两个词组合而成,因此,民主的词源学意义就是人民的统治或者人民享有权力。此后,大凡古希腊思想家们如修昔底德、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古希腊城邦民主政治的实践者伯里克利、梭伦等人都是在希罗多德的基础上理解和阐释了什么是民主这一问题。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政治学》可谓古希腊思想家研究和阐发城邦民主政治的经典之作,在当代学者眼中,他对民主政体的定义和比较研究乃是当今学界理解和比较研究民主政治的起点,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古希腊民主的本质就是“政事裁决于多数人的意志,大多数人的意志就是正义”[3]312。其主要特征为一切公民无论财产的多寡,均享有平等参与公民大会和在大会上决定国家重大事务的投票权[4]42-44;一切公民平等地轮番而治,公民的本质就在于参与政治,任何公职人员都有任期限制,除个别荣誉性职务外,不存在公职终身制[4]62。这种公民直接参与、亲自决定政事的民主模式被后人称为直接民主。
近代以来,尽管民族国家的兴起导致了人类政治生态的重大变迁,致使古希腊城邦式直接民主逐渐被斥责为一种不切实际的天外玄想。然而,即便是在规模庞大、人口众多的现代民族国家中,依旧不乏古希腊城邦式直接民主的虔诚信徒,而卢梭对直接民主的顶礼膜拜则构成了现代民主论争中古希腊情节派复兴古典民主的精神支柱。在古代城邦的直接民主制下,人被看做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人只有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才能彰显人之为人的价值,在一般公民的眼中不参与政治的人不配做城邦的公民,他们不是动物就是奴隶,而奴隶和动物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卢梭继承了这一观念,在他看来,民主之所以谓之民主,关键就在于人民能够亲身参与政治,亲自参与决定公共事务。公民资格的核心就在于参与政治,只有参与政治并有权就公共事务进行决策的公民才是自由的公民,只有一切公共事务都由公民亲手来做的国度才能算是一个自由的国度。因此,“国家的体制越好,在公民的精神里,公共的事情也就越重于私人的事情……在一个坏政府之下,就没有一个人愿意朝着那里(指代表公意的大会)迈出一步了,因为没有人对那里的事情感兴趣……只要有人谈到国家大事时说:这和我有什么相干?我们就可以据此料定这个国家就算完了。”[5]124-125“一旦公共服务不再成为公民的主要事情,并且公民宁愿掏自己的口袋而不愿本人来亲身服务的时候,国家就已经是濒临毁灭了。”[5]123-124遗憾的是,卢梭复兴直接民主的理想就像他那颇具“悲剧”色彩的人生一样总是与现实格格不入,充满了矛盾——直接民主的复兴就是要让现代民族国家回归到古希腊式小国寡民的城邦时代中去。在卢梭看来,民主制度只能在城邦规模很小且人口数量很少的情况下才能实现,“除非城邦非常之小,否则,主权者今后便不可能在我们中间继续行使他们自己的权利。”卢梭的这一主张显然有悖于历史发展的潮流,不仅沦为现代民族国家背景下乌托邦式的怀旧笑谈,而且还成为此后自由主义民主批评直接民主、论证和维护代议制民主的有力依据。
最早对古典民主理论展开批评的是贡斯当。在贡斯当看来,卢梭所理解的古希腊、古罗马城邦和中世纪城市共和国的直接民主实际上是古代人的民主。之所以谓之“古代”,原因在于直接民主兴起、繁盛于城邦国家,它们大多领土狭小,人口稀少,城邦之间的贸易和交往不发达,因此,政治的领域和范围非常小,更为重要的是奴隶们的无偿劳动为作为他们主人的公民提供了丰富的物资保障和闲暇时间去参与公共生活,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公民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城邦的军事生活和公共服务之中。然而,在现代,国家规模空间辽阔,不仅幅员广大而且人口众多。辽阔的疆域相对缩小了政治的规模,这使得所有人在同一个时间聚集在同一个地点决策公共事务的方式变得非常困难,同时奴隶制度的瓦解使绝大部分人不得不夜以继日地从事劳动和交换以图个人之生计,生存而非政治成为个人生活的第一要务。在这种背景下,私人生活逐渐替代公共生活成为个人价值的主要来源。
到了现代社会,人们对私人生活的关注有增无减。与古代人不同,现代人越来越注重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强调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是保障个人生活的前提和基础。“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已经成为历史,个人权利不仅脱离了公共权力的解释,而且还超越了公共权力。国家、政府和政治社会失去了独立的善,它们更多地被看做是保护个人权利的工具抑或被看做是个人权利的结果;从古希腊、古罗马城邦国家到中世纪的城市共和国,牢牢地套在公民资格头上的政治枷锁被打碎了,一个公民不会因为厌恶或者不参与政治而失去公民资格,不参与政治不仅被看做是个人的自由同时也被确认为个人的权利。据此,贡斯当认为,古代人的自由来自于民主,只有参与决策公共事务的人才是自由的人;而现代人的自由并非必须经由民主一途才能实现,他们的政治生活已经偏离了古代人的城邦式直接民主,并且越来越难以以直接民主的方式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与决策;越来越多的人强调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二分,因而越来越诉诸中间环节以求维护个人在政治领域之外或者不参与政治之自由的同时又保障个人对政治或者公共事务决策的影响力,“他们最多被要求通过代议制度,就是说,以一种假定的方式行使主权……自由给现代人带来的好处,是被人代表,是利用自己的选择形成代表。”[6]338
因此,如果古代人的民主是公民全身心地通过直接参与政治生活来决定公共事务,那么,现代人的民主则只能是兼职的公民,是满足了私人领域基础上最低程度地参与公共生活的民主。换言之,由于绝大多数人无法直接参与决定公共事务,那么只能从广大公民中选择代表来决定公共事务。贡斯当认为,诞生于英国的代议制民主既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又成为确保个人自由最可靠的手段,是庇护自由与和平的唯一的政府形式。在贡斯当看来,“代议制就是大众希望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没有时间去亲自保护自己的利益,于是委托一定数量的人做他们的代表。”[6]65
二、现代民主理论的兴起与发展
约翰·密尔直接继承了贡斯当的观念,全面阐述了一种个人自由优先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在密尔看来,现代民主的前提是国家、政府、社会权力与个人权利的明确划分,这就意味着现代民主的基础必须是自由主义的。每个人自己才是他本人唯一可靠的保护神,只有个人依靠他们自己的努力,他们的生活境遇才会实现主动、持续的改进,个人决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和幸福寄托于他人。一个自由的政府,必须把自由的权利普及到每个人身上,无论是谁,只要被排除在自由之外,个人权利就会失去保障,社会利益的增进和国家的持久繁荣将因此而受到限制。
故此,密尔认为我们无法假定当一个排他性的阶级掌权时,它会按照公共利益的偏好行动。在掌权阶级眼中,他们本阶级的利益就是全体的利益,这样的话,少数人的利益几乎毫无保障,掌权阶级会为他们本阶级而立法,一切将以掌权者唯命是从。英国和美国的例子说明了少数人统治之下大众多是消极被动,而多数人统治之下的大众则是自力更生、积极主动。因此,密尔认为,“平民政府比其他政府形式更为优越的”[7]。不仅如此,古希腊和罗马公民精神与国家繁荣之间的紧密关系更是说明:“能够充分满足社会一切要求的唯一政府是全体公民参加的政府;任何参与即使是担任最低的公共职务也是有好处的;这种参与范围的大小,应该始终和社会进步程度所允许的范围一样;只有允许所有的人在国家主权中都享有一份,这才是令人向往的。”[7]103-105
但是,密尔又认为,鉴于如今的政治社会范围广大,而且复杂性的程度也是过去所不能及的,因此“所有人亲自参与公共事务是不可能的,因而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一个完美政府的理想模型一定是代议制政府。”[7]105“代议制政体的内涵,就是由全体人民或者大部分人民,通过他们自己定期选举的代理人行使最后的控制权。这种权力一定存在于每一个整体的某一个地方。他们必须彻底掌控这个最后的权力。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必定是驾驭政府一切运作的主人。”[7]129因此,尽管代议制相比于古希腊直接民主而言,在公民与政治权力之间增加了“代表”这一中间环节,但它却是充分尊重和保护个人自由的民主体制,是现有的条件下平等原则和效率原则的最佳统一,是现实中最为理想的民主政体。
自密尔之后,现代民主只能是代议制的看法几乎成为学界的共识,直接民主似乎已经成为历史。尽管古希腊直接民主的光辉使一些当代的思想家不停地憧憬现代社会中直接民主的复兴,并为此对代议制展开激烈的批评,但最终还是无法突破代议制的框架。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自由主义理论家认为,古希腊思想家对民主的解释是对城邦直接民主的描述,而现代民主已经与古代民主相差甚远,古典民主的概念已经过时了。如果说密尔论证了现代民主只能是代议制,那么熊彼特则在代议制的基础上重新建构了符合代议制民主特征的民主概念。
熊彼特认为,现代民主与古典民主已经相差甚远,“民主政治并不意味着也绝不意味着人民真正在统治……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8]415。政治家或者精英是靠竞争来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现代民主的关键就在于选举的程序上,因此,民主成了选举领导人和竞争方法的副产品,也就是说竞争的方法产生了民主。熊彼特指出,现代“民主政治的意思只能是:人民有接受或者拒绝将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机会。”[8]415因此,民主的概念也就被“选民决定政治问题”替换为“选举作出政治决定的人”。熊彼特对民主概念的修正使他成为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奠基人,自此之后,一大批著名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家,如萨托利、达尔、艾克斯坦、李普哈特等人都视熊彼特的民主定义为现代民主的精神圭臬,并把竞争和选举看做是自由主义民主的核心。
作为当代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集大成者,罗伯特·达尔在熊彼特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并对当下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作出了突出贡献。对此,萨托利曾指出,熊彼特的终点是达尔的起点,他严格恪守民主之代议和竞争的精神,并力求在全社会普及和加强精英之间为获取选民的选票而展开的竞争[1]162。
在达尔看来,从古希腊到现代,人类社会的民主政治经历了两次转型:第一次即古罗马和古希腊,人类第一次开始实践民主制度,这一时期民主制度的特点包括:公民之间是和谐的,其利益高度统一于城邦的稳定和繁荣之中;公民之间高度同质,他们财产平等,语言、教育、文化和种族背景近乎完美地一致;公民总数很少,最多的时候也不过四五万人,这大大有利于公民之间的相互交流与熟知;因为数量很少,所以公民们能够以集会的方式直接决定有关法律与政策的事务;公民参与并不局限于集会,还包括轮流担任其他的公共职务;城市是完全自治的。第二次转型发生在近代民族国家建立以后,其结果是现代民主的确立。现代民主与古希腊的民主完全不同:代议制取代了古希腊的公民会议,公民对政治的参与由直接转为间接;民主已经超越了城邦的范围扩展到了现代民族国家,而代议制民主本身具有扩大民主规模的趋势;公民的参与从直接转为间接,意味着公民参与的领域与范围是有限的;公民资格扩展到国家之内的所有人,但是公民之间的差异前所未有地多样化了;公民间差异的增强导致政治领域中不同利益诉求之间的显著冲突;公民不再以个人的方式而是以组织的方式参与政治,由于公民之间是多元差异的,因而由公民组成的组织之间必然也是多元差异的;组织内部又分为上层精英和下层民众,因此多元差异的组织与政治权力的交互使现代民主政治变成一种多头政治;由于公民参与的衰落,公共领域的范围逐渐缩小,个人权利以及私人领域逐渐扩张。
11月21日,上交所和深交所分别就《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征求意见稿)》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信息披露指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三、从古典民主到现代民主:不变的多数统治规则
现代民主是代议制民主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是,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争论的完结并不意味着有关民主争论的完结。当代著名的民主理论家阿伦·李普哈特认为,民主从直接民主转变为代议制民主只是民主转变了形式,作为民主的核心,不论它是由公民直接决策还是由代表替选民决策,决策结果所体现和包含的公民诉求的广泛性无论如何都是衡量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民主程度的重要准绳。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民主机制中不同决策过程对民主后果的影响却一直缺乏深入、认真的探讨。在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度下,公民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然而,即便是那些小国寡民的社会,公民之间也难免因不同的意见陷入持续的争吵,最初,无休止的争论总是让事事久拖不决。后来,随着城邦事务的增多,久推不决的争论直接影响到了城邦的存废,尤其是当城邦面临外部威胁的时候。为了避免民主机器因无法产出而失效、倒塌,城邦的公民发明了民主议事的程序,一些人就公共议题展开辩论,在形成对立意见的情况下,所有的公民向秉持对立意见的双方或者多方表达支持态度,或投一石子,或投一贝壳,计数最多的一方获胜,所谓的贝壳放逐法就是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前提下“民主”地判决城邦的“罪人”。
民主制度为什么要求少数服从多数呢?亚里士多德认为,“政事裁决于多数人的意志,大多数人的意志就是正义”[3]312,作为正义的对立面,抛弃城邦的公共善,追求私利就意味着腐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民主政体之下的决策之所以由多数做出,少数服从多数,其原因在于“平等是民主政体的至上法则”[9]103,当城邦是由普通公民而非那些具有超凡德性和能力的政治人物来执掌的时候,多数人的意见纷争有可能使城邦政治陷入党争,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质疑普通公民的灵魂会与单个的贤人差别多少,因此民主政体下多数人的判断在一般情况下总是比少数人的判断更加明智,同时,多数人比少数人更不易于腐败,就如同大量的水更不容易被少量的水污染一样[9]107。古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也把民主政体描述为多数人统治的政体,区别于那些由少数人统治的寡头政体和贵族政体。
随着古希腊城邦的衰落,直接民主在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以后逐渐被代议制民主取代,但是少数服从多数依然是民主决策的基本规则,以至于民主又被等同于“多数统治”。近代的霍布斯、洛克、卢梭、托克维尔和约翰·密尔等人都是从多数人统治的角度来理解民主的。
霍布斯在翻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时候就直接把修昔底德对民主的描述译成“the rule of majority”[10]。而在霍布斯本人看来,“如果全体中的大部分被认为是包含了所有个别的意志,或者说所有个别的意志服从于全体中的大部分的意志,这就是民主。正是在这样一个民主政府中,全体或者全体中的大多数自愿地组织起来充当主权者。”[11]洛克和卢梭表达了与霍布斯相同的看法,在他们看来,政治社会建立在全体一致的基础之上,但是政治社会的运作却无法总是满足全体一致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服从多数就是必要的。卢梭曾指出:“除去原始契约之外,投票的大多数是永远可以约束其他一切人的……每一个人在投票时都说出了自己对某个问题的意见,于是,从票数的计算里就可以得出公意的宣告。”[12]136因此,在无法达成全体一致的情况下,“公意的一切特征仍然存在于多数之中”[12]137。在卢梭看来,当公民意见陷入分歧的时候,针对议题所进行的讨论越广泛,那么多数所囊括的公民数量就越多也就越接近全体一致,少数的数量就越少;而当所涉议题需要迅速解决的时候,只要一票的数量差别就足以划分出多数和少数进而使少数服从多数,因为多数本身就是公意。
托克维尔也把民主理解为多数的统治。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托克维尔认为美国民主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多数统治,“民主政府的本质,就在于多数对政府的统治是绝对的,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谁也对抗不了多数。”[13]282在托克维尔看来,多数的统治可能带来多数人对少数人权利的侵犯,进而导致多数的暴政,但多数的统治并不意味着多数必然会对少数实施暴政,多数统治与多数暴政并不是同义词。因此,对无限的多数权威导致的多数暴政的批判并不能否定民主就是多数统治的事实,作为民主的本质,“一切权力的根源都存在于多数的意志中”[13]287。与托克维尔处于同一时代的约翰·密尔深受托克维尔民主思想之影响,在其自传中,密尔曾坦陈他对于民主政体的偏爱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托克维尔向世人所展现的美国民主之光辉。在《代议制民主》一书中,密尔把代议制民主政府看做是理想的政府形式,但是与托克维尔一样,在密尔看来,在个人自由不受侵犯的前提下代议制民主依然应当是多数的统治,其决策规则依旧是少数服从多数,因为“由人数上的多数掌权比其他的人掌权较为公正也较少危害”[7]115。
四、“多数主义民主”理论的兴起及其民主观
在当代,一些著名的民主理论家,如加拿大的麦克弗森就是从多数统治的角度理解民主的[14]。而英国著名学者安东尼·阿伯拉斯特在其颇具影响的《民主》一书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了民主就是多数的统治[15]。当代民主理论界另一位颇具影响的学者阿伦·李普哈特深受达尔民主思想的影响,在李普哈特看来,现代民主首先是间接民主,是代议制的民主。其次,现代代议制下“民主与寡头统治(polyarchy)是同义词”[16]。李普哈特关于现代代议制民主的这一认识得到了达尔的肯定,在《民主及其批评者》一书中,达尔指出,李普哈特眼中的民主实际上就是自己所说的多头政体[17]112。与达尔对李普哈特的看法相映成趣,在李普哈特看来,罗伯特·达尔在《多头政体》中确立的现代民主政体的八条标准已经成为当下人们审视一个国家民主资格的基本依据:一是现代民主国家的公民拥有投票权;二是现代民主国家的公民拥有被选举权;三是政治领导人为获得支持和选票而竞争;四是选举是自由公正的;五是公民结社是自由的;六是表达和言论自由不受侵犯;七是公民对各种信息的选择是自由的;八是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应当是以选票和民意为基础的。
李普哈特认为,美国保守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威廉·萨弗里和南非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乔·斯洛弗进一步回应了波洛克的观点,在当代主张多数统治的民主理论中最具代表性。在对南非的民主进程所做的评论中,萨弗里认为,民主的要义就在于人人平等,具体而言,就是一人一票(one person,one vote),但是无论如何,民主最终都是多数人的统治。为了更有力地伸张自己的观点,萨弗里甚至认为某一政体只要是民主的,就无法抛弃和反对多数统治的规则[20]。斯洛弗的观点则更加简洁有力,我们不需要再玩弄文字游戏了,民主只有一种,那就是多数人的统治。李普哈特把这种主张少数服从多数、多数获胜就意味着胜者通吃的民主体制称为“多数主义民主”。
总而言之,从古希腊城邦的直接民主到现代民族国家的代议制民主,民主思想的传统资源在现代人的生活中依然具有持久而深刻的影响,把民主等同于多数人的统治即是。除此之外,市场经济的兴起以及在自由主义的推动下,个人权利的膨胀推动了政治冲突成为民主的常态,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原则的民主不仅没有消弭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反而加剧了这种冲突。从霍布斯、洛克的学说到密尔的功利主义民主观,再到达尔的多元主义民主理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差异几乎成为现代政治的永恒主题,而民主决策所面对的正是这种日益增加的冲突和差异。对此,达尔在其新近的著作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冲突而非和谐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标志。”[17]18与此同时,在民族国家大规模、复杂的代议制民主制下,“任何人都不能肯定竞争和对抗的结果总是对自己有利……因此所有的力量都必须反复进行斗争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每一个人必须将其利益置于竞争和不确定之下。”[21]由于竞争和冲突的结果难以确定,那些自觉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和团体往往倾向于把竞争和冲突引入政治和公共领域,这一方面导致了当代政治参与程度的深化和领域的扩展,另一方面也加剧了政治竞争和冲突的水平[22]。
在李普哈特看来,现代代议制民主和政治参与主要是通过政党来实现的,而任何一个政党都必须忠实于自己所代表的社会中的特定选民群体,并矢志不渝地至少是在表面上为了本群体的利益而与其他政党展开竞争,由此,个人及其群体之间的社会冲突往往通过政治领域中政党冲突的形式得以表达。许多西方学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制更应该表述为‘局部体制’(segmented system)的混合物,而不是‘一种单一的体制’。伴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每一个局部体制都遵从一种特殊的序列,按照独特的原则,在不同的场所被制度化。不过这一切都与社会团体的代表程序以及彼此之间的冲突解决有关。政党等组织为了努力赢得职位、影响政策,在不同的场所钩心斗角,他们结构化的行为可以把冲突和竞争导入公共舞台,从而避免诉诸私人手段,例如依靠暴力解决冲突。”[23]正因为如此,以多数统治为原则、以政党竞争为手段的代议制民主又被称为“对抗性民主”,它的主要特征:一是高度保护和遵守市场经济中的公平竞争和等价交换法则,肯定政治领域中个人权利伸张经济权益的合理性,因此,现代民主政治充分保护个人以及由个人形成之团体、组织的利益,不主张公共利益高于个人权利,充分肯定选民、代表按照自身的利益所开展的合法的政治活动。二是由于市场领域中存在的只是永恒的利益博弈,每一个个人和集团都想在利益博弈中获取最大限度的利益,因此政治领域中很难达成完全一致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依然坚信最为方便和简单的方法就是无论是选民之间还是选民的代表——政党之间,所有的竞争和冲突最终都将依靠少数服从多数来决定,也就是多数决定。
[1][意]乔·萨托利.民主新论[M].冯克利,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
[2]施治生,郭方.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27.
[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泽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M].日知,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5][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6][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7][英]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8][美]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9][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颜一,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0]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M].Translated by Thomas Hobb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109f.
[11]Tomas Hobbes.The Elements of Law:Nature and Politic[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12][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3][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4]Crawford Macpherson.The Real World of Democracy[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1.
[15]Anthony Arblaster.Democracy[M].Milton Keynes:Open University Press,1987:13.
[16][美]阿伦·李帕特.多元社会的民主[M].张慧芝,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3:5.
[17][美]罗伯特·达尔.民主及其批评者[M].曹海军,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354.
[18]Arend Lijphart.Thinking about Democracy[M].New York:Routledge,2008.
[19]J.Rol,Pennock.Democratic Political Theory[M].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370.
[20]William Safire.The Suzman Plan[J].New York Times,1986,(7).
[21][美]埃尔斯特.宪政与民主[M].潘勤,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71.
[22][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69.
[23][日]猪口孝,[美]爱德华·纽曼,约翰·基恩.变动中的民主[M].林猛,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33.
D082
A
1007-4937(2012)02-0028-06
2011-12-1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古典民主理论与现代民主理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当代西方共识民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GD11YZZ04)
李鹏(1984-),男,甘肃武山人,副教授,政治学博士,从事国家学说、当代民主理论与实践前沿问题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