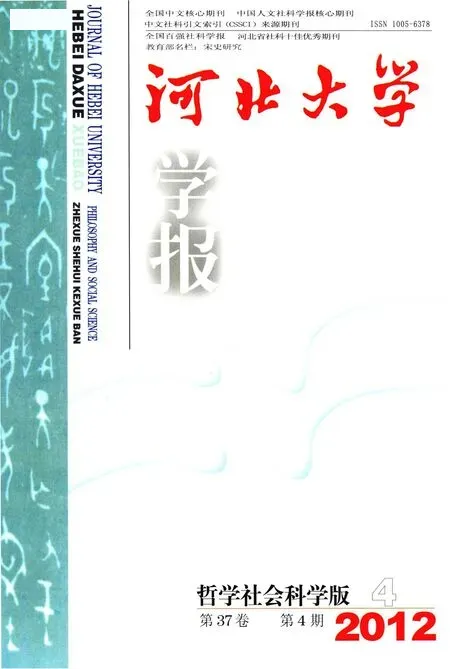论“银都”武侠电影创作的美学特征
2012-04-09金晓非
金晓非
(河北大学 艺术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论“银都”武侠电影创作的美学特征
金晓非
(河北大学 艺术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银都系统所涉及的电影公司拍摄的武侠电影,贯穿了香港电影史的各个时期。继承了香港左派进步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秉承南下影人“影以载道”的思想,既具有浓郁的传统文化气息,又呈现出香港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银都”一贯倡导的“导人向上、向善,爱国,不渲染暴力与色情,多姿多彩,寓教于乐,百花齐放,观众喜闻乐见”的创作方针,鲜明地体现这些武侠电影中。
银都;武侠片;左派电影
作为一种类型片,武侠电影是香港商业电影的主流,也是华语电影中发展得最完整、最成熟又最具民族特色的类型电影。从数量上看,银都系统60年来出品或参与的480电影中,武侠电影不过30部左右,未能象邵氏公司那样形成庞大的产业规模。但是,武侠片的制作贯穿了银都系统六十年的历史,即使“十年动乱”“银都”的电影事业元气大伤时,武侠电影仍没有停止制作(1971年,长城公司还出品了“文革”期间少见的一部武侠片《侠骨丹心》),此外,作为香港左派电影的代表,“银都”制作的武侠电影有着鲜明的“银都特色”,迥异于“邵氏”等电影公司纯粹的商业制作,表现出强烈社会责任感和鲜明的美学特征。
一、开拓性的题材与“不纯”的类型
银都系统制作的武侠电影虽然数量不多,但胜在题材、类型丰富多彩。往往独树一帜,开风气之先。像20世纪60年代的《云海玉弓缘》和20世纪80年代的《少林寺》,都是影响武侠电影历史的里程碑之作。在美学风格上,“银都”的武侠电影既不同于张彻的浪漫阳刚,也不同于胡金铨的京剧禅意。银都的武侠电影格调清新,雄浑厚重,场面气势壮观,格局架构宏大,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尤其古装题材,具有香港电影制作中罕见的史诗风范。梳理一下“银都”60年制作的近30部武侠电影,所涉及的类型大致包括:改编自新派武侠小说名著的古装武侠片,如《云海玉弓缘》《白发魔女传》《书剑恩仇录》《香香公主》等;具有民族传奇特色的侠义片,如《金鹰》;少林题材电影,如《少林寺》《少林小子》《南北少林》和《少林豪侠传》等;有“侠”无“武”的侠义片,如《我来也》及续集《我又来也》;革命历史叙事特点的侠义片,如《过江龙》等;历史战争题材,如《西楚霸王》等;注重视听奇观的武侠大片,如《英雄》《无极》。虽然这些武侠电影丰富多样,但具有一个共同特点:“不纯”。所谓不纯,是指这类影片不仅具有武侠电影的类型元素,但又兼杂糅有其它类型电影元素,具有混合的特色。如侠义片《金鹰》,便是一部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情的动作片。《五虎将》从叙事素材来源上来说,采用的是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中“智取威虎山”的故事,类型模式上来说是属于警匪片中的“剿匪模式”,但视听手段和动作设计又有着武侠片的特征。拍摄于1970年的《过江龙》,从形态上看,酷似同一时期香港开始流行的功夫片,但其精神内核却和内地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一脉相承、息息相通。
银都制作的武侠电影在题材与类型上的突破,核心是对武侠电影中侠义精神的独特诠释,以及对“武”与“侠”两个武侠电影中核心元素的全新配置。关于“武”与“侠”的关系,梁羽生先生曾说过“武是手段,侠才是目的”。因此,影片的主旨是否具备了侠义精神,是判断影片是否为武侠电影的关键。银都武侠电影一大特色,对“侠”的弘扬往往大于对“武”的表现和渲染。比如鲍方导演的《我来也》及续集《我又来也》,无疑属于功夫片的类型,但影片中的主人公已经不再是武侠电影中经典的“侠”的角色,或者说影片中作为盗贼的主角是个另类的“怪侠”,导演鲍方想在影片中探讨“甚么是中国武侠片应具的精神和风格?甚么是‘侠’?甚么是‘义’?为谁而‘侠’?为谁而‘义’?”[1]因此,影片几乎放弃了武侠电影中作为视觉奇观的武打场面。
二、真实的历史感与浓郁的地域特色
香港电影学者林年同认为,国家感、民族感、政治感、历史感的缺乏,使新一代香港人成为无根的一代。“这一切加起来,便造成了香港人的目光如豆,没有时代使命感,缺乏民族国家意识,不知理想为何物,只知道为钱卖命,寻求感官刺激,今朝有酒朝醉。”[2]由于视野的狭窄,使香港电影一向缺少历史感和史诗格局的电影作品。
例外的是,“银都”的武侠电影具有强烈的历史感与鲜明的地域特色。究其原因,首先,这是由于三、四十年代上海“左翼电影”及香港左派进步电影的写实主义传统的影响,具有鲜明的人文观念与历史情怀,影片所表现的中国历史文化风情,呈现出一种悠远的神韵和绚丽多姿、朴实淳厚的艺术风格。如凤凰公司赴内蒙古阿巴嘎旗的大草原拍摄的侠义片《金鹰》,草原美景,骏马奔驰,歌舞优美,民俗独特,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左派电影人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赋予了“银都”作品开阔的视野和积极健康、宏大深刻的思想主题。超越了传统武侠电影脱离现实、夸张虚幻的类型局限,有意识地舍弃了江湖恩怨、夺宝复仇的陈腐模式。与此相关,银都系统的武侠电影塑造的主人公也不再是传统武侠电影中抽象化的理想化的草莽侠士,而是更具有历史真实感的民族英雄。“侠义精神”在银都武侠电影中的体现,不仅仅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锄强助弱、济困扶危的侠义之举,更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对“侠”的现代诠释。他们在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中,心系国家民族的安危,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和自我牺牲精神。这种精神和香港左派进步电影中的“家国情怀”一脉相承的。可以说,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主题始终是包括武侠电影在内的银都电影永恒的主旋律。
其次,以金庸、梁羽生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在五十年代中后期的兴起,为武侠电影的繁荣提供了文学基础。也为武侠电影的写实风格奠定了历史依据。1954年,吴公仪、陈克夫比武哄动港澳,《新晚报》总编辑罗孚提议梁羽生创作武侠小说,赛事后三天开始在该报连载《龙虎斗京华》,掀起新派武侠小说的热潮。此后,香港的金庸、蹄风、倪匡,台湾的卧龙生、诸葛青云等新派武侠小说家的作品,成为新派武侠片的重要素材。尤其是“武林盟主”金庸,具有较为深厚的史学修养,他创作的武侠小说,格局宏大,意境深远,大都有明确的时代背景和真实的历史人物,融历史与传奇于一炉,有着鲜明的历史感。为武侠电影的改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许鞍华导演的《书剑恩仇录》的强烈的历史感很大程度有赖于原著扎实的基础。
第三,银都武侠片的历史感得益于认真严谨的制作态度。港产古装片限于资金、技术及外景资源,大都制作粗糙,更有甚者为了娱乐性任意歪曲历史。“银都”一方面得力于可以去内地拍摄外景的“地利”优势,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严谨的制作态度。如银都制作的历史战争巨片《西楚霸王》,投资高达4 000万港币,凭借雄厚的资金及内地的丰富资源,场景宏大壮观,布景道具均有考证。片中刺秦、鸿门宴、活埋秦兵、火烧阿房宫、划分楚河汉界,乃至四面楚歌、霸王别姬、乌江自刎等著名的历史场景,都相当忠于历史,拍出了逼真的历史感。
三、独特的空间意识和造型手段
港产武侠电影,大多在香港的片场内取景,及至功夫片时代,虽摆脱了摄影棚内布景的束缚,外景也不过限于港岛、台湾拍摄,所以,胡金铨要拍《山中传奇》和《空山灵雨》两片,要借助韩国瑰丽空灵的山川景色;李小龙为了追求中外武林高手大决斗的气氛,要远走意大利古罗马斗兽场取景。利用祖国内地丰富的地域景观、人文资源来反映武侠文化,一直是电影人遥不可及的梦想。而银都系统由于充分利用内地风景名胜的“地利”资源,从六十年代拍摄的《金鹰》开始,便频繁来内地实景拍摄,这使得银都制作的电影,尤其是古装武侠电影,具有不同于片场拍摄的影片的独特的空间感和造型风格。
文革后,在粤北拍摄的《碧水寒山夺命金》开启了港台电影来内地拍片的新风潮。此后,仅银都制作的武侠片,便有在山东泰山拍外景的《泰山屠龙》;在河北及山东拍摄的《密杀令》;在黄山拍摄外景的《白发魔女传》;在山西云岗实地拍摄《云岗游侠》;在山水甲天下的广西桂林拍摄的《少林小子》。尤其是在河南登封县实地拍摄的《少林寺》,巍峨挺拔的嵩山,飞流直泻的瀑布,幽深庄严的古寺,千姿百态的佛像,以及塔林、壁画、书法等诸多文化奇观,与影片的剧情融为一炉,使观众大饱眼福。影片中精心设计的几场塔林的武打戏,通过空间调度和光线的变化,很好地发挥了实景拍摄的优势,有力地烘托了环境氛围。内地的外景资源打破了武侠电影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片场置景的虚假舞台感和狭小局促的空间格局,带来了开阔的视野和宏大的格局。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钱塘潮的实景拍摄,《书剑恩仇录》开场壮观的一幕如何呈现,同样,张鑫炎的《黄河大侠》,如果没有真实的壶口瀑布做故事背景,影片的气势和氛围将会逊色多少。
四、鲜明的民族意识和强烈的政治诉求
作为香港左派电影公司的代表,银都系统制作的各类电影,都具有鲜明的社会意义。即便是商业特征突出的武侠电影也不例外。与各类商业类型片一样,武侠电影也反映着每一时代价值观念的转移与意识型态的变动。香港电影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转型,此后,左派电影所倡导的写实主义传统日渐衰微,面对香港的社会现实,大多数影片或者回避,或者制造脱离现实的奇诡梦幻。电影的大众娱乐和造梦功能被空前地张扬。写实主义电影20世纪60年代之后在香港的传承者,依旧是“银都”为代表的左派电影公司。这种传承体现在武侠片中,便是鲜明的民族意识和强烈的政治诉求。
按贾磊磊先生的观点,自新中国成立后,武侠电影并未消失,而是以“潜在文本”的形态继续活跃在内地的银幕上。它所采取的“是一种英雄化的叙事策略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3]。于是“昔日的客栈与荒野,变成了漫长的铁道线、苍茫的林海和无边的青纱账;在银幕上驰骋纵横的英雄豪杰,也不再是刀客、剑侠和义士,而成为革命历史上的传奇英雄”[3]。比如《红旗谱》中的高老忠;《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铁道游击队》里的刘洪。他们身上都带着古代侠士那种舍生取义的精神品格。于是,侠义文本演化为以革命英雄主义为内核的历史文本,武侠电影中刀光剑影转变成革命战争的烽火硝烟。这一时期“银都”武侠电影的叙事策略与类型形态与内地革命现实主义电影可谓一脉相承。不仅像《双枪黄英姑》《沙家浜歼敌记》这样的类似于内地红色经典的情节剧电影,即使具有鲜明娱乐特征的武侠功夫片,也如出一辙。
比如1970年凤凰公司出品的《过江龙》,表面看来是武侠片的题材,但是导演许先认为影片并不是一部传统武侠片,而应该叫做“侠义片”,“是在反抗异族侵略的斗争中,歌颂劳动人民中英雄人物机智杀敌的影片”。许先在导演阐述里写道:“侠,就是英雄人物。……《过江龙》也描写英雄人物,歌颂英雄人物,但决不是个人英雄主义式的人物,而是在激烈的民族斗争、阶级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他是广大劳动人民中间的一员,但又集中了广大劳动人民英勇和智慧,领导群众和侵略者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义,就是国家民族的大义。”[4]许先的导演阐述固然有特定时代的政治色彩,但却很好地说明了银都武侠电影在历史感上与众不同的特色。
《少林小子》是在《少林寺》获得巨大商业成功之后,因势利导拍摄的娱乐性更为丰富的功夫喜剧。张鑫炎在谈《少林小子》拍摄体会时说:“我倾向多拍武侠片,又爱在片中表现一种抱打不平的态度,像《少林小子》实在是想写一种一河分隔两家,本来互不相让的中国人,如何在面对外敌时,反过来联合对抗外敌的故事。虽不知观众能否感受到,但我当时是有感于海峡两岸及中国人常搞对抗,故写成此带有寓意的故事。当年我们拍戏,公司均会要求故事必须有主题,武打片亦然。”[5]
张鑫炎在谈《黄河大侠》时也说:“其实我拍的片中,最喜欢的是《黄河大侠》,原因是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总抱有一份为人民做点事的心态,就如片中的主角即使受到多大打击,甚至惹上杀身之祸,也决不灰心,只会不断地以‘为民请命’为目标。在此想法下,我当时创作此戏,亦抱着要把主题丰富的原则,以‘为民请命’为目标。”[5]从张鑫炎谈话中,可看到武侠片导演的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历史使命感,他们执着于传统道德使命,带有浓厚的载道意识,赋予武侠电影一种难能可贵的现实意义和批判精神。
五、家庭伦理剧的叙事策略
银都系统制作的电影中,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家庭伦理片一向占有很大的比例。可以说,伦理写作是左派电影“以情切入”、“以家切入”故事创作的重要手法[6]。银都的家庭伦理片沿袭了中国电影的写实传统,多取材于家庭伦理,写中国人社会的人伦关系,表现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和睦美满,鄙夷恶行。大都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劝善”主题,强调互助互爱,团结、凝聚力。在艺术上,家庭伦理片讲求戏剧结构,注重故事与情节和悬念的营造,并借鉴了好莱坞通俗剧的故事模式。风格委婉清新,细腻深刻。家庭伦理片广受欢迎的原因,在于影片所面对是背井离乡的观众,不管是南下香港的内地移民,还是移居国外的海外游子,他们经历了多年的战乱和动荡,有着浓郁的思乡之情,去国离家的迷惘和安身立命的急切,对故乡的印象刻骨铭心,家庭伦理片的流行正是左派电影中注重伦理关系表达的社会文化背景。正如张燕在《夹缝中求生存——香港左派电影研究》一书中所分析,“就社会本质而言,家庭是最基本的单位,以血缘为基础的家不仅是生命的源头,承载着个人理想与情怀,而且是生命的港湾和终极归宿,是个人始终不可舍弃或背弃的生存依托。因此,家成为电影创作中情感表达和文化表现的重要载体,既可以浓缩丰富复杂的道德伦理,也可以折射多样各异的人生百态。”[6]而且,“由于港英当左派电影政治审查的严苛,香港左派电影无法高调进行意识形态宣教,而只能采取迂回含蓄的策略表达,于是,‘以家切入’便成了理想的创作策略”[7]。
得益于银都电影社会写实的传统,武侠电影也具有鲜明的家庭伦理片的特色,或者说采用家庭伦理片的叙事策略。武侠片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影片的类型包装。《云海玉弓缘》《泰山屠龙》《书剑恩仇录》等影片都有这个特点。比如《云海玉弓缘》,便是围绕金世遗、厉胜男与谷之华三位少侠和他们上代的帮派化之间的恩怨情仇而展开。影片表面上讲的是江湖儿女的侠义故事,但编导有意突出的确是原著中的人伦关系,情感与道德的矛盾冲突,有着鲜明的伦理片的特点,几乎像一部武侠伦理剧。罗卡评论此片说:“《云》片不倚重大量激烈的武打,而以写情细致、人物性格和戏剧处理生动入味取胜,对白充满机智幽默,人物造型亦有新意……在‘邵氏’一路堆砌厮杀的武打片以外,另辟文艺武侠片之途。”[7]而张鑫炎导演同样改编自梁羽生小说的《白发魔女传》则像一部武侠爱情剧。
银都系统所涉及的电影公司拍摄的武侠电影,贯穿了香港电影史的各个时期,深受海内外观众欢迎,几度引领潮流,对后来香港武侠电影的繁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香港首部票房过百万的《金鹰》,引领“彩色武侠电影世纪”潮流的《云海玉弓缘》,再到轰动海内外的《少林寺》,开启新世纪武侠大片的《英雄》,直至即将上映的王家卫导演的《一代宗师》,银都机构在武侠电影的浪潮之中,始终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鲍方.我来也[M].上海:三联出版社,2010:242.
[2]李以庄.香港电影与香港社会变迁[J].电影艺术,1994(2):15-23.
[3]贾磊磊.中国武侠电影史[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73.
[4]许先.过江龙[M].上海:三联出版社,2010:275-276.
[5]香港电影口述历史展览《再现江湖》宣传资料[M].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出版,1999.
[6]张燕.在夹缝中求生存——香港左派电影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48.
[7]罗卡.《云海玉弓缘》影评[M].上海:三联出版社,2010:268.
The Statement on the Aesthetic Features of the Creation of Kung Fu Genre movies Produced By the sil-Metropole Organisation
JIN Xiao-Fei
(Colloege of Art,Hebei University,Baoding,Hebei 071002,China)
The Kung Fu genre movies produced by the production companies related to the Sil-Metropole Organisation run throughout various periods of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movies.It inherited the tradition of Realism of“left-wings”movies in Hong Kong and adhered to the idea of“Movies are for conveying truth”put forward by the film makers who were going down the south.It was of strong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distinctive and native culture of Hong Kong at the same time.“Sil-Metropole”always advocates the art creative policy that people who are watching movies should be guided of being upwards,doing good deeds and loving their countries.And movies should render non-violence and non-pornographic,and be colorful,entertaining,flourishing and loved by the audience.This policy is clearly reflected in these Kung Fu genre movies.
Sil-Metropole Organisation;Kung Fu genre movies;left-wings movies
J901
A
1005-6378(2012)04-0132-05
2012-03-18
金晓非(1964-),男,辽宁沈阳人,河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影视理论。
[责任编辑 周云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