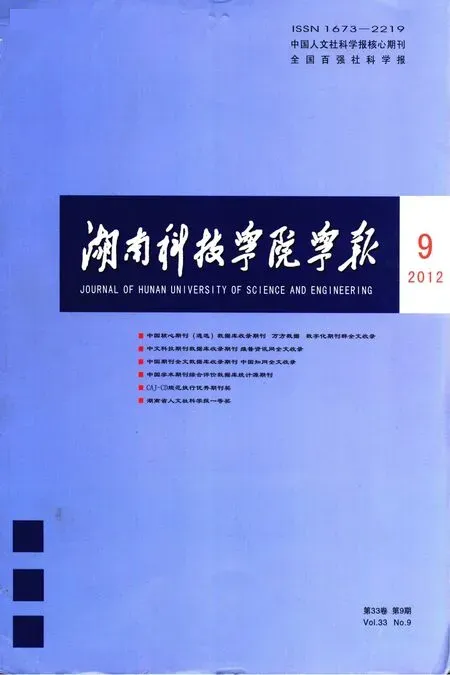30年代周作人个人主义思想的困境
2012-04-09林强
林 强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30年代周作人个人主义思想的困境
林 强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30年代周作人的个人主义思想是一个复杂的观念综合体,其中有西方个人主义关于人的独立、自由和发展的观念,也有以蔼理斯“中庸”思想为核心的生命本体意识,在时代的作用下二者相互渗透形成了30年代周作人个人主义思想趋向保守的总体特点。更为内在的问题是,周作人对自我与理性的绝对坚执使他深深陷入了自以为真理的乌托邦心态之中。
个人主义;中庸;自我;理性
一 引 言
五四时期,周作人以《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新文学的要求》诸篇论文奠定新文学人道主义理论基石。周作人的人道主义是以 “灵肉一致”的自然人性论为基础,强调 个体生存的自然和精神属性。他的人道主义逻辑起点首先是“使自己有作人的资格”,然后才能“利己又利他”。这种人道主义并非“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而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价值与尊严、个性的解放与发展,这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核心价值,也是五四时期启蒙思想家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强大的理论武器。正是这种重视个体尊严、自由与发展的个人主义成为周作人终生持守的信念。[1]从 20年代中后期以后,周作人对群众的狂信和盲从的反感已极为强烈,他建造起十字街头的塔,“想在喧闹中得安全地”,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周作人的个人主义逐渐疏离了群众和现实思想斗争,企图在纯粹的思想自由中“自由而且写意”的活着。到了1927年,国民党在清党中大肆屠杀革命者和群众,并严格钳制思想言论,这让周作人感觉到思想言论自由之难。于是他在“闭门读书”中企图“苟全性命于乱世”寻求“得体的活着”,并将对“狂妄与愚昧之察明”作为“这虚无的世间第一有趣味的事”进行“伟大的捕风”。自此以后,周作人虽时时讽刺时弊,发发胸中的牢骚,但他已完全躲进十字街头的塔中抽象地坚持个人主义了。脱离现实血与火斗争的个人主义成为一种纯粹的信条,并在自我观念的强化中陷入了困境,最终使周作人走向了深渊。无可否认,周作人的个人主义思想及其对现实的批评在某种层面上确实能够发人深省,正视这些合理的思想成分和批评尺度是一个必要且有益的工作。但同时我们更要关注他的个人主义思想内部基本的观念要素、思想原则,分析产生困境的逻辑矛盾以及可能导致的后果,这样才能理清30年代周作人个人主义思想问题。
二 个人主义与“中庸”思想的合谋
以1928年《闭门读书论》为标志,周作人从思想文化论争前沿阵线中退回到书斋,以读书为消遣,通过对古籍特别是明清笔记的阅读,深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问题。这种转向一方面是迫于国民党的思想压迫和言论钳制,另一方面则是对当时思想文化界的宗派主义、载道主义的一种反动。有感于言论界文人谈武武人谈文肆口乱道的言论陋习,周作人从孔子的知行精神出发,一再强调对于自己的言与行要负责任。这种知行态度使他时时检点自己的言行,强调自己的历史责任,意识到自己对时局“无话可说”。另外,相信文学无用、教训无用的周作人,在文体的认知上也发生了转移。在《苦茶随笔·后记》中,周作人比较了《苦茶随笔》与《夜读抄》的文体:“《夜读抄》的读书的文章有二十几篇,在这里(指《苦茶随笔》——笔者注)才得其三分之一,而讽刺牢骚的杂文却有三十篇以上,这实在太积极了,实在也是徒劳无用的事。” 周作人发现那些针对社会问题而写的文章不能对社会发生任何效力,反而显示出论者的“卑下怯劣”和“野蛮神气”,成为看客观赏对象。因此他贬低《苦茶随笔》中的杂文而赞成《夜读抄》中的读书笔记。
退守书斋的周作人实际上依然坚持其一贯的个人主义立场,强调个体的价值与尊严、思想独立与自由和个性的自由发展。但是,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与新文化阵营的分化,单纯地坚持个人主义原则,以个人为本位而不依附任何政治势力和思想主义,这种思想路径很难使自由知识分子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中并发挥影响力。实际上,诸多坚守个体价值的自由主义分子埋首于专业领域而退出当时的思想文化舞台。[2]周作人选择书话写作批判传统文化,这使他既拥有自己独立的专业空间,又能够间接地参与思想文化论争,使他的个人主义思想在30年代呈现出独特的形态。问题是周作人在与传统文化的对话中砥砺个人主义,这就有可能使个人主义陷入传统思想文化和士大夫生活方式的包围中失去了积极的现实意义。虽然周作人很明确文化批判的工作是“涉猎前人言论,加以辨别,批沙拣金,磨杵成针,虽劳而无功,与世道人心却当有益”,[3]P2并一直强调抄书标准是“要在文词可观之外再加思想宽大,见识明达,趣味渊雅,懂得人情物理,对于人生与自然能巨细都谈,虫鱼之微小,谣俗之琐屑,与生死大事同样的看待,却又当作家常话的说给大家听”[4]P126;但是,在反思传统文化和寻找自我存在的价值过程中,在与古代士大夫思想与性情交流过程中,周作人却一直流连传统文化:“知道是梦了却还想在梦境中多流连一刻。”[5]P130无法排解内心孤独与寂苦的周作人在传统文化中营构着一个理想的思想文化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周作人或与志趣相投者闲谈,共主思想自由反对思想专制;或于国家危亡之际与士大夫共寄忧愤;然而,这毕竟只是一个话语空间,对现实的间接指涉也只是个人牢骚罢了,丝毫不能解决周作人现实的思想问题。这个话语空间反而促使个人主义发生变形:与社会紧密相连的个人主义的积极性、斗争性与创造性消弭了,代之而起的是保守性的自娱自乐的个人趣味。与30年代历史文化语境失去了血缘联系的个人主义,成了个人单纯的思想原则,这不但无视社会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而且也使自己陷入虚无主义与自我迷醉的陷阱。
30年代周作人的个人主义思想不是一个独立的思想存在。个人主义与周作人所理解的中西方思想资源呈现一种混杂纠结的复杂状态,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与其对蔼理斯“中庸”人生观的体认。“中庸”人生观为周作人提供生命本体意识,并有力支撑了周作人个人主义的思想原则,而个人主义的消极姿态也使“中庸”呈现为个体姿态上的保守与退避,二者的相互渗透形成了30年代周作人整体的思想方式和价值取向。
20年代中期以后,周作人一直强调蔼理斯著作于他是最有影响的启蒙之书,使他“对于人生与社会成立了一种见解”。周作人从蔼理斯那得到的是一种“中庸”的人生观,即在过去与未来交点的“过渡时代”,不要迷恋过去或未来,而是以一种“明净的观照”的态度,招呼晨光感谢落日;并在时间的流逝中,作为一个光明使者,手持火炬照亮周围的黑暗,将炬火传递给后来人之后自己隐没在黑暗之中。[6]P31这种“中庸”的人生观带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它明确自己的历史责任,要照亮黑暗传递光明,有其积极意义。但它也以一种“沉静”、“坚忍”、“自然的”、“科学的”态度体味这种近乎注定的生命过程,这就使这种生命意识所可能具有的激进精神转化为一种闲散的、静观的保守姿态。当遇到历史曲折与人生苦难时,这种“招呼晨光”“感谢落日”的雍容自在,就会转变为一种贪图安逸、逃避黑暗现实的胆怯。而所谓的“光明使者”也只能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照亮自己,却不能给后来者以光明,甚至连照亮自己的光明都很微弱并最终为黑暗所吞没。与周作人“过渡时代”相似的生命体验是鲁迅“中间物”意识,但二者在选择自己的生命姿态时却有质的差异。在鲁迅看来,“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7]P302。
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然而我不愿徘徊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8]P169
所以,鲁迅要承担起“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的历史责任。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由的精神个体”的鲁迅,他拒绝“天堂”、“地狱”和“将来的黄金世界”等一切实有,选择黑暗和虚空,这个拒绝“有”而选择“无”的决绝源于他那焦虑、孤独和绝望的生命体验。在现实的思想文化心理冲突中,鲁迅时时解剖自己、冲破任何既定的思想文化心理樊篱,用独特的心灵怀疑、审视周遭纷繁的社会文化现象。在这种近乎无所凭依的思想原点上,鲁迅在黑暗和虚空中看到“一切暗”,并领受着“夜所给予的光明”。这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生命的澄明状态:“如此的安详而充盈,从容而大勇,自信而尊严”。[9]P125鲁迅的“中间物”意识是一种深刻的形而上生命哲学,正是这看到“一切暗”的勇气使他决绝地反抗绝望,并对黑暗现实以及传统文化予以猛烈的抨击。在这种激烈的思想文化撞击和深切的现代体验中,鲁迅创造出了有别于传统的现代思想意识和知识分子话语体系。而周作人虽然接过蔼理斯手中自由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火炬”,对封建伦理和思想专制予以批判,但他并没有跃进到20世纪的思想文化范畴,反而由此追溯,发现了古希腊文化的中和之美与日本文化的“洒脱”、“有礼”。这两种文化参照系统与周作人内心对中国旧文明的迷恋暗合[10]P43-44,使“过渡时代”意识纳入传统生活与思想方式之中。周作人在希腊、日本以及中国古代文化中沉醉,把“中庸”精神的生命本体意识和多重向度单一化。在这种文化的想象性沉醉中,周作人无法更深切地审视、剖析、批判自我,无视个体在20世纪激烈的思想文化撞击中所可能创造出的现代生命哲学的可能性,从而也彻底消除了“中庸”精神的创造性。
“中庸”精神犹如一把双刃剑,在将“过渡时代”意识的积极性吞没时,也使周作人自觉承担起“文化批判”的历史使命。30年代的周作人,虽然脱离了血和火的现实思想文化斗争,站在各派政治力量和思想主义之外,冷眼旁观着这个世界,但是他也不无自负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价值,这种半新半旧的“过渡时代”的人物具有批判地继承古今中外思想文化资源的历史使命。周作人清醒地意识到这种使命,认为国家大事不会管也管不着,但至少对“思想文章的传统”的辨别批评是自己的权利也是对后人应尽的义务,这是身处“过渡时代”的人的生命价值所在。[3]P5周作人选择书话写作的方式进行文化批判,他要从中国传统文化话语内部寻找传统文化的病灶并时时予以警醒。然而这种向后回顾式的文化批评眼光虽然以现实思想文化问题作为一个参照系,但还是会在古代文化和思想语境长久浸淫中逐渐漠视现实问题的尖锐性,进而迷失了批判主体。这就使他逐渐疏离了现实斗争和时代历史语境,进入自我营构的思想文化空间。而且,周作人在为文化批判的历史价值进行辩护过程中,越来越强化其进行文化批判工作的信心,并在对诸多思想文化主题进行辨析时逐渐建构起一个封闭的思想文化空间和支撑这个空间的理论自信。这就使本来肩负历史重担的文化批判工作成为一个个抽象的自娱自乐的话语空间,自我也在这个话语空间中逐渐膨胀,最终走向荒谬的虚狂。
“中庸”的生命本体观提供了一种闲淡、静观的生活方式,也提供了对传统文化和人生理想的一种想象方式;而个人主义则在这种生命意识中逐渐与时代语境疏离,在固有文化和生活方式中沉没,从而也就丧失了思想自由、个性自主发展诸原则反抗专制的现实意义。“个人主义中的消极因素适应了中庸主义,反过来,中庸主义的消极因素也适应了个人主义。”[11]“中庸”主义与个人主义合谋,使个人主义具有了一个近乎宿命般的生命本体意味,并使周作人在消极的个人主义思想中越走越远。
三 自我与理性的双重陷阱
个人主义最基本内涵就是尊重个体价值和思想独立。周作人终其一生都坚守着这些原则。30年代,面对左翼知识分子批评时,周作人以无信仰作为自己的理论主张:“把灵魂卖给魔鬼的,据说成了没有影子的人,把灵魂献给上帝的,反正也相差无几。不相信灵魂的人庶几站得住了,因为没有可卖的,可以站在外边,虽然骂终是难免。”[12]P192对一切主义和信仰都持怀疑态度,这种怀疑主义背后的心理是对自己所拥有的知识渊源、理性判断和价值追求的高度自信。“我不是非宗教者,但实是一个无宗教者。我的新旧教育都不完全,我所有的除国文和三四种外国文的粗浅知识以外,只有一点儿生物的知识,其程度只是秋浅治郎的《生物学讲话》,一点儿历史的知识,其程度只是《纲鉴易知录》而已,此外则从蔼理斯得来的一丝的性的心理,从弗来则得来的一毫的社会人类学,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别无用处,却尽够妨碍我做某一家的忠实的信徒。对于一切东西,凡是我所能懂的,无论何种主义理性信仰以至迷信,我都想也大抵能领取其若干部分,但难以全部接受,因为总有其一部分与我的私见相左。”[12]P186生物学、人类学、神话学、性心理学以及历史知识诸多学科共同形成了周作人“杂学”的理论视野,也养成了周作人独立思想、不偏信、不盲从的个人主义思想品格。但是,对一切的怀疑又可能消解个人主义反权威、反正统、反思想统一的社会意义,并转变为偏执自我的“怀疑主义的虚无主义”。[13]P380在这积极与消极之间,根本的评判标准是周作人的自我观照方式和价值理性。遗憾的是,周作人对自我的绝对信任导致天平的失衡。“他自信已经洞察一切,先前相信过的这个那个主义固然已经不值再提,蔼理斯等等也只是为我所用,他只相信他自己,他以对自己的信仰代替了其他一切信仰,所以他宣称一无信仰也可以说毫无矛盾。正是这种‘万物皆备于我’的自信,和足以配得上这种自信的渊博的学识,形成了他的小品文的什么都可以谈,什么都谈得有意思,掉臂游行,卷舒如意的特色。”[14]P41实际上,周作人对“我”的固执背后有着更为复杂、深刻的自我意识——自我观照和理性精神,而不是仅仅建立在知识渊源之上。
30年代的周作人十分反感文字上的论争,他从文字论争的背后看到的不是思想的冲突而是个人的意气之争与流氓相的“乱骂”:“我从前以责备贤者之义对于新党朋友颇怪其为统一思想等等运动建筑基础,至于党同伐异却尚可谅解,这在讲主义与党派时是无可避免的。但是后来看下去情形并不是那么简单,在文艺的争论上并不是在讲什么主义与党派,就只是相骂,而这骂也未必是乱骂。”[12]P6130年代文坛上的论争确实存在着因个人私仇或者党派争斗而产生的攻讦性文章,但是,那些情绪性强烈的论争性文章同样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产物,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思想界的不同倾向。然而,周作人看到的不是这一面,或者他根本就无视这种意识形态斗争。他看到的只是打架的丑态,成为被看客玩味的谈资:“我觉得与人家打架的时候,不管是动手动口或是动笔,都容易现出自己的丑态来,如不是卑怯下劣,至少有一副野蛮神气”。[12]P196周作人以看客的身份来观察思想论争,实际上是将自身置于其中进行自我观照,因此,他看到的是自己的“丑态”。这种身份意识显然只看重自己的形象,爱惜“个人的羽毛”,颇有一种“顾影自怜”的士大夫风致。陷于这种自我观照方式,周作人就只能在个人性情之中辗转赏玩,他不但无法参与到现代思想文化斗争中,而且还使自己陷入了更深的心理怪圈之中:自我成为一个看客,成为观照自我言行的一个客体性参照,并时刻指导着自我言行。这就取消了他者观照方式存在的意义,并使自我在自我中心中不断徘徊。周作人虽时时自我反省却只能是一种更深的自我禁锢。实际上,自我是一个历史的生成物,是“叙述和被叙述交互作用下的产物。当‘我’叙述自己的生活经验时,‘我’获得了一种完整的自我意识,而当我被他人所叙述时,我便在特定的社会群体中获得了某种身份或角色。叙述意味着一种交流,一种流动不居的丰富性和灵动性。因此,自我总是呈现为一个敞开的场所,而叙述的具体的语境因素——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则构成了自我内容中不可剥离的重要部分。”[15]然而,周作人的自我观念恰恰是对他者叙述的一种反驳与漠视,是对具体历史情境的完全封闭。在这种自我筑就的堡垒中,异质性的声音都被阻挡在外,开放性的自我遭到监禁,社会“自我”被个体“自我”所奴役。更为致命地是,周作人并未发觉这种潜在的奴役,他反而感觉到自我在想象的乌托邦中得到了新生,他可以写个人的“永久的烦恼或愉乐”,可以倡导自然人性论的“灵肉一致”,可以在文化批判中提倡个人独立思想自由……然而,脱离了社会、民族、国家的自我,个人主义就成为一种空虚的存在。当这种自我观照方式不断被坚守被强化时,“他的自我意识不断扩张,坚信自己获得了独立的人格和绝对的自我,而视他人(民众与激进的知识分子)为愚狂……自信看透了这万有空虚的世界和狂妄愚昧的人们,于是便以思想富有者或‘精神贵族’的态度,俯视这世界、怜悯这众生。”[10]P128-129这种悲悯、自我扩张与绝对自信最终成为了周作人附逆的思想源头。
周作人执守自我的信心源于对理性精神与价值向度的一种坚定信念。发现“人”、尊重个体价值这是周作人以及五四一代启蒙思想家的逻辑起点。而它的理论前提恰恰是民族主义,只有倡导个体的独立意识与创造精神,才能使本民族免于被排挤出“世界人”之外。这种逻辑使个体意识成为实现民族独立的必要条件。[16]在这种普遍的价值指归之下,周作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独特性在于:他更注重个体的存在意识,认为“个人”与“人类”是统一的,不存在着矛盾关系,只要个人有做人的资格就必然能够爱人类。这种简单化的逻辑相应淡化了民族独立作为时代主题的先在价值及其重要性。这种认识的偏差与他的自然人性论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从‘动物’进化的”与“从动物‘进化’的”自然人性论以人的动物本能为起点,强调人的自然属性,这无疑是合理的。但是在强调人的精神属性时,周作人显然以一种普遍的理想性的道德价值来规范“兽性的遗传”:“关于道德的生活,应该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原则,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使人人能享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17]P11不能从具体的社会关系角度来阐释道德的具体性与普遍性,而单纯地强调普遍真理性的道德,周作人显然无视了社会关系对人性的影响与制约因素,使其所提倡的道德观念显得过于抽象,也使道德评判标准过于单一。被抽象化单一化的道德理性一方面要求个人具有强烈的道德意识与理性主张,另一方面又使个人自信自己掌握了这种真理性道德。因此,当个人进行道德判断时,很可能陷入自我中心意识之中。表面上真理性道德观成为裁量一切道德的标准,实际上它只是自我意识独裁下的虚假外衣罢了,这种道德观成为自我扩张与自我明证的工具性存在。而自我一旦陷入这种乌托邦心态之中,就会在这种冠冕堂皇的理性意识中不断膨胀,并以真理言说者的身份评判其他道德观念。因此,在周作人怀疑一切思想信仰的背后,始终有一个掌握真理言说的自我傲视着这个世界。周作人显然没有意识到启蒙理性与自我意识之间的矛盾,他越是以启蒙者的理性主义评判思想文化,自我就越能够在理性主义的掩护下怀疑一切、肯定自己,进而产生近乎迷醉般对自我的爱惜之情。而理性主义被自我意识所驾驭,实际上成为自我意识的护身符。
相比之下,鲁迅在提出“立人”思想时就表达了对启蒙理性主义“全人”的怀疑。他的“个人”是对启蒙理性原则的反叛。因为启蒙主义用“普遍的、一般的东西,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压抑了唯一性的个体的自由和独立”,而“个人”则是以主观意志为本体的非理性主义思维的结果。因此,鲁迅离开了启蒙哲学的思想路径,他将人的情绪体验置于思维的出发点,在“吃人”礼教的批判中“人”的分裂感,进而在自我批判中提出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命题。国民性的命题将民族的解放归结为个人精神的解放,“这个精神解放不是一般的‘人的觉醒’,不是‘人’对外部世界的一切强暴的反抗,而是认清自己的‘罪恶’,进行‘赎罪’式的自我否定”。[16]鲁迅对启蒙理性和自我的否定与周作人对自我的迷醉和对理性的工具性运用,这二者构成截然相反的思想对照。这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周氏兄弟在人生道路和思想路径上的不同选择。
[1]王铁仙.周作人的人性观和个性主义思想的嬗变[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4,(3).
[2]陈思和.关于周作人的传记[J].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 (3).
[3]周作人.秉烛后谈[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4]周作人.秉烛谈[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5]周作人.雨天的书[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6]周作人.夜读抄[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7]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C].石家庄: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8]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C].石家庄: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9]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0]赵京华.寻找精神家园——周作人文化思想与审美追求[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13][韩]赵恒瑾.中庸主义、个人主义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的影响——以周作人及与鲁迅的比较为例[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4).
[14]周作人.苦茶随笔[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6]钱理群.周作人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17]舒芜.舒芜集(第三卷)[C].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20]倪伟.个人主义与主体性的创制[J].文艺争鸣,1997,(1).
[22]汪晖.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J].文学评论, 1989,(3-4).
[23]周作人.艺术与生活[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责任编校:王晚霞)
I206.7
A
1673-2219(2012)09-0040-04
2012-06-15
林强(1982-),男,福建福清人,文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散文与海外汉语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