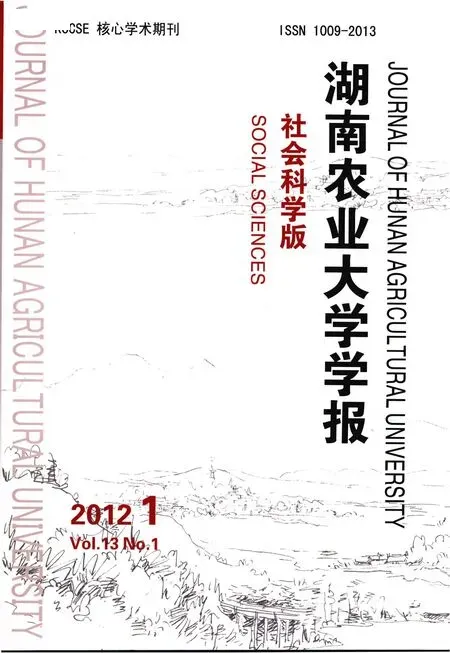宋代女作家自我意识的觉醒及其诗词呈现
2012-04-08谢穑
谢 穑
(湖南女子学院 旅游系,湖南 长沙 410004)
宋代女作家自我意识的觉醒及其诗词呈现
谢 穑
(湖南女子学院 旅游系,湖南 长沙 410004)
相对而言,宋代妇女生活在一个较为宽松自由的社会家庭环境中,出现了以李清照、朱淑真、魏夫人等为代表的女性作家群体,其自我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觉醒,主要表现在对理想抱负的主动追求、对自我才华的充分自信、对自身爱情主角地位的确认三个维度,并鲜明地呈现在她们的诗词作品中。
女作家;自我意识;诗词呈现;宋代
宋代,女性文人群体逐渐形成一支不可忽视的文学力量,尤其是李清照在女性词学领域取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辉煌成就,登上了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制高点。这种文学现象的产生与当时女作家自我意识的觉醒不无关系。
魏晋时期曾短暂出现过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当时因为战乱频仍,儒学所制定和提倡的秩序、规范等受到质疑,班昭《女诫》中所标举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行和七诫有所松懈,女性在长期封建礼教的压迫中寻找到了一个透气口,有少部分女子因才识而彪炳史册。这时期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主要表现为女子对于才学的追求。唐代即使是并称唐代四大女诗人的李冶、薛涛、鱼玄机、刘采春留下来的诗作也不多,其中三大女冠诗人李冶、薛涛、鱼玄机加在一起留存下来的诗作也只有150多首,刘采春是艺人,《全唐诗》归入她名下的作品仅6首。总体而言,魏晋南北朝和唐朝女性作家数量不多,离女性文人的崛起还有一段距离,她们的影响还很有限。另外,在唐代以及元明清时期,对女子礼法教训非常完备,出现了许多规范妇德教育的女书,桎梏着当时女性意识的觉醒。如长孙皇后的《女则》三十卷(唐太宗就曾以此颁行于世),著名才女宋若莘、宋若昭姊妹撰有《女论语》,侯莫陈邈妻撰有《女孝经》。明成祖徐皇后著有《内训》二十篇;蒋太后撰《女训》十二篇。吕坤著《闺范图说》,温氏著《母训》,黄尚文等著《女范篇》,王相母刘氏著《女范捷录》。清朝的“女学”教科书有陆圻的《新妇篇》等。它们对于妇女的言行举止,为人女、为人妻、为人媳的规矩、礼法规范备至,成为套在妇女头上解之不去的牢固绳索。
宋代是继魏晋后中国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又一个时代,而且女性作家群体的人数更多,文学成就也更加突出。宋代女作家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当时宽松的社会家庭环境密切相关。宋代只出现了一些零散的妇德教育篇目,如司马光的《居家杂艺》和《温公家范》,“女学”的相对缺乏可从侧面印证宋代妇女生活在一个较为宽松自由的礼法社会中,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多半主张女子应受一定的文化教育,一些有文化背景的家庭还非常注重培养女子的文化修养。本文所强调的宋代女作家自我意识,并不能等同于现代社会女性要求地位平等、经济独立的自主意识,而仅仅是指她们在宋代这个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所表现的逾越封建道德与礼教规范的女性意识的觉悟,更多的是一种内求而非行动。这种觉醒一直以来也是学术界比较关注的问题,相关的研究成果也较丰富,但多集中于对李清照和朱淑真个体自我意识的解析,把宋代女作家群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作为研究范畴并对其进行归纳概括的研究相对比较缺乏。这种自我意识觉醒虽然在女作家个体上的表现因人而异,但她们争取自己独立自由的思想和精神仍有着一些共同之处。笔者拟结合宋代时代文化背景和女作家群体的身世经历,并通过她们的诗词来分析概括其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具体表现。
一、对理想抱负的主动追求
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男权封建社会中,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宋代女作家根本不可能有建功立业、施展抱负的机会,但这并不妨碍她们在其诗词作品中张扬远大理想,去追求一种独立和自由的女性自我意识。
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女人应该谨守妇德妇规,不能议论政事。但李清照在其大量作品中却无所顾忌地表现出自己高明的历史见识和不同寻常的政治眼光,其雄心勃勃的理想与抱负甚至和一般士大夫相比都毫不逊色,甚至境界更高,眼界更广。如“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乌江》)[1]344借项羽宁死不辱、所向无惧的豪气来批判和抨击南宋朝廷议和苟安之派和朝中文武的懦弱自私,浩然正气和爱国情绪跃然纸上。“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佚句》)[1]348借称颂辅晋中兴的王导和与北方侵略者顽强作战的西晋爱国将领刘琨来感叹在南宋的统治阶层中竟然难以寻觅为国建业、杀敌立功的文臣武将。“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1]344(《咏史》)表达出对一身正气反对司马昭篡权的爱国志士嵇康的钦敬,希望南宋能走东汉的中兴之路。“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知易水寒。”(《佚句》)[1]348讽刺以宋高宗为首的投降派,表达对南宋朝廷偏安一隅、苟安偷生的强烈不满,希望朝廷早日出兵打退敌兵、收复失地、灭耻雪恨。在国势颓败的残酷现实下,她更以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凯旋而归的木兰直抒自己烈士暮年的壮志,展现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气:“木兰横戈好女子,老矣不复志千里。但愿相将过淮水。”(《打马赋》)[1]362其《渔家傲》将她宏大的理想抱负展现得淋漓尽致:“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2]这首词格调昂扬,豪迈奔放,通过对梦境的描述,充分反映出词人积极进取的豪迈气概和对远大理想的热烈追求。结尾更是借乘风展翅、志在千里的大鹏来抒发个人抱负,希望凭着自己的努力,探寻到一条通往理想境界的道路。李清照与丈夫一起收集整理校勘金石书画,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金石录后序》)[1]357的远大志向,因而即使在晚年的流亡生活中,她仍尽最大努力保存着不少古器书画,珍视它们到了“与身俱存亡”[1]357的程度。
在古代传统社会,女性的话语权和才情表现权被无情剥夺,但朱淑真强烈渴望打破社会强加在女性身上的这种精神束缚。《自责二首》就是她这种愤懑感情的直接展露:“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闷无消遣只看诗,又见诗中话别离。添得情怀转萧索,始知伶俐不如痴。”[3]307在第一首诗中朱淑真反话正说,表面上看,诗中的意思正符合“才藻非女子事”的妇德要求,是诗人对自己行为的自责和反省,但从作者一生的所作所为来看,实际上是作者在对封建伦理秩序的嘲讽中抒发心中蕴含的不平和愤怒,是对封建礼教歧视与压迫妇女的现实进行严厉的抨击。“始知伶俐不如痴”,朱淑真说自己如果不是有知识、善思考,而只是一个浑浑噩噩、困守封建妇德的女子就不会有这种苦闷与感伤了。这些悲愤的反讽言辞,直接谴责了封建礼教对自己的摧残。说到底,朱淑真并不认可“绣折金针”的“妇功”最高标准,而是希望能像须眉男子那样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抱负,成就经天纬地的大事,在其“春暖长江水正清,洋洋得意漾波生。非无欲透龙门志,只待新雷震一声”中,(《春日亭上观鱼》)[4]123这样的心迹表露无遗。其《余氏攀鳞轩》也集中表明了自己的远大志向,希望自己有一试锋芒的出头机会:“潇洒新轩傍琴岑,攀鳞勃勃此潜心。易惊谁羡叶公室,入梦当为传说霖。变化一声雷霆远,腾凌千里海波深。卧庐曾比崇高志,肯忆当时梁父吟。”[4]109在这首诗里,朱淑真借攀鳞轩的气势磅礴,赞扬轩主的超凡出众,说他正如隐居卧龙的诸葛亮有着宏大的志向,必将是位了不起的人物。实际上是借轩主抒发自己的崇高理想,希望凭借自己出众的才华、渊博的知识而作出一番光辉的事业。其《月台》诗“下视红尘意眇然,翠阑十二出云颠。纵眸愈觉心宽大,碧落无垠绕地圆。”[4]110也是以居高临下之势抒发自己心志高远、超凡脱俗的情怀。其《题斗野亭》诗则以登临所见气势辽阔、境界高远的景象来表现自己非凡的胸襟。
在众多歌咏项羽的诗词作品中,魏夫人的《虞美人》从女性角度借古喻今,重新审视项羽和虞姬这一对悲剧性的人物。在此诗中,作者不顾女性身份,透露出“刚强”的大丈夫气概,“英雄本学万人敌,何用屑屑悲红妆”,“香魂夜逐剑光飞,清血化为原上草”[3]268等句,都尽力洗除脂粉气,追怀一种英雄主义精神。“滔滔逝水流今古,汉楚兴亡两邱土。当年遗事久成空,慷慨尊前为谁舞。”[3]268慨叹自己空有满腹才华无所施展,既不能追随丈夫替他排忧解难,又不能到社会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虞美人》实际上是魏夫人借古喻今、渴望自由平等和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真实写照。
二、对自我才华的充分自信
胡云翼在《中国妇女与文学》中说:“因为生活的层层桎梏,那些被压迫在宗法社会底下的妇女,她们一切值得讴歌的天才和能力,都不容许表现出来,简直可以说,她们的能力是受礼教的摧残而葬送了……然而,宗法社会尽管是宗法社会,压迫尽管是压迫;尽管压迫的重力能够使妇女各方面发展的能力都全部斫丧,却不能压抑女性特殊的艺术天才在文学里面的表现;虽说学术史上不曾有女哲学家、经学家、史学家,然而在文学方面,女性却曾遗下卓越的成就,使一部中国文学史还笼罩着女性文学的异彩,给与我们一点读文学史时的安慰。”[5]
应该说,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少有的女性文学取得卓越成就的朝代,这与宋代女性宽松的文化教育环境和她们本人对自我才华的自信息息相关。宋代一些有文化背景的宦门之家比较注重女子的文化修养,如李清照、朱淑真、魏夫人、张玉娘等从小都受过很好的家庭文化教育,在文学史上几乎是作为专业作家的身份而出现,甚至都留下了自己的专集,如李清照的《漱玉集》、朱淑真的《断肠集》、魏夫人的《鲁国夫人词》、张玉娘的《兰雪集》。与古代女子一般只带着夫家或者娘家的姓氏作为身份符号不同的是,她们多以居士即居家文化人自命,如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朱淑真自号“幽栖居士”,张玉娘自号“一贞居士”,孙道绚自号“冲虚居士”,胡与可自号“惠斋居士”。由她们给自己居家才女的定位即可看出这些女子一开始就存有打破男性独占文坛的传统,存有与男性文人比肩而立的自信。这种自信在李清照身上表现尤为突出。李清照生活在一个文学气氛浓厚的家庭,其父李格非为当时著名学者、文学家,母亲王氏也是一位文学修养很高的女性,良好的家庭文化教育对李清照卓越的文学才华起到了重要的培养和引导作用。李格非有一句诗“中郎有女堪传业”,借赞誉蔡邕和蔡文姬父女而表达自己对女儿的赞赏以及继承自己文风的欣慰。这种宽松的家庭文化环境,造就了李清照一种逞强好胜的思想,并对她的整个人生形成了巨大影响。她在《感怀》诗序中说:“宣和辛丑八月十日到莱,独坐一室,平生所见,皆不在目前。几上有《礼韵》,因信手开之,约以所开为韵作诗,偶得‘子’字,因以为韵,作感怀诗云。”[1]346无须思考,信手开韵即可为诗表明李清照对自己的诗歌才华非常自信,这种不经意之作,显然也有逞露才华之意。她作诗甚至喜用生僻、难押的字作为诗的韵脚,其“险韵诗成,扶头酒醒”(《念奴娇》)[1]352的表述即为明证。
在文学批评上,李清照在其创作的《词论》一文中,鲜明地提出“词别是一家”的词学理论,从思想内容、艺术风格、表现形式等方面对词坛名家作了独到的评述,批评的矛头直指前代和当代的词学大家,对于后世的影响极大。这种对于文学大家的批评正是李清照对自己才华充分自信的表现。这种自信甚至时时弥漫在她的生活琐事中,如《金石录后序》中所记和她丈夫赵明诚比赛智力的情事:“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决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1]358宋人周辉《清波杂志》卷八中也记载了她踏雪寻诗、邀夫唱和之事:“顷见易安族人,言明诚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寻诗。得句必邀其夫赓和,明诚每苦之也。”这种夫妻间的即兴唱和往往是李清照胜出,令赵明诚感到苦恼。这虽然有着赵明诚公务繁忙无暇陪伴的因素,但赵明诚苦于文采不足难于唱和,令他有江郎才尽之感应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正是这种对自我才华的充分自信,使李清照站在了女性文学的至高点上。历代评论家对其文学成就也是推崇备至。如“才力华瞻,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文采第一。”[5]“闺秀词唯清照最优,究若无骨,存一篇尤清出者。”[6]“易安居士能书能画又能词,而尤长于文藻。迄今学士每读《金石录序》,顿令心神开爽,何物老妪,生此宁馨,大奇大奇。”[7]因为李清照卓越的词学成就,更多的批评家则完全把她与男性一流大家相提并论,给予其极高的盛誉。如“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8](沈谦《填词杂说》)“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词之正宗也。”[9]“清照以一妇人而词格乃抗轶周、柳,虽篇帙无多,固不能不宝而存之,为词家一大宗矣。”[10]就连曾经指责李清照“不终晚节,流落以死”的朱彧也在《萍洲可谈》中极力称赞她:“本朝妇女之有文者,李易安为首称……词尤婉丽,往往出人意表,近未见其比。”
朱淑真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就受到文学艺术的熏陶,擅诗词、工书画、晓音律,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大家闺秀。少女时代即对自己的才学非常自信,她曾说“谢班难继予惭甚”(《贺人移学东轩》)[4]32,把自己比为晋朝的谢道韫与汉朝的班婕妤。但封建社会不会给她提供展现自己才干的机会,诗人只能“默默深闺掩书关,简编盈案小窗寒。却嗟流水琴中意,难向人前取次弹。”(《春书偶成》)[4]35“孤窗镇日无聊赖,编辑诗词改抹看。”(《寓怀》其一)[4]38阅读和写作激发了朱淑真在封建礼教压抑下蒙昧的女性意识,伯牙在深山弹一曲《高山流水》竟能惊喜地遇到钟子期这个知音的赏识,但有着不随流俗的清操雅志的自己,却是只能“难向人前取次弹。”孤寂中只能嗟叹机遇难逢、知音难遇的惆怅,以抒发自我价值难以实现的忧思。朱淑真也如李清照一样非常善于表现自己的诗歌才赋,朱淑真曾去魏夫人家赴宴饮酒,魏夫人叫丫鬟们表演歌舞,并向朱淑真索诗,朱淑真当即赋诗五首。这五首诗的题目是《会魏夫人席上,命小鬟妙舞,曲终,求诗于予,以“飞雪满群山”为韵作五绝》。从其题目来看,五首诗的韵正好组成了一句诗。朱淑真杰出的文学才华在她死后不久即引起了后人的关注。在现存的资料中,最早见于魏仲恭的《断肠诗集·序》:“尝闻摛藻丽句,固非女子之事。间有天姿秀发,性灵钟慧,出言吐句,有奇男子之所不如,虽欲掩其名,不可得耳。如蜀之花蕊夫人,近时之李易安,尤显著名者。”孙寿斋在《断肠集》后序中对朱淑真也略有评价:“有如朱淑真禀嘲风咏月之才,负《阳春》《白雪》之句,凡触物而思,因时而感,形诸歌咏,见于词章,顷刻而就。一唱三叹,听之者多,和之者少,可谓出群之标格矣。”正是朱淑真在文学上表现出的卓越才华,自元代以来,已有不少文评家对朱淑真的诗词细加评论,有些甚至把她提升到了和李清照相提并论的地位,认为她们是宋代女作家中的双璧。
三、对自身爱情主角地位的确认
宋代女作家有着较高的文学修养、聪慧敏感的内心,在感情生活上她们往往不甘囿于传统礼教的束缚,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而是主动追求爱情,寻求美满幸福的婚姻。作为婉约派正宗,李清照写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爱情词,这些爱情词中的女子,不再作为循规蹈矩、只是被动接受男子爱恋的传统女性出现,而是以一种主动的姿态追求自己爱恋的对象。如李清照《点绛唇》中的“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2]13把她借嗅青梅而偷瞥意中人时娇羞、俏皮的神态活泼灵动地表现出来。后世有人认为此词是一首娼妇之词,因为在封建卫道士的眼里,这样的行为是不符合封建礼教规范的,但这正好从反面表明李清照在爱情方面的大胆和自主。其《浣溪沙》(绣面芙蓉一笑开)中那位娇美多情的青年女子与心上人幽会并相约在月夜花影中再度幽会的情景,也正反映出她内心对爱情主动热烈的追求。《减字木兰花》(卖花担上)的女主角从花担上买得一枝含苞待放的梅花时,担心情郎认为“奴面不如花面好”,因此“云鬓斜簪,徒要叫郎比并看。”[2]18貌似撒娇的执拗中,表现的也是女性对于爱情大胆而巧妙的追求,是同所爱之人在情感交流中的主动态势,明确表现出超越封建女性的自尊自爱与大胆自信。她的写相思之苦的闺情词,在缠绵悱恻之中也始终掌握着一种与对方平等交流的话语权。其中首屈一指的当属《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此词是李清照前期抒写别愁的代表作,极力倾诉对丈夫的苦思深念之情,但这种倾诉是建立在与对方平等交流的基础上的。尤其是“一种相思,两处闲愁”[2]19,在写自己相思之苦、闲愁之深的同时,充分显示了夫妻情爱之笃和彼此信任之深。她的《瑞鹧鸪·双银杏》中的“居士擘开真有意,要吟风味两家新”[2]18借“新”“心”谐音隐喻自己和丈夫两心相连。
与封建社会传统女性在感情婚姻中只能处于一种完全被动的地位不同,宋代部分觉醒的女作家在爱情中采取主动态势追求自己的知心伴侣。朱淑真从少女怀春开始,就编织着美好的爱情理想,在她看来,诗女配才郎,才是理想中的爱情生活,她的“待将中秋抱满月,分付肖郎万首诗”(《秋日偶成》)[4]71就明确表达了这种追求。而“更深露下衣襟冷,梦到阳台不奈醒”(《夏夜有作》)[4]46中则借“阳台”之事,极言自己在梦中与意中人追逐欢乐的情景。“愿教青帝长为主,莫遣纷纷落翠苔。”[4]46(《惜春》)祝愿连理之花常开不败也是基于她对永恒爱情的期待。在现实生活中她也是毫不畏惧地寻求爱人,并找到了自己理想中的爱人,从“坐上诗人逸似仙”(《湖上小集》)[4]47可知这是一个英俊潇洒、才华横溢的年轻诗人,作者本来把自己与这个青年诗人认定为一对佳偶,“白璧一双无玷缺”(《湖上小集》),但“吹箫归去又无缘”(《湖上小集》)[4]47,美好的爱情终究只能以悲剧结尾,这种有情人难成眷属的遭遇不能不令她感到痛心和遗憾。所嫁非偶后,朱淑真在反思自己感情的同时进行了不屈的抗争,其《愁怀》、《黄花》、《秋日述怀》等诗中的忧愁怨恨之语就是她对封建礼教作出的大胆的叛逆。夫妻关系破裂后,朱淑真与丈夫分居,返回娘家杭州过独居生活,朱淑真在怨恨交集的哀愁生活中,奋起抗争,试图找回自己失去的幸福,其感情生活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对昔日情人的爱火更加炽热地燃烧起来。在《清平乐·夏日游湖》中,朱淑真描述了自己与情人幽会时甜蜜幸福的爱情:“恼烟撩露,留我须臾住。携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黄梅细雨。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2]87这是她大胆表达自己惊世骇俗的恋情的一首词。烟雨蒙蒙的梅雨季节,朱淑真和恋人漫步游湖赏花。情至浓处,再也按捺不住爱的激情,情不自禁地躺在恋人怀里如痴如醉地享受这爱情的甜蜜与幸福。虽然朱淑真的爱情最终在封建礼教的扼杀下酿成了一幕人间悲剧。但在强调“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森严的封建社会,朱淑真这种不避世俗的目光,主动勇敢地追求自主爱情的行为,无疑是对封建礼教的大胆反叛。
张玉娘是宋末元初的诗人,其爱情生活可称得上是一出“梁山伯”与“祝英台”式的爱情悲剧。张玉娘与未婚夫沈荃自幼青梅竹马,在沈荃赴京应试的几年时间里,刻骨的相思折磨着玉娘,也成就了她众多的爱情名篇。如《山之高》写出了玉娘在皎洁的月光下热烈而满怀忧愁地思念被高山阻隔在远道的心上人,尤其是“汝心金石坚,我操冰雪洁”[3]411的告白充分表达了诗人对爱情的不懈追求和忠贞不渝。沈荃死后,父母欲替其另择佳偶,玉娘悲苦不已,矢志守节,五年后因相思抑郁而死。但玉娘的死与封建妇道所要求的“贞节”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他们虽然也曾凭了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有过形式上的订婚,但终究还是与当时那些男女双方一面不识毫无感情者不同,而是有着坚实的感情基础,因此玉娘为情而亡的举动不能说是困守封建礼教的贞节,而是对于自己纯真爱情的坚守。
[1]王延梯.中国古代女作家集[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
[2]李清照,朱淑真.漱玉词·断肠词[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
[3]郑光仪.中国历代才女诗歌鉴赏[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
[4]黄嫣梨,吴锡河.断肠芳草远——朱淑真传[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
[5]胡云翼.中国妇女与文学[M].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125.
[6]王 灼.王灼集·碧鸡漫志卷二[M].成都:巴蜀书社,2004:11.
[7]周 济.词辩·介存斋论词杂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58.
[8]张 丑.清河书画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78.
[9]张 璋,职承让,张 骅,等.历代词话全编[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189.
[10]徐釚,唐圭璋.词苑丛谈[M].上海:中华书局,2008:69.
Awaking of self- awareness of Song authoress and its poetic presentation
XIE Se
(Tourism Management Department,Hunan Women’s University,Changsha 410004,China)
The awaking of women’s self-awareness is a long and arduous process.Compared to the Yuan,Ming,Qing dynasty,the women in Song dynasty lived in a more relax and fre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their self-awareness awoke in certain degree.A group of female writers such as Li Qingzhao,Zhu Shuzhen and Medame Wei appeared in that period.This paper presents their awaking of self-awareness in their poetries from three aspects: Seeking actively for ideal; having self-confidence for artistic talent; self-confirming the female’s subject position in love.
authoress; self- awareness; poetic presentation; Song dynasty
I205
A
1009-2013(2012)01-0087-06
2011-12-21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0YBA123)
谢 穑(1970—),女,湖南益阳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宋词。
曾凡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