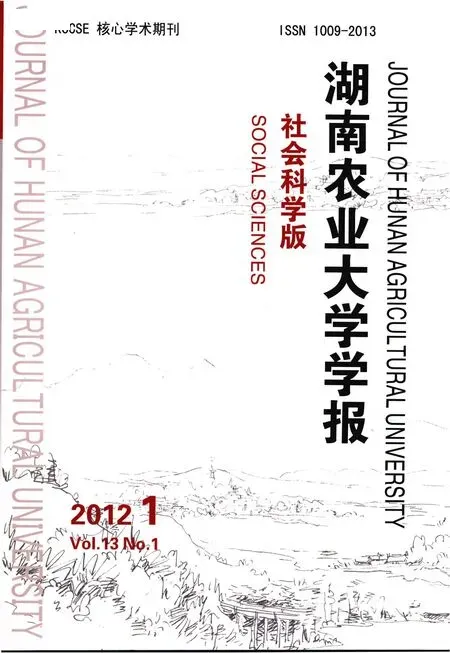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优化路径——再论“国家与农民二元产权制”
2012-04-08窦祥铭
窦祥铭
(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优化路径
——再论“国家与农民二元产权制”
窦祥铭
(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土地制度历来是农村变革的关键,其要义在于产权。中国现有农地产权制度存在土地所有权主体虚位、土地使用权不稳、土地收益权受限、土地处置权不完整等缺陷,亟待改革。本着间接或直接地淡化农地集体所有制,给予农户更多的具有所有权特征的永佃权或财产权的共识,学术界形成了三种主要观点:取消农地集体所有制,实行私有化;取消农地集体所有制,收归国有;保留农地集体所有制,对其进行改良完善。单纯的国有化、私有化以及改良完善化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都因存在无法克服的障碍而不足取,考虑到中国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制度和私有产权对农业生产强大的激励作用,为减少制度改革成本,实行农地“国家终极所有,农民永久使用”的“国家与农民二元产权制”比较而言更为合适。
农地产权制度;集体所有制;二元产权制
农村土地是一个涵盖范围较为宽泛的概念,一般定义为农业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前者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用地等;后者包括城乡住宅和公共设施用地、工矿用地、交通水利设施用地、军事设施用地等。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为避免在一个论题中将农村土地全部囊括进去而造成主题混乱甚至繁杂,本文中的农地概念专指农业用地中与农民关系最为密切的耕地。农地制度是指人们占有、支配和使用农地过程中所结成的各种经济关系的总和,包括农地所有权制度、使用权制度、经营制度、储备与征用制度、用养制度等。农地产权是指以农地所有权为基础、以农地使用权为核心的一切关于农地财产权利的总和,它主要包括农地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等各种权利组成的权利束。农地产权制度是指一个国家在法律上对农地产权结构和产权关系的制度安排,它主要包括农地产权结构及其性质方面的制度安排、农地产权关系的制度安排和农地产权国家管理和调控的制度安排。农地产权制度是农地制度的核心问题,农地产权制度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农地资源及其它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基于此,运用现代产权理论,合理界定和安排农地产权,构建一套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农地产权体系,就成为当前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重点和必然。
一、中国现行农地产权制度的主要问题
中国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伊始,这种制度安排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还原了中国传统农业家庭经营的最优特征,曾产生过巨大的制度收益。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地产权制度所固有的内在缺陷也不断凸显出来,从产权构成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土地所有权主体虚位
中国《宪法》、《土地管理法》、《民法通则》、《农业法》和《物权法》等法律都规定了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但对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主体是谁,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含糊不清。《宪法》第10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土地管理法》第10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民法通则》第74条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1986)》)《农业法》第11条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各该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1993)》)《物权法》第60条规定:“对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依照下列规定行使所有权:1)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2)分别属于村内两个或两个以上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3)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宪法》仅笼统规定农村土地属集体所有,对所有权主体并未涉及。但从《土地管理法》、《民法通则》、《农业法》和《物权法》的相关条款中可知,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农业生产合作社都可以成为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代表。尽管以上法律都规定集体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但“农民集体”属于何种民事主体在法律上没有作出界定。目前,“农民集体”是法律形式意义的能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民事主体,而不是法律实质意义的能真正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民事主体,造成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虚位或虚化。
2.土地使用权不稳
土地使用权是指经营使用土地的权利。虽然国家从法律和政策上明文规定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第一轮承包期为15年,第二轮承包期为30年),但是因为土地目前承担着农村社会保障的重要功能,因此在实践中因人口的变动而相应产生的对承包地的调整也就不可避免。据 1997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对全国266个村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在调查的266个村中,有212个村进行过土地调整,占调查总数的80%,其中调整2次及以上的村有149个,占调查总数的56%。[1]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所2008年组织的对17省1656个村农地使用权状况调查数据表明:自分田到户后,被调查村进行过土地调整的次数平均为2次。63.7%的村在二轮承包时进行过土地调整,34.6%的村在二轮承包之后还进行了土地调整,调整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变化(64.5%)和征地(10.6%)。[2]趋于普遍和频繁的土地调整使农户对土地使用权缺乏安全感,难以形成对土地投资的长期预期,导致农户土地经营行为的短期化。
3.土地收益权受限
土地收益权是指在土地上取得某种经济利益的权利,土地使用者可以通过土地收获物,土地自身增值,土地转让、转租等取得经济收益。土地收益权是农地产权最实质内容,农民如不能有效拥有土地收益权,那么土地及土地产权对于他们也就失去了现实的意义。因为土地属有价物品,农民作为土地的承包经营者,有权利通过处置土地和转让土地使用权获得土地收益。但在实践中,农民土地权益并未得到有效保障。尤其是国家对农民土地收益权的侵犯,妨碍了土地本身价值对农民经营土地的激励。中国《宪法》和《土地管理法》都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样的制度安排,使政府垄断了土地一级市场,成为土地征收和土地供应的垄断者。政府利用征地权将农地转为非农用地(建设用地),通过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给予被征地农民一定补偿后,将建设用地使用权按市场价出售,通过这一征一售两定价,政府从中赚取巨额差价。这种做法对农地所有者和使用者十分不利,因为集体和农民无法分享自己的土地在城市市场所产生的增值效益。[3]据有关学者估算,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通过一征一售两定价方式从农民手中获取的经济收益达 15万亿人民币,而被征地农民获得的补偿不到其中的5%。[4]此外,被征地农民土地补偿款在逐级纵向分配过程中被截留现象也愈发突出。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2006年的调查,在被征地的农民中,仅有41.2%的人拿到足额的补偿款,另有29.4%的人完全没有得到补偿。[5]
4.土地处置权不完整
土地处置权是农民具有对土地进行独立处置的权利,包括处置经营土地所获产品的权利和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权利。农民是否享有对土地财产的处置权,是农民是否拥有土地产权的象征,也是土地使用权是否完整的一大标志。但在现实中,农民土地处置权往往是不完整且缺乏保障的,从目前最能诠释土地处置权的土地使用权流转来看,即可略知一二。虽然中央2001年第18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指出“土地流转的主体是农户,土地使用权流转必须建立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农户流转土地,也不得阻碍农户依法流转土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 33条也明文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应当遵守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2002)》)但近些年来,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内地农村的一些地方,都出现了集体经济组织甚至乡(镇)政府出面,为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强迫或半强迫农户流出土地的现象。《土地管理法》第 2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但是事实上征地权已被滥用于非农建设的任何领域,但凡农地变为建设用地政府就会动用征地权,“公共利益”的范畴往往被“蓄意”扩大。可见,国家征地的行政性强制色彩颇浓,实践中也能验证这一特点。东部沿海省份1997―2004年,每年建设用地达40―50万亩,征用土地占建设用地比重高的到90%以上,低的也要到75%。陕西省1994―2003年各类非农建设占用耕地达72.79万亩,其中征地仍是主要手段,占建设用地近90%。[6]在政府与农民土地权益博弈中,政府往往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拥有超法律的强制力和决定权,农民无法自由决定自己的土地是否被征用,征用用途和价格等,而只能屈从于政府的意志。因此,土地最终处置权掌握在政府手中,农民对土地的处置权是残缺的。
二、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观点评析
针对现行农地产权制度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尽管学术界对于应如何改革的观点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基本认识是相同的,即应间接或直接地淡化农地集体所有制,给予农户更多的具有所有权特征的永佃权或财产权。[7]在此基础之上,学术界形成的改革观点主要有三种:
(1)取消农地集体所有制,实行私有化。该观点以杨小凯、周其仁、文贯中、蔡继明、温锐等学者为代表。例如,杨小凯教授就认为,“土地私有化会加剧贫富分化,造成社会不安定”的说法完全不合经济学逻辑。他认为,如果土地所有权完全私有了,农民将成为自由民,若农民要弃农进城,或从事他业,他可以卖掉土地,不但有一笔收入,而且有一笔资本,因此,他进城时是有钱人,而不是盲流。杨小凯还认为,土地所有权私有化不但对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减少社会纠纷,安定社会,稳定地方财政有重大意义。[8]对于农地私有化方案,其实施的收益具有可预期性,因为农民获得真正独立、完整、排他性的土地产权,满足了农民占有土地的心理需求,且因私有产权本身具有较强的利益激励和较硬的财产约束,因而可以激发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激励农民珍惜土地、增加对土地的长期投入,并为农地市场的建设奠定明晰的产权基础。[9]但是,目前在中国实施农地私有化方案的成本太高,存在很多难以逾越的困境:第一,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必须坚持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土地私有化会引发社会基本制度的巨大变更,有悖于中国的政治理念,具有极大的政治风险,其变革和运行必然会遭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刚性制约。第二,在土地依旧承担着农村重要社会保障功能的背景下,在非农就业渠道还不宽泛的情况下,部分在土地自由买卖过程中出让土地所用权的失地农民势必会面临生存危机,这无疑会增加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甚至引发社会动荡。第三,鉴于土地资源的特殊重要性和其在中国的极端稀缺性,土地私有化后,农民会把保有小块土地作为财产增值的手段而不愿轻易转让和出卖,这样非但不能促进土地的集中,反而妨碍土地的流转和集中,最终影响到农业的规模化、现代化和企业化经营。
(2)取消农地集体所有制,收归国有。支持该观点的学者以周天勇、刘俊、张德元、刘恒中、钟良等为代表。例如,刘俊教授认为,土地国有化不仅可以实现效率目标,而且通过制度设计还能实现公平价值目标。在集体土地国有化后,土地问题主要在于土地利用问题,如果土地利用合理而有效,不会引发社会的贫穷问题。他还认为,农地国有化方案是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必然走向和最优制度设计,也是顺应社会发展趋势、释放新制度绩效的必由之路。[10]农地国有化方案在理论上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它能够有效地提高国家对土地资源的管理效能,有利于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防止土地兼并,国家可以在较大的范围内调整对土地的使用,为国土的统一整合和利用提供可靠的保障。同时,产权的明晰还有利于遏制乡(村)干部利用土地所有权营私舞弊和任意加重农民负担等违法现象。但囿于现实的客观因素,在当前和今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都不具备全面实施农地国有化方案的条件:第一,农地国有化无非有无偿剥夺和有偿赎买两种途径。无偿剥夺农民的土地,贸然将土地收归国有,强行割断农民与土地之间的感情,势必会遭到农民的强烈反对,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而有偿赎买农民的土地,如按土地市场价购买,粗略估算花费约需两万亿人民币之巨,国家目前根本没有如此大的财力去收购农村集体土地。可见,上述两种途径都不具备现实的可操作性。第二,农地国有化后,土地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不管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农民集体”这个概念如何模糊,国家拿地总归还需走征地程序,须与“农民集体”沟通协商,对被征地农民给予一定的补偿。而“农地国有”实践上很可能逐渐演变成为土地基层政府所有。绕开“农民集体”的制度约束,基层政府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似更加可能发生。第三,农地国有化后,国家对土地的管理效率是否一定比农民个体高也值得考虑,因为对国有后的农地管理会异常复杂,需要一个庞大的机构,行政成本会大幅增加,更有可能会出现以地寻租的行为。
(3)保留农地集体所有制,对其进行改良完善。该观点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持此观点的学者较多,以周诚、党国英、陈小君、王利明、张红宇、韩俊、李昌平等为代表。例如,周诚教授认为,保留土地私有的历史时机已经失去,实行土地国有的时机还未到来,最好的选择是完善农地集体所有制。长期研究中国农地问题的罗依·普罗斯特曼教授也建议中国继续实行农地集体所有制,而给农民较长期的农地使用权。[11]改良与完善现行农地集体所有制确实能有效避免农地国有化或私有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剧烈政治斗争和经济利益冲突,减少制度变迁中的改革成本,也符合中国的政治理念和政府倡导的意识形态。但这种改革方案只是对原有制度的小修小补,不能从制度根源上解决农民土地财产权问题,问题比较突出:第一,中国现行的农地集体所有制是移植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衍化而来的,斯大林模式是斯大林歪曲马克思主义推行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只能统一、不能分离的极端国有化模式。因此,农地集体所有制不是中国农村改革与建设实践的产物,背离中国具体实际,几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它并不是一种最有效、最合理的的农地制度,其正效能已经释放完毕,目前其存在的问题显示其亟待彻底改革。第二,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农业集体化是国家为发展工业化而强制性地在农村建立起来的一种制度,而并非农业生产自身发展的需要,它违背农民的意愿,背离当时中国的国情,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民公社解体后,农村集体经济名存实亡,但由农业集体化而产生的农地集体所有制并没有随着人民公社的消亡而被废除,现在仍阻碍着农村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第三,只要农地集体所有制继续存在,就决定农地所有权主体是空泛的“农民集体”,空泛的“农民集体”必然需要安排代理人代表其行使农地所有权,而代理人也存在重视土地经济效益的逐利性,因此也可能对土地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产生诸多不利的影响,并威胁到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并且,农地集体所有权很可能会出现被代理人架空甚至滥用的状况。[12]
三、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优化路径
在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问题上,单纯的国有化或私有化以及改良完善化都因存在或此或彼的无法克服的障碍而不足取。究竟什么样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才是与中国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相适应的优化路径选择呢?笔者认为,考虑到中国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制度和私有产权对农业生产强大的激励作用,为减少制度改革成本,慈鸿飞教授提出的农地“国家终极所有,农民永久使用”这样一种“国家与农民二元产权制”比较而言更为合适。[13]农地“国家终极所有”,国家获得的是土地法律形式意义上的所有权,这与中国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刚性要求相适应。事实也早已证明,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存在,直接原因在于产品的所有权在分工不同所有者之间的互相交换中发生了转移。这种发生转移的所有权,可以是完全所有权,包括法律和经济上的所有权;也可以是因两权分离而只限于法律上的所有权。而土地“农民永久使用”,农民获得的是土地经济实质意义上的所有权,因为赋予农民土地永久使用权,表面上看似乎是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的两权分离,但实际上却暗含两权在某种意义上的统一。因此,这样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一方面,它具有和私有产权一样的效用,能最大限度地调动经济人生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它或可被看做是私有产权制度的一种适度运用;另一方面,国家具有最终的控制权和裁决权,它可能比单纯的法律调控更具效力。可以说,这是一个利国利民,兴利除弊的最佳农地产权制度。[13]
1.支持依据
“国家与农民二元产权制”并非凭空构想,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依据。通过梳理 1949年以来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历史,我们能得到某种历史规律性的启示,那就是私有产权与个人利益相关联的农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生产具有巨大的激励效用,农地产权制度的选择最根本的应是激励机制的选择。例如,土地改革彻底废除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确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农民获得了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在内完整的土地产权,农民有了自己可以支配的生产要素,也就有了从事农业生产的动力;土地改革后的合作化运动逐渐侵蚀直至剥夺了农民对土地等财产的私有产权,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直接导致国民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在农地所有权与使用权两权分离的基础之上,实行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民获得了较为稳定的农地使用权和部分收益权及处置权,生产积极性相比合作化阶段大大提高,从而增强了农业发展的后劲,使中国农村经济焕发出前所有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因此,实行“国家与农民二元产权制”,赋予农民相对完整的土地产权,这应是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逻辑性选择。并且,现实土地政策的演变也能在某种意义上支持“国家与农民二元产权制”。在家庭承包责任制初期,土地承包期比较短,只有1―3年,土地经常变更。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把土地承包期延长至 15年以上。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十次会议通过的《土地管理法》第一次将土地承包期限30年明确下来。[14]2005年3月14日,对于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期限,温家宝总理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则明确肯定将会“长期不变,也就是永远不变”。2008年9月30日,胡锦涛总书记到安徽省小岗村考察时,更强调指出“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实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年10月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规定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土地承包期限从最初的 1―3年,到后来的15年、30年,再到目前的“长久不变”,农民已获得了土地趋于“永久”的使用权。况且,当前的农地集体所有权在收益、处置等方面的权能受到国家严格的控制和限制,是一种不完整的所有权,在国家的最终控制和裁决下更多地是“徒有虚名”而已,而农地国家终极所有只不过是为其“正名”的顺理成章举措,根本不会损害农民的土地权益。在此基础之上实施“国家与农民二元产权制”,可谓是顺应时势之举。
2.实施的基本路径
为兼顾效率与公平,减少制度变迁中的改革成本,笔者提出一种渐进的以实现“国家与农民二元产权制”的实施方案:第一步,国家通过立法,直接赋予农民一项无期限的、不再承担生存保障社会功能的、可在限定用途范围内自由流转的、可继承的、可抵押的、可买卖的真正独立的土地使用物权,即“永久使用权”。第二步,国家通过政策调整或立法在法律和事实上继续“虚化”目前已没有太多实际意义的农地集体所有权,逐步确立国家对土地在法律形式意义上的所有权,即“终极所有权”。第三步,待前两步做实之后,国家颁布新的《土地法》,从法律上肯定农民对土地的永久使用权和国家对土地的终极所有权;国家授权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对全国土地进行宏观管理的“警察权”,并以国家名义向农民颁发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土地永用权证以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永久使用权;国家征收象征国家权力的土地税和象征所有权权力的平均地租、级差地租。
3.优越性表现
“国家与农民二元产权制”与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相比,具有显著的优越性:第一,从法律上直接明确了国家对土地的终极所有权,并通过立法保障农民土地永久使用权的合法性、排他性和不受侵犯性。因为农民手中的土地永用权证是由独立于政府的国家直接颁发的,所以基层政府干涉和侵犯农民土地权益的行为会有所遏制。第二,将土地使用权明确地、永远地、完整地交给农民,农民等同于获得了土地经济意义上的所有权,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两权统一使农民手中的土地产权趋于清晰和完整,农民对土地使用有了长期预期,这有利于激励农民对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并鼓励农民在土地上进行长期规划和投资。第三,将农民手中有限的、不确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变为永久的、确定的使用权,农民可以根据个人意愿和市场规则自由地保持或流出土地永久使用权,这有利于农业走向适度规模化经营的现代化道路。[15]
4.需要考虑的问题
“国家与农民二元产权制”的实施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它是一项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在实践过程中必定会出现诸多难题。例如,很多人认为,土地国有就是剥夺农民,此项改革违背农民意愿,侵犯农民权益,势必会遭到农民的强烈反对,改革风险大,成本高,甚至会引发社会动荡。但在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下,农民很难成为土地的主人,因所有权主体虚位或虚化,农民的土地权益更易受到多方的侵害。因此,将土地所有权收归国有,通过明晰所有权主体,在国家的最高监管和调控下,农民的土地权益非但不会过多失去,反而会得到更持久的法律上的保障。况且,这种国有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土地国有,国家仅在宏观管理、协调监督、政策指导、收益分享、最终处置等方面享有土地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还有不少人担心,赋予农民土地永久使用权,此举与土地私有化无异,这必然会造成一部分农民在土地自由买卖过程中出让土地所有权而失去基本生活保障,甚至面临生存危机。这不仅有悖于党长期坚持的“耕者有其田”的理念,而且会造成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加剧农村贫富两极分化,不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但事实上他们的担心很可能是多余的,参照国外典型国家高效、发达农业的有益经验,农地最终归少数农业经营者、甚至非农业经营者所有,这是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必然趋势,我们须关注的重点是如何让这个变化合理、公平、有效、平稳地发生。并且,失地农民真正需要的并不是土地,而是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充分就业的机会。而且,土地农民永久使用,赋予农民的是在占有支配、经营使用、自主决策、收益占有、合理处置、产权继承等方面的土地经济意义上的所有权,与私有化不可同日而语。此外,还有很多人提出如何分配土地,怎样征收土地税、地租等等问题。这些问题是实施“国家与农民二元产权制”必须面对的客观难题,需要事先作好大量的论证和准备工作,但它们超出本文探讨的范围,就暂且存而不论了。
总之,农地“国家终极所有,农民永久使用”这样一种“国家与农民二元产权制”既可保持土地社会主义公有的性质,减少土地国有或土地私有的改革成本,又能赋予农民稳定、明晰、排他这样一个完整的土地产权,摒弃现行农地产权制度所固有的弊端,因此它是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优化路径选择。但是,“国家与农民二元产权制”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综合性制度改革,必须以农民的利益为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进行充分的理论、思想和舆论准备,做好改革技术方案的设计,并充分关注和尊重农民对土地的特殊感情。
[1]申端锋.农村土地问题不只是农民权利问题——以中部某省粮食主产区三个村庄的土地调整为例[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26-32.
[2]叶剑平,丰雷,蒋妍,等.2008年中国农村土地使用权调查研究——17省份调查结果及政策建议[J].管理世界,2010(1):64-73.
[3]张立彦.中国政府土地收益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139.
[4]叶 檀.警惕以名义剥夺农民土地红利(2010-12-17[2011-10-12].http://epaper.jinghua.cn/html/2010-12/17/content_613433.htm.
[5]陆益龙.农村土地征用问题:现状及成因分析[J].学习与实践,2009(1):112-116.
[6]蒋省三,刘守英,李青.中国土地政策改革——政策演进与地方实施[M].上海:三联书店,2010:10、46.
[7]曾令秋,胡健敏.新中国农地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92.
[8]韩 俊.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农村经济卷1978―2008[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43.
[9]易永锡.中国当代农地制度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249.
[10]刘 俊.土地所有权国家独占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319.
[11]廖洪乐.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六十年——回顾与展望[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99.
[12]王安春.1949年以来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及创新选择——以江西省铅山县为例[D].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169.
[13]慈鸿飞.西部农业开发与生态中外比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75.
[14]叶国文.土地政策的政治逻辑——农民、政权和中国现代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251.
[15]刘恒中.再论“国家所有、个人永用”的土地制度[C]//蔡继明,邝梅.论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114-133.
Path of optimizing China's rural land property rights system reform: More discussion on the system of nation and farmers' dual property rights
DOU Xiang-ming
(Social Development Department,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7,China)
The farmland system has always been the key to rural reform,its righteousness lies in property rights.The defects of China's existing farmland property right system mainly are absence of land ownership subject,instability of land use right,limit of land usufruct,incompetence of land disposition and etc.In line with desalt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e collective ownership of land,give farmers more ever-growing right or property rights having ownership's characteristics,academic circles formed three main points of view: 1)to cancel farmland collective ownership and implement privatization;2)to practice nationalization instead of collective ownership;3)to keep collective ownership of land and improve it as well.However,analysis shows that none of the three views mentioned above can be carried out because all of them exists obstacles.Considering the fact that China's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have powerful incentive effect on agricultural industry,the author suggests to implement nation and farmers' dual property rights system in which the nation enjoys the ownership of farmland ultimately but farmers enjoy the use right of farmland permanently so as to reduce the cost of system reform.
rural land property rights system; collective ownership; dual property rights system
F301.1
A
1009-2013(2012)01-0001-07
2011-11-30
窦祥铭(1986— ),男,安徽太和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农村土地制度。
李东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