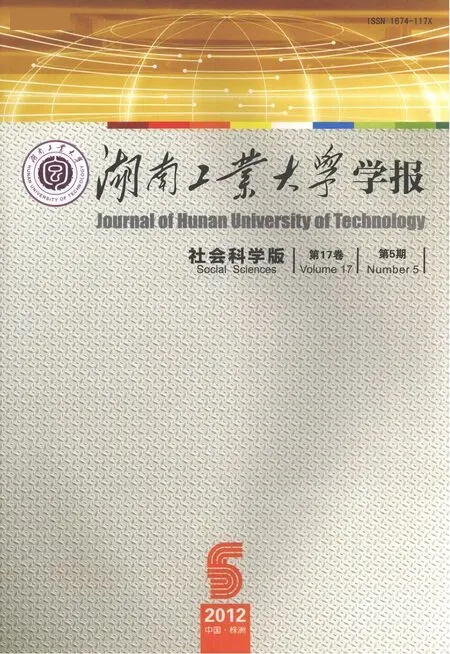少鸿小说的意义阈
2012-04-08夏子
夏 子
(湖南文理学院 文史学院,湖南 常德415000)
一般来讲,阈的所指是某种精神维度,或即文学思想意义的深度、广度和高度。意义深、广度是根系,是大地的厚重,是历史纵深,是绵延的“人生之心境情调”;[1]意义高度则是花朵,是智性的芬芳和未来召唤,是海德格尔特指的那种缄默的本真能在。
对于写作经验,少鸿一直是审慎甚至回避对待的,这一“缄默”态度使他很少“慷慨地捐献‘创作谈’”[2]140之类文字,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有关文本意义或“意味”的阐述。在他看来,作家的最大收获和价值实现“不在于他写了多少作品……而在于他建立了自己的一块精神领地,他可以邀请人们来这块领地上做客,领略心灵世界的旖旎风光,让人们认识他,也认识人们自己”。[2]135据此,少鸿进一步认为,“所谓小说创作,简而言之,就是叙述有意味的故事。”[2]153“我要考虑赋予故事某种意味,让意味弥漫其间,让它从文本中氤氲起来,散发出来,进而感染读者。没有意味的故事难以成为小说,更难以成为好小说。”[3]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少鸿创作力图超越经验,直面灵魂,自觉追问和探寻人的存在,就实际情形而言,新世纪以来接连出版的《溺水的鱼》《花枝乱颤》《抱月行》《大地芬芳》等长篇小说也的确呈现着一个个具备丰富可能性的寓言状态,由此构筑起属于他自己的精神领地和意义世界。
一 那个孤独的人
从几个主要形象看,尤奇、袁真、覃玉成、水上飙、陈秀英乃至陶秉坤等人物明显就是克尔凯郭尔所说的“那个孤独者”。
那个孤独者的本质实即主观思想者,是立足个体此在而又连接和通往“上帝”或所谓终极存在的一种精神自我。有“意味”的是,孤独的个体常常要面对一些悖论式的生命尴尬,正如柏拉图《泰阿泰德篇》记载的那位泰勒士先生一样,一心仰观天象,不慎跌入井中,结果被侍女嘲笑:你急于了解高天之上,却忘了脚边身旁一切!无独有偶,上世纪末人文精神大讨论中,“躲避崇高”的那一群与“拒绝妥协”那一派几度交锋,煞是热闹,最终仍只落得个“废墟嘲笑废墟”[4]而草草收场,回头看看,躲避者不见得就那么恶俗不堪,而拒绝者也未必就那么冰清玉洁。其实,按照海德格尔的解释,此在之外还有一个共在,它们是蜗牛在壳中式的一个整体,而那孤独者同时也必然地和“常人”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在首先是常人而且通常一直是常人。”[5]150惟其如此,他才能在人生“被抛”历程中不断消解那些悖论式尴尬并从而获得一种诗意栖居品格。所以,躲避也好,拒绝也罢,问题症结就在于忽略了整体可能而把一个方面推向极端。
尤奇、袁真(或者还有那个秦小谨)都是被抛和栖身“官场”的孤独者。应该加以区分的是,这个官场并不完全等同于一般所是的那个官场,其意义指向已经被充分虚拟化、能指化。对此,少鸿曾明确表示:“我也不太认可官场小说这一说法,我写的是官场人小说。文学关注的是特定环境中的人,官场不官场,只是人物所处环境而已。”[3]这类区分、界定本来是必要的、有价值的,值得商谈的是,“官场人”这一颇具歧义的说法仍然只是意识到了人的存在的主导事实,相对弱化了此在与共在作为一种结构整体的本体论意义。换言之,人(尤奇、袁真)与环境(官场、周围世界)是鱼水一样密不可分的结构整体,他们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的关系(尽管往往是那种悬浮、冲突的联系)。强调这一常识绝非意指少鸿企图拔着自己头发脱离地球,相反,一般所是的“那个”官场环境恰恰是需要加以弱化的,如此才凸显出“这个”官场环境的在场及人的“在其中”意义。那么,“这个”官场又是什么呢?米兰·昆德拉认为,“答案首先要求人对世界是什么有一种想法。对它有一个本体论的设想。在卡夫卡眼里的世界:官僚化的世界。办公室不是作为许多社会现象中的一个,而是世界的本质。”[6]45“……和约瑟夫·K 在法庭或土地测量员K面对城堡的处境一样。他们都处在一个世界中,这个世界不过是一个巨大的迷宫式的机关,他们逃不出那里,永远不明白它。在卡夫卡之前,小说家经常把机关揭露成个人与社会利益冲突的竞技场。在卡夫卡那里,机关是一个服从它自己的法则的机械装置,那些法则不知是由什么人什么时候制定,它们与人的利益毫无关系,因而让人无法理解。”[6]98可见,“这个”官场不是那种“个人与社会利益冲突的竞技场”,其“在场”意义十分重要,不仅不能弱化,相反应成为一种理性自觉,因为它就是世界,所涵盖、呈露的是人的利益(冲突)和世界的本质。
办公室是机关或“这个”官场的细胞。这个所在,如此纤小如此庞杂,如此空洞如此真切,仿佛牵系着世间万有和一切可能,又仿佛通往一个巨大的虚妄、虚无。这就是那个汇聚了诸多世故、摇曳着万般风情的“常人”,是那个“鲁四老爷”和弥漫在鲁镇上空及每个角落潮冷的空气……这个所在,好像什么都不缺,唯独缺少人——那种被海德格尔习惯称作的“本己的自己”;这个所在,所有祥林嫂们都将无可饶恕,所有“本真的自己存在”都将无处遁形。难怪不幸栖身于此的两位可怜的孤独者——尤奇、袁真刚一出场就都上演着(精神)逃离的悲剧。袁真是那种纯得让人心痛、美得无可挑剔的知识女性。她的逃离方式很沉静:上办公楼楼顶去“透口气”。这一再自然不过的举动居然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常人”们骇然以为她要跳楼了;秘书长吴大德匆忙前往“现场”信誓旦旦做劝说工作;几乎所有人都坚信袁真这下子“仕途”无望了;丈夫方为雄颇觉殃及池鱼、沮丧至极;表妹吴晓露甚至凭借色相代为寻求解释……被荒诞“包裹”的袁真好笑之余,也体验着一种彻骨的凄怆!这一场景不由使我们联想到约瑟夫·斯克沃雷奇讲述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捷克籍工程师前往伦敦参加学术研讨,回来就发现自己成了官方报纸所披露的那样的叛国者。上帝!他再也无法安宁地生活了——监视、窃听、跟踪、悻然、噩梦终于使他真的移民到了国外。[6]96这一情形,西方人称为卡夫卡现象,中国人叫做众口铄金。由此可见,庸常的力量对一切纯粹而言只是一种恶心、一种孤独和悲哀。再看看“那个孤独者”尤奇。他的逃离方式则更具某种形而上的苍凉意味,一出场就发出一声亘古旷世的“天问”:“什么是我该待的地方?”这一追问立即暴露出他全部的生命尴尬:贫寒的出身,卑贱的职位,微薄的薪水,虚伪的上司,“庸常”的妻子,沉重的义务……不,这些都不算什么,常态的日子并不可怕,“畏惧”常态并不能解决问题。这条“溺水的鱼”、这个年轻男人的全部委屈就在于:何处安置灵魂。实际上,他是非常清楚“自己”的真正需要的——睿智的思想的阳光、理想与信念的空气、真诚的情感的水,也许,这才是他该待的地方。
如果说知识者的精神孤独主要表现为这种极致对立、对抗的话,民间孤独形态是否更具一些融合、调和性质?或者说,民间孤独更基于某种情感的、道德的、诗性的选择?
把覃玉成跟水上飙放在一起对比考察是很有意味的(尽管不是同一作品中的人物)。他们绝对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日常存在,而在“本真的自己存在”意义上却又表征着高度的同一:逸出常态,回归孤独。覃玉成患有(后天)心因性性功能障碍,惧怕女人裸体,“不喜欢”女人,新婚之夜便逃离洞房去追逐一把月琴,这一去就是他的一辈子。常态来看,他的确就是个不可理喻、只知迷琴的“玩货”,过日子几乎一窍不通。然而,也正是这种无经验成就了宝贵的执著和本真,使他以一种懵懂的轻盈、精神的健全扛起了生的艰难与沉重,使南门小雅这样的好女人心甘如饴地坚守、相伴一生。与覃玉成不同,水上飙体格壮实,生命力健旺:喜欢和追求乡村女子黄幺姑,却又终生未娶;孤身一人,却又背负种种牵挂;无根无业,却能四海为家;性情桀骜,却能虔诚追随革命。相对而言,水上飙更具常态色彩,但常人却很难有他那样的快意恩仇,率性自由境界,因而,他又只是一个传奇、一种渴望,同覃玉成一样,本质上是诗意的、孤独的。
至此,需要强调的是,孤独现象涵盖和建树的是清晰而坚定的生命高度和精神气度,其本质并不指向迷惘、无助之类负面意义——上述人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二 大地芬芳
秘书长吴大德这样指责袁真:“(跑到楼顶)你不怕死吗?”袁真颇感好笑,心里嘀咕道:活都不怕我还怕死?这话说得好,倒过来说就更好、更具一种向死而生的勇气。“创世纪”有言: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来自泥土,仍要归于泥土。佛家也说,生本不乐。诚然,生命维艰,死是最广泛的事实,是命定和无奈的终极,是每一此在与生俱来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或“与众不同的悬临”(海德格尔语)。但是,生的意义向来就是在超越死亡阈限的途程中得到显现的。“向死存在的意思并不是指‘实现’死亡,那么向死存在也就不能是指:停留在终结的可能性中。”[5]300这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位匆匆过客一样,明知前面是坟,仍要奋然前行,更何况“那里有许多许多的野百合,野蔷薇”,死亡所见证、所激励的恰恰是九死未悔的坚韧和向死而在的新生。
和他心爱的人物陶秉坤一样,少鸿从来没有忘记自己脚下的土地,是一位真正在大地上行走的人。能这样行走的人,眼里便只有世事如潮、人间沧桑,胸中吐纳的只是对生命途程的感怀、悲悯和关切,体内缭绕的便是智性的芬芳。
20世纪是少鸿小说最主要的“曾在”,资江北岸的石蛙溪、沅水之阳的莲城是确定的大地,涌流、绵延、蒸腾于大地之上的所有那些忧烦、期待、操劳、撞击、挣扎、恶心、惊叹、好奇、愉悦、狂欢等等极具民间特质的“人生之心境情调”随即氤氲、散发为“芬芳”的意义世界,这一世界才最终“赋予”大地以新的姿态和品质。所以说,“作品使大地成为大地。”[7]石蛙溪这一大地形态的意义在于,它是南中国百年乡村的象征,“在其中”的陶秉坤是那些岁月的见证人,土地和人成为贯穿世纪的生命主题。活了102岁的陶秉坤为土地而生,为土地而死,有着近乎顽固的土地意识,这一意识就像那七星岩的星光,“悬临”、照亮他“方圆五十里,上下百余年”人生。地之吐生万物。的确,土地是血脉,是延续,是踏实,是安慰,是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流。整个20世纪就是土地问题的世纪:土地契约;土地争夺;打土豪、分田地;土地革命;土地战争;土改;土地公有;土地承包;土地开发……土地问题撼动世纪风潮,摇荡万家忧乐。从一位百岁老人的视角诉说百年情态,虽不是什么新奇创造,却仍然是十分必要和非常务实的,这种民间态度或民间视角所特具的方法论意义,使人们获得了关于百年乡村“曾在”清晰、完整、真实的印象。在陶秉坤意识深处,土地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其他都不过是浮云,是无价值、无意义的。他的一生表明,对土地的眷爱是生命的最后理由。四时流转,泥土芳香,薯藤乱爬,草茎甘冽,甚至牛背上丁丁草鸟的啼啭、瘦腿鹭鸶的闲适,一切都有着“说不出的熨帖和惬意”。缘于这种自然之爱或赤子之爱,才有了与土地问题密切关联的企望、忧思、受难和争斗,即便对待乡土地上的那一系列“革命”,价值评判与取舍的依据仍然是土地。土地意识赋予这一价值标准以更为本真的属性,合乎这一标准,“革命”便获得一种乡村合理性,否则就只是灾难。较之石蛙溪,莲城这一大地形态更多废墟性质和精神荒原意义。这是一个无根的所在。“被抛”的人群酷似“溺水的鱼”,跌跌撞撞,争先恐后,真可谓“花枝乱颤”,呈现着冷冰冰的闹哄哄:机关小人物尤奇满眼是“灯红酒绿”“高谈阔论”之类“俗流”;市委办公室科员袁真承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强奸”;保卫科长徐向阳求证了冠冕堂皇的下流;民间艺人南门秋、覃玉成面对折磨和荒诞弹奏善良、诉说纯粹……看来,这真是一个已然迷途、值得怜悯、亟需救赎的所在,需要培植,需要建树,甚至需要陶秉坤那样的开垦、耕作,而这一类关切和努力所面对、表达的已经是一种“将在”。
人们确实很容易形成这样的印象:少鸿的小说世界似乎没有什么十恶不赦,哪怕是吴清斋那样的地主,龙老大、二道疤那样的匪首。仅仅“停留在”这一意义层面将是滑稽可笑的,因为这种线形单一的好坏评判正是消解意义、否认冲突、模糊善恶、削弱对抗的真正手段。“冲突是为他的存在的原始意义。”[8]行走在大地的少鸿从来不会如此轻松随意地忘却使命、有意忽略世界的艰难“处境”与“恶心”现象,比如,社会学者一般所指的那个“游民无产者”或“流氓无产者”现象就一直是一个巨大的存在。“石蛙溪–莲城”处境中同样存在一个堪称庞大的“流氓无产者”群。举凡:伪道的木瓜寨族长、下作的地主吴清斋、褊狭的伯父陶立德、轻狂的堂兄陶秉乾、刻薄的烟鬼陶秉贵、偏执的支书陶玉财、滑头的议长蔡如廉、可恶的败类周布尔、混账的长工铜锁、鄙俗的社员岩巴、无聊的小人李世杰、贪婪的县办主任老梁、腐臭的秘书长吴大德……他们,居然如此声势浩大,如此甚嚣尘上,如此“正大光明”,如此十恶不赦!追踪“师门”,阿Q或那些帮会头子大抵应算是“师傅”,而这后起人众相比“前辈”更是“青出于蓝”、过犹不及。阿Q“师傅”也许顶多有些油滑,某种意义上还显出小小可爱,这却是一群穷凶极恶、十足流氓的无产者;阿Q“师傅”倒真因无产而“流氓”,“徒儿”们却是因流氓而无产——彻底的精神扭曲,灵魂肮脏,人格残疾,品质孱弱。因此,这里的“冲突”意义即在于,同枪毙几个“坏人”相比,救治这样的恶心才是更为棘手的事情。
三 缄默的本真能在
先知穆罕默德曾诙谐说,既然山不来就我,我便去就山罢。作品无处不在的意味便是这样的“山”。任何有成就的作品都只是一种所谓召唤结构、“都包含一个未完成的部分”,[6]63这就需要读者亲往“山中”,亲身领会和聆听那“缄默的本真能在”,以期(“部分”地)完成“未完成”。
话语及其形式是小说质料与意味的基本承载。极端主义更进一步认为,形式即内容,话语即意味或本质,譬如盐之于菜,盐的形态消解了,质料与意味却在菜中,能看见的只是菜这一形式。“唯有所领会者能聆听。”[5]192稍加“聆听”就会发现,少鸿创作是很在乎怎么说、很用心经营语言的,而其目的,自然还是为了指向某种蕴含、某种意味,并非全为一份光鲜。“(陶秉坤)放下柴刀,脱下上衣,绾起裤腿,又将长辫在头顶盘紧扎牢,然后往手心里啐一口,操起了锄头……锄尖深深地锲进土里……”一串动词很是精致、很见功夫,那锄头便挥舞了蓬勃着的年轻与燃烧着的热望。这是一类。“用乡下话说”又是一类,这类表达往往更见精神、更显本色。还有一类,就是通过具体语句或细节、段落来“散发”某种意味,借用海德格尔的说法,即通过“此在的展开状态”与“话语的分环勾连”(含义整体)而预示、期待一种聆听的可能。“(等人)等得腿杆上长出了菌子”,“有酒有肉,十几条喉咙响得快活”,“他(水上飙)发现岁月都充实到女儿身子里来了”,“陈梦园瞻望前程,但见群山重叠,绿水迂回,苍茫山水间一只雪白的江鸥孤独地滑翔,消失在空蒙的远方”,“(陶秉坤)能感觉蒸发的水气火焰一样在身下摇曳”,“龙老大说完,瘸着腿转身,钻到另一个山洞里去了”,“这一声叹息是陶秉坤妥协的先兆”,“天空阴沉沉的,似乎也蒙上了往事的色彩”,“之后,(于亚男、黄慈予)两人都不吱声了,她们用身体温暖着对方。窗外的风平息下来,在这个寂静寒冷的雪夜,她们感到被一种广阔无边的温馨所包容了”,“陶秉坤生命中的最后一天并无特别之处,秋风飒然,茅花飞白,阳光明净,牛铃悠扬,一派亘古相承的安详与宁谧”……孤立地看,这类表述也许并非什么惊人语,但置于具体语境、联系一生行止或整个此在,就发现它们都呈露一种“展开”着的“勾连”状态,“散发”一种撞击灵魂、摇撼心魄的“本真能在”。
语词及结构形态也承载着能在或者意味。语词所覆盖的意义阈和蕴含的能在,已经令小说家们着迷,以至于形成了一种“词典小说”现象。昆德拉就是用那些“不解之词”来表述人的存在状态与生命意义的。例如,弗兰茨说“萨比娜,您是个女人”,“女人”就是很“有趣”的一个词,因为它至少“代表着一种价值”——“并非所有的女人都称得上是女人。”少鸿也很讲究用词,讲究到常常使我们仿佛看到摆在他案头的那本厚厚的词典(尽管有的时候我们并不太愿意看他刻意地依赖那本词典)。“大地”之类具有母题意义的词汇自不必说,单是从泥土中“长”出来的那些词就尽够回味的了,像“挖他一眼”、“蚂蟥”一样叮在心里的念头等等,都是一种“未完成”,留下了一定的解读空间。“妄混”是个方言词,如果用在陶玉林身上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因为那就是他的“途程”、他的一生。无论如何也不能把陶玉林归入“流氓无产者”一类,他的歪理、荒唐、冲动、仗义等等生命轨迹只能用“妄混”来解释。“水上飙”这个名字本身已经传递了一种本然意义,而对陈秀英(于亚男)却始终没有给出一个恰当的语词。当然,这是个近乎故意的“未完成”。陈秀英是一位令人感佩、令人尊敬的女性:美丽、知性、执著、旷达,怀抱大爱一生未嫁,历尽坎坷担当道义,矢志革命无怨无悔。这样的女性已达圣洁,语词形式已无关紧要,也许在昆德拉“七十一个词”中可以找到一些切近的词:激情、背叛与忠诚。激情是生命燃烧,背叛是走向新生,而忠诚,则注定只是一种诗意的悲壮。从上述这类“聆听”中应该可以看出语词所具有的某些结构功能,还可以通过袁真的此在状态更明确地证实这种结构意义。袁真也是那种美丽、才华、纯粹、独立的女性,但给人总的印象是干净。干净一旦孤独地面对周围龌龊,生命便翻滚着无可回避的悲怆气息。“跳楼”风波的当晚,丈夫便一面发着牢骚,一面晃荡着“暄软的肚腩”和庸常的嘴脸“蛮横地”“冲撞”了她。受伤的袁真痛苦地呜咽:“我被你强奸了!”“强奸”这一语词立刻成为整部小说的基本连接点:从家内到家外,从生活到工作,从肉体到灵魂,无处不游荡着这种“强奸”感。
如果“能在”是指由此在而“展开”的丰富可能,那么,缄默与本真就成为这些可能的必要的属性。海德格尔一再强调,真正的缄默只能存在于真实的话语中,不是哑巴,也不是故意不说,更不是随意乱说。这也就揭示出,作品一经形成便是缄默,同时,这一缄默也在静候另外一种缄默——聆听。本真,就是那些“真实的话语”,是此在“本身的真正而丰富的展开状态”,正所谓真理是朴素坦荡的、无遮蔽的。无疑,少鸿本人与他的小说都是很本真地缄默着的,有时甚至到了“忘言”“无语”的地步,比如说,他从不直接评价自己的人物,也好像没有给小说章节安一个什么标题的兴趣、习惯,总是充分信任人们的聆听力,尽可能充分地腾出空间,增强挑战性。这样的特性显得很有魅力,也显得很有境界——正如米兰·昆德拉所期望的那样,小说家真正消失在了自己的作品之后。
[1]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M].靳希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7.
[2]陶少鸿.水中的母爱[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2.
[3]吴了然.与少鸿谈《抱月行》[J].江南·长篇小说月报,2008(5).
[4]愚 士.以笔为旗——世纪末文化批判[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8.
[5]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
[6]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孟 湄,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
[7]马丁·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要[M].郜元宝,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101.
[8]让·保尔·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宣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