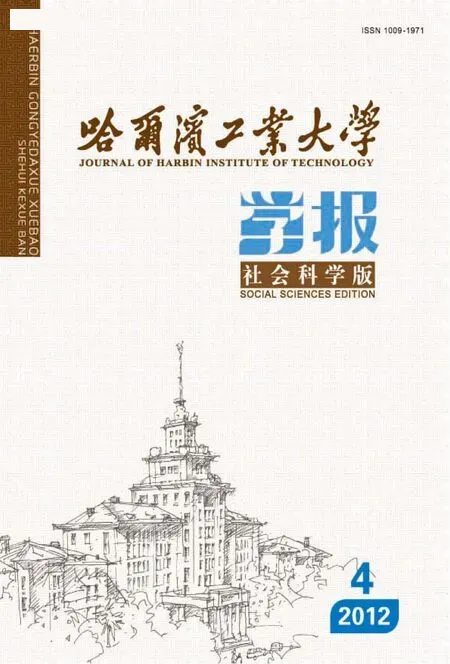生态伦理对生产技术方式选择的制约
2012-04-08佘正荣
佘正荣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广州510050)
·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伦理对生产技术方式选择的制约
佘正荣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广州510050)
在工业文明时代产生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主要是通过人与自然作用的生产技术方式、经济活动而形成的,最终也需要通过生产技术方式的选择来克服,但人们不应简单地认为,它可以在工业文明的框架内仅仅利用技术生态化的途经得以解决。新的生态文明以地球生态过程的健康持续为根本前提,倡导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非物质增长的经济观,由此势必要求人们在生态伦理的制约下来实现以此相适应的生产技术方式的选择。
生态文明;生态伦理;非物质增长的经济观;生产技术方式
在工业文明时代产生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主要是通过人与自然作用的生产技术方式、经济活动而形成的,这些经济活动由于没有对生态伦理的主动遵守和受环境法规的强制性制约,而人们只顾追求经济利益,必然使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积累为突破地球生态极限的严重危机。有一些站在维护工业文明立场上的学者主张,对技术进行符合生态规律的工业生态化的改造并引入环境法规,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工业文明的生态危机。笔者认为,采用工业生态化的办法和严格的环境法规,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与自然的生态冲突,然而在维持原有工业文明的基本格局之内,仅仅采取一些改良与修补的办法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完全消除生态危机的。因为工业文明具有自身不能解决的根本局限,即生产技术方式与经济组织中资本运行的根本机制是建立在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和剩余价值的基础之上,这个问题必须以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生态伦理来加以约束,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一、哲学家关于技术与环境的不同观点
在工业文明的生产技术方式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造成的影响中,通常存在着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立场。占主导地位的是大多数人所持的工具论立场,它认为技术是一种人的物质活动的中性手段,技术只是偶然地与它所要达到的目的有联系,并不对人类的各种价值追求具有本质性的关系,这是由于在技术的普遍规律中存在着由其因果关系决定的“工具理性”特征。比如,制造汽车的环保技术既可以用于资本主义的汽车生产企业,也可以用于社会主义的工厂,其他各种技术也如此,其衡量标准都可以运用到不同背景的社会中,都可以提高不同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达到技术设计的目标和效果。而技术秩序就是所有这些中性技术的工具作用的总和。所以,工业文明社会中的技术精英们,大都主张以符合生态学原理的工业技术来解决人与自然的对抗和冲突。
与工业文明中占主流思潮的这种工具主义技术观相反,海德格尔则持一种将技术视为单一整体的实体论的观点。海德格尔认为,将技术看做一种价值中立性的工具和达到人类目的之手段,是一种常识性的肤浅看法,而不是技术的本质。他从词源学上对技术一词进行了仔细的考察,认为技术一词的原初含义是揭去遮蔽,所以技术的决定性的东西不在于操作和使用,而是一种让存在者显示出来的展现。在他看来,支配近代技术的展现是一种挑战,它对自然施以过分的要求,实际上就是强迫自然物以非自然状态展现出来,强迫自然提供作为能够提取和储存的能量之类的东西。因此,这种展现方式与古代那种顺应自然的手工技艺的展现方式截然不同。他将这种强迫自然的挑战性要求称为“座架(德文Gestell)”。座架即为一种设定的结构,人类坐落于这一结构之中,就必然要通过技术去挑战自然,将人类展现为限定、强求自然的技术员。自然界坐落于这一结构之中,就是要通过技术将自己以持存物的存在方式呈现出来。海德格尔认为,正是这种作为施之于人的挑战性要求的座架充分表明了现代技术的本质[1]。显然,他所指的技术实质上就是技术世界中人类对自然的强制性关系。由于海德格尔将现代技术看成是存在天命的展现,所以他认为人类要改变和控制技术的想法是错误的,人类对技术只能采取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
美国的技术哲学家安德鲁·芬伯格认为,关于技术的工具论和实体论的解释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工具论的看法强调技术的使用不是由技术本身自主的决定的,它反对技术的宿命论态度。技术的实体论则认识到,人们在选择技术时,技术是可以从价值观上进行评价的选择,技术已经不是一种简单的工具,而是变成了一种实质上影响到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具有支配权力的东西。人们在选择技术时,人变成了技术之所是,这又影响到对未来的选择。技术秩序实际上构造了世界,人的技术选择实际上已经被技术所渗透,因此技术不能按照工具论的观点来理解。芬伯格认为,尽管技术工具论和技术实体论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它们对技术都采取了一种“或者接受或者放弃”的简单化态度,而没有探讨作为一种处于复杂的“两重性”过程中的技术的可选择性。芬柏格立足于马尔库塞对自由社会的新技术的解释,吸收技术的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建立了一个“技术批判理论”。他主张,在现代性或工业文明的框架下,通过基于公众参与技术决策、工人控制的激进民主道路,现代技术是可以被选择的,可以被设计来适应更自由的社会[2]3-20。
芬伯格认为,任何得到发展的现代技术都是技术要素本身的内在逻辑和社会情境的结合。像弹性、电路、杠杆这些特殊的“技术要素”,它们的联系有着自身的因果规律,在不考虑统治阶级和其他的社会群体的目的时,这些技术要素的关联本身的内在逻辑是相对中性的。但是技术在实现的过程之前,必须将这些看似中性的技术要素的配置结合到受到限制的特殊的社会目的中,因此可以从技术中发现技术要素配置的网络与社会关系的网络的双重性:技术的认知功能和霸权功能,二者不是作为单独的部分,而是作为整体的互补方面。由于这个原因,技术要素联系的内在逻辑或者技术的规律,能够为它们所服务的霸权提供其所要求的应用。芬伯格将社会需求和技术需求结合到技术合理性中的统治体系称为技术代码。“资本主义的社会需求和技术需求被聚合在一种‘技术合理性’或‘真理的政权’中,而这种‘技术合理性’或‘真理的政权’使技术体系的构造和解释适应了统治体系的需要。我称这种现象为技术的社会代码,或者更简单称为资本主义技术代码(technical code)。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霸权是这种代码的一个结果。”[2]94显然,为了实现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目的,技术代码需要将霸权与技术的应用结合起来。“资本主义的独特性在于它的霸权很大程度上建立在通过技术抉择来再生出自己的操作自主性的基础上。这一点通常能够实现,因为现代社会中的权力可以通过技术控制而得以掌握,无需贵族头衔或宗教的认可。”[2]92而资本家对操作自主性的掌控,是通过在技术应用的战略决策和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管理,牢固保障资本最大限度地增加剩余价值,彻底排除工人参与决策和工人所追求生产安全、审美、物质、社会福利要求,以及整个社会的其他目标。在芬伯格看来,每种技术选择都是多种社会利益、社会价值的争论和博弈,而对操作自主性的掌控至关重要,资本家的操作自主性是一种战略位置的占有,它提供了将工人和消费者置于从属的位置,使他们的利益和价值目标在技术的应用中得不到实现。而通过激进的社会改革,实现生产过程中工人的民主,让工人自主决策和管理与社会多种合理价值的整合,就可以把在资本主义社会被排除的上述多种价值目标纳入到生产技术中,实现其在工程技术中的内在化,并且不会造成生产的无效率后果。
对于资本主义的技术在经济活动中造成当代人类与自然的剧烈的生态冲突而言,许多环境保护论者认为,只有退回到前现代的技术状况才能得到解决。芬伯格认为,这种对自然回归的浪漫逃避,是一种海德格尔似的消极的怀乡病,这种办法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在他看来,解决的办法只能通过对技术的总体性批判,在一种工人民主参与决策和管理的技术应用过程中,把满足健康、安全、清洁的空气和水、审美等环境保护的软价值,组合到具体技术的结构中,即将保护自然的目标包括进具体技术的自身结构中,才能促进技术力量、自然力量和人类发展要求协同作用的总体性技术的发展,才能真正有效地保护环境。
应该说,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是迄今为止技术哲学中较为深刻与合理的一种理论,他批评技术的工具论和实体论的简单化看法,认为技术是一个包含着技术规律和社会利益的复杂整体,是可选择的。尤其是他关于技术的设计和选择是一种双面现象,技术的社会价值目标可以通过掌控技术决策和应用中的操作自主性来实现,因而通过社会的民主改革,让工人参与对技术发明和应用的决策管理,把环境友好的价值目标内在化为工程技术的自身结构,以实现环境保护,为从工业文明过渡到生态文明的生产技术方式,提供了较好的方法和途径。现在的经济发展中的技术决策和管理确实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观,从而可以缓解人类与自然的生态冲突。比如,现今各国政府对经济发展中关于环保技术的各种提法,如清洁技术、低碳技术、封闭循环技术、环境友好型技术等,这些可以包含在“工业生态化”范畴下的技术方式,就表达了经济发展中对技术的生态要求和对环境破坏的限制。所谓工业生态化,通常是指工业生产的经济活动与生产技术,要求按照生态学的原理,将其各个环节形成类似于自然生态链的关系,以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最大程度地减少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当然,如果能够通过广泛、深入的社会改革,让工人充分参与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发明和应用,把环境保护的社会目标内在化到工业技术体系中,较好地进行清洁生产,使污染物质在生产过程中实现封闭循环,而不是进行事后的环境污染治理,这种工业生态化的办法,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与自然的生态冲突,使资源使用的时间比在原来的技术状况下更长一些,环境污染的可承受力更大一些,全球气候变暖的速率更慢一些,地球生命维持系统的衰退更久一些。然而,即使我们假定芬伯格的这种技术选择构想能够在现实中完全得到实现,最多也只能是在工业文明格局下争取到相对于其他技术选择战略更好的结果,而无法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工业文明与地球生物圈的冲突,不能有效地保护地球的环境。因而人类必须按照生态文明的伦理要求来选择和制约技术,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与自然的生态冲突。
二、物质增长的经济与生态保护的内在冲突
工业文明给予经济发展的技术选择的致命要害是,它是一种物质增长的经济,这种经济本质上就是与地球的生态安全相冲突的,只要不改变这种物质增长的经济的根本性质,地球生态系统的崩溃就是迟早的事情。这里的道理并不是特别复杂,而是因为工业主义的经济增长论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愿承认以下基本事实: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地球养育人口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地球调节人类生产、生活产生的污染的能力是有限的。而主张物质经济可以无限增长的经济学家,一般都以坚信技术进步是无限的来反对经济增长的各种物质极限。然而,事实上技术上的最好解决结果只是提高能源、物质材料的利用效率,减少物耗、能耗,但不能把有限的东西变成无限的东西。有的经济学家甚至主张技术的高度发展可以使人造资本替代自然资本,这正是著名的稳态经济学的提出者赫尔曼·戴利所批评的“可替代性教条”。可替代性观点认为,人类积累足够多的人造资本,就足以弥补自然资源的损耗,这就好比说,修建的工厂越多,制造的机器越多,经济增长越快,人们就越是不必担心资源的短缺。实际上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的。因为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是互补物而不是替代物,要进行生产二者必须同时使用,而不能完全相互替代。劳动力和机器是将资源(石油、木材等)转变为最终产品家俱的生产投入,但它们并不能替代作为自然资本的资源。没有森林,家俱厂是不能生产家俱的。没有鱼,渔船也不可能打到鱼。而工业文明以来200多年的经济增长,已经使人类从一个自然资本充足而人造资本相对短缺的时代,进入到了一个人造资本相对充足,而自然资本越来越短缺的时代,显然,自然资本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限制性要素了[3]。但是,主张经济可以继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学家们不愿承认这种严酷的现实,而宁愿相信技术的进步可以使人造资本完全替代自然资本。显然,这些人是在自己幻想的技术伊甸园中生活,完全忽视了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的区别。
在工业文明的框架内物质增长经济不仅不可能实现长期的持续,而且还会由于其组织经济的方式加速到达自然的生态极限。这是因为工业文明的大机器生产,是靠市场经济来组织的,市场经济的逻辑就是资本和利润增长的逻辑。为了获取最大的利润和资本最快的增长,掠夺最多的资源和消费最多的商品就成为资本增长的两个根本支点,也即物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因此,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就是这种增长经济的必然结果。资本家和企业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或利润,只会考虑如何用完更多的自然资源,把人变成消费的机器,而不会考虑人类健康、文明的生活对许多自然物的使用价值的需要,如清洁的空气和水、动植物的审美价值、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服务功能,等等,完全不会主动考虑那些有关人的健康、环境保护、污染防止等“公益性支出”。这是因为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这样做会增加成本、减少利润,会妨碍他们达到最大限度地增加利润的目的。从世界的范围来看,在工业文明的社会中,每一个国家,为了提高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也会努力促进经济增长,而不会把维护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放在物质经济增长的目标之上,用以约束对自然资源的耗竭行为、对生命维持系统安全的破坏行为。即使世界各国在全球生态危机的严峻情势下不得不采取了一些环保政策和环保法规,但各国的政治精英追求物质增长的努力没有丝毫减弱。因此,我们也就能够对一些极为矛盾的现象见怪不怪了:人们一方面主张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大力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另一方面又在加快耗能耗财的能源、原材料、石油化工、采矿、冶炼、重型机械制造和建筑业等产业的发展;人们一方面主张节约水、电、油气、纸片、金属碎屑等各种资源,节约每一个产品的使用次数,另一方面又在大力刺激消费,想尽办法引诱人们购买各种各样的工业产品;人们一方面为了保护环境,主张步行、骑自行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班,另一方面为了经济增长又生产出城市公路都容纳不了的个人用小汽车;人们一方面主张企业采用清洁技术、环保技术、低碳技术来进行生产,另一方面,人又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总量来扩大随时尚提高的人均物质消费水平……结果也是如此,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环境保护技术日益提高、生产的物耗能耗平均水平也日益降低,而物质耗费的总量却高速增加,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也越来越严重。世界各国为环境保护在技术方面作出的改善,与物质增长的经济在规模和总量上的破坏力量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无法从根本上缓解它加速恶化地球生态环境的趋势。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工业文明条件下物质增长经济造成的经济发展的目的性异化,经济的发展不是为了人类在地球上安全健康的生存,不是为了人的有意义的生存,而是为了经济增长本身带来的资本和利润的增加。
当然,也有些人会想到用价格机制来实现工业生态化,从而实现物质经济的长期增长。他们认为,人类保护环境主要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通过自由市场建立起全面的价格机制,就能使企业外在化的成本内部化,使价格完全反映生产成本和环境成本,并且由法律来保障污染者支付环境治理的费用,就能既促进物质经济的增长,又能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但是,这样的方案是根本行不通的。因为市场的根本动力建立在自私自利的基础之上,人们只会考虑自己的当前利益,不会考虑后代和未来的长远利益。众所周知,市场的价格机制更加重视现在而不是将来的价值,人们必须为现在的市场生产才能赚钱。反之,要考虑人的健康生存和人类整体未来的长远利益,就必须维护地球生物圈正常的生态过程,就必须保障生命维持系统的安全、健康和长期的可持续性,因此,就不能不停止追求物质经济的增长。
三、生态文明只能以非物质增长的经济为主导
根据联合国2001—2005年的重大国际合作项目《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报告,发现过去50年来,人类为了满足自己快速增长的物质需要,对各种生态系统和全球生态系统已经造成了巨大的改变,虽然这些改变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福祉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造成了各种生态系统的严重退化,生物多样性的巨大损失,而且大部分是不可逆的。在生态系统各种功能退化的严峻挑战下,人类如果不能进行政策、体制、技术和价值观上的重大改变,并且作出巨大的努力与合作,未来的生态将继续恶化下去[4]。另外,从生态足迹来看,全人类已经耗费了1.25个地球,即人类早就于20世纪70年代起就已经开始超过了地球的生态极限,而此后由经济全球化引导的全球物质经济的增长,正是现今整个地球生态恶化加速的原因。从中国来说,中国的生态足迹已经达到需要两个中国,才能养活所有人的困难局面。现在世界争夺资源的竞争越来越严重,继续追求物质经济长期的高增长已经没有现实可能性。因此,无论是全世界还是中国,如果要真正追求人类的健康生存和地球生物圈的生态安全的真正可持续性,物质经济的收缩就是不可避免的,否则,继续追求较高的物质经济的增长,地球上所有生命所遭遇的生态灾难就会迅速到来并日益加重。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整个世界经济必须收缩,西方发达国家要带头适应这种收缩,而发展中国家也只能有追求满足基本的健康的物质需求的较短的增长时间。从中国来看,现在中国已经达到人均GDP 3 000到4 000美元,即使再翻一番,达到人均GDP 6 000到8 000美元,也不可能超过欧美,更不能让所有的人都过上欧美社会中那种高消费的物质生活。由于物质经济的高增长只能靠市场经济的方式来实现,而市场经济必然使资本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因此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就必然存在。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状况已经出现了较大的就业困难,个人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两极分化现象严重,社会保障也处于较低水平,而贪污和腐败现象在社会中非常普遍,整个社会也存在着非常明显的金钱拜物教和物质享乐主义风气,人们对西方奢侈的物质生活方式非常向往,青少年普遍缺乏崇高的理想价值追求,而这些都是影响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单靠物质经济增长不仅不能解决,反且会更加严重。
生态文明要保障人类在物质生存上的健康和安全,就必须把经济的组织置于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根本生态价值目标之下,为此,经济的组织和生产技术的选择就必须接受生态伦理的制约,必须要保障地球生命维持系统的安全,即地球生物圈生态过程的可持续性,因而这种经济只能是一种非物质增长的经济。只有这种非物质增长的经济,才是以人类与自然和睦生存为基本前提的经济,才是一种真正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所谓非物质增长的经济,是指以材料、能源耗费为主要产品的物质构成部分的经济,是受一国的生态容量和整个地球的多重生态极限所制约的,因而不能再有所增长,而且必须保持在动态平衡的水平,即赫尔曼·戴利所说的“稳态经济”。戴利认为:“稳态经济具有四个特征:一是持衡的人口数量;二是持衡的人造资本(体外资本或人体的延伸)数量;三是上述两个数量的持衡水平要足以使人们过上较好的生活并可延续到未来;四是维系人口和资本数量所需的物质—能量流通率要降到最低的可能水平。”[5]363-364同时,戴利还考虑了建立稳态经济的客观共同价值与道德基础,这就是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以及考虑到当代人和后代人长远的可持续的最大利益的功利主义[5]396-404。对于戴利所说的稳态经济,笔者认为,戴利的这些看法具有许多深刻的合理性成分的。这些都是我们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肯定并加以合理吸收的。
不过,戴利的稳态经济是指整个经济的不增长,而不光是以物质产品为主体内容的经济不增长。这一点,笔者是不同意的。笔者认为,由于地球生态系统多重极限的突破和全球环境的急剧恶化,以物质内容为产品的经济,必须停止增长,而且,为了恢复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生态过程的正常,甚至在一个时期内还需要实现负增长,在整个地球的生态过程恢复到安全之后,才能追求稳态经济所要求的零增长。不过,以非物质内容为产品的产业经济,如信息产业、文化产业、教育产业、预防医学和养生保健产业,各种劳动型服务等产业,是可以增长的。当然,这些产品并非是不需要一丝一毫的物质载体,而是说这些物质载体所占的比例极其微小,它对环境产生的压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例如,有些产品,在已有的物质设备下即可进行生产,而不需要另外的物质条件,如各种软件,电子图书的制作,无纸化的办公自动化。各种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娱乐性活动的培训和教育,包括传统的琴棋书画,以及现代的曲艺、表演等;以及社交沟通的辅导等,也可借用已有的影院及会议场所。像推拿按摩、健身气功、太极拳、五禽戏、易筋经这些既具传统文化奥秘,又需要专业师父指导的健身性体育活动,不仅极为有利于人们的健康,也具有普遍推广的经济价值,对维持身体健康,使生命充满活力,又能防止高危重病的产生,减少难以忍受的病痛,还能省去大多数人模仿西方生活方式而必须付出昂贵的医疗费用。
人类之所以有物质性需要和非物质性需要,是因为人是身心合一的特殊生物物种。作为具有自然性的生物,人的健康安全的基本物质需要是必须满足的,但最终也是有限的。现代消费社会以物欲主义的价值观为引导,把人从小就培养和装备成了只知消费大量物质和能量的极其不自然的动物。可怜的只知物质消费的现代人,即使是那些财富过亿的有钱人,有多少人的生活是幸福的?钱能买来物质财富和物质生活的富足,但能买来健康、长寿、安宁、美德、善终吗?显然,仅仅靠物质生活,并不能使人幸福,因为在人的两种生活中,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更为重要,精神生活是无限的,而物质生活是有限的。而非物质经济的增长,能满足人们的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多方面需要,降低消费社会人们病态的攀比的物质生活,调节人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平衡,减少物质资源的浪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从而有助于抑制物质经济的增长,恢复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健康和美丽。非物质经济的增长和长期发展,还能不断促进人的创造天赋、道德良知、团结互助、社会公平、仁慈友爱这些生态文明建设中极其缺乏的社会资本、道德资源、精神价值的全面发展。显然,生态文明只能以非物质增长的经济观为主导。
关于概念问题,学术界现在已经有“非物质经济”的提法,笔者认为这一概念是不尽合理的。它给人的印象是,生态文明需要的经济好像只是单一的非物质成分的经济,但是,事实上生态文明完全不能离开物质的经济,而只是说工业文明以来的以物质财富的高度增长的经济是不可能持续的,必须尽快停止其增长;另外,需要加以强调的是,非物质部分的经济是可以增长,并且是未来生态文明中的主导性的经济形式,它可以引导和调节物质经济形式的发展。这两种含义在“非物质增长的经济”这一概念中都可以完全含摄,而不会产生任何歧义。所以,应以非物质增长的经济这一概念来取代非物质经济的概念。
四、生态伦理对生产技术方式选择的要求
要达到人类安全、健康、持久生存的目的,就必须把握地球生态系统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所提供的各种基本服务功能,按照其支持人类发展的多种目的来合理利用这些服务,防止为了单一的物质经济增长目的而破坏地球生态系统提供的其他服务,甚至危害地球生命维持系统支撑所有生命存在的支持服务和调节服务等重要功能。人类需要以建设生态文明必须的生态伦理为依据,把在工业文明中被物质增长经济所排除的全面维护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的目的,纳入到经济组织与技术选择之中。这些目的有许多自然的和社会公益性的性质,都是很少赢利或者根本就不赢利的,有些甚至是要付出一定的经济成本和社会代价才能实现有效的保护,有些虽然提供经济服务,但是过度使用会导致其提供能力衰退,有些提供人类的社会文化服务,虽然也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然而经济价值并不是主要的,它们是人的健康生存和有意义的生存所必须的。下面,我们分为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以实现生产技术方式的选择中如何分别保护这些重要的服务功能。
在地球生物圈提供维系所有生命生存的支持和调节服务功能方面,需要保护维持必须的生物多样性,以使得生命正常生存必需的氧气的生产、土壤形成与保持、养分循环、水分循环和提供栖息地等生态功能得到安全的保障,维持地球生态系统调节气候、水分、空气质量,控制土地侵蚀、风暴侵袭,调控人类与生物疾病,净化水质和处理废弃物等的能力的持久存在。为此需要严格保存和恢复那些所有生命存在都必需的自然生态系统,如原始森林、湿地、江河湖泊等淡水水体,草原、海滨红树林、珊瑚礁区域等重要生态系统,或者需要确立为不得人类进入的自然保护区来加以严格保护,或者只允许不会导致这些重要生态地区退化的少数原住民人口存在。只有成功地长期保障了地球生命维持系统的支持功能和调节功能,人类的生态文明才有可能存在和持续下去,所以,任何国家的任何团体和个人,都必须承担起这个维护生态系统和基本生态过程,从而保障地球生命家园长期安全和健康的根本的生态责任。这是生态伦理对人类生产技术方式选择的强制性要求,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起码的生态责任。
在地球生物圈提供给人类的供给服务功能方面,人类需要合理地节约使用不可再生性资源,需要合理地保护性地使用可再生性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以此来实现开发利用资源的经济利益,满足自己的物质生存的健康需要。生态系统提供给人类可以获取的各种自然产品,如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大量食物产品,提供各种木材、棉麻、丝绸原料产品,提供木材、牲畜粪便等燃料,提供动植物繁育和生物工艺的基因和遗传信息,提供生化药剂、天然药物和医药用品,许多医药、生物杀灭剂、食物添加剂(例如藻酸盐)和生物原料都是来自生态系统,而地球表层提供生产粮食的土壤,江河湖泊提供人们饮用的淡水,地表下埋藏着丰富的金属与非金属矿藏,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地球还提供风能、海洋潮汐、地热、水力梯度,人类只要合理地利用技术,更多地利用可再生性能源和可再生的生物资源,尽量少用稀缺的矿物资源,把人口数量和人均物质消费水平减少到地球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的范围之内,减少不健康的奢侈性的病态物质需求,对生态系统和地球表层提供的各种资源进行保护性地加工和利用,就足以满足人类长期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这是生态伦理对人类技术方式选择的导向性要求,也是各个国家的经济、技术发展与环境实现协调友好应该承担的一种生态义务。
在地球生物圈提供给人类的文化服务功能方面,人类应该充分利用地球自然提供的这些极其美好的事物来充实自己有意义的生存,并主动开发人类自身的各种精神能力、社会的创造力,以协调有限的物质需求和无限的精神追求的关系,使人类的崇高生存境界得以逐渐拓展开来,弘扬下去。生物圈提供给人类的文化服务,是一种非物质的益惠,它包括人类对它的科学研究的价值,提供教育的价值、审美的价值、自然遗产价值、消遣和旅游的价值,提供汇聚文化的多样性根源的价值,提供宗教信仰和文化象征的价值,塑造和培养人的性格的价值,巩固乡土情谊的社会关系价值……这些丰富的文化服务和精神价值,能够帮助人们从沉溺于无止境的物质消费的中毒状态中觉醒过来,重新寻找到人的生活的真正意义,并且培养和开拓出使人性不断升华,人的天赋和创造才能得以全面展开的丰富需要。同时,这些丰富的文化需要可以通过经济活动与技术的创新,生产出日益增多的精神文化产品,作为精神食粮,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们以精神生活引导物质生活,物质生活有益于生态健康,达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相和睦的新文明状态。这也是生态伦理对生产技术方式发展的一种理想要求。
当然,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转型,并非是一种突然产生的暴力性的革命过程,而是现今人们就应该自觉探索和努力实践,并争取不发生重大社会冲突和破坏的一种过渡过程。这个过程包含了经济组织活动的战略性转变和与之适应的生产技术方式的选择。从世界范围来看,人类在地球上的各种活动造成的后果,已经超过了地球的供养能力和生态极限,经济强大和物质富裕的发达国家已经不需要再追求物质经济的增长,只能追求非物质经济的增长,同时应该把维护和修复生态系统的任务放在首位,并且不要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而是应该以补偿生态债务的态度,以足够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援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而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还需要在一定时期内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采取节约资源,降低能耗、物耗,采取有利于环境的技术来达到经济发展的目标,在这个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还要特别严格地控制人口增长,以避免经济增长带来的物质财富被人口增长的分母效应完全抵消。而已经解决了温饱生活、达到了小康物质生活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则不应该以欧美国家的物质富裕为榜样,继续追求较高的经济增长,而是应该追求生态安全、社会公正、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为此必须继续严格地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耕地、森林、水体、治理荒漠化等,维护长期生存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的安全。而且在物质经济的发展方面,应该开始努力选择有利于环境的清洁技术、低碳技术,形成生态化的技术体系和产业结构,降低矿产、冶炼、钢铁、化工、建材、造纸等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比重,彻底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传统工业化模式。同时,在经济发展中还应该自觉地控制以高消费拉动的物质经济的高增长。因为以高消费来促进物质经济的高速增长,从生态文明的建设来看,是极为短视的、不明智的,它会浪费很多的宝贵资源,污染环境,危害生态系统,造成经济发展的生态基础的不可持续性,从而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因而是得不偿失的,而且对后代来说也是严重地违反环境正义的,对非人类生命来说也是违背生态正义的。而明智的做法是追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控制好人口增长、人均资源消费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时,利用各种高新技术提供的机遇,大力发展那些有利于人们各种高尚的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的非物质的经济部门,推动经济发展的非物质化,保障经济的健康发展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
[1][德]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M].宋祖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57-72.
[2][美]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M].韩连庆,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美]戴利.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M].诸大建,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109-113.
[4]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Mille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Ecosystems and Human Well-being:Synthesis[R].Washington,DC:Island Press,2005:1-18.
[5][美]戴利.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M].马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Restriction of M ode of Production Technology of Eco-ethics
SHE Zheng-ro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eaching and Research,Party School of CPC Guangdong Provincial Committee,Guangzhou 510050,China)
The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 ultimately needs to be overcome by choosing anothermode of production technology,but people should not simply believe thatmaking technology ecological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will be 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New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akes the health of the earth's ecological processes as a fundamental precondition,and it holds a non-material view of economic growth that promotes a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which is bound to require people to choosemode of production technology under the restrictions of eco-ethic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eco-ethics;non-material view of economic growth;mode of production technology
B82-058
A
1009-1971(2012)04-0121-07
[责任编辑:王 春]
2012-04-10
佘正荣(1956—),男,贵州凤岗人,教授,从事生态伦理学和科学技术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