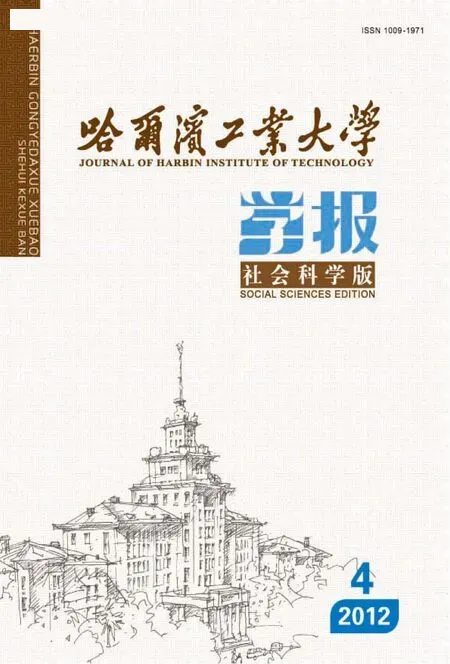汉代骊靬故县是否为骊靬降人而置
2012-04-08宋国荣徐蓉蓉
宋国荣,徐蓉蓉
(甘肃永昌县文化馆,甘肃永昌737200)
·文学与文化研究·
汉代骊靬故县是否为骊靬降人而置
宋国荣,徐蓉蓉
(甘肃永昌县文化馆,甘肃永昌737200)
骊靬县是西汉时期设在今甘肃省永昌县境内的一个故县,这在中国史书当中多有记载。长期以来中外媒体就此多有报道论述。以汉唐至清代诸多经学家的考证为基础,对不断提出的就此问题的看法与推断进行梳理,全面展现当代学术界对此县为何而置所引发的争议与讨论,并以金关汉简所反映出的信息进行推理分析,骊靬县为自西域内迁的骊靬降人而设这一观点更为可信。对历史材料与对已有成果的梳理串连,对研究中西方文化交流、民族迁徙融合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骊靬故县;骊靬降人;汉代;罗马
骊靬,是西汉时期设在今甘肃河西走廊中部永昌县境内的一个故县。有关骊靬县的设置,历史典籍和地方史志多有记载和注解。其遗址在今永昌县城西南10公里处,又名者来寨。2000年改设为骊靬行政村。其地处祁连山下,海拔约2000米,辖面积约30平方公里,大部属前草地和山坡林地。现有居民80余户,300余人。该地多数居民有着明显不同于周边地区住民乃至东方人种的一些特殊的体貌特征,而关于这个人群的来历则也渐渐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并且在数十年以来关于其成因的探讨可以说绵绵不绝。本文对骊靬故县与骊靬降人这一文化迷团进行探讨。
一、历代学者对骊靬的解读与认知
东汉经学家应邵《汉书集解音义》注:“骊靬,大秦也,张掖骊靬县为西域蛮族而置。”唐初学者颜师古《汉书·张骞传》注解中说:“骊靬即大秦国也,张掖骊靬县盖取此国为名耳。”《晋书·张祚传》载凉王张祚“永和十年,遣其将和昊率众伐骊靬戎于南山,大败而还。”《后汉书补注》、《二十五史补编·新斛地理志集释》、《大秦一统志》、《甘肃通志》、《乾隆府厅州县志》、《凉州府志备考》、《永昌县志》记载略同:“盖骊靬国人降,置此县以处之也。”“今凉州府永昌县南,本以骊靬降人置县,者来寨是其遗址。”1936年中国出版的《辞海》,198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马部骊靬条均说:“古县名。西汉置,西域骊靬人内迁居此,故名。北魏以后作力乾,隋废。在今甘肃永昌县南。”前凉张祚遣将伐骊靬戎于南山,大败而还,即此。《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今其土俗人呼骊靬,疾言之曰力虔。按《隋志》开皇中并力乾县入番和,当即此县。”
清代学者惠栋,在其著《后汉书》补注中说:“骊靬县,本以骊靬降人置。”王先谦在《汉书补》、《后汉书集解》中说:“骊靬县,盖以其骊靬降人置。”治经史并精于西北地理之学的张穆(即石州)说:“骊靬本西域国,汉以其降人置县,有定音,无定字,故《张骞传》作嫠靬,《西域传》作犁靬,与此作丽,皆同音也。”钱坫、徐松、王筠等清代经史学家,考证认为“骊靬县,本以骊靬降人置”是具有可信度的。
1920年,史学家向达在《中外交通小史》提道:“汉代中国人称罗马帝国为大秦,又称之为犁靬,其实都是罗马帝国的别名。”“汉书地理志,张掖郡有骊靬县,此外有陇西郡的大夏县和上郡的龟兹县,都是为处置归义降胡而设,而汉时罗马帝国与中国交通之盛,于此也可概见。”[1]1944年,中外交通史研究专家冯承钧认为:“公元前36年,汉西域副校尉陈汤,发西域诸国兵四万余人攻康居,擒杀郅支单于。罗马士兵参加了此次战役,支持郅支单于,这是罗马人首次和汉兵发生接触。”[2]林干编《匈奴史论文集》所录著名历史学家齐思和的《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中提到公元前36年陈汤伐郅支时说:据现代学者考证,罗马士兵参加了此次战役,支持郅支单于,首次和汉兵发生接触。北匈奴郅支单于既死,臣服于汉的呼韩邪单于遂统一匈奴[3]。有关研究骊靬的历史学家和著述还有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维华[4]、西北师大历史系教授王宗维[5]、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孙毓棠[6]、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常征[7]、法国学者L.布尔努瓦的《丝绸之路》[8]、美国历史学家罗兹的《亚洲史·中国文明·中国和罗马帝国》等。他们都论证到骊靬县的设置与骊靬人来华有关,尤其是张维华提出“骊靬为祁连译音”之说,然后又接着说:“兹采众说,重加考核,大抵仍以服虔、师古之说,似为近于事实,虽其间亦有若干不可解决之问题,然终较他说为长。”[4]
从上述学者对骊靬的解注中可以看出:骊靬县的设置是为安置从西域归降的一批特殊人群——骊靬人而设,古来就有记载,是有历史传承性的,并不是今人的所谓新的发现。
二、20世纪以来有关骊靬的学术争议
20世纪中叶,美国汉学家德效谦曾发表一篇著名的论文《古代中国之骊靬城》,当时因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在1989年,时在甘肃省兰州大学任教的澳大利亚学者戴维·哈里斯,通过法新社在新华社《参考消息》发表了《中国西部有古罗马城市》一文,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了内容更详细的报道。一石击起千层浪,国内外许多媒体和学者纷纷就此发表不同意见和观点。而且,这里并没有发表哈里斯等人在学术上的任何成果性的东西,为此,这种说法实际上被学术界持根本的否定态度。
这件事情的缘由是西北民族学院副教授关意权、兰州大学苏联史学者陈正义、苏联专家弗·维·瓦谢尼金和在兰州大学任教的澳大利亚教师戴维·哈里斯等,通过合作研究认为:公元前53年,古罗马军事首领克拉苏率领7个军团、4万多人的军队进攻安息(今伊朗东北),第二年在卡尔莱(今叙利亚的帕提亚)与波斯人的一次大战中失败,克拉苏被杀,只有部分军团士兵突围逃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卡尔莱战役。这些逃出突围的罗马人后来流落到西域的乌孙、康居等国做雇佣军。十余年后的公元前36年,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联合康居、乌孙等西域15国兵讨伐匈奴郅支单于,战于郅支城,发现了这样一支奇特的部队,“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讲习用兵”。且“土城外有重木城”。他们认为,这里的“鱼鳞阵”和“重木城”只有罗马军队采用。而这些使用“鱼鳞阵”和“重木城”的士兵就是克拉苏兵败后逃亡西域一带,后来依附匈奴郅支做雇佣兵的一批罗马士兵。这次战争汉朝军队获胜,西汉政府便设了骊靬县来安置这批罗马战俘。
20世纪80年代至今,永昌骊靬古县引起国内外有关人士的关注。中国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专栏于2001年7月15日,在永昌骊靬村作了现场直播报道。中国的香港电视台、广东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浙江电视台、甘肃电视台,还有西班牙、美国、加拿大、韩国、新加坡等国外的电视台都来永昌拍制过有关骊靬的专题片。此外,美国的《时代周刊》、英国的《泰晤士报》、日本的《朝日新闻》、德国的《镜报》、波兰的《共和国报》、法国的《欧洲时报》等中外百余家报刊对永昌骊靬故县和骊靬降人的历史文化脉络均进行了有关报道。
骊靬古城为骊靬战俘而设,或者说也就是与甘延寿、陈汤俘获的战俘有关联这一说法,同样也受到了学术界的质疑。如援引《汉书·陈汤传》中的记载,汉军伐郅支匈奴所俘获的千余战俘都“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而根本未被汉军带入玉门关,跟骊靬城的设置似乎没有关系;哈里斯等人也没有发表过相关的后续学术研究报告。为此,一些学者根据新闻报道中的一些相关内容,提出一些疑问和商榷的观点。其主要有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对此说有感而写的散文《天涯何处骊靬城:读书献疑》[9]、北京大学教授杨共乐的《中国境内哪有罗马城:西汉骊靬城与罗马战俘无关》[10]、甘肃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德芳的《汉简确证:汉代骊靬城与罗马战俘无关》[11]等等,显现出一部分学者通过研究史料得出的对骊靬城与骊靬战俘的关系的各自看法,并以自已的观点对前文支持性说法提出疑问甚至于否定意见。
三、对居延金关汉简所记载骊靬苑、骊靬县的不同解读——兼与张德芳先生商榷
汉代著名的居延海在张掖以北,当时是重要的边防关塞。现在这里留有不少汉代烽燧遗址。1972—197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队在这里挖掘出两万多枚汉简。简册内容广泛,涉及汉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其中以屯戍内容为多,且保存了一部分汉代官方文献。这批简又被称为居延金关汉简。《光明日报》2000年5月19日第四版张德芳先生发表文章[11]公布了这批汉简中涉及骊靬内容的13枚,这是至今见证骊靬的文物之一,而且张德芳先生的文章见解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不过,到底如何解读,似存在还需要商榷之处。在具体探讨之前,兹将这13枚汉简,先行抄录如下:
简一:“□和宜便里,年卅三岁,姓吴氏,故骊靬苑斗食啬夫,乃神爵二年三月庚寅,以功次迁为□。”
简二:“□公乘,番和宜便里,年卅三岁,姓吴氏,故骊靬苑斗食啬夫,乃神爵二年三月辛□。”
简三:“闰月丙申,骊靬长东亡,移书报府所□。”
简四:“骊靬尉史当利里吕延年,年廿四□。”
简五:“□出钱五十,栗五斗,骊靬。”
简六:“觻得□□,骊靬常利里冯奉世□,”
简七:“骊靬万岁里公乘倪仓,年卅,长七尺二寸,黑色,剑一、己入、牛车一辆。”
简八:“出栗二斗四升,以食骊靬单门安。”简九:“骊靬武都里户人,大女高者君,自实占家当乘物……”简十:“□过所遣骊靬禀尉刘步贤□。”简十一:“骊靬苑奴牧番和宜道里□□。”
简十二:“骊靬苑大奴尹福长七尺八寸。”
简十三:“骊靬苑监、侍郎古成昌以诏书送驴橐”。
上列汉简,乍一看来,确实有点缭乱无章。简一中“神爵二年三月”六字,张德芳先生文中认为:“骊靬建县与古罗马人无关,因为神爵二年已经有了骊靬县,神爵二年是公元前60年,古罗马入侵安息的卡尔莱战役发生在公元前53年。”
但是,这里有“神爵二年”字样的简文,毋庸置疑讲的是骊靬苑,而不是骊靬县。苑、县之别,前者是马场,后者是行政建置,放得无论怎样错乱,仍然能够分辨出上列汉简的时间段。
如果再加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它们清楚地分为骊靬苑、骊靬县两大类,凡是记录苑的,都牵连着番和县,凡是记录县的,就找不到番和的影踪;凡提到苑内的工作人员,必然来自番和县,凡在县衙服差的,都与番和县无关;凡涉及苑的村庄,都是番和县的村庄,凡涉及骊靬县的村庄,也都与番和县无关。为何对苑、县的记录是如此的泾渭分明,道理也很清楚:苑跟番和脱离不了联系,是因为苑本身就设在番和县境内,所以勤杂人员必然也只能来自周围的番和县村庄,作为马场的骊靬苑不可能有自己的行政村;骊靬县跟番和没有纠葛,是因为骊靬苑已从番和境内分割出来,以县的面目出现,有了骊靬县自己的行政村,所以其当差人员不是来自番和而是来自骊靬本县。至此,我们再回头来看,毋须假设,也毋须估算,和骊靬有关的13枚简文,已一一显山露水,清晰地呈现出它们的真面貌。他们历史地分成两大类,属于两个历史时期。其中:简一、简二、简十一、简十二、简十三等五枚,为一大类,属于骊靬苑时期的文书内容;简四等另外八枚,为另一大类,属于骊靬县时期的文书内容。骊靬苑时间在前,骊靬县时间在后。前者表明,骊靬苑设在番和境内,故啬夫、杂役、牧奴等固然都来自番和,负责人为苑监;后者表明,从番和分割出来的骊靬县,以行政建置独立存在,人员再不需要从番和招募,自然要从骊靬本县的行政村招募来,负责人为县长。
有“神爵二年”字样的纪年简面目也清楚了。神爵二年为公元前60年,它明确告诉我们,此时只有骊靬苑,没有骊靬县,此简是骊靬苑时期的。换句话说,汉简确定地告知我们:公元前59年之前没有骊靬县,它是在公元前59年以后若干年的某年,骊靬作为行政县的面目得以出现。
西汉王朝为抵御外侮,在西北边郡建立养育军马的牧苑三十六所。祁连山下,番和之地,有丰富的草场,西汉政府在这里建立了骊靬苑马场。《汉书》告诉我们,西汉建县有一条基本准则,即就是“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汉书·百官公卿表序文》)也就是以百里见方为标准,民稠则可在方百里以下,民稀则可超过方百里。河西属“稀则旷”的地区,还为什么从民众稀少的番和县内切割出一地另建起一个在历史地图上紧紧相靠的县呢?
显然,其中当有着极其特殊的历史原因。也就是说,不建置这样一个骊靬县,很大程度上就不能最妥善地处理当时出现的特别事件。那么,究竟又是何特殊事件呢?这就是后来的公元前53年至公元前36年之间,一批自称骊靬人的异族从西域内迁,或者说流亡在中国西界之外的古罗马的士兵归顺了西汉,他们正好来自遥远的“骊靬”国,番和县有个骊靬苑①汉武帝时,已知西域有所谓“骊靬”国;大宛、安息等国又献骊靬魔术师若干名于皇上。作为对大汉眼中蛮戎的称呼,用字以含“马”、“革”为旁的字是正常的,故以“骊靬”之类给马场苑进行命名并不奇怪。“骊靬苑”之名出现,但与骊靬县是两码事。,汉王朝将这批异族安置在骊靬苑,因设置县条件具备,故将者来寨从番和县分割出来,以把这批人安置在这里,建县以领之。骊靬县为骊靬降人而设,正是。
结 语
近年来,虽然人们在骊靬的相关问题上热情不减,但争论的焦点较多集中在一个“古骊靬城与骊靬降人是否有关”。其中存在的疑点还需要有关专家学者继续进行研究和商榷。但如果把学术界、媒体报道中的一些人和事,拿来做否定骊靬县在历史上的存在和为骊靬降人而设的理由和论点,显然是有失偏颇与欠妥当的。在可能的前提下,根据考古实物旁征引据,捕捉历史信息,避免断章取义,而作出符合逻辑的推理,可以针对一些质疑观点与声音进行讨论层面的反驳。例如针对上文张德芳先生就汉简问题而提出的反对观点,笔者本着学术争鸣以及“求真而不求胜”的态度予以回应;通过出土汉简反映出的信息,提出了不同观点,一定程度上从一个侧面支持了骊靬县为骊靬降人而设。
骊靬故县与骊靬降人,以及两者之间一系列因果关联,在历史上千百年来引起众多学者们的关注和研究。它相关的史料体系与引发的现象关联性,是深博的历史长河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独特的文化遗产,是中国早期以汉朝时期为代表阶段的高度发达的东方文明和当时同时代的西方文明、欧亚地缘文明的交汇点与表征之一,也是以古代丝绸之路这样的显性符号为代表的多元文化的具体反映。研究、揭示和保护性地适度开发骊靬,尤其是适度地开发高端的深度文化旅游,在新的历史时期展现地方人文风采,使更多的人体验这种神秘的历史因缘,对研究古代中西文化交往,中华民族的发展形成,充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基石,都具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特殊的现实价值。
[1]向达.中外交通小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0:7.
[2]冯承钧.西力东渐记[M].重庆:中华书局,1944:1.
[3]林干.匈奴史论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124-125.
[4]张维华.汉史论集[M].济南:齐鲁书社,1980:329-339.
[5]王宗维.汉朝西域路的开辟和骊靬人来华[J].西北历史资料,1985,(1):1-10.
[6]孙毓棠.汉代的中国与埃及[J].中国史研究,1979,(2):142-152.
[7]常征.中西关系史上失记的一件大事——数千罗马兵归化中国[J].北京社会科学,1992,(1):39-50.
[8][法]布尔努瓦.丝绸之路[M].耿升,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1-4,58-73,140-149,284-294.
[9]葛剑雄.天涯何处骊靬城[G]//读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2):144-151.
[10]杨共乐.中国境内哪有罗马城:西汉骊靬城与罗马战俘无关[N].光明日报,1999-05-21.
[11]张德芳.汉简确证:汉代骊靬城与罗马战俘无关[N].光明日报,2000-05-19.
Former Liqian Town and Liqian Surrendered Peop le
SONG Guo-rong,XU Rong-rong
(The Cultural Centre of Yongchang County in Gansu Province,Yongchang 737200,China)
Liqian Town is an old town which is located in present-day Gansu Province in Yongchang County.This fact is clearly recorded inmany Chinese History Books.Since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media have reported much about this.This paper quotesmany scribes constantly raised by the issue to sort out opinions on why this town set,from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to Qing Dynasty,to the contemporary academic circle.Through the analysis,specially bymeans of Jinguan bamboo-slips of Han Dynasty,people have amore credible view that the Liqian town was built up for peopleswho came from Roman and surrendered to Han Dynasty in the war.Historicalmaterials cited and the existing achievements of the series have an important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researching on cultural exchange,ethnicmigration,and nationality amalgamation.
former Liqian town;Liqian surrendered people;Han Dynasty;Roman
K232
A
1009-1971(2012)04-0095-04
[责任编辑:郑红翠]
2012-03-17
宋国荣(1960—),男,甘肃永昌人,永昌县文化馆《骊靬》杂志执行副主编,从事文史研究及骊靬文化研究;徐蓉蓉(1982—),女,甘肃永昌人,馆员,从事永昌地方文史研究及骊靬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