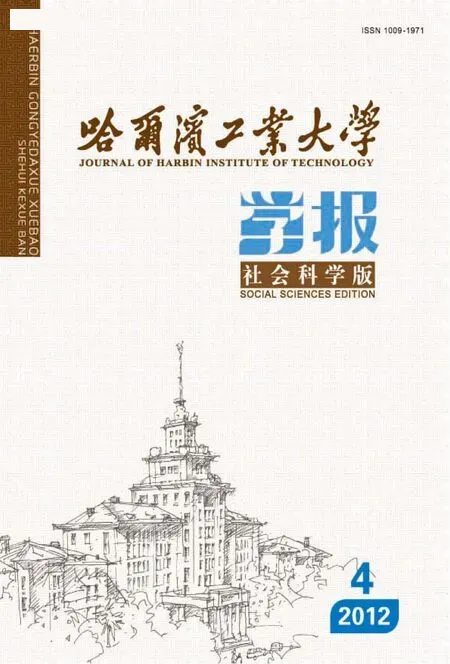骊靬文化之历史钩沉及再认识
2012-04-08赵向东
赵向东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天津300072)
·文学与文化研究·
骊靬文化之历史钩沉及再认识
赵向东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天津300072)
骊靬文化是近年来史学界一个热点话题。一方面,着重于一些历史细节的梳理与比较,如对其字词演变线索、对“骊靬”之名的来由属地与渊源进行了推测;另一方面,结合军事文化、基因旁证,以及参照世界古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建筑史等领域的诸多线索,从特定的历史地理视角来分析与审视这一文化现象,尽可能客观勾勒骊靬文化的历史轮廓。我们应该置于更广阔的视角中去体会这一问题所展现出的文化包容的辩证内涵,获取文化动态演变中富于哲理的启示。
骊靬文化;古罗马军团;西亚地区;文化包容
物阜民丰的甘肃省河西走廊中部腹地永昌县,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历鸾鸟、番和、骊靬、显美、焉支、嘉麟、天宝、永昌八县名相沿至今。在数千年的变迁中,经汉、高昌、北凉、隋、唐、西夏及以后多个政权势力范围,历史文化遗迹丰富。
距县城十余公里焦家庄乡楼庄子村六队的者来寨一带地处祁连山脉沟口,地形开阔,是个宜耕宜牧的好地方。历经战乱的十余处古城堡、古烽燧、古兵营遗址峭然耸立。从地理上看,据峙祁连入口,背依大山,进退相宜。而这里一处古城遗址,与历史上一支古罗马失散军团竟有关联。这就是由来已久的“者来寨即骊靬古城”的学术关注,骊靬文化因而有着相当的国际知名度。目前针对骊靬文化的历史脉络在学术界虽未形成完整定论,但我们仍然可以从特定的历史地理视角来分析与审视这一文化现象。
一、骊靬悬案及史海钩沉
1957年英国著名汉学家H.德效骞就曾明确提出:中国古代称罗马帝国为“骊靬”,后又改称“大秦”,并引《后汉书·大秦》即以“大秦国一名黎鞬”起首[1]。1989年,澳大利亚阿得来德大学历史学者戴维·哈里斯先生也曾经提出假设并出版著作《黑马奥德赛》,提出在公元前53年的安息卡尔莱(今叙利亚帕提亚)战役中战败突围溃逃后失踪的古罗马军团,东移中被匈奴收编,在后来的汉匈之间的郅支城战役时又被汉军俘虏,被西汉王朝收降后专设骊靬县用来安置这批战俘。他认为者来寨是古骊靬城遗址。如今历经消蚀的骊靬遗址附近尚生活着具有非典型东方民族特征的居民人群,为这个假设提供了一定支持。1989年9月30日,《参考消息》报曾转载法新社关于骊靬古城学术研究的报道,披露了这件鲜为人知的事;同年12月14日,新华通讯社播发兰州大学与国外学者进行这一学术研究的简讯;15日,《人民日报》也以《永昌有座西汉安置罗马战俘城》为题发了消息。1997年10月11—14日香港《文汇报》也曾对此作连载报道。近十余年来,关于两千多年前的这支古罗马军团是否流亡并被汉安排到番和县(今属永昌)并设“骊靬”城,而展开了相关研究并多有争鸣。尽管由于没有进行过大规模考古发掘以及出土实物佐证的缺乏,并且有学者提出了诸多疑问,但仍有支持声音认为永昌骊靬古城应是当年西汉安置那支军团战俘之地。
公元前53年,即西汉甘露元年,古罗马共和国正处于权力重组时期。当时,罗马三巨头之一、古罗马共和国执政官之一兼叙利亚行省总督克拉苏决定向东部扩张势力。在恺撒进攻不列颠的前一年,崇尚武力的克拉苏纠集七个军团发动了对安息(今伊朗一带)的侵略战争。但古罗马军队却在卡尔莱(位于幼发拉底河中游以东)遭到安息军队的围歼,克拉苏败亡。第一军团首领、克拉苏长子率领数千残部突围而去。据学者的研究推测[2],这支散军辗转东进,流徙西域投奔到了郅支(于今哈萨克斯坦境内)以雇佣兵的形式继续存在。《汉书·陈汤传》中记载:公元前36年,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讨伐匈奴郅支单于,战于郅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陈汤等人在这里发现了一支奇特军队,他们以步兵百余人一组,排演鱼鳞阵、盾牌方阵,城外有“重木城”的战法。郅支城之战汉军大获全胜,俘千余人。甘延寿、陈汤等将这些战俘带回中国。为了安置他们,汉元帝下诏在番和县①现遗存有古番和城故址,即为汉置古番和县所在,位于现永昌县焦家庄乡水磨关南1公里处。南(今永昌县)的照面山下“初设骊靬县,取国名为县”。
这个被命名为骊靬的县出现在西汉河西地区的版图上,在今甘肃永昌县城之南,从《汉书》到《隋书》都准确无误地记载了这个县。史学家在公元前9年绘制的布帛地图上也发现有清晰可辨的“骊靬”标注。而恰在公元前20年古罗马帝国与安息签订和约并遣返俘虏。这两者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这两大事件之间似乎有着某种关联。为此历史学家们认为,这极有可能就是在卡尔莱战役中溃退并已失踪十余年的那支罗马军残部。
历史上“骊靬人”后裔据《三国志·贯丘俭传》及《三国志·武帝纪》马超曾收编入“西凉兵”,与曹魏军激战并以鱼鳞阵获得了成功。《晋书·张祚传》记述了公元31年“前凉张祚遣将伐骊靬或于南山(即照面山),大败而返”的史实。历史上的骊靬人东晋时曾威震陇右。《隋书》当中记载改“骊靬”为“力乾”,并于“开皇中,并力乾入番和(县)”②隋文帝开皇十一年(公元592年)之中,鉴于骊靬人已被汉族同化,下诏将骊靬县并入番和县。。这时骊靬人成为南北朝时期北凉卢水胡人的主要组成部分[3]31-32,227-229,后来渐渐与其他民族融合。
二、历史地理背景的辨证求索
(一)历史上若干同音不同字的命名
细细释读犁靬、黎靬、骊靬、力乾等一系列的命名,其用字的变异或通假似乎并不是偶然与随意的现象。因为从选字组词上讲,中国人历来重视对事物之命名,而且汉语是“音”、“形”、“义”三位一体的符号群,在命名取字上具有从音、形去捕捉意象的特点,具有一种全息的训解系统。
中国自古有尊重外来民族与文化的传统,有对异类语言语境中的名称在进入中国后起汉语谐音作为命名的传统,往往采用的汉语发音、字义易记,对骊靬也并不例外。多种文献记载当中针对这个发音有多个用字的出入,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把罗马帝国称做黎靬,后又有犁幹、梨建[4]395、犁轩、犁鞬、驪(骊)靬,至隋又称力乾等等。但仔细把味,在零散的文字信息中,似可探寻出一条骊靬文化的若隐若现的轨迹。
西汉设置以骊靬命名的县在《后汉书》中有载:“汉初设骊靬县,取国名为县。”清代学者惠栋在《后汉书补注》中说:骊靬县“本以骊靬降人置”。“骊靬”正是当时中国人对罗马的称谓。既然是“取国名为县”,那么,这个新出现的县应是为了安置这批战俘而设置的,在安置后分拨了土地,开始了屯垦卫戍的生活。
这支外来部队余部被西汉政府收编到番禾之时,放下兵器,务农戍边。他们被赋予的是耕作务农的外在形象,因此,用“犁”这个充满农耕意味的字眼来表达屯垦卫戍的生活写照,而“黎”也有黎民百姓之意,也表达着类似“虎落平阳”般的民众意识与怀柔意识。随着时光的推移,骊靬人骁勇善战、骠悍尚武的气质渐渐显示出来,正如哈里斯先生曾经著述《黑马奥德赛》所表露的,命名用字上就用“骊”字取代了“犁”和“黎”,此“骊”在汉字当中即表示“黑色的马”,其势骠悍。“犁鞬”中之鞬字,表示马上盛弓箭的器具。如:《说文》中:“鞬,所以戢弓矢者。”《方言·九》:“所以藏弓谓之鞬。”《后汉书·西羌传》注:“鞬,箭服也。”可见,“鞬”字选用也是因为其字义属性含意勇武。
随着一次次战争中的出色表现,这样一支富于战斗力与独特战法的队伍渐渐展露头角,出人头地,以至于隋时又将“骊靬”改为“力乾”。此二字中“力”意为刚强勇武,“乾”则为八卦之最阳者,《周易·系辞》中更释之曰“乾,健也”。两字组合而成的“力乾”之称谓则进一步表达并强调着他们所向披靡的勇猛、强力与骠悍。这是其异域特征的文化融入中国文化之时被赋予的烙印。
(二)“骊靬”是“亚历山大”的近似译音
公元前340年到330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建立了西至巴尔干半岛、东到帕米尔高原的广阔的马其顿帝国。这是世界古代史上第二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①第一个为波斯帝国(公元前550年至公元前330年)。。为了炫耀武力与征服,在所经之处的重要港口与城市,常被改为亚历山大的纪功称谓以“亚历山大城”命名。故此古代西部亚洲及亚欧、亚非结合部出现过多个叫做“亚历山大”的地名。仅在波斯、伊朗高原以东就有八个亚历山大城[5]。这还不包括如地中海东岸沿岸一带的数个亚历山大城。
从现亚、欧、非三大陆交接地区东延至现在的阿富汗,多个地方曾有“亚历山大”这个近似音的地名是不争的事实。有学者指出,根据通用的对音法,“骊靬”是希腊文“亚历山大(A lexandria)”的汉文对音[6]。“骊靬”虽然是“取国名为县”,但却并非就指古罗马的大秦之名(东汉时代才使用大秦称谓古罗马),较大的可能是指当时地中海东岸至西亚一带的“亚历山大”城(今叙利亚北部临地中海的当年被命名为亚历山大的港口城)。汉代的骊靬县,可以说是在当时特定的中国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东方亚历山大”。
公元前115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已将“黎轩”列入通使范围。这说明“黎轩”的出现早于后来的“骊靬”。张骞代表汉廷派出的使者大概未到达黎轩,但他派往安息的使者却与黎轩人有过直接的交往。据《汉书·张骞传》(卷六十一)等文献记载,曾有波斯人带犁轩魔术师入朝表演。《史记·大宛列传》也有记:“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虽犁轩音近于骊靬,但此犁轩疑非彼骊靬。从离波斯较近的地区来看,这个“犁轩”很有可能是指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两河流域一带的某个内陆“亚历山大”城,即此城未必就是彼城。
(三)骊靬与古罗马的“关联”
大秦古代被用做古罗马的汉名,已在后汉时代了。过去通行的说法是将《史记》、《汉书》中凡是出现类似于犁轩或犁靬之称谓统统当做罗马帝国,至于它的原音则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是琉塞西王朝,有的认为是那巴提国都城彼特拉的别名Rekem。也有的说法则是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但仔细辨认《史记》中的犁轩,实际上却是中亚细亚木尔加布河以西的特莱西那,《汉书》中的犁靬则在乌弋山离以西,《汉书》说乌弋山离“西与犁靬、条支接”。这里的犁靬并非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而是波斯湾北岸普林尼称为阿曼西亚的地方区域中的亚历山大里亚,在古拉希坎特附近[7]51。
后汉时代把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称为犁鞬。奥古斯都(公元前30年至公元14年)时代以后,罗马以亚历山大城(位于埃及北部地中海沿岸)为基地,积极开展东方贸易,于是中国才和西方最富有的罗马世界进行频繁的贸易往来[7]51。
早在1885年,著名学者夏德就把中国史籍中有关大秦和拂菻(隋唐以后对拜占庭帝国的称谓)的记载辑录并翻译成英文,书名《中国与罗马东部地区》,结论是大秦或拂菻主要是指罗马帝国或拜占庭帝国的东部地区[4]393,即叙利亚一带②但也有学者研究认为中国史料中的大秦,不是夏德所认定的罗马东部地区(叙利亚),也不是伯希和认为的埃及亚历山大城,而是指以罗马为都城的整个罗马帝国。在此存此一说。据参考文献[4]中D.D.Leslie和K.H.J.Gardiner《汉文史料中的罗马帝国》一文。。
综罗百述,可基本推断,“骊靬”与“亚历山大”在发音上与其历史渊源上的关联性可证明二者极可能指称同一逻辑对象;而骊靬所指的位于地中海东岸及西亚一带区域中的确切位置,极大的可能应是地中海东岸北端、小亚细亚半岛逶迤东南沿地中海拐角处的港口亚历山大,这里也正是当年克拉苏任罗马共和国叙利亚总督时的统治区域叙利亚的北部地区。由于这一带的极度繁荣,将这一带贸易名城之名波及后来的“取国名为县”,也是符合一定的情理逻辑。
(四)军事文化线索
到了公元前100年左右,罗马通过一系列对外战争使其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但实际上此时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兵源不足,素质下降,屡有败绩。故罗马从征兵制走向了职业雇佣军制度。
历史上的罗马军队有着自身的严整建制和战术理念。比如棋盘式的步兵阵列布置,距敌阵至二十米的距离开始投掷标枪。此外,罗马军队在和欧洲游牧民族作战时,还发展出一种夹门鱼鳞阵③这种阵法是收拢队形,第一排步兵以蹲踞姿势将盾牌拄地,第二排步兵将盾牌置于前排盾牌之上,第三排及之后的步兵将盾牌举过头顶,如同瓦片一般相迭。这样就组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叠锁盾"的盾阵,主要用以防护对方的箭矢和步兵冲击。。古罗马军队系列主导战法是欧洲古代军队阵列战法的典型代表,但不适于与骑兵对战,不论是克拉苏军团深入安息腹地遭遇轻骑兵后的失败,或是与汉军骑兵团作战的结果均说明了这一点④甚至后来13世纪的蒙古大军铁骑横扫欧洲,所向披靡,也说明西方战阵和战术多难以匹敌组织严密的机动灵活的骑兵突击。。他们后来归于匈奴和康居等国,而匈奴和中亚国家历史上在军事技术方面是比较落后的,所以就彰显出这支军队的独特。鱼鳞阵、重木栅城[7]37(以多重木栅作为土城的外围,这是古罗马城防工事的典型构造)等战术战法未必一定就是古罗马军团所独有。安息等与之常年交战的地中海东岸及西亚一带极有可能掌握相同的一系列战法。因此,“骊靬”并非是专指古罗马,更不是现在的意大利,而是古代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时期加入到东征的这支军团所组成的人员被世人指称的代语,其主要来源地集中于属罗马帝国东部行省的地中海东部亚洲地界一带,及雇佣军制度下极大可能的西亚、中亚地区。
(五)科学的旁证
近年来陆续有当地体貌异常者在权威机构①如2003年5月兰州大学生命遗传科学院及1999—2004年间中国科学院人类遗传研究所等。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骊靬人其基因与阿富汗、土耳其、伊朗等西亚腹地人有较近的血缘关系,个别甚至有着近一半的欧洲血统。实验结果也说明这些人的基因与维吾尔、蒙古等族相差较远。如中科院马润林教授认为,虽然存在源于欧洲的基因单倍型,只是有助于认定这些居民祖先在历史上可能与欧洲人或带有欧洲基因型的其他人有基因交流,谈不上欧洲血统[3]273-276。这种认识马其顿帝国东征中的通婚现象也可作为一种例证。显见,鉴定结果并不足以说明这些人是什么“欧洲人”后裔,不过将“骊靬”发祥地范围已经大致圈定在了相对缩小的地理范围内。目前可以确认,骊靬人与罗马人绝不是一个概念。
为什么西亚有较多的欧洲血统呢?甚至血缘横跨四千英里的欧亚大陆腹地而直至阿富汗呢?由于亚欧版块紧密相连,世界历史上发生重大事件联系最为紧密的就是这两个大洲。而帕米尔高原巍峨的雪峰阻拦住了一些来自西方的东征,使得中国鲜有与欧洲文化直接碰撞。而从地中海沿岸东进,经两河流域,伊朗高原至恒河流域,地势并无天堑之虞,所以,历史上的一次次跨越式的远途作战与奔袭,已将这万里之路纵横捭阖而成一条文化走廊。战争、迁徙、经商、宗教等使得东西人群之间交往频频,因此,西亚、中亚至今也有着相当多的欧洲血统,而且由于强势文化主导的影响,当时欧洲及西亚较富庶,其聚拢效应使得在偏远一带地区有着更多的受雇佣关系,即使地道的“古罗马军团”大部分兵士也并不是来自古罗马本土,而是西亚一带的雇佣兵,这其中有较多的诸如今阿富汗一带雇佣兵确是合理的。
逻辑的历史推理,事实说明与以往认为骊靬人为“古罗马”后裔的草率的大众看法不相符合。这容易产生矫枉过正,从一个认识极端走向另一个认识极端。应避免出现由于对历史缺乏宏观了解所造成的片面认识与片面“噱头”式的情感,对骊靬文化的健康认识应坚持辩证的历史观。
(六)历史地理层面的综合推断
作为骊靬文化的事件背景,关于地中海东岸及西亚地区之间历史地理关联性理解十分必要。
罗马共和国和安息帝国接壤的东部边疆,属地中海东岸的内陆一带。越过紧邻着沿海平原的群山,便是两河流域的上游。渡过幼发拉底河,再向东五十公里就是发生当年古罗马军团东征安息的卡尔莱之战所在。这一地带的核心叙利亚公元前333年连同波斯帝国一起被马其顿人征服。公元前64年该地被罗马共和国吞并并作为罗马共和国及后来的罗马帝国地中海东岸的一个行省,包括今日的以色列、叙利亚、约旦和黎巴嫩,这些地区在近千年的历史变迁中留下了许多古城。
而汉代以来司马迁和班固先后记载了大夏(今阿富汗一带)、大宛、安息、身毒等地域诸方面的特征,及其与汉地的文化交流。神秘的犁轩人进入汉地首先在这些记载中出现。据《汉书·大秦国传》:“大秦国一名犁犍,在西海之西……其城周回百余里,屋宇皆以珊瑚为饰,琉璃为墙壁,水精为柱础。”《后汉书·西域传》:“(大秦)以石为城郭……宫室皆以水精为柱。”这一描述并不完全像地中海腹地亚平宁半岛一带的建筑,更像古罗马所属西亚领地的建筑特征。“风格上更接近于东方。建筑风格上的东方化,实际上反映了罗马文化对东方文化的认同。罗马人统治之下的叙利亚……建筑东方文化色彩更浓厚一些。”[8]114事实上,叙利亚一带曾经是古罗马时期的重要疆域,当时古罗马时期的地中海东岸属地建筑工艺及技术相当发达,古罗马历史上不少重要建筑物均为这一地区的建筑师所设计,如罗马城中著名的图拉真广场,建筑师就是叙利亚人阿波洛道鲁斯[9]。当时叙利亚这一带地区是罗马帝国各行省中繁荣程度最高的,是古丝绸之路上重要驿站点,是古罗马时期的建筑迄今保存完好度最高的地区,至今存有大批当年古罗马的建筑遗迹,如巴斯拉阶梯剧场可谓全世界保存最为完整的古罗马建筑之一;又如在今黎巴嫩有建于2-3世纪的巴勒贝克大神庙[8]113-114。
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是此地最古老的城市,许多重要的商道会聚于此。鼎鼎大名的大马士革钢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好的钢,也是当年冷兵器时代这一地区兴盛的标志。在大马士革的集市上,曾经琳琅满目地汇集着来自亚非欧三大洲的物品,中国丝绸正是通过这一繁荣地区而销往罗马帝国。而当时,克拉苏正值任叙利亚总督;顺理成章地,他手下的罗马军团士兵似应多为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地区,并兼及西亚一带的兵源。联系上文曾有国外学者研究认为“大秦”指现今叙利亚一带的结论,逻辑上也是趋于吻合的①历史上甘英等出使大秦,实际也只是到达地中海东岸一带,没有深入罗马帝国的腹地。。
从上述历史地理的角度,也可从侧面支持本文观点:至少绝大多数骊靬人应不是出自现在的欧洲地理区间,虽然有不少应来自古罗马本土——这个“本土”就是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一带(这一带欧洲血统本就非常普遍),更兼其雇佣兵制度,所以,其人种与基因来源固然有一定的欧洲因素,但更多的来自于西亚地区是毫不为怪的。
三、骊靬文化的内涵及启示
骊靬文化,是连结紧密的亚欧版块的历史激荡中产生出的独特篇章。
由于历史的久远、欧亚版块长期的多种族融合与变迁,确切地追寻历史中的“纯正血统”已无可能。但当我们抛却纷乱迷扰的无谓纷争而再来仔细审视骊靬文化,并结合汉代及至古代中国与西域关系史,却可以另辟蹊径,对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有若干新的认识。
第一,骊靬文化反映在古代两种高度文明之间军事文化交流与碰撞范畴内。在这支军团归附汉朝之前实际上反映的是东西古代首次也许是元代以前唯一的一次军事交锋——西汉正是中国历史上军事力量较为强大的帝国时期,骊靬人虽然精悍,但由于势单力孤而难以避免失败的结果。换个角度,如果从中西文化交流的层面上去看从此处衍生出的一系列战事,它可以说是早期东西方两种高度发达的文明之间在偶然条件下的军事文化层面上的碰撞。
第二,骊靬文化实质上反映出了以当时古中国占据思想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宽仁范型。
汉代是中西交流的一个高潮期。当时的汉帝国为了保护丝绸之路,不得已在河西走廊北线建汉代长城,所以中国古代建长城并非以往所只注意到的防卫性和封闭性,恰恰相反,建长城的目的正是为了获得开放性的地理空间,进而与西方与中西亚地区进行全方位的交流与互访。秦汉以来多种宗教、人种、生活方式在中国并存,甚至在中国获得新的生机。中国自汉以降的骊靬文化并不单单是一支疑似异域散军流落至中国境内在此休养生息的简单过程,若放在国际文化大视野中考察其精髓与内涵,尤其是当今世界正处于以一种新的哲学眼光来审视东方思想与东方文化的这种时代契机中的时候,这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韶华史迹,在中西文化交流史当中实际上正彰显着中华大国文化的深厚积淀与对待异己所具有的强大包容性的独特人文魅力。
中国的自古传统,道德的力量大于政治。儒家把天道与民心放在一起来看,从民心中看天道。如《诗经》中所说“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中华为五行之中,主张中庸。中庸确切地说是不主张走极端。对待臣服之人,以宽仁之心相待。如《论语·里仁》中“德不孤,必有邻。”中国古代的政治行为(即御政)总是要与道、德、仁、圣、义、礼文化哲学结合在一起,以德治人、以礼推于天下,处处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对伦理和睦的追求。古中国的这种文化哲学与古中国的天道、地道、人道哲学等等也是共生共存,正如《荀子·王制篇》中“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而且《大戴记·盛德篇》云:“以之道则国治,以之德则国安,以之仁则国和,以之圣则国平,以之义则国成,以之礼则国定。”中华文化推行与天地之道相契合的体仁思维,其道理就在其中。在秦汉时期中国行政区划为郡县制,县的级别属于较高的一种行政设置,以县级单位的设置来看也是汉朝对外来人员安置的相当等级的礼遇。古代中国对于当时属于外族的骊靬残部的仁义收容,看似一起偶然事件,但其背后体现的却是必然的中华大国四海一家的思维模式与理念。
第三,世界古代史中,多次出现过东方、西方之间从血缘到地缘的大融合,如横跨欧亚大陆(甚至连跨到北非)的大帝国,除较早一些的波斯帝国外,更以亚历山大三世(即亚历山大大帝)的马其顿帝国为最典型的东西方大规模的全方位交流。例如他就企图使希腊人和亚洲人杂居融合,并曾强制上万名部下与波斯女性通婚。并且,汉唐时的丝绸之路上,无数前来东方的商贾客旅辗转迁徙,停留不还,成为欧洲及西亚、中亚的血统东传的重要途径。可以说,骊靬文化的千年流变,正好说明了历史事件所造成的血缘融合与印证。
除此之外,应当看到,骊靬文化是古代中国长城沿线这一“文化共同体”的典型,是波澜壮阔的民族、种族“互融线”上的融合变异的产物。由于历史上边境地区人群的迁移流动性更大,自秦汉起,匈奴、氐、羌等各民族不断来到长城内外。汉末魏晋更形成大规模少数民族内迁;与此同时,大量汉族也被迫或自愿进入大漠南北、西域等地,与乌孙等“人皆长大”的种族共存,与多民族杂居以至相融。长城一带各族之间也由杂居到相互吸收,后经隋唐长期交流与通婚的积淀,同当地民族融合为一体。两宋时期长城沿线一带的民族,大规模在这一线各地流动迁徙;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相互杂处的环境中共同劳动、相互学习。元、明及清初,蒙、回、满、色目等民族再次大迁徙,造成新的杂居与融合。这样,自唐至明,许多民族后来不见于史载是因为融合于汉族或同其他民族一起渐次演化成全新的民族实体。
生活在大杂居、小聚居的长城地理文化带上的各民族,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又在继续进行着新的民族融合的进程并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即以农、牧两大经济、文化形态之间的民族融合为基础;长城内外民族融合范围极广、规模极大;历代各民族由杂处交流到民族融合数千年经久不衰,最终发展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今日中华民族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共同体,甚至不断地有“反常规”的“亲缘”关系得以昭示。
中国文化一向讲究“天地中和同心”,理想的太平世界是人与人、人与各个层次的自然事物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世界。这种万物一体化的社会生态伦理精神告诉人们,和谐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归根到底要营造和谐共生的人类文明。骊靬文化正是通过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中的象征符号性,将异域与本土文化和谐有机地联结起来。正如前文所述骊靬文化带给后人的启示一样,它代表着一种中华文明极大的包容性和同化性,跨越广阔地域的“融合”之美。
[1]张一平.丝绸之路[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30-31.
[2][英]德效骞.古代中国之骊靬城[G]//中外关系史译丛:四.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364-373.
[3]宋国荣,等.骊靬探丛[M].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5.
[4]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5][日]21世纪研究会.地名的世界地图[M].洪郁如,译.北京:万卷出版公司,2007:17.
[6][法]伯希和.黎轩为大秦别名考[R].通报(P.Pelliot,Li-kien,autre nom de Ta-ts’in,T’oung Pao),1915:690-691;[日]白鸟库吉.西域地理[G].东洋文库.东京,1950:73-155.
[7]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8]张晓校.罗马建筑[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9]陈志华.外国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79:52.
Looking Backward,How Long the Bygone Years:The Recognition of Liqian Culture and History
ZHAO Xiang-dong
(School of Architecture,Tianjin University,Tianjin 300072,China)
Liqian culture in recent years has been a hot topic in history research group.This article analysis the relevantmaterials in the fields and focuses on thinking and reasoning of some historical details such as its literal terms and the word evolution clue,the cause of“Liqian”naming,logical possibility of location and origin;On the other hand,according to the combination ofmilitary culture,gene circumstantial evidence,as well as reference to ancientworld history and Chinese-Western culture-exchange history,architectural history,this cultural phenomenon is analyzed and examined from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as objectively as possible to outline the contours of Liqian culture.Placed in a broader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this issuemay show dialectical connotation of the cultural inclusion and guides people to get access to philosophical revelation of the cultural dynamic evolution.
Liqian culture;Legions of Rome;West Asia;cultural inclusion
K232
A
1009-1971(2012)04-0089-06
[责任编辑:郑红翠]
2012-01-17;
2012-04-23
赵向东(1973—),男,河南郑州人,博士研究生,从事建筑历史及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