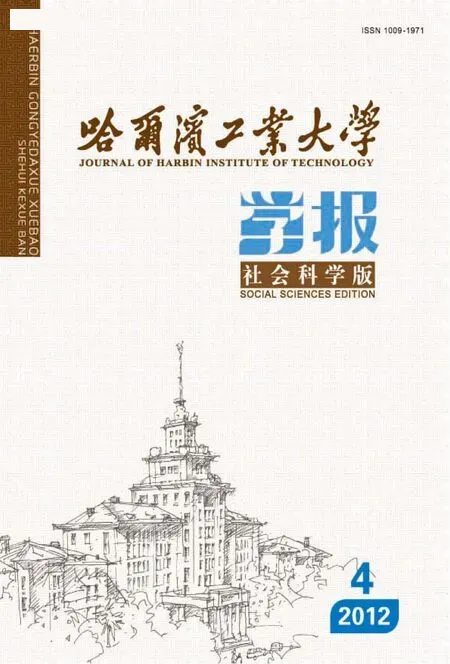基督教与当代中国诗坛
2012-04-08荣光启
荣光启
(武汉大学文学院,武汉430072)
·文学与文化研究·
基督教与当代中国诗坛
荣光启
(武汉大学文学院,武汉430072)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许多有基督徒身份或者倾向于基督信仰的诗人。对于他们的写作,诗坛往往以“宗教诗歌”或“次要诗歌”轻视之。这种轻视是国人对文学与宗教之关系的简单理解。随着当代中国文学日益世俗化,诗人们也一直在寻求种种“神性”的写作来应对。他们尊重文学的自身特性,正视生命的沉沦境况与救赎之需,敏于自我生命的问题、关注人的历史与命运。他们虽未高举“神性”大旗,在这个时代,却具备了真正的“神学立场”。他们的写作,尤其值得当代汉语诗坛关注。
基督徒诗人;当代中国诗坛;宗教诗歌;次要诗歌;神性写作
一、有基督徒身份的诗人
20世纪90年代初期,刘小枫先生在一篇谈论“‘文化’基督徒现象”的文章里写道:“自本世纪中叶以来,基督教的合法传教活动在大陆实际中断,无神论意识形态取得了实质性的社会法权,以至于基督教的信仰和社会生活只会引起人们的政治警觉意识。然而,近十年来,社会层面对基督教的政治警觉意识至少在城市区域有明显减弱,基督教的认信在已成为社会基础意识的无神论语境中自发漫生。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文化知识界中出现了宗教意向和对基督信仰的兴趣。这一精神意识之趋向在文学、艺术、哲学和人文科学领域中,尽管实际上不仅丝毫不具普遍性,而且显得脆弱孤单,但确有增长的趋势……”[1]应当说这一描述是真实的,仅就文学界而言,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等著作、先锋小说家北村认信基督之后的小说、年轻的批评家谢有顺的小说评论……一批与基督信仰有关的文化/文学文本在国内影响甚大,许多在大陆教育体制中的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人其思想受到极大冲击。
也是在基督教的思想与美学的參照下,90年代中后期,刘光耀先生在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中宣告“中国文学的终结”:“中国文学是空间文学。中国文学的终极是空间物。道家的道、儒家的天、禅宗的佛是中国文学之终极的三种物化形态”,由于“存在物不是终极”,“以物为终极”的中国文学已“深陷于一片意义的真空”,走上了“终结之途”。刘光耀先生也指出,“走向终结”的中国文学,其重生之途在“走向终极”,“走向终极就要走向上帝”[2]。刘光耀先生的观念显然是有预见性的。在诸多诗人自杀或颓丧之后废墟般的中国文学图景中,浮现出许多“走向上帝”的写作者、许多有基督徒身份的诗人。
仅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许多人都知道,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意识形态一体化的松动、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和国人对生命意义更深的渴求,中国文坛(如小说界和诗歌界)出现了一批有宗教信仰或倾向于某种宗教信仰的作家,其中还有人用通俗的话说,还真正的“入教”了,他们的名字其实大都为人所共知,这已是当代中国文坛一个醒目而值得关注的现象。本文所关注的是那些有基督信仰或倾向于基督教的诗人的命运。迄今为止,一个对当代中国诗坛熟悉的人,会看到一些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成名的诗人在世纪之交的巨大变化,他们当中,或早或晚,有人是终于认信基督、在人生的中途获得重生,像耿占春、施玮、刘光耀、鲁西西、宋晓贤、李建春、姜庆乙、沙光、李浩、黎衡等人当是如此;有人则是因为出身于基督教家庭,在此时代渐渐明晰神的救恩,像以创办中国最大的诗歌民刊《诗歌与人》的诗人黄礼孩即是如此;当然还有一些诗人应当说在人前并不一定乐于表明自己是基督徒,但在诸种宗教信仰中,内心显然倾向于基督信仰,像诗人谭延桐。但不管各人境况如何,他们的写作(早)已渐渐为当代汉语诗坛所瞩目。
除了这些在狭义的国内“诗坛”大家比较孰知的诗人之外,还有一些“基督徒”诗人因其独特的诗歌写作也值得我们注目,比如前面提到的刘光耀先生,他的《十四行诗》[3]①另,在他和杨慧林先生主编的《神学美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一辑封底的那首十四行诗《致琼玛》也是一首杰作。显示出很深的诗歌造诣,当代汉语诗歌缺乏神性意味,而刘光耀在诗歌形式上的自觉意识与探寻意识更是值得称道;比如小说家北村(时常有诗歌发表),比如研究欧美文学的比较文学学者齐宏伟(著有诗集《彼岸的蛩音》,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比如在北美的诗人、小说家施玮女士,由她主编的《琴与炉·诗歌卷(第一辑)》(灵性文学丛书)2008年1月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这是国内目前集中展现有基督信仰或倾向于基督信仰的诗人作品的一部优秀诗集,而这部与基督信仰有关的“丛书”,在当代汉语文学序列中应当有自己的分量和一定的地位。
这些诗人已经展示出一种别样的诗歌写作和文学实绩,尤其是他们的诗,呈现出的气质和风格明显区别于诗坛多数作品。这种诗歌的独特品质出于他们在(基督)信仰中得救的“属灵”事实,出于他们因看见上帝的恩典与荣耀、敏感于人的亏欠与堕落的心,这些写作不再是彰显人的经验与智慧、肉体感觉及放纵的想象,而是尊重文学和信仰经验表达的双重特性,正视诗之特性、也正视生命的沉沦境况与救赎之需,诗人们试图回归那个起初的“人”,挖掘人之“灵性”,敏于自我生命的问题、关注人的历史与命运,在真实、丰沛的生命感觉与诗意想像中书写“灵性文学”,“让人看见繁琐平淡生活中的美善之光,让人从自己扭曲、污损的生命中看见人里面‘神’的形象,看见人原初当有的尊严与荣美”[4]3。他们以信仰的眼睛看见上帝的荣耀,并用合适的言辞和特定的诗歌形式将这荣耀见证出来。
二、被轻视的写作:“宗教诗歌”
不过,对于这些基督徒诗人或者倾向于基督信仰的诗人,随着他们的宗教信仰倾向的日益明朗,有一定的评价机制和审美积习的当代诗坛对他们的写作的评价却在降低。至于那些基督徒身份人所皆知的诗人,其作品受到的待遇会更糟,许多人会因为这一身份、因为他/她的“入教”而觉得其诗作不值一读。大约1999年底,鲁西西一首描述灵魂得救中的一种瞬间感觉的诗作《喜悦》让很多人至今津津乐道:
喜悦漫过我的双肩,我的双肩就动了一下/喜悦漫过我的颈项,我的腰,它们像两姐妹,将相向的目标变为舞步/喜悦漫过我的手臂,它们动得如此轻盈/喜悦漫过我的腿,我的膝,我这里有伤啊,但是现在被医治/喜悦漫过我的脚尖,脚背,脚后跟,它们克制着,不蹦,也不跳,只是微微亲近了一下左边,又亲近了一下右边/这时,喜悦又回过头来,从头到脚/喜悦像霓虹灯,把我变成蓝色,紫色,朱红色。
应当说,仅从一个诗歌写作者的角度,鲁西西也是当代汉语诗坛的佼佼者②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批评家王光明先生就对她的诗颇为喜爱。2004年以来,王光明主编的《中国诗歌年选》(花城出版社)每年都选鲁西西诗作多首。王先生并不赞成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皈依基督的选择,但他可能是国内对诗歌本体的认识最自觉、对诗歌文本的感觉最好的批评家之一。。但认信基督之后、基督徒身份渐为人知的鲁西西,作为一个诗人,其写作上的成就与其诗坛名声应当说是不大相称的(尽管她本人对此并不在意)。近年来,鲁西西出版诗集多部,像《鲁西西诗歌选》(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源音》(台海出版社2006年版)、《语音》(台海出版社2006年版)都是值得关注的诗集,但大多数人印象深刻的还是这首《喜悦》。对于她的诗作,诗坛普遍的认识是,“鲁西西转入了宗教题材的写作”,人们通常从“基督教教义”来解读。诗人刘春提道,2005年5月下旬的“青春诗会”上,“鲁西西的宗教题材诗歌引起了争议,一些诗人认为她在这方面的探索尚处于初级阶段。从鲁西西的辩解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她的不以为然”[5]。将鲁西西的诗作视为“宗教题材诗歌”以及认为她还未达到国人先验中的某种宗教诗歌模式,这不仅隐含着国人对宗教诗歌的一般认识,更重要的是隐含着人们对诗歌写作与宗教信仰的复杂关系的简单化理解。
在当代汉语诗坛,人们对宗教信仰与诗歌写作的复杂性还没有真正的认识,这也导致很多人有一种先见:那些基督徒诗人由于“逃遁”至宗教信仰领域,缺乏足够的意识和感受力来处理复杂的现实经验,他们只是在简单地分享宗教题材。这当然是一种偏见,前面提及“基督徒”诗人,许多人其实并不常常使用明显的宗教素材、《圣经》词汇,而是在用“宗教的感受力”在感受自我、用“宗教精神”在想象世界,他们的诗作为当代汉语诗歌提供了一种新鲜的生命感受和极有震撼力的心灵剖露,仍然可以归入那些可以称得上“优秀”或“杰作”的诗歌文本序列。兹举前面提及的集结了海内外多位有基督教信仰(倾向)的汉语诗人的诗集——《琴与炉》中的两首诗,一首叫《减数》:
从妈妈的年龄里减去/我的眼睛/这枚近晚的夕阳/贴着/我的晨光转动
从她皱纹里抽取/我的年轮/落满一地的星子/偷换了/满面苍翠
从她脚步声中/安顿好我的方位/一盏灯/因墙壁收拢/不再暗灭/但需轻一点推门
我们远行而来的时光/一路上删去言语/像一个人的辞海/不给标点余剩空白一首叫《无题》:
当我还是盲人时/是立在光与无光之间的一块界碑/当我还是一个受苦的人便听到呼唤——/“是的,我在这里”/受难让我在此等候多时
……
当我摘掉墨镜和这世上/更多的多余/风,摸到他医治的手指/如同形象从语言脱身/“看”在我眼前如此亲切/我不做声、怕美再一次/错过了亲人
这真的是一位盲人的诗作,他也许已感受到上帝的恩典,写出了许多动人的诗篇,但他的诗篇绝对不是观念性,你看不到明显有宗教性的“题材”,哪怕是相关的词汇,他完全是以心灵的手指在触摸、以心灵的眼睛在“看”这个世界,他是以自己独特的感受力和某种“精神”在言说。在这样的诗作面前,你可能首先不会想到他的宗教倾向,你只会为一种感觉化、经验化和个人化的生命言说而触动。你会看到,因身份或信仰上的认定而小视那些有宗教信仰倾向的诗人的写作实在是偏见。他们的写作使人们看到,像艾略特(T.S. Eliot,1888-1965)的诗歌写作一样,你可以认为他的诗是“宗教诗歌”,但绝不是那种所谓的“次要诗歌”[6]241。
三、文学与宗教之关系:一个合理的认识
艾略特在汉语学界因《荒原》(The Waste Land,1922)而著名,他晚期的代表作《四个四重奏》(Four Quartets,1943),最终使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948)。他作为诗人的伟大举世公认,而另一方面,文学批评家雷纳·韦勒克(René Wellek,1903-1995)则称艾略特是“20世纪英语世界至今最重要的批评家”[7]。作为“现代派诗歌之父”的艾略特,同时亦是“宗教上的英国天主教徒”,他“现代的”文学理念与“保守的”宗教信仰之间关系如何?他在写作上是如何处理这个关系的?这些问题很值得当代中国的基督徒诗人关注,也可以启发我们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的“宗教诗歌”。
艾略特认为文学与宗教彼此独立又紧密相连,他反对混淆宗教与文学的界限。他反对把宗教定位为一种文化的看法,因为在他看来,宗教关注灵魂、指向彼岸的意义与价值远在这种定位之上;同时,作为一个文学家,他尊重文学的独特性,反对说教的文学,认为如果“宗教文学”存在并且要实现其存在的意义的话,应该是一种不自觉地、无意识地表现宗教思想感情的文学,而不是一种故意地和挑战性地为宗教辩护的文学。批评家应该确立宗教的尺度、神学的立场,以应对文学的、乃至世界的世俗化。艾略特对英语诗歌中的一种类型“宗教诗歌”持审慎态度,他说:“从乔叟时代以来,基督教诗歌(religious poetry)在英国几乎完全局限在次要诗歌的范围里。”[6]241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你用‘宗教的’这个形容词来修饰诗歌,你就在给诗歌划出了十分明显的界限。对于大多数爱好诗歌的人来说,‘宗教诗歌’是一种类型的次要诗歌:宗教诗人并不是用宗教精神来处理全部诗歌的题材的一位诗人:这位诗人排除了人们通常认为是人类特性的一些主要激情,因此也就承认了他对这些激情的无知。”[6]241
艾略特认为,“宗教诗歌”“是一种特殊的宗教意识的产物。这种特殊意识,即便是在我们通常期望于大诗人的总意识不具备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存在。在某些诗人身上,或在他们的某些作品中,这个总意识也有可能是存在的;但是表现这个总意识所经历的那些准备步骤却没有表现出来,而只是呈现了最后的产品。要想区别这一类诗人或作品和以宗教的或虔诚的天才所表现出特殊的和有局限性意识的那些诗人或作品,可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我并不敢说,凡恩,或索思韦尔,或乔治·赫伯特,或霍普斯金都是大诗人:我可以肯定地说,至少前三位都是具有这样局限意识的诗人。他们不是但丁,或高乃依、拉辛那种意义的伟大的基督教诗人。即便是在高乃依和拉辛的那些不涉及基督教主题的剧本里,这两位诗人仍然是伟大的基督教宗教诗人。上面提到的前三位有局限意识的诗人不能算是这个意义上的伟大的宗教诗人。就连维永和波德莱尔,尽管他们有那么多的缺陷和越轨行为,仍然是基督教诗人。”[6]241艾略特“要求的文学是一种不自觉地、无意识地表现基督教思想感情的文学,而不是一种故意地和挑战性地为基督教辩护的文学”[6]241。在他看来,基督徒诗人不一定就是“伟大的宗教诗人”,而一些非基督徒诗人的作品恰恰是真正的“基督教诗歌”,比如说维庸(Franois Villon,1431-1463)和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的部分诗作。①T.S.艾略特在《波德莱尔》(《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衷编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07—118页)一文中,认为波德莱尔虽然在他的诗歌里运用了大量渎神的意象和词汇,但他并非真正渎神,他所关心的是善与恶的问题,他直接指向的是基督教永恒教义“原罪”的问题。他的“恶魔主义”(Satanism)如同一种想通过后门挤进基督教的尝试。他认为没有明确宗教信仰的莎士比亚比虔诚的清教徒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更深沉地表现了宗教的精神,“在原则的正统性和情感的虔诚方面,你很难找到一个比约翰逊更真挚的诗人,但是,莎士比亚的诗表现出一种更深层的宗教感受性,尽管他的信仰与实践情况只是我们的猜测。”[8]艾略特的看法来自他对现代诗歌的认识,现代诗歌面对的是一个人的意识纷繁复杂的时代,诗歌应该有能力来言说这种复杂的“意识”。而很多“宗教诗人”,他们写诗的“意识”非常“有局限”性,缺乏艾略特说的那种“总意识”。
在艾略特看来,当人们用“宗教的”这个形容词以前缀来修饰诗歌,其实是在给诗歌划出了十分明显的界限,对于大多数爱好诗歌的人来说,“宗教诗歌”其实是一种“小诗歌”(m inor poetry)[9],或曰低级的诗歌、二流的诗歌。当一个诗人“不是用宗教精神”在写诗而只是在使用宗教性的“题材”、写诗的“意识”非常“有局限性”时,人们难免轻看这样的诗歌:读你的诗我还不如直接读圣经、看《旧约》的先知书(先知书大多是诗体)和《诗篇》。艾略特对“宗教诗歌”的要求至少有三:诗人需要的是“宗教的感受力”而不是狭隘的宗教题材;诗人要处理的是“全部诗歌的题材”、更丰富的现实经验、“人类特性的一些主要激情”;重要的是作为诗人必须的“宗教精神”、写现代诗所必须的“总意识”。
艾略特关于宗教与文学关系的观点,简要地概括起来就是:文学与宗教彼此独立又紧密相连。所以他反对混淆宗教与文学的界限、将宗教同于文学艺术的观点,从广义上来说,他反对的是这个时代把宗教定位为一种文化的看法,因为在他看来,关注灵魂、指向彼世的宗教的意义与价值远在这种定位之上;同时作为一个文学家,他尊重文学的独特性与魅力,强调文学的文学性、尤其是诗歌,更有自身的功能(“制作”、“转化”)。反对说教的文学,认为如果“宗教文学”、“基督教文学”存在并且要实现其存在的意义的话,它们应该是一种不自觉地、无意识地表现宗教思想感情的文学,而不是一种故意地和挑战性地为宗教辩护的文学。也就是说,“宗教文学”、“基督教文学”应该寻求文学形式与宗教精神自然完美的结合。艾略特始终强调自己关注的不是“宗教文学”或“基督教文学”,他关注的是宗教与文学、文化的关系。作为一个杰出的批评家,他一再强调批评应该具有宗教的尺度、神学的立场。
四、当代中国诗坛的几种“神性”话语
艾略特的“宗教—文学”观也向我们这个时代提出了一个相关的问题:我们若认同当今时代在精神上的急剧世俗化的话,我们是否也应该呼吁建立一种神性尺度的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来应对世界的世俗化与人类精神的某种不良趋向?其实当代中国文学早已有这方面的诉求。曾有批评家如是感叹:“我们的文学实在已烂到不能再烂的程度了”[10]。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艾略特面对“当代文学”的世俗化提倡神学立场相应的是,在当下的中国诗坛,针对口语化写作、“下半身写作”及“低诗歌”、垃圾派运动等诗歌世俗化运动,亦有不少人提出纠偏与疗救的策略,其中不乏有关“神性”的诗歌话语。较早的有世宾、黄礼孩、东荡子等发起的“整体性写作”;后有陕西诗人刘诚、归主诗人南鸥倡导的“神性写作”;后有北京诗人蝼冢、白鸦等人针对刘诚的新的“神性写作”的意见。
“整体性写作”是一种“光明的写作”(黄礼孩语),以“消除人类精神中的黑暗”(东荡子语),按照世宾的说法,其目的是希望获得“‘不朽’或叫‘神圣’、‘永恒’的可能”,但令人惊讶的是,世宾的构想完全是建立在“无神”的哲学臆想基础上,“在谈论完整性之前,我们重新回到对存在主义,特别是海德格尔和萨特的无神论者的存在主义的认识上。我们是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度,因此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1969)和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的基督教存在主义不能成为我们的背景。”那么如何在“无神”的语境中获得“神性”?世宾认为,“完整性写作的理想就是对这种人的有限性的默认,并在此基础上紧紧抓住可能因我们对责任的‘担当’而可能闪现的‘照亮’,并以诗歌凝固下来,为我们的生存在一个高于现实的层面上打开另一个世界。”“如果也可能希望诗歌成为《圣经》失效之后的新一本《圣经》。”[11]而陕西诗人刘歌则发起文学的“第三极”运动,高举“神性写作”:“神性写作强调心灵的自由和真实,反对诗人退场,主张在还原生活的时候,将诗人的判断添加进来,强调神性对于所有诗歌题材的全方位照亮和诗性处理……神性写作不准备在存在面前保持零度,强调写王者之诗,圣者之诗,让人类得救之诗和世界得救之诗。神性写作形式与内容一次成型,主张工具回到工具,反对将诗歌语言和技术神化。神性写作强调兼容并蓄,强调集大成,强调重建以诗人为主体的人格力量,让诗歌成为人类得救的关键部位,让诗歌就像天上的大神,以王者的气度统领起生活中所有的正面力量。”[12]
诗人蝼冢则不认为神性在文学的“第三极”、也不在自我之外:
神性。物性。人性。/物性和神性是一个东西。/不存在所谓的人性(必须强调这一点)。/所以救赎和超度也是不存在的。/神性并不在文学的第三极。它从来就是终极的。/譬如:创造射线,它哪一端都不是终极。尽管它是无穷的。/终极的意思是大象无形和万物资始乃统天的“一”。/“一”仍然是象征和隐喻。//“我”是神性的基础。/也是神性写作共时性的基础。/宇宙空间中有我,群我-我群。它们同时而在。/“我”是复杂的。所以神性是复杂的。神性写作也是复杂的。/神性只能以象征和隐喻来阐释,和抵达。/以及依靠可信的感知。/感知的基础是“我”(生命)和形式(结构)。/说出来的都不是神性……[13]
蝼冢的神性话语充满哲思,但似乎神秘莫测,缺乏实际的操作性。除上述言论之外,在目前中国诗坛,倡导诗歌写作的“神性”维度的个体、流派其实还有很多。
五、对当代中国诗坛“神性”话语的反思
这些倡导所谓“神性写作”的诗人,毫无疑问,都是对自我和人类充满关注的热情和救赎的愿望,这当然好。只是让人疑问的是:他们所说的“神”,既不是艾略特坚持的“创造万物的主”、上帝,亦不是苏格拉底坚持的那位主宰智慧和理性之“神灵”,其实只是“人类整体心灵”、含混的“心灵”、自我生命的理性之境,与通常在宗教意义上所说的那个作为终极存在的、超越于人的“神”根本无关。
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这一提法也有可能对文学写作有束缚对批评有桎梏,个中原因:一是如前所言文学确实需要文学的标准来衡定,不能以道德化、理想化的某种“神性”来轻视文学性的追求;二是在中国语境中,大多数作家都没有艾略特式的向一位位格“神”的回归,以生命亲历“神”没有在祷告中亲近“神”的喜悦,更没有痛苦不堪的约伯式的与“神”的争辩。他们根本并不明白“神”,这种与“神”割裂的“神性写作”从何谈起。
艾略特曾这样描述19世纪的英国:“那个思想解体的时代——艺术、哲学、宗教、伦理和文学的彼此独立的进程,被试图促成它们非理想状态之联合的各种各样的空想打断了。这些空想把宗教变成道德,宗教变成艺术,宗教变成科学或哲学……企图把它们结成联盟。每一个半吊子的‘先知’都以为自己掌握了全部的真理。把艺术、哲学、宗教、伦理和文学胡乱混淆在一起,就如同把它们彻底割裂开一样,到处造成危害。”[14]在我们这个时代,同样有一些“先知”式的诗人高喊“神性写作”,但此种“神性”话语往往只是来自血气的一己之念,准道德化的主张、宣言、口号,而非从启示而来的真理。这种真理迥异于从经验和理性而来不断变化的“知识”,这种真理人们会一次信服永远信服,这种真理的核心事实上就是在中国语境内名声并不大好的某种“教义”。
“教义”的意味往往使一些有宗教信仰倾向的人或教徒都会反感,“教义”是否只是一些与真理无涉、只与仪文有关的教条?艾略特说:“大多数人都以为某些人,由于他们欣赏基督教宗教情感的高级享受和基督教宗教仪式的激动人心,容忍或假装容忍不能令人置信的教义。对有些人来说,这个过程恰恰相反……”也是新批评和意象派诗的大家、诗人休姆(T.E.Hulme,1883-1917)就说:“我并不是为了宗教感情而勉强接受教义,而是为了教义在可能程度上忍受这种情感。”[15]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教义”才是根本,它比宗教情感和宗教仪式更重要更美好,是“神学”、“神性”的根源。不理解这一点,何谈“神学立场”、“神性写作”?
前面提及,当代汉语诗坛也有一些象施玮(北美)、姜庆乙、鲁西西、齐宏伟这样的诗人,他们并没有宣扬什么高言大志,只是尊重文学的自身特性,正视生命的沉沦境况与救赎之需,回归那个起初的“人”,挖掘人之“灵性”,敏于自我生命的问题、关注人的历史与命运,在真实、丰沛的生命感觉与诗意想象中书写“灵性文学”,“让人看见烦琐平淡生活中的美善之光,让人从自己扭曲、污损的生命中看见人里面‘神’的形象,看见人原初当有的尊严与荣美”[4]3。从这个角度,他们虽未高举“神性”大旗,在这个时代,却具备了真正的“神学立场”。他们的写作,尤为值得当代汉语诗坛关注。
[1]刘小枫.“文化”基督徒现象的社会学评注[G]//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215.
[2]刘光耀.中国文学的终结与终结的中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神学谈论[G]//基督教文化评论:5.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3]刘光耀.十四行诗[G]//许志伟.基督教思想评论:总第7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4]施玮.丛书总序[G]//施玮.琴与炉·诗歌卷.灵性文学丛书:第1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
[5]刘春.鲁西西:磐石与山寨[G]//刘春.朦胧诗以后:1986—2007中国诗坛地图.北京:昆仑出版社,2008: 162.
[6][英]艾略特.宗教和文学[G]//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
[7][美]韦勒克.西洋文学批评史:第5卷[M].章安祺,杨恒达,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255.
[8][英]艾略特.什么是经典作品?[G]//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衷,编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195.
[9]ELIOT.Religion and Literature[G]//Selected Prose of T.S.Eliot.London:Faber and Faber,1975:99.
[10]刘诚.文学应当为时代提供希望[J].第三极:第1卷(神性写作诗歌专号),陕西汉中,2007.
[11]世宾.完整性:担当即照亮[J].黄礼孩.诗歌与人:总第5期.广州,2007.
[12]十品(刘歌).山峰正在悄然崛起——从《第三极》创刊号看第三极文学运动诗学[J].第三极:第1卷(神性写作诗歌专号),陕西汉中,2007.
[13]蝼冢.神性写作的一般性阐释[J/OL].大诗刊(北寒带),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91128901000ahe.htm l。
[14]ELIOT.Selected Essays:Arnold and Pater.London:Faber&Feber,1932:404-403.
[15]ELIOT.关于人文主义重新考虑后的意见[G]//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208.
Christianity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Circle
RONG Guang-q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Since the 1990s,there have beenmany Christian poets or poetswho tend to believe in Christ,but their poetry writing was despised as religious poetry orminor poetry by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circle because of Chinese oversimplified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religion.With the seculariz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Chinese poets have been seeking for a variety of sacred writing.In different discourses on sacred writing,the voice of some Christian poets should be concerned and deserving ofmore attention.
Christian poet;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circle;religious poetry;minor poetry;sacred writing
I299
A
1009-1971(2012)04-0078-06
[责任编辑:郑红翠]
2011-12-15;
2012-03-26
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荣光启(1974—),男,安徽枞阳人,副教授,文学博士,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