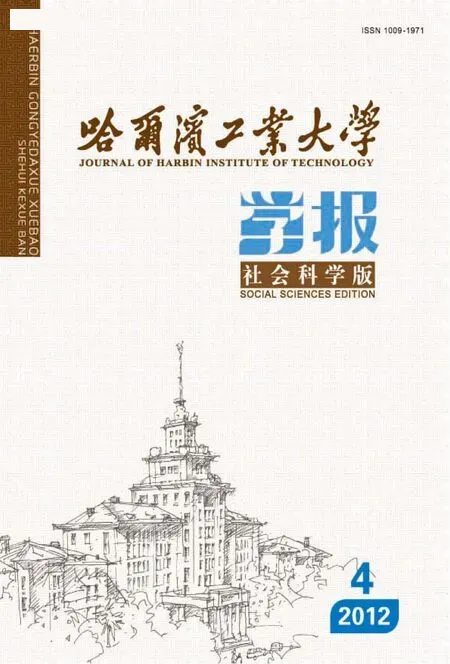中国国民性格重塑的政治哲学考察
2012-04-08教军章
教军章
(黑龙江大学a.政府管理学院;b.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哈尔滨150080)
·政治文明与法律发展·
中国国民性格重塑的政治哲学考察
教军章a,b
(黑龙江大学a.政府管理学院;b.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哈尔滨150080)
诠释中国近代国民性格批判的思想文化运动,对近现代乃至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深层意蕴,构成了公民文化建设和公共精神培育的一个历时性政治哲学反思的主题。从政治国民与文化国民的交互关联出发,强调了社会政治生活成为文化国民具体而直观的存在世界。政治国民不仅成为特定政治文化的价值表达,也是民族文化精神的践履者和承载者。型塑国民性格就必由广泛而生动的政治生活来完成,政治精神、政治制度等的整体融合担负着国民性格塑造社会路径。这一途径实际表现在制度观照和伦理观照的架构内,制度批判与重塑和伦理批判与重塑明示了社会政治发展的归旨在于塑造优良的国民性格,也确定了国民性格问题批判性研究的现代价值。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运动;国民性格;政治哲学;政治发展;政治责任;公民文化;公共精神
近代思想家无论从传统获取社会变革的资源抑或从西方文化拿来解题之方,都已意识到国民寻求自由、自觉、民主的启蒙是一种政治文化的智识求索和政治运动的伦理觉悟,因此,其本质就是政治变革中的国民性格批判与重塑过程。美国政治学家科迪维拉曾经指出:“懂得各民族的心理基础和总体性格的人握有制定政策的金钥匙。”[1]重新审思中国国民性格问题的核心价值,政治哲学维度的考量方式就表现为一种政治使命或责任的历史与现实对接,它隐喻着政治文化及其制度表达与国民性格之间的深层关联,也实际地厘定了政治运行的现实基础就在于重塑优良的国民(或公民)身份,以人的现代化或曰全面的“真正自由”为民族国家政治发展的归宿。因此,中国国民性格研究就不只是一种历史叙事,还应该是接续历史的现代政治文明建设与发展的价值回应。
一、政治发展中的传统国民性格批判
中国近代“国民性”(或“民族性”)一词主要来源于日本引介西方社会民族国家理论中“national character”(或national characteristic)一词的日文对译。这个专属概念是伴随着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思潮的勃兴而广为流传的,日本明治时期将其译为“国民性”,梁启超等维新思想家从中国政治改革的实际需要出发直接引入中国学术界[2],并在戊戌维新至五四时期形成中国思想史的一个核心的话题表述范畴。中外学者从各自不同的学术背景讨论国民性格问题,最终定位在一种整体批判的维度上,便提出了国民性格改造或重塑的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的现代化使命,人的现代化就成为政治发展的主题。
中国国民性格问题研究已经成为一个被时代超越的话语,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国民革命”浪潮掀起的关于中国社会各种势力政治斗争的实践赋予社会思想研究浓厚的政治意识韵味,民族文化建设也就成为政治运动的辅助资源。然而,人们并未停止对国民教育的求索,国民素质的培育仍然是政治革命的潜在主题。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仍然在思想界拥有较大影响,在其所进行的一系列演讲中仍然对国民素质建设多有论及。他认为,教育应该成为国民政治生活的教育,青年人对于政治生活必须养成“政治意识”,形成“政治习惯”,具备“判断政治能力”,并认为“养成习惯为最要而最难”的问题,这是国民必备的三项政治素质。在他看来,“政治不过团体生活所表现各种方式中之一种。所谓学政治生活,其实不外学团体生活。惟其如此,所以不必做实务的政治才能学会政治生活;惟其如此,所以在和政治无关的学校里头,很有余地施行政治生活的教育。”(《教育与政治》)他指出,教会国民学做“团体生活”是最为艰难的工作,“现代的团体,不是靠一两个人支持,是要靠全部团体员支持。质而言之,非用德谟克拉西方式组成的团体万万不能生存于现代;非充分了解德谟克拉西精神的人万万不会做现代的团体生活。因此,怎么样才能教会多数人做团体生活,便成了教育上最困难最切要的问题。”(《教育与政治》)这与其早年主张“合群”思想相联系而又增加了民主的内容。他还将国民政治视为国家政治生活走上正规的标志。“政治轨道,是要把政治建设在国民意识之上。想引他上轨道,除了市民群众运动没有别条路。”(《市民群众运动之意义及价值》)已日渐落伍的梁启超的言词绝非个案,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分途带动着近代中国喧嚣一时的国民性批判思潮激起了国人的政治兴趣,从一定意义上对于由五四运动产生的广泛社会影响所孕育的知识精英的政治性格转型,以及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新思潮在中国社会的迅速传播,均产生了积极作用。
关于政治生活特别是政治制度对人的能力发挥产生的深刻影响问题,一些学者有很精辟的论述。活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心理学家、政治哲学家芙丽特(玛丽·帕克·福莱特)经过长期社会实践研究发现,现代社会的阶级对立形成的“深沟大壑”已使人类孕育的巨大潜能造成无谓浪费。她指出,“代议制的民主制度不能弥合阶级差异的巨大鸿沟”,它未能使广大社会民众实现真正联合起来的巨大力量,“真正的民主必须依靠每一个人内在的创造力的发掘”,发挥了潜能的人才具备“真正的人”的意义;而“我们只能通过集体组织找到真正的人。个体的潜能除非在集体生活中释放出来,否则,就只能是潜能”;因此,“民主制度的精髓就在于创造,民主制度的技巧就在于集体的组织。”[3]这样,她提出了一种建设性社会矛盾的解决方法——完美的“融合统一”的方法。政治民主化发展必然依赖于人的现代化发展,这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就体现为政治变革运动与国民性格改造之间互融互进的历史过程。为了掀起政治改革的伟大民族救亡运动,知识精英逐渐体悟到人的基础性地位与作用,以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说为理论指导,以西方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思想主张为逻辑工具,国民性格批判就持续地融入到中国近代社会政治革新运动的每一个历史阶段。作为寻求组织化的“真正的人”的价值存在所标志的就是政治现代化发展的核心命题。
现代化是发展理论中较难把握的一个范畴,虽然现代化理论家几乎都将其视为与“传统”相对待的范畴,但若想准确概括其本质并非易事,况且当现代化理论家忙于构建或重建体系时,所谓“后现代”又以大肆批判的态势出现在世界理论舞台。①有关现代化问题的理论研究成果,可参阅谢立中、孙立平《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不过,不管理论争论的结果如何,作为一种人类对自身存在状态的积极性价值诉求的表达方式,它需要表现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现代化无疑是最主要方面之一。政治发展首先就是政治系统面对生存环境中寻求适应与选择程度的历史进程,而政治系统的适应与选择必然是组织化的政治主体的实际行为——意识行为和潜意识或无意识行为。在理论研究中,很多系统理论家都关注到这一问题,如著名社会结构系统学家帕森斯指出:“任何普通的系统,一方面都可以为了方便的目的而描述成一种结构、一组带有稳定特征的单位或成分的集合,这些特征当然是理性的;另一方面,也可以描述成‘发生了某事’以改变某些特征和某些关系之过程中的一组事件,一组进程。”[4]因此,政治主体的理性进步在政治发展实践中就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成为政治结构的稳定与变动程度的决定力量,同时也是作为政治进程描述者以揭示政治变革关系进而确定政治革新方向的决定性力量。但是,正如由个体构成的社会整体总是反而约束着个体行为方向一样,只是宏观地认定国民对民族国家政治发展的决定作用显然意义有限,或者说这与社会有机体说的观点并无本质区别;我们意欲解释的正是问题的另一层面,即如何在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寻求政治主体的价值定位,或者说,政治生活变革给予国民性格型模的影响又将怎样推动政治本身的进一步革新,亦即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探寻“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鲁迅:《“立此存照”(三)》)。
传统国民性格批判是在批判旧有的延续数千年历史的专制政治制度基础上展开的,对于传统国民性格之生成根源的制度分析引导国人的这种政治觉醒,对国民生活的无知无欲、一盘散沙而又安于命运的悲剧状态的观察体验使其直接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吃人”的礼教,呼吁社会变革特别是通过文化革命指涉政治革命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成为国民政治性格改造与重塑的内在主线。在这一议论归旨的约束下,文化背景的比较分析显然不仅是限于文化性质长短优劣的结论选择,而关涉中西政治民主与专制体制的根本性差异;国民性格表现的种种根性归原在传统文化、道德伦理、地理环境等层面引申的也还是最具可视性的政治生活状态彰显的强大驱动张力,是政治性格成为一种文化性格的凝练性表现;于是,国民性格改造的价值取向也就只能是西方政治民主社会崇尚的自由、平等、权利等的个体本位的确立,并在中国特定背景下对其进行的民族意识的培育以获得群体与个体紧张关系的政治文化消解。这样,关于中国国民性格问题的理论创建就实际地渗嵌于中国近代政治变革乃至革命的基本环节中,它意味着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激活群众和塑造群众成为必要的政治艺技,而且这种政策艺技运用的程度将决定政治主张的命运,也便成为衡量政治势力之先进或落后、进步或反动的主要标签。
如上繁述想说明的就是国民性格研究的政治哲学意蕴。第一,特定的政治文化铸就了特定的政治国民,特定的政治国民表达了特定政治文化精神。这意味着民族国家生成的过程就是政治国民被型塑的过程。政治国民与文化国民相比尽管传承的民族文化道统血脉的成分并非总是持续的一致性,即政治主张在不同环境中会显示出某种文化精神的背离趋向亦即政治对文化的反动性,诚如罗素在观察到俄国人的生活境遇后不无感慨地指出:“理论家完全有可能增加许多人的痛苦,因为他们强迫人们采取那些违背他们原始本能的行动,但我认为靠传播工业主义和强迫劳动的福音是不会给人们带来幸福的。”他还极其义愤地说道:“我终于开始领悟到所有的政治都是由咧嘴而笑的恶魔造成的,他教唆那些精力旺盛、头脑灵活的人去折磨那些逆来顺受的广大民众,以夺走他们兜中的钱财、手中的权力和脑中的思想。”[5]虽然这种认识不免有失偏颇,确也反映出政治活动与人类的文化活动之间存在着事实与价值的深层矛盾。因此,作为社会政治文化陶铸的政治国民在更直观的平面上显示着政治文化的印痕,承受着政治生活的福祉或痛苦。正如有人言:“错误政治的代价通常要求立即偿付:人的苦难。苦难有多种形式,但都可以追溯至同一个源头。这些苦难都有自我持存性。它们源于政治的不当,也是政治清明的最主要障碍。”[6]导言政治的不当选择就是政治文化精神的导引作用。
第二,政治变革与发展的文化精神通过政治国民的具体行为加以体现,激活国民政治情怀便成为政治进步不可回避的客观选择路径。近代国民性批判矛头指向封建专制制度对个体政治自由愿望的粗暴压抑,充满情感激愤的话语表述体现了民族革命时代的急于启蒙的特色需求,而深层关怀的是政治革新的现实落位,这就是政治发展必然植于广泛的社会民众的实际行为中,政治精英的作用在于引领方向,国民的活动则成为政治革新文化最具意义的实施过程。尽管近代思想家更多的言语在于批判国民性格的弱点——这多少助长了社会的悲观情绪,然而其核心主旨并不在于宣告传统政治国民的无望,而恰恰在于注入一种激励,寄望于民众获得群体主义的广泛觉醒以担负起民族危亡拯救的使命。所以,有人通过研究近代中国“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生态状况得出结论:虽然近代中国并不存在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相对于西方的观念,中国并没有产生那种‘朴素个人主义’的本土的自觉思想”,“中国本土也没有有关个人权利的词汇”,但是“无论是在上层知识传统还是在较为普世的大众话语中,都展开了具有广泛基础的对传统观念的重新评估”[7],这种情形对于促长市民社会的生成起到积极作用;而市民社会又直指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产生,有知识精英促使广大公众政治能力的提升,就是为了追求“他们能在被来自下层的广泛讨论和理性论争赋予合法性的政治制度基础上,实行自我管理”的理想目标[8]。所以,关注政治国民的具体而复杂的政治生活理念及其政治活动表现,也便是现代政治发展理应确立的政治路线准则。
第三,政治生活必须解决公民共同体的行动趋向问题,而公民性格的养成为共同体行动逻辑困境的破解提供了基础条件。公民共同体集体行动的困境始终是社会理论与实践的常态。尽管公共选择理论家面对这一非市场化问题给出了一些答案,试图从经济人假设找到突破集体行动困难的内在因素,但是共同体的利益却并非能够真正解决集体行动逻辑的悖论,这为政治生活中的公民共同体行动的价值取向选择留下了更广阔的空间。既然仅仅依赖市场规则难以圆满解释公共行动的逻辑矛盾,那么通过政治生活培育公民共同体的价值体系,使公民性格的养成达到某种趋同性,或许就为破解集体行动的逻辑困境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条件。因为,“公民性有着非同寻常的延续力”[9]183,公民性格承载着公共精神的历史传播使命,它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本”而促使“合作性共同体”引导“理性的个人能够超越集体行动的悖论”[9]195。帕特南等人经过20余年对意大利地区治理结构的制度化改革研究发现,“自由制度的成败取决于公民的性格,或曰他们的‘公民品质’”;“诚实、信任和守法是最重要的公民美德”[9]127;公民性的强弱直接影响着共同体合作行动的程度,即“公民性较弱的地区的国民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解决霍布斯式的公共秩序困境”,而“在公民性强的地区,权力不大的政府却非常有力,因为它可以依靠国民更加主动的合作与法律和契约的自我实施”[9]130。所以,政府的政治行为和政策导向需要关注公民性格养成的理性路径安排,在自觉和自由的制度绩效获取中,依赖公民诚信守法的秩序过程逐步完成共同体内外竞争合作行动的实现,从而使政府公共制度绩效的取得所付公共成本降低到令人满意的水平。
二、国民性格塑造的政治发展途径
从国民性格问题研究的理论成就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制度与伦理在国民性格塑造过程中的重要功能。这是受到近代思想家国民性批判理论特别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对传统专制制度的无情批判和致力于广泛的道德舆论宣传便是这种努力的表现。杜威在评论人们讨论的经济制度是否对于人性的实现需要产生某种改变或者说“现在的制度或其某些方面是违反人性的”观点时指出:“事实上,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是属于人性的表现方式之最易改变者。历史便是这些改变的活生生的证据”[10]161,比如“在世界史上的某时某地,存在着差不多一切可想象的各种社会制度的这一事实,即是人性可塑性的证明。”[10]163他认为,人性中只有那些与生俱来的基本“需要”可能不可改变,其他的性质则是可以改变的,人类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生活的转型都是表达人性可变的充分说明,而其中的立场也是公民教育得以自古及今受到重视的一个主要理由。社会心理学家弗罗姆也明确肯定制度对个性塑造的意义:“当人出世后,他的活动舞台就已被准备好了。……必须以他出生在的那个社会的种类而决定工作方式。他作为一个个体,原则上是不能改变他的生存需要和社会制度这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是其他那些显示出更大可塑性品质的决定力量。”因而,“对于个人来说,由经济制度所决定的生活方式成为决定他整个个性结构的基本因素;因为自我保存的迫切需要迫使他接受他必须生活于其中的环境。当然,这并意味着他不能联合其他人去试图影响某种经济和社会变革,但他的个性首先由特殊的生活方式所铸成,因为在他童年时就已经通过家庭环境面临这种生活方式,而家庭则表现了某一特定社会或阶级类型的全部特征,并是它的缩影。”[11]许多文化(心理)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米德等)对于社会制度或社会结构方式——包括道德规范体系——的优先存续对于个体生活方式等产生的深刻影响,也都从不同侧面给予了应有的关注[12]5。
人们肯定制度的本质是“表示非个人关系的一种手段”,是一种规约社会主体行为关系的普遍社会现象[13];它是“规范化、定型化了的”社会行为关系及其结构体系的总括。所以,从一般意义上可以将制度理解为普遍的约束工具或准则体系以及制定约束与准则的活动[14]。一方面,它指具有规范作用的一系列有机的规则系统。它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准则体系和社会群体、行业、部门根据其具体情况制定的要求、程序和行为准则。按照新制度经济学派学者道格拉斯·C.诺思的看法,可以将制度定位为“为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行为准则。在政治或经济制度方面,财富或效用的最大化要利用交易带来的增益是专门化(包括暴力行为的专门化)的结果。”[15]另一方面,它是指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制定、完善并执行准则、规章的活动即制度创生和制度实施的过程,它是创生规则并使之普遍化和社会化的活动过程。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康芒斯就认为,制度是指约束社会个体行为的集体行动运行规则,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16]87,亦即“集体行动抑制、解放和扩张个体行动”[16]92;罗尔斯也认为制度是“一种公开的规范体系,这一体系确定职务和地位及它们的权利、义务、权力、豁免等等”,亦即形成的规范体系在于约束人们的权利义务等关系并规范人类社会行为以便形成相应的社会秩序[17]54。所以,自人类文明以来,制度一直成为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主导工具或基本表现形式,尽管政治自由主义者对其进行了多项罪责的指控。制度学派并非制度绝对主义者,他们同样看到制度作为社会“底线伦理”的功能局限,因而对道德伦理价值赋予了社会发展特别是人性解放的更深层意义,于是就出现了所谓“制度伦理”的新命题。从约束和规范的本质内涵上看,伦理与制度显然具有共通性。它们都是关于在相应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及其行为关系的合理性原则(精神)及其实现的问题。伦理的意义就是面对社会生活的基本状况——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赋予一个关于“合理程度”的价值评判,从而为人类追问公正、至善或完美的终极关怀至少提供一次又一次的理性慰藉和继续追求的动力,正是这种带有某种本能性的评判和再评判,进而在现实生活实践中进行约束和规范化的社会性安排以唤醒并引导社会主体的良知和情感趋向,使现存的主要依赖外在强制力发挥作用的约束和规范转型为内在的自觉德性约束和规范,即旧有的所谓“底线伦理”界域被冲破而升华为更高层次的表达“善”的形态,才会有社会发展的持续的文化精神存在。尽管伦理和制度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担当的社会角色有所差别,但是社会系统本质性的不可分割特点还是给予二者足够的交融机会或空间,尤其是当社会发展进入一种现实的纷扰而造成理解困境时,对基本社会结构和生活状态的意义和价值的“正当”追问就成为必然,而这种追问也就不可避免地指向了制度与伦理约束下的社会公民的共同体行为问题。这样,对民族国家构成主体特性生成途径的制度过程与伦理过程解答实际上也就是由社会文明本身的结构性特征所要求和决定的。
近代思想家在批判传统国民性格的话语体系中无疑对制度和伦理的型塑功能形成了初步的理性认识。戊戌思想家重点强调政治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在极力鼓吹学习西方政治民主体制——主要是君主立宪政制——的过程中,从个性自由、人权平等原则出发提倡“求乐免苦”、“背苦趋乐”的人性论,主张“利群”、“大我”为主题的伦理观,掀起了近代中国“道德革命”浪潮。辛亥思想家更为集中的传统专制制度批判以及实践中“武器的批判”铸成的社会制度的全面革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基本维度上颠覆着国民奴隶根性的制度基础,使制度批判达到了近代历史的高峰;同时他们仍旧继承了前代思想家伦理批判的武器,在利己主义伦理观的提倡上进行了多方面延展,为树立西方资产阶级伦理观作出了应有贡献。五四思想家本着激进文化革命立场对传统制度与伦理进行了全面清算,他们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从中西文化比较的宽阔视野定义传统专制制度的“吃人”本质,揭示出专制制度作为塑造国民奴隶性格的根源,宣传“破坏偶像”权威以成就个人独立自由之人格;同时又从理性批判精神出发深刻审视中国近代社会环境的特点,明确提出了自利利他、“健全的个人主义”伦理观,主张国民个体改造与社会整体改造双轨并进的社会进化逻辑。这些都表明,近代中国国民性格改造已经实际地在制度观照和伦理观照的框架内进行尝试,国民性格的制度批判与构建和伦理批判与构建在某种程度上是同时展开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由于人们认识问题的侧重差异而显示出各自行动的主线不同而已:戊戌时期制度批判与重建成为社会的主导型任务,而五四时期以“伦理的觉悟”为“道德革命”内涵构成国民性格批判与改造的核心主题。
制度和伦理作为制约人们行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复杂矛盾的社会承认并遵守的准则,体现出的约束力量具有社会普适性的旨向。任何社会的国民性格塑造显然离不开制度的强制他律与伦理的内省自律作用,作为国民性格塑造的基本途径,对制度与伦理价值的深层反思,就成为我们批判继承近代传统以进一步构思人的现代化问题的重要遗产。事实上,社会制度与社会伦理从来就不是截然分离的问题,制度伦理的综合考量基本上可以表述为“制度的伦理——对制度的正当、合理与否的伦理评价和制度中的伦理——制度本身内蕴着一定的伦理追求、道德原则和价值判断。”[18]也就是说制度伦理是站在制度与伦理有机统一的维度寻求二者之间的互补性优势,期待制度和伦理在社会生活变迁中发挥反映人性价值最充分的约束与指导功能,以实现二者现实性的统一:一方面是对制度合理性的伦理追问——关于制度的“善”的评价问题,另一方面是对伦理精神的制度性转化的现实安排——关于制度体系的伦理化设计问题。这样,制度伦理就具有了制度伦理化与伦理制度化的双重特征,并且制度伦理化与伦理制度化也成为制度人与伦理人相统一而成就公民性格实现的基本途径。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情形看,无论是制度还是伦理既是人之为人的社会化整合工具,也是人之进步程度的衡量尺度,制度从专制到民主的的演进与伦理从限制到自由的跃升是一个共同反映人性解放程度的过程,制度在伦理化过程中体现着人的自觉性增强——伦理精神的渗透预示着人越加具备了对制度强制的自觉认同而使制度功能实现自然化(自组织化、自律化),伦理在制度化过程中凸显着人的秩序意识的强化——制度方式的普及涵蕴着人更加关注伦理自省的规约导向而使伦理功能实现社会化(组织化、他律化),即康芒斯所谓已经是具有“制度化的头脑”的人[16]92。于是,在制度与伦理的双重约束下,国民性格在获取二者共同备有的社会公共资源的蓄养中逐渐生成环境适应与主体选择的“融合统一”的整合模式。
伦理对社会制度人格的作用在于诉求制度的合道德性本质,从而规范制度人格的伦理框架结构及其运作效能机制中所导引出的道德精神,即把伦理道德作为一种价值尺度和标准体系对制度人格做出合人性评判,以界定并裁别制度体系的人格特征。它将涵盖首先对制度来源的合理性追问。这种合理性追问既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关于包括元制度在内的道德形上学的一般考察和求证,从而形成制度创生过程及其型态的道德评判,为制度人格产生的合理性渊源提供必要的伦理依据;同时,它又具有方法论的阐释学意义,即这种道德追问本身建立在对既定制度存在的反思基础上,通过对制度人格发生过程和转型过程的理性认识和效度的综合评估,达到对现存制度及其结构的伦理性确证。“从逻辑上看,规范系统的建构总是以价值的确认为前提:人们首先是根据价值形态来规定行为的规范和评价的准则。”[19]而价值——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又首先是关于人类行为“善”、“应当”或“好”等的政治道德哲学概括。其次是制度人格本身蕴涵着的伦理价值追求——道德理想。制度本身的道德性是由制度内在的基本结构确认的,并通过现实的社会结构关系和相应的政策、法律法规、条例等成文的或传统、积习等不成文的规范体现出来。这就是说特定社会制度道德上的合法性,主要不是通过制度下个体道德体系显示出来并得以确证,而是通过制度自身价值的道德性显示出来,是通过不同制度的道德理性比较而加以求证的。再次是制度结构即经济、政治、法律等制度中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制度蕴涵着相应的道德伦理精神,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制度的安排必然以人的道德性原则为前提和基础,这便是制度人格体现的伦理性资源。罗尔斯强调“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也就明确了“正义”作为首要的伦理资源在建构社会制度时所处的前提和基础地位的重要性[17]1。因此,如果说个人负有支持制度的义务,那么制度必须首先是正义或接近正义的,制度人格就应该是正义的化身。又次是制度人格作用机制的伦理评价——制度人效能的现实合理性。这种评价一方面成为检验制度基本结构及其表现形态构建的合伦理性程度的最为重要的标准体系,从而为制度的总体评价提供依据;同时,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制度安排的伦理性评价来检验制度及其具体化设计本身对制度作用对象的规范与导引的效度,从而为制度的道德性调整与变革提供现实依据。最后是制度人格的总体性伦理评价。一般而言,这应该是建立在上述四种评价基础上的一种根本性道德追问,是对制度性质的道德理性评判,是关于制度的“善”、“正当”或“好”的程度的抽象概括。比较而言,政治哲学的制度伦理本质追问更具现实化,所以人们认定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20]。
从内在旨趣看,伦理制度化首先是一个制度普遍社会化问题,是一种制度功能普适性扩张过程,亦即制度对伦理人格的普遍规约问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伦理的制度化实践可谓由来已久,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尤其是政治制度的发展过程实际地充斥着丰富的伦理内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在儒家伦理精神的统摄下构建成完整的体系,其中不乏诸多的家庭伦理、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等方面的内容。亚里斯多德在设计古希腊城邦政治制度时明确指出,“法律的实际意义却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进于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这样它才会获得“无上的权威”[21]138。因此,从制度本身来理解,伦理人格的制度化走向实际上是使制度获得更广泛社会化意义的过程,是制度由于伦理精神的融入获得社会理性认同的过程。其次,伦理人格的制度化还是一个伦理功能社会化的过程。制度的要求是最基本的因此也是最基础的,而伦理的要求则是较高层次的,它往往意味着一种理想的追求和理性发展的方向,其价值的实现主要依赖较高的个体自觉和相应的社会舆论的引导,实际上是人的一种“应然”状态的要求。将富于伦理原则和精神的约束或规范制度化,既表明社会进步的程度达到了一定层次的伦理人格要求,也说明伦理人格的功能随着环境变化越发彰显其社会价值。
从国民性格塑造的学理角度看,对社会政治制度问题进行伦理性追问是自古以来思想家们一直注意的问题。中国古代有“道德仁义,非礼不成”,(《礼记·曲礼》)“学至乎礼而至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荀子·劝学》)其中的“礼”不完全等同于“制度”,但它无疑具有制度的某些含义。西方古典政治学家或伦理哲学家关于社会公平、正义和善的理性思考同样涉及政治伦理和制度伦理的内容,如亚里斯多德指出,“政治学的善就是正义”,它“以公共利益为依归”[21]148,“公正就是幸福的给予和维护,是政治共同体的组成部分”[22]。黑格尔则通过“伦理实体”理念更明确地阐释了体现内在的、抽象的、必然的“善”的“具体的实体”就是现实的制度的思想,他认为:抽象的善总要表达为“无限形式的主观性而成为具体的实体”,“具体的实体因而在自己内部设定了差别……伦理就有了固定的内容。这种内容是自为地必然的,并且超出主观意见和偏好而存在的。这些差别就是自在自为地存在的规章制度。”[23]164(144节)这些思想都从不同层面揭示了政治、制度与伦理的内在关联性,表明了制度伦理对人的性格塑造的悠久传承性。在具体的国民性格塑造路线选择上,不同的制度类型和伦理价值取向体现出不尽相同的特色。中国传统社会历史和思想传统具备比较丰富的制度伦理资源——儒家伦理精神的制度化和制度化的儒家伦理的互动互融的安排与设计[24],其“内圣外王”的政治伦理理想始终是以“修身”为逻辑起点,以个体伦理人格的完善为政治道德运作方式,导致长期以来侧重对个人道德研究、忽视对制度人格深入研究的历史缺失。罗尔斯指出,社会个人职责确定依赖于制度,首先是由于制度有了伦理的内涵,个人才能具有道德的行为。“一个人的职责和义务预先假定了一种对制度的道德观,因此,在对个人的要求能够提出之前,必须确定正义制度的内容。这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有关职责和义务的原则应当在对于社会基本结构的原则确定之后再确定。”[17]105这说明,制度和体制的道德性对个体人格具有客观约束力。
孙隆基指出,文化结构除了显示出本身的关联性外,还具有“结构”人的功能,即中国文化结构意味着本身的关联性状态,也还意味着“这个‘结构’于中国人之‘身’被结构的方式,亦即是其‘人’被设计成的样子”,这就是说,文化的结构功能带有社会化基础上的制度化指向,而社会化的过程本身也涵寓着伦理道德普适化的程度,它构成文化人身上“非结构化”自觉的因素,因此,对于社会中具体“人”身上的文化印痕的“非结构化”解读就“不只是纯智力的批判那么简单,而是牵涉到整个人的自觉重组的问题。”[25]这样,近代思想家关注的“独”与“群”或者个人自由与社会整体自由关系问题也就具有了制度伦理的双重意涵,它强调的个体自由是民主的自由、“合群之独立”的自由,便是在公共制度规约下的个人伦理自由,即“伦理是自由的理念”,是“成为现实世界和自我意识本性的那种自由的概念”[23]164(142节)。这符合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立场,他们意识到的个体对社会秩序基础的首要依赖性——社会文化或民族文化的预先既成性存在对个体选择的先在性,即个体性格生成的初始基因或“文化密码”具有先在性。这样理解的意义在于强调伦理过程和制度过程对国民性格建设的特殊重要作用。
三、政治责任的现实归宿:重塑优良的国民性格
现代政治与政府管理的目标可以高度概括为追求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人的现代化发展无疑是最为核心的部分。政治发展目标的设计总是战略性与策略性的和谐统一,它不仅表现为一种理性认识及其实际抉择的过程,而且是政治发展实现途径的可行性目标安排,即“操作性目标是正式目标的具体内容,反映的是不同价值观的选择。它们可能根据某个正式目标而设定,也可能会推翻另一个正式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是实现正式目标的工具。”[26]操作目标主要解决政治发展总目标如何实现以及实现程度的问题,因此,人们在描述宏观发展目标时经常将其概括为:“(1)增强组织结构、过程、战略、人员和文化之间的相合性;(2)制定新的、有创造力的解决方案;(3)培养组织自我更新的能力。”[27]在政治管理中,人是当然的政治责任主体,政治责任或使命的基本归向就必须以政治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主线,亦即追求“真正的人”的价值目标的根本实现。
全球性的政治制度革命是在近代民族政治意识逐步生成的基础上产生的持续性政治运动,强有力的“民族国家表述”已经成为其最主要的成就。政治文明从开始便聚寓着政治主体的民族(或者种族、族群)特征的某些意蕴,只是这种政治责任的指向不如民族国家时代明确而已。近代中国同样也是一个中华民族国家意识最终凝结的时代,思想家关于国民性格批判的理论阐释一直与政治制度批判相表里,其意旨便是在论证国民对于国家而言极端重要性的基础上反衬着国家政治使命的核心就是实现人人平等自由的民主权利,追求的也就是政治国民优良性格的整体性塑造问题。力图在民族主义旗帜下使民族国家的主题表述囊括共同体内所有文化背景的个体认同还只是一种抱着良好愿望的政治和文化理想,“即使在现代,民族国家尚不能竭尽个人认同,更未能把民族的意义限制在自己的表述中。现代民族国家必须面对其他(包括历史的)共同体的表述,甚至与之交锋。当我们考虑到民族认同的含混性、变换性与可替代性以及与其他的认同互动时,便不难认识到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民族国家,就能在多大程度上颠覆民族国家。”[28]导论:7-8因此,将国家政治的根本责任赋予重建优良国民性格的基本表述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哲学意义上的理性构想或整体设计,这种构思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与人的彻底政治解放相关联必将成为民族国家政治发展的指导纲要:健康、理性、尊贵而又充满激情、活力的人,富有价值、理想、精神追求而又承载责任、使命意识的人,既有个性自觉、自由人生理念而又具备群体、公共生活品德的人,即从私域空间到公共领域,政治国民完成了从个体自觉到社会觉悟的完整过程,成为体现人类根本政治精神的行为主体。弗朗索瓦·佩鲁(Francios Perroux)曾从社会发展与政治发展的根本方向上对政治学研究进行过评价,他指出,“政治学不可被取代的对象是研究社会生活中人们的命运问题,而社会实质上是一个等级组织。”[29]173这与政治哲学研究的归旨形成现实的矛盾性。因此,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工作者“必须牢牢记住,个人的发展、个人的自由,是所有发展形式的主要动力之一。这种个人的发展和自由能够在每个人所赞成的和在其各种活动中所感受到的各种价值范围内充分地实现他们的潜力。”[29]175这里的核心基点就是让人们明确:社会组织发展真正的核心问题是人的问题,人的进步成为社会或组织发展的最终标志。自然性的人要受到情感和利益的驱使,具有把“自我”放置中心的倾向而漠视了组织整体的意义;社会性的人意味着人在社会化进程中对“他人”注意的一种个体超越,亦即人以个体的社会“角色”的结构关系来确定其道德价值取向,“人是多种多样的个体”,而这种认识本身是在“统一的关系模式中”获得的,即人不是被拆分的而是一种“结构上的需求”,“个人因为他们行为的不同的道德趋向而不同,反过来,道德将个人与他人相区分,这不是要妨碍社群生活,而是要为社群生活提供准则。”[30]所以,人的社会性(关系)就主要通过“组织”的形式加以体现——政治组织显然处于首要位置。当这种认识成为人的社会生活的基本理念并渗透到伦理精神内核而持久地支配着人类的存在方式,社会化、组织化和政治化的进程就将是解读善之真义的历史过程,政治组织的变革与发展就更多在理性的导航下沿着人的整体性进步方向迈进,因此,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构成了社会变革与发展的核心主题。①应该指出,哲学研究中很久以来就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或“人类主体论”的批判,如海德格尔、大卫·格里芬等。相应地,人们提出了生物中心、自然中心、人—自然中心、互为主体乃至无主体、无中心等论点。在这场争论中,人们主要关注的显然是一种生态学的逻辑视角,以“问题”的解决为逻辑归宿,其中的一些观点值得思考;但是在管理学研究中,如果放弃人的主体(中心)地位,就失却了“管理”的真实意义。所以,即使我们不是单纯的人类中心论者,也需要承认管理的核心是人的问题。有关争论的描述,参见陈昌曙《哲学视野中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96-121页。
当然,人们更认识到政治归宿与现实政治生活之间的严重背离倾向,这一方面进一步强化了我们对政治变革与发展崇高目标努力的信念,另一方面留给我们的艰巨任务则是对现存政治制度改革趋向的批判性选择,这种抉择实际上面向所有被认定的所谓善的制度和恶的制度展开,也便标识着社会发展始终是一个不间断的历史过程论断的真实性。对于封建专制制度造成的“非人性化”的批判自不待言,而西方民主制度带来的种种危及人的生存境遇的批判给予人类情感与理性的打击确也潜藏着自信力颠覆的因子。人们认识到政治民主体制划定的“私域”与“公共”同样造成“不自由便成为了压迫”的普遍状况,即“在每一项日常行为中,都有不自由这一重要的强制性因素”存在[6]69-70,当人们普遍觉悟到“压迫”的非人性本质,失望伴随着痛苦将成为社会的性格,也便成为影响政治更新的重要力量。面对这种生存悖论的困扰,国民时刻在进行着各种各样形式的抗争,这些政治行为形成对政治本身所应负责任或使命的合法性拷问,它锤炼着国民并在生动的实践中为政治国民性格重塑提供舞台。人们似乎已经认识到:“如果‘人民’只能在街上从事大众化的政治活动的话,是不能成为新秩序合法化的源泉的。要成为权威的资源,他们必须先从一个更高的‘非人格化’的机制那里获得权威;这个机制就是成文宪法。人民必须经过创造而成为人民(Warner,1990)。”[28]19尽管这种观点可能依据宪政理论意在否认群众革命的合理性,但是它所肯定的人民必须通过政治活动获得成为“人民”的身份与地位,也便蕴涵着国民政治性格塑造的意义。如果我们进一步深究其内在旨趣,我们也许会对文化人类学家的见解感到钦佩,像本尼迪克特所言:“实际上,社会和个体二者不是对抗的东西。个体所属的文化提供了构成他生活的原始材料”,如若离开“传统”我们将无法理解二者之间复杂的关系,所以“要想认识其中的潜在的东西,就要依靠科学方法论的发展,而且除非这种文化已经精心炮制了那些必要的概念和手段,不然也还会一无所获。”[12]231-232她接着说道:“一旦社会和个体之间的这种基本对立扩展成了一种基本的哲学的和政治的概念,这种基本对立的基础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了。社会只是偶然地在某些条件下才是有条理的,而且法律并不等于就是社会秩序。在那些同类的比较简单的文化里,集体的习惯或习俗就够了,完全没有必要去发展什么形式上的法律权威。”[12]232总之,作为人类生活共同体发展进步的形式——政治制度或体制的不同模式——所规划的主体特征,代表着人在其中获得的自由发展的全面程度的不同,这一结果被赋予政治制度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评价尺度,也便意味着政治本身通过变革来型塑国民性格基本方向及程度的诸种可能性。
对于中国而言,近代思想家开启的国民性格改造思潮已经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等多层面向我们拓展了新型国民性格塑造的理性尝试,不同的文化政治立场表述了进向完全不同的国民性格设计准则。大体说来,有人将其分为三种类型:“本土运动”、“综摄运动”和“创新运动”。本土运动“振兴的方向是以恢复或保持自己原有文化为目标”;综摄运动“不是要恢复或保持过去固有的文化,而是将自己原有的文化,再加上外来新文化混合在一起”;创新运动则是不仅要“恢复保持过去,也不仅是接受外来的东西,而且要创出新的观念和适用于新的环境、新的变迁”[31]。鼓吹全盘西化的陈序经也对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立场进行了“复古主张的观察”、“折衷办法的派别”和“全盘西化的理由”三个基本方面的描述,并充分肯定选择西化—现代化道路的依据[32]。而张岱年先生进一步作了细致分别,将16世纪以来中国文化论争区分为“会通以求超胜”、“中体西用”、“西学中源”、“中西调和”、“东方文化”、“全盘西化”、“中国本位文化”、“儒学复兴”、“西体中用”等多种派别[33]。这些派别总体区分为西化派、本位派和中西调和派,他们分别表达了对传统政治文化熏染下国民性格的价值判断,明示或隐喻着政治国民性格塑造的基本走向。我们应该给予近代思想家以足够学术尊重的就是他们执著追问的这种精神,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全盘西化、文化本位以及简单的调和立场都难以将中国带入本土现代化的道路;历史发展还将进一步证明,任何放弃民族传统的民族也都难以实现真正的现代化。所以,从近代国民性问题研究的成就与缺失给我们的启示看,所有的民族文化立场都可以视为一种民族政治立场,文化国民、道德国民都将通过政治国民的身份认证来表达民族国家的情感和理性抱负,而政治责任的归宿也只能就是围绕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线索展开所谓现代化的国民性格重塑,这一使命也将决定着政治现代化本身的基本行程。正如杜赞奇所言:“同样,在中国和印度那样的新民族国家,知识分子与国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工程之一,过去是、现在依然是重新塑造‘人民’。人民的教育学不仅是民族国家教育系统的任务,也是知识分子的任务。……民族以人民的名义兴起,而授权民族的人民却必须经过重新塑造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人民的塑造与再塑造是时间问题在政治上的表达:历史的形而上学等同于同一体的进化。”[28]19
中国国民性格问题是思想史中的一个胶着性问题,因而也成为中国政治文化变迁中具有强烈惯掷力的思想因子,在此后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阶段,文化的、民族的、社会的、政治的、伦理的拷问几乎不曾间断过,成为或显或潜的时代言说主题。尽管后现代乃至后殖民批评理论家对其合法性进行了过多质疑,然而历史的价值可以重估却难以真正达到改写“真实历史”的目的。在政治发展的视野中重新审思国民性格批判的理论成就,给我们以巨大的激励可能就是:政治文明进步如何依赖觉醒中的国民优良性格的生成程度,思想史的价值归向如何在政治责任的落位中表达时代政治精神,进而完成历史使命与政治责任现实切换的艰巨任务。
[1][美]科迪维拉.国家的性格[M].彭强,黄晓京,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中译本前言.
[2]刘禾.国民性理论质疑[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68.
[3][英]格雷汉姆.玛丽·帕克·芙丽特——管理学的先知[M].向桢,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10.
[4][美]帕森斯.关于变迁的功能理论[G]//谢立中,孙立平.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87.
[5][英]罗素.中国问题[M].秦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9.
[6][英]鲍曼.寻找政治[M].洪涛,周顺,郭台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7][美]罗威廉.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G]//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85-186.
[8]赵文词.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和道德共同体[G]//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27.
[9][美]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M].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10][美]杜威.人的问题[M].傅统先,邱椿,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11][美]弗罗姆.对自由的恐惧[M].许合平,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11-12.
[12][美]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王炜,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13][美]汤因比.历史研究:上[M].曹未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59.
[14]龚天平.论制度伦理的内涵及其意义[J].宁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3).
[15][美]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M].厉以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95-196.
[16][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M].于树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7][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18]方军.制度伦理与制度创新[J].中国社会科学,1997,(3).
[19]杨国荣.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77.
[2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
[2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亚里斯多德选集·伦理学卷[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5.
[23][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杨,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24]干春松.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57-109.
[25][美]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一版序.
[26][美]霍尔.组织:结构、过程及结果(第8版)[M].张友星,等,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270.
[27][美]尚普.组织行为学——基本原则(第2版)[M].宋巍巍,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347.
[28][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M].王宪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9][法]佩鲁.新发展观[M].张宁,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30][法]麦克林.传统与超越[M].干春松,杨凤岗,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43.
[31]韦政通.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3.
[32]陈序经.东西文化观[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3]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论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Political Research on Reshaping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JIAO Jun-zhanga,b
(a.School of Governmental Administration;b.Research Cen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 150080,China)
To interpret the profound significance that thinking culturalmovement of criticism in Chinese modern national character has on the social revolution in China in ourmodern contemporary time,whichmakes up a diachronic subjectof political&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in the civil culture construction and public spiritual cultivation.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correlations of political citizen and cultural citizen,and emphasizes that social political life becomes the concrete and direct existing world of cultural citizen.Political citizen not only becomes the value expression of specific political culture,but also becomes the practitioner and carrier of national cultural spirit.Therefore,the task of reshaping national character should be fulfilled by extensive and vivid political life,and the integralmixture of political spirit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 assumes social channel of shaping national character.This channel is practically expressed in the structures of institutional sense and ethic sense.Institutional criticism and ethic criticism and reshaping indicate that the core value of social political development lies in shaping superior national character,which establish themodern value of criticizing research on national character.
thinking culturalmovement in modern China;national character;political philosophy;political development;political obligation;civil culture;public spirit
D08;B82-051
A
1009-1971(2012)04-0031-10
[责任编辑:张莲英]
2012-04-08
教军章(1962—),男,辽宁凤城人,院长,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从事公共行政理论、管理哲学、中国近代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