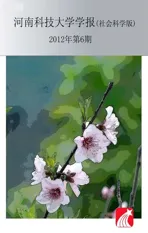席勒传声筒和工农兵文学传声筒
——兼析政治倾向文学和政治斗争文学
2012-04-07刘江
刘 江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科研处,广西 柳州 545007)
【外国文学】
席勒传声筒和工农兵文学传声筒
——兼析政治倾向文学和政治斗争文学
刘 江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科研处,广西 柳州 545007)
德国剧作家席勒的剧作,曾被马克思称作“传声筒”,我国的工农兵文学,也被研究者称为“传声筒”。两者有着许多不同之处:前者是政治倾向文学,后者是政治斗争文学;前者传的是时代精神之声,后者传的是阶级之声;前者从个人感受出发,后者从宣传目的出发;前者显露,后者直露。但两者又具有某种相同的审美价值。从马、恩和毛泽东的不同态度中,又可以感受到“传声筒”的不同意义。
席勒;工农兵文学;传声筒;政治倾向文学;政治斗争文学
1859年4月,马克思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中说过一句话:“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1]91从此,“席勒”和“传声筒”便常常出现在理论家的文章中。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认为“十七年”文学(指以赵树理小说为代表的工农兵文学)也“被视为政治的‘传声筒’和‘吹鼓手’”。[2]然而,通过工农兵文学的“传声筒”和席勒个人的“传声筒”,我们可以了解政治倾向文学和政治斗争文学的差别,以及文学与时代、政治的关系。
一、不同的“政治”
马克思关于席勒剧作是“传声筒”的说法,主要指他的早期作品,即《强盗》(1780年)、《阴谋与爱情》(1783年)和《唐·卡洛斯》(1787年)。《强盗》的主人公是德国“狂飙突进运动”高潮时期的一位青年,他既对当时的封建专制不满,又无力改变现状,最后只能以悲剧收场;《阴谋与爱情》讲述的是贫民少女路易斯和贵族青年费迪南的爱情悲剧故事,展现了市民阶级和封建贵族之间、真挚爱情和宫廷政治之间尖锐的矛盾冲突,主人公是封建宫廷权力的牺牲品。显然,两者都“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精神”。[1]94而《唐·卡洛斯》则“体现了自由和专制、人权和奴役、启蒙思想和封建教会反动势力之间的斗争”。[3]26正因为此,恩格斯才说《强盗》是“歌颂一个向全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的青年”,[1]94《阴谋与爱情》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1]94这也适用于《强盗》。虽然《唐·卡洛斯》“把人民自由解放的希望寄托于统治者,比起《阴谋与爱情》来,反封建的现实意义已大为减退了”,但仍然“有一定的反封建专制的倾向”,[3]26-27所以可以说:席勒的这些作品都是政治倾向文学。
由此,我们自然想到了工农兵文学。众所周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正式提出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随之催生了工农兵文学。毛泽东说:“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4]70文艺工作者“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4]58“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4]49从此可以看出,他所倡导的工农兵文学完全是作为阶级斗争武器的文学。20世纪40年代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还有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等等,有哪一部不是用于阶级斗争的呢(民族斗争其实质也是阶级斗争)!至于建国后的《红旗谱》、《创业史》、《林海雪原》、《红岩》等等,也都是宣传革命思想,为某一政治变革和阶级斗争服务的作品。所以,从其本质属性上看,工农兵文学就是政治斗争文学。
虽然席勒剧作和我国工农兵文学都与“政治”紧密相关,但是,两者其实又有许多不同之处。
其一,作品政治思想的总体性、模糊性与具体性、明确性的差别。席勒的剧作,反封建是总体性的。也是模糊性的。究竟怎么反?没有具体的策略和步骤,只是一种思想的总体意向而已。而工农兵文学所表现的政治思想是非常明确的,如反映土改斗争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都有非常明确的政治斗争目标(就是“斗地主,分田地”,“把地主恶霸拉下马,穷人翻身坐天下”),有具体的政治斗争策略(如对待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的一套政策),同时,人物和故事都有明确的政治指向(比如某人代表地主,某人代表贫下中农,他们之间的斗争即代表农村的阶级斗争)。其他如反映抗日斗争的《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甚至不是专门表现抗日的《白毛女》,亦是如此。
其二,自由写作与使命写作的差别。政治倾向文学是从作家自己的生活体验出发去表现政治倾向的,所以其表面层次是感人的情节和人物。席勒《阴谋与爱情》中的爱情故事是感人的,观众只是在感动之后,才注意到它的政治倾向。工农兵文学却是带着使命去写作的,其初创时期甚至还不是像鲁迅那样去“遵命”,而是直接带着明确的目的任务去深入生活,尔后才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进入创作过程,实际上是任务写作。《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过程就是明证。只有到了建国后,像《红旗谱》、《林海雪原》的作者那样,才是遵无产阶级革命之命去构思作品,但使命感仍然十分突出。作家不是个人在写作,而是代表整个阶级在写作,肩负着政治斗争的使命,所以作品是在表达明确的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去感动读者的。
其三,表现思想意向和直接描写政治斗争之别。这是最为明显也是最为重要的不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和《强盗》等作品整体故事虽有政治倾向,但并非直接表现政治斗争,其正面描写的是别的故事(比如爱情等);工农兵文学,如《暴风骤雨》、《红旗谱》等却是正面、直接地描写政治斗争。即使是表现婚姻爱情的《小二黑结婚》和反映农村合作化进程的《创业史》,也在描写正面的、直接的阶级搏斗(对金旺兄弟的斗争)或政治思想的冲突(围绕农村合作化问题展开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封建守旧思想以及私有制观念的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马克思批评席勒把戏剧作为“传声筒”的做法,但是恩格斯在致考茨基的信中,又说“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并由此引申出自己“决不是反对倾向诗本身”的观点。[1]130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不但不否定文学的政治倾向,反而是对它大加赞扬,把它作为文学价值判断的重要根据。当时,还没有“政治斗争文学”的命题,但是从马、恩对待政治倾向的态度看来,完全可以推论出:他们也并不会否定文学的政治斗争的内容。
二、不同的“传声筒”
诚然,作为政治倾向文学的席勒戏剧,是“使作品主人公变成某种抽象的道德观念的化身”[1]195的“传声筒”,而我国作为政治斗争文学,并且直接表达作品的政治见解的工农兵文学,毋庸置疑,更是传声筒。
那么,到底什么是“传声筒”呢?换句话说,什么是“传声筒”的表现方式和手法呢?
恩格斯在致玛·哈克纳斯的信中说:“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1]135-136这是马、恩对文学表现方式和手法的要求。按照中国的说法,就是要含蓄蕴藉,即思想观点要“藏而不露”。而“传声筒”正好走向了它的反面:露。从这一方面看,同有“传声筒”之弊的席勒戏剧和工农兵文学是一样的。然而,又是有所区别的。
其一,传时代精神之“声”,还是传阶级之“声”。席勒的《强盗》和《阴谋与爱情》都是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精神的作品。反封建在当时是全社会的意识,是18世纪欧洲的时代精神,并非某一阶级独有的主张。也就是说,它们是传达社会之声和时代之声,马克思说的就是“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而且,席勒作品也只是从某一角度去反封建的。恩格斯说:“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1]131其实中国的古代、现代许多著名的作家也都是具有政治倾向的作家。这些作家的作品所表达的也都是进步的社会意识,是站在社会的进步立场上的。这是一般政治倾向文学的特点,也是席勒剧作的特点。而工农兵文学并不是一般社会民众的文学。所谓“工农兵”是指被压迫的社会底层,即广义的无产阶级,因而工农兵文学其实质就是阶级文学。虽然工农兵文学也反封建,但并不是以社会民众的立场去反封建,而是以无产阶级的立场去反封建。同时,它是以铲除整个封建制度及其思想体系为目的的,并非只是反对某一方面,例如只反包办婚姻、等级制度之类。因而它的反封建是最彻底的。正因如此,所以无论初创时期还是发展时期的工农兵文学,不管是《新儿女英雄传》、《暴风骤雨》、《小二黑结婚》,还是《红旗谱》、《创业史》、《林海雪原》和《红岩》,所表达的都是对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对各种腐朽思想和侵略战争的总的反叛,所传达的是无产阶级之声。
其二,从个人感悟出发,还是从宣传目的出发。虽然席勒剧作的情节和人物不完全和现实生活相吻合,严格说来是“为了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1]100并不是莎士比亚式从生活出发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1]136如他“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1]136但是,席勒的剧作说到底还是作者先从生活中产生了个人的感受(尽管这一感受是社会性的,并不独特),尔后出于个人情感表达的需要(并非宣传的需要)而产生的,只是后来他把这种感受变成一种理念,并以这一理念来设置人物、编织故事,以致“使作品的主人公变成某种抽象的道德观念的化身”。[1]95个人感悟是席勒剧作“传声筒”的出发点。而工农兵文学所表达的,并非是个人感悟,而是所要宣传的思想,其写作灵感是由宣传目的所触动的。不用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其写作目的就是要宣传土改政策和土改胜利,《山乡巨变》就是要宣传合作化的政策和胜利,就是《红旗谱》、《林海雪原》和《红岩》等反映革命历史的作品,也都是为了赞颂革命斗争。这些都是革命的要求,虽然不能否认个人的一些感悟(这表现在对某一生活事件上,而不是表现在作品的主旨上),但其写作动机则无一不是出于革命宣传的需要。因而其人物设置、情节安排都要和政治目的完全吻合。比如,凡是反映革命斗争的作品,都要写出斗争的艰难和曲折,最终我方都必然取得胜利。这是由宣传目的所决定的,作者不能随意更改。由此可以说,工农兵文学的“传声筒”,是从阶级的宣传目的出发的。
笔者曾经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情感因由文学和思想因由文学”的命题,[5]实际上,所谓自由写作即作为政治倾向文学的席勒戏剧的写作,就是情感因由文学的写作;而使命写作即作为政治斗争文学的工农兵文学的写作,就是思想因由文学的写作。
其三,显露,还是直露。还要特别说明的是,作为政治倾向文学,席勒早期剧作只是其中的一种,更多的政治倾向文学,如巴尔扎克、司汤达的小说,我国的小说《红楼梦》、戏剧《西厢记》等,都不同于《阴谋与爱情》等剧作,它们并不是传声筒,而是含蓄蕴藉的作品。那么,现在要探讨的是,《阴谋与爱情》这样作为“传声筒”的政治倾向文学它和作为政治斗争文学的工农兵文学的“传声筒”,在表现手法即“露”这一方面,还有区别吗?
答案是有的。其实,即使是《阴谋与爱情》这样的“传声筒”作品,还是以人物和故事为中心的,其之所以成为“传声筒”,是因为其人物成了某种观念的化身,即人物的政治思想色彩过于明显,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也就显露出作品的政治倾向,所以席勒戏剧的政治倾向是显露性的;而工农兵文学,不但人物是政治思想的化身,情节也是毫不隐晦、直接地指向这一政治思想,实际上是通过人物和故事对政治思想进行阐释,即上世纪80年代批评界所说的“主题先行”,《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好,《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也罢,《小二黑结婚》同样,都是在阐释党的土改思想、抗战思想或婚姻政策。甚至于《红旗谱》、《创业史》和《林海雪原》等等,也是在直接展现革命思想。这是直露。
三、共同的美学意蕴
提出“传声筒”作品的审美问题,人们不禁要问:“传声筒”的作品还会有审美价值吗?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光是从阅读效果就可知道:席勒的《阴谋与爱情》是受到许多人欢迎的,虽然马克思批评席勒的“传声筒”做法,但恩格斯对于整个作品还是给予了一定的肯定、甚至赞扬。至于《红旗谱》、《创业史》、《红岩》、《林海雪原》等等同样被认作“传声筒”的工农兵文学,不说在当时,就是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吸引着大批读者。近年就有人说,“《红旗谱》还活着,自有其价值,归根结底还是它的有些主要人物还活着,比如朱老忠……我觉得这是作品生命力的一个根源”;[6]又有人说《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是民间话语的审美形象……其本身散发的民间气息……具有难以遮掩的艺术魅力”。[7]照样有人说:“在文学史上,的确有一些正面的人物,如杨子荣、保尔、许云峰、江雪琴等形象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8]那么,为什么政治内容的“传声筒”,还会具有如此的魅力呢?这里牵涉到审美的问题。
其一,内容的审美意义。西方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美学家往往认为只有形式才是美的。其实以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才是美。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美是生活。”[9]而生活,就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其中,内容是更为重要的。同时,既然“美是生活”,而生活中很难离开政治,那么,有政治含义的生活也就是美的组成部分。别林斯基说:“如果一件艺术作品只是为描写生活而描写生活,没有任何植根于占优势的时代精神中的强烈的主观动机,如果它不是痛苦的哀号或高度热情的颂赞,如果它不是问题的答案,它对于我们时代就是死的。”[10]286这“时代精神”中不就包含着政治吗?即使像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样,“把美割裂为两种:内容的美,即‘本质的美’(这种美与形式无关),和形式的美(这种美与内容无关)”,[10]319而含有政治的内容同样不也是一种美吗?既然如此,席勒戏剧的那种反封建的时代精神,那种表现着社会进步的内容,不是一种美吗?工农兵文学中那种反侵略、反封建、反压迫、反剥削的现实故事,不同样是一种美吗?特别是,被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认作是评价作品“最高的标准”[1]101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其实就是“内容重于形式”观点的具体运用。对于内容的强调,也就使含有政治意义的作品显出美。虽然政治倾向文学和政治斗争文学两者都是“传声筒”,但传达的都是代表着社会进步的声音,这种声音当然也是一种美。从这一意义上说,肯定“传声筒”的审美意义,实际上就是肯定作品内容的审美价值。
其二,“露”的审美价值。应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是站在精英文学立场,以最高标准即“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来评判席勒早期剧作的。然而,美感因人而异,它有个别性和特殊性,也有层次性。就文学的审美者即受众而言,可以分为精英文学受众和大众文学受众两大群体。前者以含蓄蕴藉为美,后者却以浅白易懂为美,即以“露”为美。作为政治斗争文学初创时期浅白直露的工农兵文学,为什么当初会大受欢迎?就是因为这些读者都是大众读者,从这些作品中,他们可以找到审美的情趣。
其三,文化化的工农兵文学更是一种美。实际上,和初创时期按照政策演绎政治斗争过程的工农兵文学相比,席勒的“传声筒”剧作还是较有文化意蕴的。比如《阴谋与爱情》就有西方宫廷文化的气息。而我国的工农兵文学,当它们发展到了高峰期即建国后的文革前17年时,像《创业史》、《红旗谱》等等作品,其本身是政治,却又超越了政治,因为它们无论人物和事件,都含有历史的意蕴和地域的文化气息。作品中朱老忠、梁三老汉等等典型人物,不但有政治性,且有文化性(比如前者的燕赵文化,后者的关中文化);其所写的斗争,也不是一般单纯的阶级斗争,还是新旧文化上的较量(前者身上的正义与邪恶的斗争,阶级反抗对个人复仇思想的超越;后者身上“社会主义思想”同私有观念、个体经济思想的冲突),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政治斗争范畴,这种直露不但让人容易接受,而且还给人以文化意蕴的美感。
四、导师对“传声筒”的不同态度
上面说过,马、恩是明确表示否定席勒剧作的“传声筒”手法的,因为他们在肯定政治倾向的同时,也十分强调艺术性,即强调政治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统一。而“传声筒”则被认为缺乏艺术性。特别是恩格斯,他一再称赞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并以之同席勒的“传声筒”作一褒一贬的比较,这足以说明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对现实主义的重视。在马、恩眼里,现实主义不但是一种表现手法,更是一种创作精神。他们把文学创作同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和创作精神直接联系起来,强调要用文学的现实主义手法和精神去表现进步的政治倾向——这才是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创作观。在这里,现实主义和“传声筒”是矛盾的,“传声筒”是破坏政治倾向的表达的。
而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政治标准第一”的同时,也强调政治和艺术的统一,这也是既强调内容重于形式,又不忽视艺术的思想体现。从政治和艺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看,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的观点是一致的。这也说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完全属于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范畴。但是,我们又不可否认,马克思、恩格斯同毛泽东到底是不同时代的人,他们各自面临的社会背景和阶级斗争形势不同,因而在文艺具体问题上也难免有不同的认识。比如毛泽东对于文学的政治性更为重视和强调,他要求文艺直接为工农兵政治服务,即要求文学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4]49因而他对赵树理小说的“传声筒”手法并没有表示过否定的意见。在抗日根据地,还把赵树理确立为“方向性”作家,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副主席陈荒煤还写过一篇题为《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文章。[11]毛泽东一再强调的并不是巴尔扎克那样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而是理想化的现实主义。正如他所说:“我们主张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但这并不是那种一味模仿自然的即流水账式的‘写实’主义者,因为艺术不能只是自然的简单再现。至于艺术上的浪漫主义,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4]16他强调的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4]64他是把文学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性、工具性与表现手法上的理想化结合起来。在这里,理想化和“传声筒”并不矛盾。某种情况下,“传声筒”甚至可以是理想化的一种形式。因为“传声筒”可以达到某种理想化的效果,比如直接描写贫下中农同农村地主斗争的曲折以及最后的胜利,就能理想化地体现出我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历程。所以说在毛泽东那里,“传声筒”是适用于政治斗争文学的。
从今天的角度看,或者说,从文学的本质属性出发,我们完全可以作出判断:马、恩对席勒式“传声筒”的否定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在席勒剧作中,文学性减弱了;同样,毛泽东不否定“传声筒”的做法有违于文学的发展规律,也有违于他“政治和艺术的统一”[4]74的主张,因为这是以政治性压倒文学性。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看待文学作品,内容永远重于形式!且看如今的许多文学作品,其内容的浅薄让人感到乏味,尽管不是“传声筒”,那又有什么用!
还要指出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那些对工农兵文学作出“传声筒”评判的论者,并不像马、恩那样追求政治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而是反感于意识形态,特别是工农兵即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最明显的佐证是:《红旗谱》、《创业史》明明在典型形象刻画以及文学语言运用等方面并不逊色于《水浒传》,且在思想内容上还明明超越于后者,可他们并不否定后者而去彻底贬损前者,不但以“传声筒”之恶名奉送,而且还说:“《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12]这种学术立场有失偏颇。他们排斥意识形态文学,站在所谓“纯文学”的立场上,当然反感于政治意识浓厚的工农兵文学。
[1]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2]董之林.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反思——以赵树理小说为例[J].中国社会科学,2006,(4):65-69.
[3]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主编.欧洲文学史:下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艺论集[M].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2.
[5]刘江.情感因由文学和思想因由文学[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7(1):59-63.
[6]雷达.《红旗谱》为什么还活着[N].文学报,2010-05-20(4).
[7]尹婧.试论《创业史》的两个人物形象[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84-87.
[8]蒋红艳.从典型文本看文学形象的美学特征[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2):41-45.
[9]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研究室.文艺理论学习资料: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74.
[10]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11]董大中.赵树理研究述评[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3):108-112.
[12]王彬彬.《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十七年文学”艺术分析之一[J].当代作家评论,2010,(3):22-39.
Schiller M outhpiece and the Literature as the M outhpiece of W orkers,Peasants and Soldiers——Analysis of Literature of Political Tendencies and Literature of Political Struggles
LIU Jiang
(Liuzhou Railway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Liuzhou 545007,China)
German playwright Schiller’s plays were called the“mouthpiece”by Marx,and the literature of Chinese workers,peasants and soldiers is also referred to by the researchers as“mouthpieces”.However,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the former are the literature of political tendencies,while the latter the literature of political struggles;the former represent the spirit of the times,while the latter social class;the former start from the personal feelings,while the latter from propaganda.As for the purpose,the former is revealed,while the latter directly exposed,having a certain aesthetic value in common.From the different attitudes of Marx,Engels and Mao Zedong towards“mouthpieces”,differentmeanings of the“mouthpiece”can be impressed.
Schiller;literature of workers,peasants and soldiers;mouthpiece;literature of political tendencies;literature of political struggles
I022
A
1672-3910(2012)06-0056-05
2012-05-15
刘江(1948-),男,广东梅县人,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