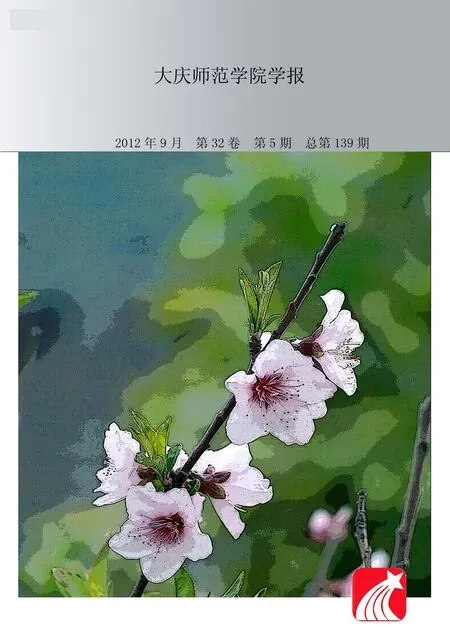神圣与诗意
——广西南丹白裤瑶葬礼仪式的审美意蕴阐释
2012-04-02雷文彪
雷文彪
(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系,广西 柳州 545004)
广西南丹白裤瑶主要分布在广西西北部,云贵高原东南边缘红水河以东,约东经107°1′~107°55′,北纬24°42′~25°37′之间的里湖瑶族乡、八圩瑶族乡和瑶山瑶族乡等地,是我国瑶族的一个重要支系,自称“吉努”,因白裤瑶男子常年穿白裤而得名。有人口三万左右,被联合国科教文卫组织认定为民族文化保留最完整的一个民族,具有“人类文明的活化石”之称。广西南丹白裤瑶作为瑶族的一个重要支系,至今仍保留着独特的宗教观念、婚礼仪式和葬礼习俗。本文主要对广西南丹白裤瑶的葬礼仪式中所蕴含的神性与诗性的审美意蕴进行阐释。广西南丹白裤瑶的葬礼仪式具有比较固定的仪式规程,它主要由阴朝报丧、铜鼓造势、开牛送葬、跳猴鼓舞、沙枪送葬、长席宴客等六大仪式组成[注]对于广西南丹白裤瑶葬礼的仪式规程,笔者曾做过较为详细的田野调查,其具体的葬礼仪式规程可参见拙作《广西南丹白裤瑶葬礼仪式的审美人类学考察》,《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第110—114页。。
海德格尔说:“死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种须从生存论上加以领会的现象。这种现象的意义与众不同。”[1]289“死亡的生存论阐释先于一切生物学和生命存在论。而且它也才刚奠定了一切对死亡的传记学、历史学、人种学和心理学研究的基石”[1]297。广西南丹白裤瑶的葬礼仪式是白裤瑶族群对于生命存在观念的集中体现,孕育着非常丰富的美学内涵。广西南丹白裤瑶族群的整个葬礼仪式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民族文化现象,它既具有“祭祀生命里程”的神圣性又富有“向死而生”的诗意性。
一、祭祀生命的里程:广西南丹白裤瑶葬礼仪式的神性彰显
人类学家弗兰西斯说:“无论何时,仪式都与社会性的生死冲突相联系,因而必然趋向于成为一种神圣或祭献礼仪。”[2]15在白裤瑶的葬礼仪式中,采用印有“瑶王印”的布来包裹尸体、敲打铜鼓、砍牛是彰显白裤瑶葬礼仪式神圣性的三个重要表征。
在广西南丹白裤瑶族群中,男子裤子上都有五条“红印”(“五指印”),女子花背心上都印有“瑶王印”,这些印记符号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富有相当浓郁的神圣性。白裤瑶的《天地始歌》这样唱道:
呕唷唷——
为什么我穿的花背心上印着一个金印?
为什么我穿的花裙上印着九十九个花纹?
今晚我才知道唷,
是雅海[注]雅海:白裤瑶的女祖先。要我们记住金印的教训,
是雅海要我们记住九十九次苦难的历程,
呕——唷——
苦胆一样的巴楼人[注]巴楼人:白裤瑶人。唷,
要把金印和苦难刻进自己的心!
呕唷唷——
为什么我穿的白裤有五条红纹?
今晚我才知道唷,
五条红纹是阿者[注]阿者:白裤瑶的男祖先。血战楼刻[注]楼刻:瑶语音译,白裤瑶对汉人的称呼。留下的血印。
呕——唷——
青冈木一样坚硬的巴楼人唷,
永远牢记祖宗的战斗精神。[3]239
此外,在白裤瑶地区还有这样一个广泛流传的关于“瑶王印”来源的故事:
相传在很久以前,南丹地区就是瑶、苗、壮、汉各族人们和谐聚居的地方,在这里各族人们都是遵照瑶王印鉴办事。壮族有一莫氏土司为夺得这一地区的主导权,设计骗走了瑶王印,并攻进瑶区。瑶王被迫迎战,在战斗中瑶王负伤战败,血流不止,爬山时手撑膝盖,在裤腿上留下十条血指印,临终前,在衣襟上画了瑶王印的图案。瑶族后人为纪念瑶王,便在裤子的膝盖处绣上十条红杠,在衣背上绣上瑶王印图案。
也有研究者认为,白裤瑶男子裤子上的五条“红印”和女子花背心上的“瑶王印”与传说中的瑶族神话有关。相传瑶族神话中,龙犬身有五彩,瑶好五色,即红、黄、蓝、白、黑等,瑶族刺绣采用五色,而白裤瑶族群在服饰上秀刺“五指印”和“瑶王印”,其目的是以此显示自身是龙犬(盘瓤)的后裔。而有研究者认为,白裤瑶服饰图案与瑶族《评皇券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研究者认为:“白裤瑶服饰图案‘瑶王印’是易经记载的‘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历史的形象刻画,保留着八卦形成之前河图与洛书融合的早期文明形态,是上古人类从结绳记事阶段进步到数字记事阶段的标志图案。”[4]
可见,无论是从白裤瑶的《天地始歌》记载来看,还是从白裤瑶族群中流传的故事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瑶王印”是白裤瑶族群祖先崇拜的产物,它与对神鬼的敬畏有关,“瑶王印”不仅承载着白裤瑶族群厚重的历史记忆,而且已经积淀为白裤瑶族群集体意志的象征,甚至已成为白裤瑶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神器和护身符。白裤瑶人用印有“瑶王印”的布覆盖死者的尸体,一方面表现出白裤瑶对祖先瑶王的怀念和敬仰,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白裤瑶人期望以此获得祖上和神灵的保护,抗拒鬼神袭击与侵扰的美好愿望。
鼓(铜鼓、皮鼓)是白裤瑶葬礼活动的主要打击乐器,击鼓是其葬礼仪式的主要程序。在白裤瑶中,铜鼓被视为神圣之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能随意接触铜鼓,宋人朱辅《溪蛮丛》一书中曾有“溪蛔爱铜鼓,甚如金玉”的记载。如果需要取出铜鼓,就必须举行一个“隆重”的“请鼓仪式”,民间有“凡有丧事,必有鼓声”的说法。据清代《广西通志》记载,“思恩瑶……岁首祭先祖,击铜鼓跳跃为乐”;此外,乾隆((庆远府志》也记载了广西南丹白裤瑶击鼓治丧的习俗:“瑶、壮俱尚铜鼓,而所用之时不同,有用之于吉礼,有用之于凶礼。南丹惟丧事用之,犹须吉日,可击则击,不可击则止。”对于南丹白裤瑶族群对敬畏铜鼓的神圣性表征,著名的瑶学研究专家玉时阶先生有很好的论述:
南丹县瑶族人办丧事,把讣告发出去后,就拿出铜鼓来敲打。他们过去曾是非死人不许敲铜鼓,现在虽略有改变,允许过年敲铜鼓,但死人时敲铜鼓的习俗一直未变。浑厚低沉的鼓声如诉如泣,在村寨和山谷中回响,把不幸的消息传递到近邻远村,人们闻声便知有人遇难,赶来帮助。鼓声昼夜不断,传播悠远,惊动冥冥中的神灵,通知他们准备接纳死者的灵魂。在他们的观念中,人的灵魂是不灭的,人死之后,仍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团体,共同生活,在九重天之外,有个隐蔽的地方,是他们的始祖和历代祖先共同居住的地方,死者的灵魂必须到那里去与他们团聚,所以,必须敲铜鼓将此事告诉冥冥中的神灵。因为铜鼓是可以沟通人、神的神器。[5]
同时,由于南丹白裤瑶族群对铜鼓始终怀有一种敬畏之情,击鼓丧葬的仪式规程也是非常讲究的,整个仪式主要由一面皮鼓和多面铜鼓组成,皮鼓是击鼓仪式的指挥,由具有一定威望和击鼓技能的鼓师控制。在白裤瑶族群中,人们认为送死者灵魂去阴间要经过七或九道关卡,而死者的灵魂从阴间返回人间则还需要增加两道关卡,因此,民间有“七去九返”或“九去十一返”之说。这样,击鼓丧葬时击鼓是有一个比较严格的规程:在击打皮鼓的过程中,每三面三边为一小节,九面九边为一大节,如此反复,其节奏规律要严格遵循“七去九返”或“九去十一返”,否则就会触犯葬礼仪式的禁忌,影响死者灵魂的“超度”,甚至被视为是对神灵亵渎和对死者的不敬。
在南丹白裤瑶族群中,“开牛”仪式有着深厚的伦理背景,它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的远古白裤瑶族群“食人俗”的野蛮陋习,是白裤瑶族群孝道文明发展的一个表征形态。同时,“开牛”仪式是南丹白裤瑶族群一个重大、独特的祭祀活动,也是一个遗存着原始暴力性又富有神圣性葬礼仪式。克利福德·格尔兹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指出:“每一个民族都热爱各自特有的暴力形式。”[6]508而“对于暴力的理解和认定必须建立在某一特定的文化语境之上……暴力不能简单地被看做是一件事情本身,而是属于一个意识形态的行为,一个充满连贯性和延续性的社会行为,也可以是特定条件下的行为分类和规范。所以不能简单地认定为‘反常’或‘变态’,必须将它置于某一种社会背景或族群伦理体系里去看待和对待。”[2]258在白裤瑶族群中,“开牛”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仪式,尽管“开牛”实质与砍牛、杀牛同义,但在称呼上是不能替换的,其原因在于,在白裤瑶族群中牛是具有一定“神圣性”的意味,牛既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一部分,同时牛也是死者必须具备的伴侣和财富的象征。因此,看似充满暴力的“开牛”仪式,其实是族人祭祀死者生命里程的一个神圣仪式,是践行对逝者生命尊严的“庄严承诺”。在他们看来,没有“开牛”就意味着死者的来世生活就没有财富,并以此带来死者来世生命尊严的缺失。可见,“开牛”并不是白裤瑶族群“反常”或“变态”的表征,而是一种神圣性的仪式。诚如彭兆荣教授所说,任何一个民族特有的暴力行为的指示性和逻辑性是密切相连的。“暴力是任何民族和社会的‘合理性存在’,每一个民族无论其做什么华丽的标榜,暴力无不充斥在整个历史文化的表述中。暴力形式各种各样,它们构成了民族和社会的象征性结构,它们可以起到对社会关系的整合,对社会秩序的控制和对社会冲突的平衡作用。特定和特殊的暴力形式又构成了所谓的‘文化感’;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因为这种文化感可以被感知和体认。暴力的社会性特征是通过某一个个体的活动行为以折射和展示特定群体的社会心理样态和共性。”[2]256—257
二、“向死而生”的精神还乡:广西南丹白裤瑶葬礼仪式的诗意呈现
日本美学家今道友信说:“死是最高的美学命题!” 广西南丹白裤瑶的葬礼仪式就是一个寓意丰富的美学现象,整个葬礼仪式规程中充满着一种诗意的向死而生的精神还乡情节。在广西南丹白裤瑶族群意识中,人类的存在可分为“现实”和“虚无”两个层面,即人类生命的存在既可以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又可以是一种“向死而生的存在”,因此对于广西南丹白裤瑶人来说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生命的延续和诗意的精神还乡。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只有死亡才是使生存得以实现的条件”,“所谓死亡,即意味着现象的消失,意味着离开实存而进入到可能的、纯粹的超验界中去。在死亡中,实存中断了,而我们的实存被切断以及它的片面性,恰恰使我们有可能从死亡处境出发来认识实存的局限性。此外,便站到实存与生存的分界线上,看到了我们的实存的边缘,望到了包围着我们的实存的那个无边无际的大全,确立了我们的现实立场,从而成为真正的自身,成为生存”[7]。在广西南丹白裤瑶葬礼的“阴朝报丧”仪式中,死者亲人要用刻有五个或七个瑶王印的布将死者尸体盖住,一方面表示白裤瑶族群对先祖瑶王崇敬和悼念,另一方面也寄寓死者亲人希望先祖瑶王能够在阴间接纳和关照自己的亲人。请道公作法式,是为死者超脱而作。他们希望通过道公的做法使死者摆脱人世间所有的不幸和累赘,超脱凡尘进入另一个极乐世界。对于生活条件恶劣和生存艰苦的广西南丹白裤瑶人们来说,“死亡是精神通向彼岸世界的风帆,唯有它才引导心灵走入绝对自由的宫殿;也唯有它,生命个体可以穷尽一切知识、真理……作为生命存在的另一种形式,活着却是不自由的,而死可以摆脱现实世界的物质之累,知识之累,道德之累,法律之累,等等。”[8]274—275
任何仪式都具有一定的形式特征和表达性质的功能。“仪式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在于能够把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关系、状态加以颠倒,从而使现实生活中无法解决的矛盾得到想象性解决,使异化的、破碎性的现象凝固为一种完美的整体。现实中的痛苦转化为艺术的优美,现实中缺少的东西也以幻象的形式重新出现。”[9]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死亡意味着生命的结束,死亡是一件充满悲凉可怕的事件。而葬礼仪式通过一定的仪式规程,将死亡悲凉氛围得以缓解,使人们的凝重压抑的心境得以释放。列维·斯特劳斯将仪式的这种功能称为“修补术”,他指出,仪式的功能在于通过一定仪式阈限阻断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关系,有利于与神交流、沟通。仪式欣赏者通过表演仪式的动态过程将主体与对象联系起来,在这里表演仪式完全成了人类自我注释的方式,表演的过程也是审美的实践过程。在白裤瑶葬礼仪式中,无论是击鼓仪式、开牛仪式,还是跳猴鼓舞、沙枪送葬、长席宴客都可以称得上是具有浓郁民族风情和特色的仪式展演,这些仪式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心理不断消解,使现实中因死亡而建构起来的悲凉氛围,在仪式阈限内转化为艺术性展演。悦耳鼓声是为死者升入天堂开路,壮观的“开牛”是为死者在天堂生活奠基,富有节奏和韵律的猴鼓舞是为死者饯行,沙枪送葬的枪声是为死者向天堂“报到”,长席宴上淡定从容的大碗喝酒、谈笑风生是为死者摆脱困难而高兴。整个葬礼仪式无不成为人们观赏的对象。在丧葬当天,很多附近乡里的青年男女前来参观,他们打扮得漂漂亮亮,边观看葬礼边寻找对象,当遇到自己喜欢的人就跟他对唱情歌,并逐渐离开葬礼去偏僻的地方约会。从某种程度上说,白裤瑶葬礼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很强观赏性的艺术展演,葬礼仪式的现实功利性被艺术的审美性所抵抗、消解,在这里葬礼仪式转化为一种优美的艺术形式,葬礼仪式的艺术性弥合了现实的功利性,修复了因死亡而造成的阴森、恐怖、可怕、悲凉的境遇。
在广西南丹白裤瑶葬礼中最具有诗意性的仪式是“立牛角天柱”,所谓“立牛角天柱”就是将砍杀的带角牛额骨订在雕有龙凤的杉木上,然后立在死者的坟墓前,供死者登天之用。“牛角天柱”中的牛角是白裤瑶族群葬礼中必不可少的陪葬品,它们是死者财富的象征,死者坟墓前立的牛角天柱越多,表示死者到天堂后就会越富有。杉木上雕刻的纹路代表死者由阴间登上天堂的“天梯”,杉木上雕刻的龙凤图则寄寓着死者的“美好前景”。白裤瑶这种诗意的想象与其浓郁的鬼神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白裤瑶对于生与死没有截然断裂的观念,他们甚至认为现实中的人可以与死者的灵魂进行一种“互渗性”交流。这种诗意的思维模式类似于列维·斯特劳斯所称的具象性“野性思维”,这种思维模式“指向生命自我的想象性,它把内外世界的统一性确定在自我意识对对象的想象性把握中,个体的生命状态是这个世界的尺度,整个世界包括自我存在都是生命感受的由内及外的想象而已”[8] 265-266。在白裤瑶人们看来,生与死没有绝对界限,二者可以互相渗透和让渡,这种隐喻性的认识使他们坚信生命的永恒性。可以说,白裤瑶“立天柱”这种诗意的想象消解了“死亡”这一冰冷的理性法则,它承认世界的生命流动性,对死亡的冷酷性予以强烈的情感否定,它建构了一个生命由死复生的审美境界。对于他们来说,或许死亡是生命的最高虚无,死亡是对生命起点的回溯,是对生命之家园的归返,更是对精神家园的归返;死亡代表了一种灵魂的升华,它表征着白裤瑶族群“向死而生”的精神还乡。
[参考文献]
[1]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2] 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3] 陈日华,韦勇团.莲花山仙踪[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
[4] 磨现强.白裤瑶服饰文化刻录的上古文明[M].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7.
[5] 玉时阶.瑶族铜鼓考[J].民族艺术,1989(3):83.
[6] 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M].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7] 雅斯贝尔斯.存在主义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278-279.
[8] 颜翔林.死亡美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9] 王杰.审美幻想与审美人类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