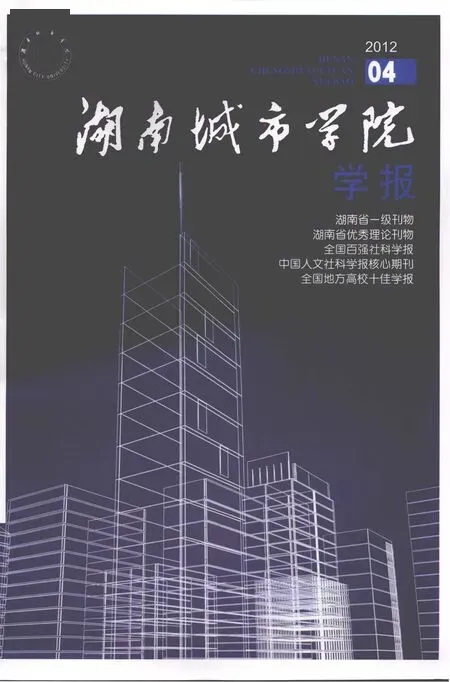公民身份的历史语境与当代困境
2012-04-01朱天培
朱天培, 吴 杰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公民身份是现代政治学中最基础、最正式的认同,然而其在公共领域中的重要性却常常被忽视。公民身份的历史充满排斥与抗争的主题,不同时期的公民身份有着不同的内涵。对于现代人来说,公民身份是生而有之的,然而大多数公民对公民身份的内涵不是十分清楚。在现代社会的规模、复杂性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公民身份正遭遇一系列困境。追溯公民身份的历史语境,能够了解其变迁,使得对现代公民身份的困境有更清晰的认识。研究我国公民身份同样必须考虑中国的特殊语境,这种特殊性来自于传统。对中国来说,公民身份实际上仍是一种较为陌生的概念,因此要实现公民身份的内涵也需要更多的努力。
一、公民身份的基本内涵
现代公民身份既是一种政治身份,也是一种法律地位。它是已完成民族国家构建的社会中较为成熟的政治与法律概念。公民身份在现代政治中一般被认为是一种法权确认,确认的是民族国家内的政治权利。这样的理念源于近代启蒙运动时期天赋人权的观念,而后历经多次抗争与妥协,演化为现代的公民身份。但现代公民身份仍保留了近代的特殊印记,它不局限于政治共同体这一范围。它所反映的人权的一些基本内容,具有一定的普世性,放眼世界,各国的公民身份具有一些相同点。从理论上看,公民身份通常被限定在微观领域,被认为与个人相关。马歇尔认为公民身份是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的复合,他指出“虽然不存在决定这些权利和义务应该是什么的普遍原则,但在那些公民身份作为一种制度正在发展的社会中,很容易产生一种理想公民身份的形象,它被用来衡量取得的成就,引导人们的想望。沿着这种方式所计划的道路前进,就是要实现更加充分的平等,公民地位之内容的扩展,获得该地位的人数的增加。”[1]马歇尔概括的公民身份是时空的总结,强调的是一种平台式的公民身份,它具有扩展性。这虽然反映了一定的事实,但不能完全涵盖公民身份的全部内涵。公民身份始终受到时空的局限,对它的争论则集中在它是个人基本权利还是关于集体身份的认同这一不同见解,这也是从古典到现代这一转换的必然结果。公民身份的内涵在历史中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古典的公民身份与现代殊异,要认清公民身份的内涵仍旧需要对其演变做适当的回溯。
二、公民身份的历史语境
公民身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城邦时期,甚至在近现代以前还只是西方独有的范畴。公民身份几经沉浮,承载它的世界也发生了剧变。从古希腊城邦到罗马帝国,再经过中世纪的城市共和国,直至近代启蒙运动沿革而来,公民身份历经历史的长程旅途,其内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一)身份认同和政治参与
也许要探究公民身份的萌芽极为困难,但在历史中寻找早期的公民身份,都将溯及古希腊。公民身份“最早是首领用来寻求把忠诚和杰出的人物从共同体的非正式成员中区别出来的一种方式”,[2]这意味着公民身份的缘起就具有排他性。对比东方特有的家天下观念,“忠诚和杰出”代替了血缘,权力关系也是更纯粹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容纳更多的议题。这样的区分构筑起了城邦这样的政治共同体,这是一种比乡土——邻里关系紧密得多的联系。更重要的是,这为公共事务与公共领域划定了边界,很大程度上使其自成一体。美德或者说德性一直在古典政治学中占据中心位置,这不是理论家的臆想,而是古典政治实实在在的动力。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城邦是自我管理的,公民管理着城邦内的所有事物,这种自我管理通过抽签、投票、选举等不同的方式实现。单单这样的自我管理并不稀奇,关键在于其直接参与的形式和取向,亚里士多德就将公民表述为“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3]这在后来的历史中都极大的削弱了。公民身份的范围是直接参与的现实条件,古希腊城邦的地域、人口甚至比不上现代一些城镇,而其中具有公民身份的人基本上又是极其有限的,它排除了占人口多数的奴隶、外邦人和妇女。城邦中的公共事务确实是自成一体的,但并不意味着不受其他因素影响。城邦有各自的神,祭祀与占卜很多时候决定公共事务如何决断,占卜的依据甚至可以决定公民、将领的生死或者流放。另一个不容遮蔽的事实是,城邦所谓的公共事务并非现代所指的公共领域内的事务,事实上城邦内的一切事物都可能成为公共事务,即使是现代看来非常私人的信仰、婚姻方面的事务也需要众人决断。
(二)信用资格与自治凭据
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公民身份与古希腊城邦时期有相似之处,但罗马共和国更多地体现贵族政治的特点,其公民身份更多的与荣誉联系在一起,而随着帝国时期公民身份的扩展,积极公民的形象逐渐暗淡。在整个中世纪,公民身份已经基本消失,与君主、领主相对的是臣民,服从是政治领域的基调。然而,中世纪并非铁板一块、密不透风。公民身份实际上并未完全消失,而一直存在于城市中,到中世纪晚期的城市共和国,公民身份的问题则凸现出来。城市公民身份的保存依赖于贸易的开展,公民身份是城市间贸易得以进行的信用保证,公民身份背后是城市作为信用担保的角色,在贸易编织的关系网络中,公民身份的偏重清晰可见。城市公民身份在整体的封建结构中创造了独特的认同体系,这种体系似乎仍可追溯到古典时期,但实质上却不具有古典公民权的一些内容,只是在形式上以公民身份来判别行业往来的资格。而后来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充实了公民身份的政治意涵,这也是城市公民身份的奇妙之处。中世纪晚期的城市共和国存在于“教廷、拜占庭、伊斯兰世界和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帝国之间的权力角力的真空中”,[4]无论如何帝国、君主、教皇、自治城市各自关心的似乎是不同的主题,名义上的皇帝念叨着统一帝国,而城市关心的似乎是它的贸易权。但是反抗皇帝看上去始终是大逆不道的,城市共和国虽然拥有一定程度的独立,“但在法律上,它们仍然被称作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附庸。”[5]直到有一天,城市的理论家开始为城市进行辩护,宣称自己“有相应的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实行自治。”[5]26缘起于贸易权的公民身份在特殊的政治形态与权力格局中巩固了自身,并最终影响深远。也许这只是历史的偶然,但对于城市来说,公民身份不仅是现实中城市贸易得以展开的基石,也是某种历史传承。无论这种传承多么微弱,历史的“巧合”还是刷新了公民身份的内涵。
(三)政治平等和权利保护
中世纪足够漫长,漫长到足以催生一些近代政治观念。在一种时快时慢的变化中,市民阶层的形成意义重大,市民阶层开启了近代历史的大门。城市共和国最终让位于更具力量的绝对君主制,此后的变革则基本是民族国家的舞台。市民阶层的形成是西方历史的独特之处,它传承的正是中世纪晚期城市共和国公民身份的衣钵,或许它具备一定的独立精神与自主意识。但是时过境迁,民族国家兴起时代的权力角力没有留下真空,市民阶层必须选择站队。倚靠王权还是自力更生,不同时空中的选择也不尽相同。在英国,确立了立宪君主制政体;在法国,第三等级仍处于臣属地位。启蒙运动宣告了激进的天赋人权,坚持不与旧制度妥协,在一股热潮中开始的法国大革命却没有实现它的愿景。结果,公民身份大致偏向了洛克式的保护性权属。公民身份此后的扩展现在看来似乎是势在必行,但其也是漫长社会抗争的成果。财产、男性身份、种族肤色都在一定时期成为公民身份的划定依据与边界,某种程度上说这仍旧依循古典公民身份的某些形式。然而,启蒙运动奠定的权利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之前的任何时代都不可能这般地呼唤如此广泛的政治平等要求。接下来的妥协也就是当代公民身份的这般模样:财产、性别、种族等限制被基本取消,公民身份的范围得到极大的扩展。但这也意味着直接参与的可能变得微乎其微。对于许多现代人来说,公民身份异常熟悉又极端陌生,陌生到不知其为何物,更不知其有何积极之处;对于那些稍微有些概念的人,公民身份似乎也只是保护自己的法律依据,但他们也只能模糊地记得所受教育中有关于宪法对公民身份保护的内容。
三、公民身份的当代困境
(一)积极公民向消极公民的转变
从古典到现代,公民身份的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古典的公民身份“从古希腊的城邦时代一直延续到法国大革命”,[2]5现代的从法国大革命延续至今。德里克·希特概括了公民身份的两种不同传统:“对责任加以着重强调的公民共和主义传统”和“对权利加以着重强调的自由主义传统”,[6]近代以来公民身份更多的表现了第二种传统。古典的公民身份是排他性的,归根结底是一种特权。这种特权赋予公民直接参与政治的资格,而美德与奉献则始终是其主题。近代以来的公民身份走向了民主,却也造成了别的问题,它不同程度地抽离了古典公民身份的内容,最终成为个体自我保护的依据。
1. 直接参与的消失
广袤的土地、众多的人口是现代国家的客观事实,理想的参与形式已变得不大可能。在边沁、密尔那里代议制成为理想的制度选择,但这样的选择也只是一种妥协。理论家们并非完全意识不到其中的问题,卢梭就强调“公意”的不可分割性。然而,卢梭反对任何一种比城市共和国大的政治共同体,而这种更大的共同体恰是后来政治发展的现实。相较而言,代议制是一剂更为现实的药方。而从伯克那里,也能看出这种制度可能带来的广泛影响。伯克身上仍带有古典政治的气质,他阐述了代表身份的问题,坚信代表不是完全站在民众立场,而应具有自身的判断。被贴上保守主义标签的伯克保守的不是反动内容,而是英国甚至西方大部分国家此后正式的制度选择。当然,包括伯克在内的许多理论家和政治家都不相信普通公民的政治判断和能力,代议制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实现了他们的规划。无论是阴谋还是妥协,现代政治不可避免地已然基本排除了大范围直接参与的可能性。
2. 公共事务专业化与职业化
现代公共事务管理领域出现了专业化的、庞大的公务员体系,雷森伯格在论及西方社会的公共服务困境时写道:“随着大约1400万美国人为某一个政府卖命,公共服务已成为一种工作。”[3]3民主政府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追求的,然而其实际效率始终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世界是平的”,宣示的是新的竞争法则,这对于传统政府来说是全方位的挑战。全球化并未宣告国家主体地位的瓦解,而是进一步巩固了其重要性。而一个有效率的公共事务管理体系则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所需要的。在积极活跃的参与局面和高效可见的结果中,如果不是完全的偏向,做出的至少也是极大程度的妥协,而管理的专门化与职业化是不可避免的。面对着职业化与专业化的管理队伍,普通公民的参与积极性能有多大是非常可疑的。对于一般人而言,既然有专门的雇佣关系来处理公共事务,自己的参与需要就不是明显的了。而普通公民自觉面对公务问题时能力不足,认为参与的价值相应的也不会很大,久而久之这变成公民的共识:公共事务不是公民的活动领域。
3. 合法性的生成与知会的现实
现代公民的权利与法治观念强于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有力的政府必然是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上的。“人民主权”观念是现代社会的共识,只有通过授权,政府才能代表人民行使权力。但这又是模糊不清的,授权只是理论家的构想,现实中只是偶尔的投票,西方制度中一般几年一次的大选被认为是这种授权的形式。韦伯把这种形式称之为“凯撒主义”,认为公民所选择的或许只是变相的君主,熊彼特则认为公民所接受的不过是“政治家的统治”。[7]现代政治必然要面对卢梭所提出的“众意”与“公意”的问题,而现代社会的多元异质实际上早已打破了形成完全共识的可能。在四分五裂的偏好与选择中,合法性仅有少数时候通过对既定议题的投票来体现,大多数时候则是默认。给予公民的参与途径少之又少,以至于公民大多数时候都是静默的、散沙式的无关群体。这反过来给予政府更大的行动自由和权力,很多时候政府只需要在事后告知公民行动结果。公民在面对政治时体会到了无奈,这种体验逐渐演变为一种政治冷漠。
4. 公民责任的消解
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构想在于保护公民社会免遭国家权力的侵害,然而这种设置实际在相当程度上消解了公民责任,也使得权力中心远离公民。古典的公民身份意味着一种特权,考虑到古代生活与政治息息相关,一种生存的原始动力始终贯穿在公民身份之中。而且古典公民身份体现了共同体的美德,对于公民来说,为公共事务服务是一种荣誉,因此献身精神包含高度的荣誉感,积极公民形象是公民所追求的。相较而言,现代社会已经不把公共领域摆在唯一重要的位置。私人生活的价值为社会所承认,个人则拥有相当程度的私密空间。正如阿伦特所言:“行动从来不可能在孤独中存在,孤独意味着被剥夺了行动的能力。”[8]理论家、政治家可以呼唤公共精神,但是除了遵纪守法,公民似乎已经没有更多的义务。何况政治的很多机理不是普通公民熟悉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共精神也许只是一厢情愿。因此,公民大多退回到经济、私人生活领域,即使仍关心公共事务,也不会行动和献身。那种公民责任与共同体的繁荣休戚相关的观念早已淹没在现代纷繁复杂的俗务当中,那些乐于奉献的人仍值得敬佩,但他们可能是政治家、意见领袖、知名学者,唯一不可能的是普通公民。
(二)公民身份传统的匮乏
公民身份在现代社会大致已经转变为消极公民的形象,这是公民身份的普遍事实。而对于中国这样的非西方传统的社会,由于缺乏公民身份的传统,还需要面对更多的问题。
1. 陌生的公共领域
对于中国公民来说,公共领域仍是陌生的概念。虽然政府、社会不遗余力地倡导公民精神,但多年以来,除了在某些特定领域出现了一小部分积极的公民,其他大多数公民仍认为公共领域与自身无关。这是现代社会所有国家的公民都存在的问题,但在中国则更多一层因素:传统的根深蒂固。传统社会中宗法一体化结构承接了大部分的社会事务,“宗法族长、家长往往把监督族人完课税、服役、承办官府事务作为自己的要务”。[9]表面上官府的权力不伸展到基层家族,但实际上正是通过乡绅、族长,整个农业社会的一切事务都得到有效控制。在这里既无公共领域,也无私人领域,有的是常识理性之下的臣服与适应。传统中的“家国同构”观念对于现代来说可能是摒弃个人原子式社会的一种资源,但是它也破坏了最基本的公民身份认同。糟糕的现实是:传统优质资源没有得到发挥,现代政治的规划也没有得到有力实现。现代社会的交往关系远比传统社会复杂,知识的传播、技术的进步带来了生产力的飞跃,但是相应的公民身份观念却没能铭刻于公民心中。当中国在完成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同时,公民责任却没能及时有效地建立起来,而今社会责任意识、公德心的缺失不断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现代问题的范围与复杂性早已超出传统宗法一体化结构的能力范围,传统资源能否构建共同体价值是十分可疑的。当前紧迫的仍是与公民身份有关的公民意识、公民精神、公民责任等观念的建构与积极实行。
2. 对政府的倚赖
治理理论在中国的兴盛为社会管理提供了一定的新思路。对于政府和公民来说,治理的有效性是现实的目标。治理理论的一大优点在于整个社会管理中不再只强调政府的责任,公民责任也灌注其中,可以说当前社会管理的开展开辟了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新天地。但不同于西方,在中国目前的治理结构中公民更加处于从属地位。一是由于公民参与精神的匮乏,还有就是普遍存在的对于政府的倚赖。孱弱的公民需要相对全能的政府,而长此以往,不但不能培育出公民精神,反而将进一步固化对政府的倚赖。将问题抛给政府对于中国人来说一直是极其简单的,但是在现代政府的压力与职能范围被越来越多的公民认识的今天,问题已经不再是出现一个保姆式的政府或者一个极具奉献精神的团体那般简单。公民应该意识到现实生活的许多问题需要自身参与和付出,也许最终能否形成一种中国的公民传统仍是未知的,但如果没有公民的积极行动与参与,结论只能是悲观的。在当前的参与结构中,要面对的不仅是公民参与数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公民本身的意识,即使只有部分具有积极参与精神的公民存在,也好过所有公民都只扮演消极公民的角色。
现代公民身份已与古典积极公民的形象大不相同,古典积极公民的参与和奉献精神是现代社会缺乏的,但也该认识到现代公民身份具有古典时期没有的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这亦是十分珍贵的。制度的变革对公民身份的性质有着巨大影响,公民身份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是客观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完全认同消极公民的形象。对于现代公民身份来说,其确实缺乏与积极公民身份相关的参与和责任意识,现代社会也在很大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关键是如何培育公民的参与精神和责任意识。在这个复杂的问题中,制度、政府以及公民个人需要协力合作,共同创造良好局面。
[1] T·H·马歇尔. 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23.
[2] 彼得·雷森伯格. 西方公民身份传统: 从柏拉图至卢梭[M].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09: 19.
[3]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111.
[4] 沃格林. 政治观念史稿: 卷 3 中世纪晚期[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242.
[5] 昆廷· 斯金纳. 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卷[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22.
[6] 德里克· 希特. 何谓公民身份[M].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07: 1.
[7] 熊彼特.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356.
[8] 汉娜·阿伦特. 人的境况[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147-148.
[9] 金观涛, 刘青峰. 开放中的变迁: 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0: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