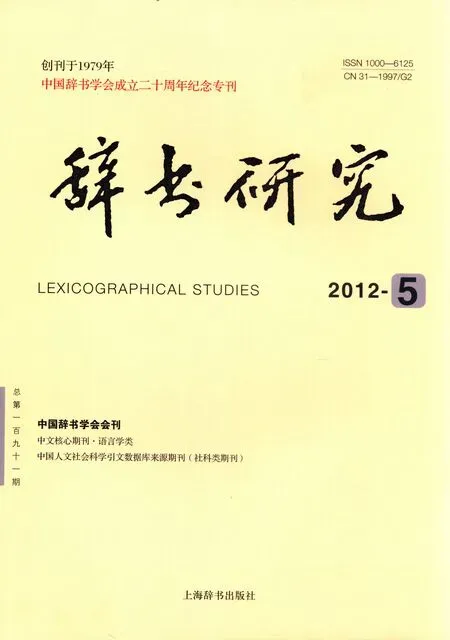我与《汉语大字典》和中国辞书学会
2012-04-01汪耀楠
汪耀楠
(湖北大学 武昌 430062)
一、我与《汉语大字典》
1975年,“文化大革命”还在乱糟糟地进行,周总理批复了《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关于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的报告》,这个规划要求从1975年至1985年间完成160部中外语文词典的编写出版任务,改变“大国家,小字典”的落后状况。《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是最大的两项工程。《汉语大词典》由华东五省一市承担,《汉语大字典》由湖北、四川两省承担。当年10月,我参加了这项工作。
这是一项十分浩繁的任务,川鄂两省组成一支四百多人的编纂队伍。我是湖北大学编写组(含孝感师专,共有四十多人)的一员,任副组长,主管业务。从此我便被《汉语大字典》“套牢”了。韩愈在《进学解》中所说“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的这种艰苦和精神,编大型字词典的人是最能体会的。从搜集资料、制作卡片,到编写审稿,每一个环节都要耗费巨大的精力。《汉语大字典》于1990年出齐,在人民大会堂开了庆功会,我参加了这个会议。一位日本学者撰文说:“无论什么人看,这一事业可以说是和修建长城一样艰巨和伟大。”《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是“文化的长城,汉语的双璧”。诚哉斯言。
《汉语大字典》是一部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大型字典,它的规模和编写难度远远超过了《康熙字典》。古文字字形的演变、古今声韵、字义训诂,涉及传统学术、现代语言学的方方面面。仅征引书目,就达两千种以上。重大的实践活动提出了繁多的学术课题,不在理论上解决这些问题,就不可能编出一部高水平的字典。
我是《〈汉语大字典〉编写方案》的三个起草人之一,武汉大学陈世铙、华中师范大学陈克炯和我对《汉语大字典》做了全面的规划。《编写方案》完成以后,我又思考着若干学术课题,写出了一些论文和细则。六书原理问题、正体字和异体字问题、名物字问题、通假字问题、大型语文词典释义的特点和要求问题、义项的概括与区分及释义的历史性和科学性问题、注疏材料的运用问题、历代训诂成果的运用和吸收问题、字的释义和词的释义区别问题、举例问题、相关字释义的平衡和统一问题等等,凡传统语文学和现代辞书编纂需要沟通的问题,都在我的思考范围之内。那些年我在《辞书研究》等刊物上陆续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并于1990年出版了论文集《词典学研究》(四川辞书出版社),同时又发表了《汉语大字典通论》和《〈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对词典学理论的贡献》等十余万字的长篇论文,对《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实践和所涉及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总结。
1992年第4期《辞书研究》发表了魏世弟、李尔钢的《中国现代辞书学派的生长》一文,该文把中国辞书学的研究分为实践派、理论派和传统派三个派别,其中以赵振铎、汪耀楠为传统派的主要代表,指出:“汪先生的研究对于现代辞书学继承我国古代辞书编纂传统,沟通传统语文学与现代辞书学的联系,促进汉语语文词典编纂工艺的现代化,有重要意义。”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从自己的工作实践中、阅读中发现和提出问题,去进行研究,比什么都好。
编写字典、词典,成年累月和一个个字、词打交道,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它们的含义。中国的古籍浩如烟海,而字词就在里面存在着。假若文献还没读懂,就来注释研究,那就不能给字词以正确的解释。没有这种微观功夫,来从事词典学、训诂学、汉语史的研究,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清人的微观研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王念孙的《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经传释词》,都是经典著作。我曾要求研究生对《汉书》注进行辨补,对《康熙字典》进行考证,对释义理论进行系统研究,对《说文通训定声》假借字进行考证,就是希望他们把学术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有时讲课还即兴给出研究课题,如《集韵》的多音多义异体和通假,郑玄经注的“声之误也”研究等等。
不要做空泛的理论研究,要把宏观的理论研究建立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从事汉语史研究的年轻人,不妨做一些古文注释、今译或参加一点古汉语词典的编写工作。
编写《汉语大字典》是我这一生所做的最为艰苦又最有意义的工作。从1975年秋至1990年秋,我付出了整整15年的辛劳,我精力最为旺盛的年华就是在这一浩大工程中度过的。接着我又参加了《汉语大字典简编》(600万字),完成了百余万字的改编任务。
回忆起《汉语大字典》的工作过程,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一些事情:1975年11月我第一次参加川鄂两省在汉口德明饭店举行的工作讨论会,代表武汉市编写组(后为湖北大学编写组)做的要把《康熙字典》拉下马的大批判发言,获得了满堂喝彩。可是接着讨论编写方案时,我坚决反对“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字头、词条”的提法,成为了阶级斗争新动向,会议气氛一下紧张起来。领导召开了紧急会议,有的与会代表已开始吼叫着对我进行尖锐的批判。1976年9月在武汉大学行政楼讨论“仁”字字稿,我坚决反对据《庄子·胠箧》篇“分均,仁也”把“仁”当作奴隶阶级的哲学范畴,也不赞成为奴隶阶级争一席之地的提法,又引起了一场愤怒的甚至拍桌子的批判。而我则针锋相对,毫不退让,针对声讨我的观点做了整整一个小时的反驳,以至有人拍案而起,表示“忍无可忍”。后来我主持的《支、攴、文、斗、斤试编稿》受到会议的充分肯定。常务副主编李格非先生总结说:“这本五个部首试编稿,编出了样板,编出了方向,编出了信心。”
1982年春在荆州宾馆召开的两省教育厅、出版局和有关大学负责人及编写组负责人的业务会议上,我以“玉部”、“石部”、“缶部”为例对名物字的编写做了数小时的发言,引起了热烈反响。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汉语大字典》领导成员刘介愚先生十分动情地评价了我的发言。
我通读终审定稿,单位上给我配备了四位同志协助。我不断钩出问题,有的由我直接改定,有的则需要到图书室、资料室复查,我再定夺。400余万字稿(占全书的四分之一)都是由我签名交编纂处验收的。
《汉语大字典》1990年10月出齐前,决定出版装帧和《汉语大字典》一样的论文集,时间只有两个多月,规定我写带有学术总结性的长篇论文,字数不限。我在一个暑假,使出浑身解数,写出《〈汉语大字典〉通论》和《〈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对词典学理论的贡献》,共14万字。前一篇的基础是我十多年的编写审稿通读的经历,后一篇的基础则是我对《汉语大字典》系统的人员全部论文的阅读和了解。
一个暑假,除了家务事,少有休息,差不多每天写作4000字以上。编辑部每隔两天就来取一次稿,我连底稿也没有。至于差错,不当之处,说套话是“在所难免”。这是我年富力强时的一段经历,现在把这些写出来,也算是留下一点史迹,当然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了。
回忆起这一些,并不轻松,编写《汉语大字典》,我的工作量可以说是无以复加地沉重,有时甚至感到头脑的神经快要绷断,有“命悬一线”的感觉,几次检查身体,好些指标都处于低的极限。
二、我与中国辞书学会
从1992年学会成立到现在已经20年了,学会向我发出了参加纪念会的邀请。《辞书研究》编辑部打来电话,表示希望我写点什么。我退休多年,也不再关注周围大事。就说说学会的创办过程,留下一点史料吧。
1988年春,上海甲肝流行。《辞书研究》编辑部邀请了全国十几位有一定代表性的辞书学者开了一次会,北京与会的有金常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梁式中(中国人民大学),上海有钱剑夫、杨金鼎(上海师范大学)、王德春(上海外国语大学),武汉有汪耀楠(湖北大学)和唐超群(华中师范大学),广州有陈楚祥(广州外国语学院),哈尔滨有郑述谱(黑龙江大学),《辞书研究》有严庆龙、徐祖友等。在会中休息时我与王德春等先生谈到建立中国辞书学会的想法,他们表示支持。这次会议讨论了辞书研究的理论问题。会议同意我提出的在武汉举行全国辞书学研讨会的建议,并把这次编辑部召开的座谈会作为首届中国辞书学研讨会。
既然已经动议,我就得认真思考一些问题,我的想法是不办则已,要办就要办得出色:一、必须是半官方性质的学会;二、必须是高校、科研单位和出版部门相结合的学会;三、必须是具有辞书学领域涉及的各个专业分支机构的学会;四、必须是能促进学术发展,网罗全国语言学者、训诂学者、辞书学者和辞书编写出版工作者,并吸收港台学者和海外学者的学会;五、必须是有较充裕活动经费的学会;六、学会的领导成员必须是由学术水平高、社会影响大和出版力量强的人员组成。
1989年10月,在武昌举行的第二届全国辞书学研讨会议中,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韩敬体、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金常政、《辞书研究》的严庆龙、广州外国语学院的陈楚祥、四川辞书出版社的左大成等人,建立辞书学会的筹备工作从此开始。1991年春,在成都举行第三届全国辞书学研讨会,召开了第二次筹备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后,加快了筹备工作的进程。我主要进行申报材料、文件及在湖北办理各项手续的准备,北京方面由韩敬体、晁继周做各种联络协调工作,有时我也到北京去,和他们一起商讨问题,进行活动。国家语委、新闻出版署、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是最重要的支撑单位。当时晁继周先生是语言所副所长,他的支持和参与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92年我四上北京,住在国家语委招待所,拜访陈原(商务印书馆顾问)、曹先擢(国家语委副主任)、单基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金常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刘坚(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所长)等先生,跑教育部、出版署、民政部,有时是几个人一起去,有时是我一人跑,有时候我还拉上冯瑞生(国家语委)、李达仁(商务印书馆)一起奔波。那时用车是一件大事,继周先生保证了派车,对我是莫大的支持。上海方面的工作是由晁、韩二位去通报情况,进行协调的。
学会挂靠何处、秘书处设在哪儿是一件难以确定的大事,我的想法是挂靠社科院或语委,韩敬体先生曾给我一信,说是语言所考虑学会秘书处应设在我所在的地方。在语委开会定人选时我再一次提出学会挂靠社科院或语委问题,并表示实在不行,可挂靠四川辞书出版社或湖北大学。这是学会及秘书处设在湖北大学的经过。
办学会需要跑好些单位,要一处一处申报,盖章,而且并不像请假条,递上去就行了。一处图章有时得跑若干次,湖北大学、省教育厅、民政厅、教育部、出版署、民政部,设立分支机构与有关人员联络,都是要耗费精力的。学会下设的八个分支机构是我提出并同韩敬体先生商议后定下的。
自从1991年春成都会议后,我的许多精力都花在建立学会上去了。我找到了一本建立社团的手册,逐字逐句读过。我在武汉写了学会章程,征求意见后又做修订。学会于1992年11月在北京成立,我做了学会章程的报告,又起草了相关条例,并确定学会和各专业委员会每两年举行一次研讨活动,在研讨会后出版论文集。中国辞书学会的活动,就这样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直到现在。
第一、第二届会长是曹先擢,第一副会长是巢峰,副会长有赵振铎、林尔蔚、黄建华。我任第一届副会长兼秘书长,第二届任副会长。在我兼秘书长的一天中午又邀集李志江、徐祖友、袁世全、王春丽开了个小会,请志江和祖友二位把中青年辞书学者、工作者的活动组织起来。此后中青年这一块,在他们的带领下,进行了有生有色的学术活动,逐渐使中青年成为了学会最有生气的力量,培养和壮大了学会队伍,促进了中国辞书学会的发展。
有人说人生是一本书,也是一出戏。我这本书快要翻完,这出戏也快落幕。回首往事,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差,哪些本可做而未做,哪些本可不做而偏偏做了,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都离我愈来愈远。我写这个回忆,若可做补白,就放在刊物的末尾,做个附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