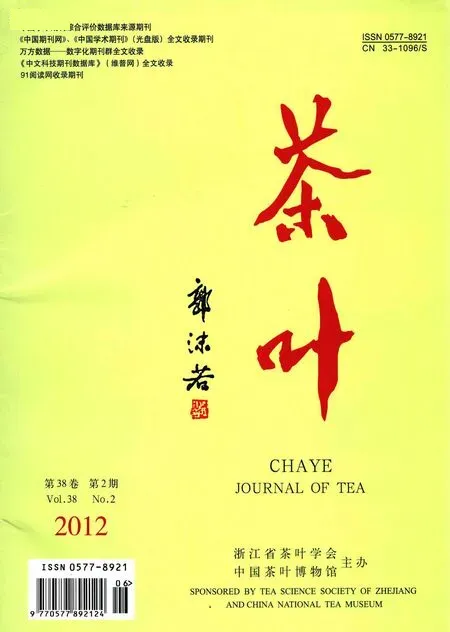“我欲因之梦天姥,渝州云乐即予宫”——忆爷爷吴觉农的好友吕允福先生
2012-03-31吴宁
吴 宁
2010年夏,我从四川重庆带回了几本吕允福先生写的笔记,这是他在1980年在北京突发脑血栓之后写的。这几本笔记,在允福伯床下的一只纸箱里“睡了”整整二十几年,好像就是在等着我去读的。很多年前,一定是细心的希蕴娘娘,允福先生的妻子用塑料纸,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好这几本笔记,可在潮湿的重庆,天长日久,顽固的青黑色的霉苔还是爬满了塑料纸,也在笔记本上留下了痕迹。小心地翻阅允福伯的笔记,我想起了允福伯最后一次来北京的情景,虽然那已是三十多年前了……
一
1980年3月24日晚,我从中央音乐学院骑车回家,去取一本忘在家里的琴谱。刚到家,奶奶就对我说,允福伯来了,可能是路上太辛苦,话也讲不清,没吃晚饭,就去睡了。奶奶觉得应送他去医院看看。可爷爷说,允福也就是累了,好好睡一觉就会好。去医院折腾一场,反而要病,再说第二天还要乘飞机。奶奶再坚持,爷爷发脾气了,于是家里人也都闭嘴。听到这里,我对奶奶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就急忙骑车赶到南池子救护站。到了那里,我把允福伯的征状和年龄一讲,医生就开着救护车直奔我家。等我骑车到家里的时候,救护车已把允福伯送往协和医院。奶奶说,救护医生来到时,人已昏迷了。
第二天,掂记着允福伯,我一上完课就回家了。爷爷到院子里来迎我,他拉着我的手:“幸亏你昨天回来去叫急救车。刚才医院来电话,允福已经醒了,真要是等到天明,允福就可能救不转了。我真太自以为是了,还把他当成个年轻人。这可是个大教训啊。”爷爷的眼里充满了眼泪。
几天后,允福伯的妻子希韫娘娘和她的女儿吕夏来到了北京。爷爷和奶奶请她们住在我家里。她们母女俩人在医院轮流照顾允福伯,还为他做一些可口的汤饭。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希韫娘娘,她和允福伯是个鲜明的对比:一个泼辣、热情,一个儒雅、沉静。爷爷、奶奶与希韫娘娘已是很多年没见了,他们在一起,就会讲起往事。
记得有一次,爷爷对希蕴娘娘说,“允福用功,在上海上大学,寒假暑假,从来不回家,总是去向一位法国人学法语。本来大学毕业时,他有去法国留学的机会,但他是家里的老大,要负担弟弟妹妹的生活和学费,所以就留下来了。”希蕴娘娘说,“是呵,他是喜欢学外文的。文革时住牛棚,他用毛泽东选集学英文,还带进一本毛主席诗词。从牛棚里放出来,竟然用英文背下了毛主席的全部诗词。”
又一次,爷爷说:“允福能文能武。别看他平时温文尔雅,是个书生,可枪法好。1937年秋,我们在三界组织抗日训练时,一开始整个茶场只有他有支短枪,会用。以后几年里,我从三界去上虞看母亲,他总是要去送。那时的路上不太平,不是地痞杂牌军,就是日本人。”
希韫娘娘说“是的喽,都说允福枪法好,可他还真没伤过人。四十年代初的那几年,日本人几次在嵊县、新昌大扫荡。那时我们从三界撤到了新昌的社古村。日本军进攻的那天,狂风大雨,也分不清是雷声还是日军的炮声。直到有村人跑来报信,允福和几个带着枪的散兵,掩护我们茶厂老小顺着村后的桑园林撤退到山里,而他们自己却被日军团团围住了。幸亏河里洪水涨到了两丈高,冲倒了大半村庄的房屋,日军弃村而逃。而允福他们所在的民房是在全村的最高点,没被洪水淹到,要不然那一次可要真刀枪了,敌众我寡,可能连命也保不住的。”
记得希蕴娘娘还讲起过他们在抗战后期的经历,爷爷那时已去了福建。1943年春,允福伯操劳过度,大吐血。可他还不肯休息,坐在床上,围着条被子,写《制茶学》。因为不能下地动手试验,又没有资料,他很是很苦恼。1944年春,他刚刚恢复一点,就拄着拐棍做杀青试验。都说江南是渔米之乡,可抗战困难的时候,他们在深山茶场里却常以野菜充饥。山里从来吃不到鱼,老百姓请客时,会把一条木头刻的鱼摆在桌子中间。”
爷爷说:“允福对三界茶场感情深呵,他那十几年真是惨淡经营。抗战胜利之后,我几次去看他,他总是在没日没夜地工作,虽然场里连雇技术员的经费都没有,他却不愿意离开。他就喜欢泡在茶园里,搞点研究。”
五月里,允福伯病情稳定了,要回重庆,我陪爷爷到医院去与他告别。以后,爷爷奶奶常常收到希韫娘娘的来信,说允福伯病后行动不便,不常出门了。但在家里写回忆,先是口述,由希韫娘娘代笔,后来又自己拿笔写了,也点写诗。
二
允福伯自1928年在上海劳动大学与爷爷认识到1990年去世,做了一辈子茶人。1928至1949年,他在浙江20年,在家乡嵊州三界茶场;1951年到了四川的重庆,在那里近四十年。读允福先生留下的三本手稿时我却发现,三界茶场那一段,他从爷爷的私塾老师七十几岁的徐三希先生写到十五岁的学员马森科,然而很少写到自己。
允福伯写自己的经历是从1949年开始的,那是风云变幻的一年。允福伯和他的许多朋友们一起等待着“解放”。1937年以来,无论是在抗战,还是内战,他与三界的茶人在艰难困苦中撑着茶场,好不容易就要“熬”到解放了。那年的四月,爷爷在杭州之江茶厂的小院里与允福伯相会,允福伯讲到了茶场经费之困难,工资发不出,已经到了瘫痪的地步。爷爷问他要不要去复旦教书,在复旦茶叶专修科的任教和的王泽农先生有建立农业化学系的想法,所以需要另聘专修科主任和茶学教授。爷爷劝他去上海走一趟。允福伯说,正值茶季,场里的人正忙着收茶、制茶,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茶场。
五月初,解放军占领了杭州,随后进了嵊州和三界,允福伯还去为他们当过向导,然而却没有人来接收茶场。这时的茶场不仅发不出工资,连口粮也成了问题。允福先生一面拿出自己的积蓄维持茶场的食堂,一面到杭州农业厅邀请解放军代表进场。在杭州,他与农业处的莫定森和过兴先两先生接上了头。
六月初,军代表许济川和吴思勋到场,几天之后,茶场的事情全部交接完毕。因为当时嵊州土匪出没,治安混乱,军代表给场里的职工每人发了两个月的工资,让大家离开。允福先生回到家之后,就给王泽农先生写信,询问去复旦教书一事。
八月初,军代表姚全岱到三界,取代了许济川做组长。姚全岱希望复兴三界茶场,所以他一到,就联络金道微(茶场的财物管理)把允福伯和其他几位技术人员招回来,提出了要重建茶场。说要允福伯回场,担保人身安全等等。虽然,允福伯已决定去复旦教书,但他想到自己最熟悉茶场的情况,就急急赶了来。姚见到允福伯后很高兴,对他说:“我们人民政府对留用人员既往不咎,希望你们以后为人民服务。”
在今天看来,所谓“既往不咎”的说法之荒唐呵!允福伯他们从建茶场到解放,在那里十几年,有制茶和种茶的经验,要复兴茶场,他们应是骨干,是老师。可军代表们只把他们当作留用人员,还说“既往不咎”。以后的几个星期,允福伯被安排在楼上写资料。不久,他接到了王泽农先生从上海的来信和复旦的聘请函,复旦系里已决定请允福伯去教课并担任专修科主任了。允福伯向军代表们请准,却没有得到批准。
9月6日,一股土匪流窜到茶场,抓走了军代表姚全岱和茶场的几个职工。根据吕增耕先生的回忆,另外两位军代表,一位躲进了树林,另一位“到楼上去看情况”。根据增耕先生和允福伯的记录,作为旁观者来看这一事件的前后,显然营救计划被拖延了,而且许军代表在营救中所作出的种种决定也多有蹊跷之处,然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随着老人们的逝去,永远消失了。最后,姚军代表被残杀,几位职工被放了回,土匪也消声觅迹。
那年的十月,上海报纸上登出允福伯将去复旦任职的消息。可实际上他不但没有能去复旦,反而连三界的场长职务也被撤销了。究竟是何原因,允福先生没有写,只是提起他收到了弟弟吕进从东北的来信。当时的浙江还是一片混乱,而东北已是很稳定了,于是他带着既将临产的妻子吴勤芬,冒险乘车去东北,看望十几年没见的弟弟吕进。他和吴勤芬在十二月坐火车从杭州到沈阳。关于吴勤芬的很多细节我还无从找到,只知道,她也是三界茶场的女工。1949年底,他的第四个儿子吕良是在沈阳到达的第二天出生。
三
允福、吕进兄弟见面极为高兴,允福伯一家就住在弟弟的供电局宿舍里。然而允福伯用自己的话说,很快他就“尝到了失业”的滋味。吕进夫妇早出晚归,很少有谈话的机会,允福伯不算“革命”家属,一家三口靠吕进的供给制,是不可能的。允福伯这样写到:“我热爱我的专业,战后有一个计划,希望对茶叶科学有所贡献,但此时却尝到了失业的滋味。独靠弟弟来供养自己,实在过意不去。”
不久,沈阳农林部招聘农业技术人员,允福伯去应试。投考的人上千,大多是伪满的官员。考的是农业方面的知识:稻麦和棉花的种植技术等等,他初试有名。在复试的几百人中,只有允福伯和蒋南翔先生的胞弟蒋南群以农业技师被录用。农林部事多人少,允福伯一专多能。那几个月里,在辽东他管稻麦工作和水利,在辽西他管棉花和苹果园。工作繁忙,但他的心情满愉快的。允福伯的要求不高,只要有工作,家人能温饱,他也心满意足了。
那一段时间里,唯一使允福伯心里不平的是在进农林部时,他填过一张履历表。交上去后,人事处的秘书说他填得有误。原来秘书要他在1949年前国民党统治下的事业、企业的职务前都加一个“伪”字:伪浙江省农林改良场技术主任、伪浙江省茶场场长等等以此类推。允福伯想不通,他说“伪”字是在抗战时为日本人做事的人留的。允福伯不肯加,人事处发话,如不冠“伪”字,只好让他退出农林部,回老家。无可耐何,允福伯只好“糊里糊涂”地加上了这个“伪”字。
1951年4月的一天,允福伯在农林部的布告栏上看到我爷爷到东北视察,第二天在部里讲话。于是允福伯早早就去了,坐在第一排。爷爷一上台就看到他了,爷爷笑了,还向他招招手。爷爷讲完话,见到他就问:“你还愿意回来搞茶叶吗?”允福伯当然愿意。随后,他把在东北填表时的情况告诉了爷爷。爷爷也是天真,他说去北京中茶,就不用耽心这个“伪”字了:“我们中茶所有的茶人还不都是从‘伪’字里走过来的。”
允福伯带着全家乘火车去北京的那天正是七月一日,党的生日。允福伯心情特别兴奋,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能够在中茶公司,与吴觉农、胡浩川、方翰周等许多熟悉的茶人在一起工作是他的梦想呵,这是新中国,是共产党给了他和茶人们这样的机会呵。到了北京的第二天,允福伯就去中茶上班。可谁想到,刚工作了三星期,他就被人事科李科长叫去,要他交待一件严重的反革命历史问题!
被隔离之后,允福伯冥思苦想不出自己历史上的“反革命”行为,所以半个月毫无进展。中茶公司缺技术人员去安徽六安建绿茶厂,胡浩川先生让他陪着同去,一面设计绿茶厂,一面反省。在六安,允福伯是主管基建设备和协助技术。他白天静心做业务,晚上连夜想问题,不觉也半个月过去了。梧桐叶落,时令已入秋。一天早晨,允福伯正在设计厂房,忽然收到电报,要他立刻回京。他心想不是死刑就是无期,但他是不会逃走的,所以就整装回京。一路心情沉重,到了北京,连家都不敢回,硬着心肠先去公司。
当允福伯迈进人事科长的办公室时,李科长劈头就问他愿不愿去西南教书,这使他诧异。李对他说:你的历史反革命案已了结。你在嵊州的亲戚原说你介绍他加入的国民党,后又推翻了。而西南大区在办西南重庆贸易学校的茶叶专业,急需茶叶教师。允福伯听了,心中的千斤大石头才落了地,他移交清楚后就立即离京。
临行前,允福伯曾去向爷爷道别。爷爷很感慨地说,以为调你来中茶,可以去掉档案中的“伪”字,谁想还不到一个月就差一点变成了“反革命”,真是令人心惊胆颤呵。他安慰允福说,还是走远点,安全些。四川是天府之国,富饶美丽;山高林密,是发展茶的好地方。
爷爷与允福伯谈起了发展红茶将云南大叶种入川一事。爷爷告诉允福伯,中茶公司在1951年春,趁着苏联向我们小叶种茶区引进4000担小叶茶种时,派人去云南采购了一批大叶种茶籽,已送到了重庆雅安、铜梁、灌县去试种。
四
1951年11月下旬,允福先生一家坐火车到武汉,然后从武汉坐船去重庆。
从汉口到重庆,逆流而上,在洪水期三天就到,可在十一月的枯水季节,行船极难,尤其是在青滩一带,水流急,暗礁多,要用钢索吊船,用机器拖船。那时没有电,全靠人力。虽然江面上有着“十丈悬流万堆雪”的景色,但船上的人都很紧张。虽然青滩并不长,却花了十几个小时,加上夜里不能行船,所以他们走了六天。虽然还没有走过秦蜀之道,可允福伯已有了李白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受。
到了重庆已是夜晚,山城的夜景极美。可他们上岸后,还要提着行李登上百多步梯,小孩加行李,累得气喘嘘嘘,当晚就在朝天门码头的一家旅馆过夜,第二天去曾家岩的贸易专科学校。下午刚在贸专的招待所住下,学校学茶的一位姓黄的学生代表就跑来找他说,情况紧急,茶专的学生纷纷要求退学。原来,茶专因为没有专业老师,所以没有人知道培养茶专人材的目的。学生以为毕业之后是在茶叶店卖茶,算算几斤几两,多少钱。他们去请教过校长,校长说,也就是这个意思。学生们都说,要是去卖茶,何必专修两年,去做个学徒算了。
允福伯听了,二话没说,就决定当晚为茶专的学生讲演。他还没有办行政手续,讲演时连件相样的衬衫和双干静的鞋都没有。在路上很多天,头发和胡子都是老长,但他也顾不得了。那天晚上,允福伯给四十一位茶专的学生从茶叶的起源、历史,到国家的茶业现状,到茶科学的分类,到世界上的茶情,到为什么需要大量的茶业人才;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民生日用,用他的话,“讲得天花乱坠”,原计划一小时,却整整讲了三个多小时,讲完之后,学生们热烈鼓掌,没人退学了。
五十年代,从贸易专科教茶到西南农学院,虽然允福伯的工作和专业不被学校所重视,但他没有灰心,从没有停止他的四川引进云南大叶种的研究和试验。1952年秋,国营新胜茶场的人到西南农学院与他讨论大量引进云南种,邀请他到永川、铜梁、壁山和大足四县栽培基地去指导研究,他欣然接受下来。允福伯每天给学生上课,一到周末,他就坐着长途车,去四县观察和指导种茶。那时的长途车,走的是山间公路。2010年我还坐过一回,从看大足石刻回重庆,我没赶上高速公路的汽车。盘山路面不平,汽车又老,虽然车开得极慢,可我还是被颠得头昏眼花,几次头撞到了车顶。那一路,我一直想着允福伯每个周末坐车去茶场的经历。
1957年秋天,反右之后,被内定“有问题”的允福伯被下放到重庆市郊的海空农场。他发现那里的气候土壤条件非常适合种云南大叶种。茶籽二、三月播下去,五、六月出土,成活率85%。到了十一月,茶苗健壮高大,发芽整齐。他快活极了,暗自庆幸“被下放”后,可以真正做一点工作。
1958年的暑假,允福伯回到西南农学院看家人,听系里的人说,西农来了位新院长李世俊,是农业专家,北京大学农学院化学系毕业,在延安当过南泥湾垦区主任。一天,他和系里的老周过西农招待所,在门口遇到了李院长。李院长与他们打招呼,然后与周谈话。几分钟后,允福伯打算先离开,李院长喊住他:“你不是老吕吗?我要和你谈谈。”李向他问起了整个四川的茶业,说要大力地发展川茶。允福伯在重庆七年了,李院长是他遇到的第一位重视茶的领导,他真是高兴,他问李院长怎么会认识他的,李说,在吴觉农副部长家里见到过他,就知道吕是搞茶的。允福伯吃惊地想,七年多了李院长居然还记得他。
在李院长任内,茶专科招生几班学生,1962,1963,1964,每年都有一班毕业。那几年,李院长常来允福伯的班里听课。有一次,李院长带着百多个西农干部来听课,参观茶园。允福伯在讲扦插。现场报告完毕之后,学生把剩下的有根的茶苗放置在路边,李院长心疼这些有根的茶苗说,“这样好的苗,可以长成大茶树呢。”
五
1972年,文革中期,允福伯收到了从西农转来的爷爷给他的信,他真是欣喜若狂,从此每个月与爷爷通信。爷爷在写《四川茶叶史话》第一稿就是寄给允福伯,请他提建议。以后,他们又合作写了《我国西南地区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和《茶树在我国西南地区的自然分布》等文。从爷爷保留下来的允福伯的多封来信中看,他们谈的最多是关于川茶的发展和四川茶史,也讲到发展大叶种红茶的远景。那时候从四川到北京是很难。允福伯是在1951年11月去四川的,1963年去北京开会才与爷爷匆匆见了一面,而下一次是到了1978年5月了,爷爷随政协考察团去四川,然后是同年十二月在昆明开会,他们才又见面了。而爷爷与他在1981年协和医院的道别,竟是他们最后一次会面,当时,我还没意识到,但两位老人心里是有数的。记得爷爷一直握着他的手要他多保重,记得允福伯的眼里充满了泪水。
允福伯在病后所写的笔记记录了他一生的心路历程,也留下最后十年他在病痛中的挣扎的痕迹。第一本笔记常能看到希韫娘娘的代笔。以后,越来越多的是允福先生颤颤抖抖的字迹,字多是斜的。听他的儿子吕吉说,他常会让家人扶他坐到他家斑竹村平房前的木椅上,沉思一阵,写一阵,腿痛了,就用手敲敲,然后再接着写。
几年里,允福伯整整写了三大本笔记,还写了不少诗。诗的草稿都是在薄薄的纸片上写的,改了又改,反复推敲。允福伯爱写诗,据说已是他的爱好多年了。而在他患病后,他写诗除了表达情感,又有了新的作用。从他的笔记来看,写诗也是为了活动头脑,帮助记忆,为他写回忆作个引子。他还特别喜欢默写李白的诗,最爱的是李白写四川的诗和他的那首《梦游天姥吟留别》。李白在四川长大,他的神笔把四川的奇山异水写得淋漓尽致,他的“梦游天姥”又写出了允福伯在晚年对家乡的无限思念。允福伯曾写过一首《答茶友》描述他的人生,而诗中的意境却是来自李白:
一堂茶课定终身,天府天堂五十春。
学浅自惭无所树,山高喜见出奇茗。
峨眉秀色普天重,蜀道崎岖一日还。
我欲因之梦天姥,渝州云乐即予宫。
人的记忆是有局限的。时间、地点、细节随着时光的流逝,也会出现偏差,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允福伯用他手中的笔和纸把他的记忆,一字字,一行行地连成一片。他的一生,从劳动大学到三界茶场,从沈阳农林部到北京中茶公司,从重庆贸易学院到西农,五十年的经历都是老人用颤颤抖抖的笔写的,这是多麽宝贵的记忆。
我收集爷爷和他的朋友们的故事已经有三年,长长短短也写了不少,而近来常有彷徨之感:不仅觉得写的内容与今天的现实和下一代的生活离得太远了,而且写的故事也是千篇一律。但每每看到案头允福先生的这三本笔记,我会提醒和激励自己 :为了失去的记忆和被人们忘却的历史,我要像允福先生那样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