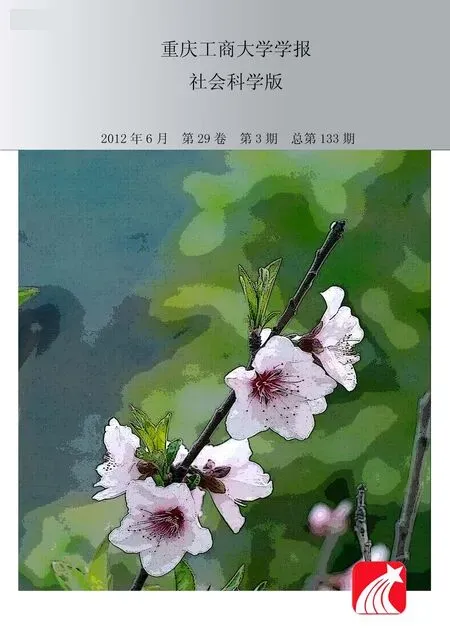约翰·菲斯克大众文化的当代美学观照
2012-03-31邓文华陆道夫
邓文华,陆道夫
(1.南方医科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州 510075;2.广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州 510006)
一、菲斯克的文化民粹主义
从上世纪30年代至今的文化研究发展轨迹来看,西方的文化研究(cultual studies)明显是一个从精英文化批评转向社会文化批评的过程。尤其是从60年代之后,当代西方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逐渐背离了审美化的研究模式,越来越超越单纯的文化内部分析,向外部的社会分析延伸,从单纯地分析作品本身向更宽阔的社会视野转变。很大程度上,文化是被视为实现政治目的一种手段。这种工具主义的理论视角,最终催生了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1939-)所代表的文化民粹主义。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位“世界知名的文化研究健将”[1],菲斯克明显超越了传统的精英主义与悲观主义态度,他将研究的关注点集中在沙滩、摩天大楼、游戏厅、二手服装、广告、牛仔装等大众文化产品上,从而推动文化研究进入了大众文化研究的时代。不仅如此,他还从学理上对大众文化进行了再定义和新辩解。如果说在霍克海默、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代表的文化工业批判学说中,大众文化一直处于被批判、被敌视、甚至被贬低的地位,如果说大众文化因呈现出简单化、平面化、肤浅化和商业化的特质而无审美价值的话,那么,到了菲斯克这里,大众文化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具体而言,菲斯克摒弃了在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以前就一直沿用的“mass culture”的提法,而代之以“popular culture”。按菲斯克的说法,大众文化的主体是“大众”(the people),而不是群众(the masses)或民众(folk):群众是愚昧的群体的聚集,是受体制奴役和欺骗的“文化白痴”,而大众则是由形形色色的个人构成的,这些个人虽然明白自己处于体制之中,却能够对这一奴役进行抵制。这就是说,大众文化的消费者并不像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受其影响的文化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同质的、无差别的、毫无鉴别力的群体,只能被动、消极地接受由文化工业灌输或强加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相反,他们具有相当大的主动性,对文化产品有着自己的判定。虽然大众的文化资源是由文化工业提供,但大众却凭借一种“权且利用” (making-do)的艺术,有创造性地、有识别力地使用和解读这些资源[2]。在这个创造过程中,大众“通过利用那剥夺了他们权力的体制所提供的资源,并拒绝最终屈从于那一权力……资产阶级受到无产阶级的抵制,霸权遇到抵抗行为,意识形态遭受反对或逃避;自上而下的权力受到由下而上的力量的抗争,社会的规训面临无序状态”[2]。在这些躲避、消解、冒犯、转化甚至抵抗宰制力量的过程中,大众进而生产出了属于自己的社会体验的意义所带来的快感。在菲斯克看来,体制提供的文化产品一旦进入大众的解读范围,就成为种种符号,人们便可以根据自己的语境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产生多种意义。体制无法控制这一过程。菲斯克用澳洲的原住民观看老西部片时的反应来说明这一点:原住民在意识到自己受到白人宰制的前提下,在“当影片中的印第安人……狙杀白人男子,抓走白人女子之际……为之欢呼鼓劲”[2]。简言之,虽则文化工业产品渗透着支配者的意识形态,大众却能利用它创造自己的亚文化。不难看出,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研究延伸了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思路。在他眼里,“文本对受众做了什么”已经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受众对文本做了什么”。这种转变使得菲斯克比前人更加关注受众的主体地位,关注受众的实践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在《理解大众文化》里,菲斯克借助法国符号学理论家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指出,大众文本应该是“生产者式文本”(producerly text), 其具有“松散的,自身无法控制的结局”,其“内部存在的一些裂隙大到足以从中创造出新的文本”。这些“裂隙”大致相当于接受美学所说的“空白”或“召唤结构”,它们给大众进行意义生产提供了空间。对于菲斯克而言,也正是这些“裂隙”和“空白”,为大众文本的“过度”“浅白”和“贫困”等特性提供了充分的辩护。大众文本的过度是指符号的泛滥。泛滥的符号带来了语义的泛滥,使作品变得煽情、夸张、鄙俗。它使“意义挣脱控制,挣脱意识形态规范的控制或特定文本的要求”。它通过展现特殊的不合规范的非常事例来突露其所违反的常规,并通过对其进行强烈的戏仿和嘲笑而促使大众从中体味到对规范的反抗与超越,从而创造出自己的文化意义。大众文本的贫困是指文本不完整,不充足,意义贫乏。菲斯克认可了文本的贫困性,但他给文本寻找到一项伟大的使命:即作为意义和快感在社会中加以流通的中介。大众文本不是单独地发生意义的,而总是在互文性的语境中生成意义。众所周知,罗兰·巴特也强调文本的互文性,比如他把具体文本放入文本的海洋之中,使个体文本的意义不断游移、转换、生成、增值,在众多文本的互文语境中对个体文本进行建构与阐发。然而,菲斯克的互文环境是指整个的日常生活,强调的是文本外的新的意义的产生。因此他说,“大众文本是行为人和资源,而不是对象”。在文本外的日常生活的互文语境中,具体的文本是不自足的,是意义的煽动者,是反应堆;大众是催化剂,点燃有限的文本资源,生产出无限的文化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菲斯克认为,“过度”“浅白”与“贫困”诸特性是大众文化的一种抵抗姿态,一种宣告独立的方式。在宰制力量的面前,大众施展“游击战术”,躲避、消解、冒犯、转化甚至抵抗宰制力量,由此在微观政治层面(日常生活当中)促成社会体制的循序渐进的进步,促进社会的最终变革[2]。
应该说,菲斯克对大众在接受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强调,对大众文化的那种积极乐观的态度,为人们理解大众文化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正如D.麦奎尔所评价的那样:“在努力为大众文化辩护方面,约翰·菲斯克一直是最雄辩、最令人信服的人之一”[3]。然而,由于菲斯克完全肯定大众文化的一切特点,他同时被看作是一个典型的文化民粹主义者[4]。约翰·斯道雷甚至认为:菲斯克代表了文化研究一个“从更具批判力的立场的退却”的阶段。其理论是“消费者权威”的自由主义观点的一种不加批判的回音,或者说,它与占优势的“自由市场经济”意识形态一唱一和[4]。诸如此类的批评都表明,菲斯克的文化民粹主义或许是一种盲目乐观,甚或是对精英主义论调的矫枉过正。进而,从当代美学的角度来看,菲斯克的大众文化观不得不令人颇感疑虑和不安,对其加以批判性的反思和审视也就变得十分必要了。
二、大众文本理论的美学批判
在《英国文化研究与电视》一文中,菲斯克开篇就表明:“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一词,侧重的既不是审美,也不是人文主义,而是政治”[5]。这就是说,文化在这里不是伟大艺术形式中的审美理想,也不是超越时间和民族边界的“人文精神”,而是工业社会内部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样一来,菲斯克的关注点就从完美的精神成就(精英文化)转向了大众文化。菲斯克坦然承认自己的学说蕴涵着强烈的世俗趣味,他本人也把大量的休闲时间都花在体验媒介文化和消费大众文化上:电视、煽情的画报、流行文学、通俗小说、好莱坞大片、迪斯尼乐园和环球电影制片场,都成为他参与媒介文化,获取媒介文化快感体验的场域[2]。
作为一个大众文化迷和实践者,菲斯克将美学视为一种赤裸裸的霸权,一套宰制性的规训系统,是中产阶级隐藏“阶级特性”而将自身的趣味和文化实践普遍化的工具[2]。菲斯克满怀信心地指出,大众辨识力是对美学霸权的拒绝和反抗。受众抛弃了中产阶级的“距离”式的审美静观,而通过积极的参与和主动的介入,创造性地使用文化工业提供的产品并从中发现自己的意义,从而产生出一种“意识形态的暂时丧失”和“逃避宰制力量”的快感。菲斯克认为,在大众的辨识力中,与日常生活的相关性是最为核心的。与中产阶级的审美标准不同,相关性“受到时间与空间的制约,”是“由每一个特殊的解读时刻所决定和激发的特质”[2]。澳洲土著居民观看西部片时,之所以有那种反应,正是由于他们能够在产品与自己的日常生活之间发现积极的联系(相关性)。相反,“如果一种文化资源不能提供与日常生活经验产生共鸣的相关点,那么就不能成为大众的”,尽管文本的‘质量’很高”[2]。质言之,大众辨识力所关注的并非质量之批判,而是相关性之感知;它所关注的与其说是文本,不如说是文本可以被如何加以使用的方式[2]。大众文本展现的是浅白的东西,内在的东西则留给生产式的读者去填写自己的社会体验,去建立文本与体验之间的关联,从而从中挖掘出关联自身个性的、吻合相关性的意义、快感和权力来。
然而,仅仅满足于将大众文化视为反抗霸权的政治工具,从而将相关性作为大众文本的评判标准,这种工具主义势必促使菲斯克放弃对文本(审美对象)自身的要求,而刻意为大众文本的浅白、过度与贫乏做合理化辩护。虽然对于拒绝话语霸权而言,这也许有着某种积极的意义,但不幸的是,这也极有可能导致一种愚民政策,不利于大众文化的发展与提高。首先,菲斯克似乎高估了大众的生产自主性和生产能力。他想当然地让大众成为高明的理想读者,假想出一种与现实阅读状况脱节的大众解读。但大众真可以用相关的社会语境来弥补文本的过度与浅白吗?这恐怕并非易事。虽然少数大众或许具备这一能力,但大多数恐怕只能停留在文本的过度与浅白。在这里,菲斯克对大众文本的辩护,与其方法论的局限性是分不开的。正如国内有学者注意到,菲斯克的研究仅仅偏重于媒介文本和媒介受众两大模块的研究,而忽视了对媒介机构和产业等其他领域的研究[6]。这使得他只关注受众的文化消费,成为了一个消费至上的平民。但正如麦克盖根所指出,这种不加批判的民粹主义“大大高估了消费者的力量”,其对通俗读物不加批判的褒扬,制造了一场“质量判断危机”,使得大众文本失去了好坏优劣的标准[4]。菲斯克的方法论决定了他眼里所谓的那些有创造力、有辨识力的大众,实际上仍有可能是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由个体组成的乌合之众,他们随波逐流,缺乏自己的判断,无法辨别和取舍那些眼花缭乱的、著芜并存的大众文本,以至他们最终逐渐失去对美和艺术的鉴赏力,而在一些贫瘠的、没有价值的文本中浮浮沉沉,变成了思想简单的,被塑造成集体类同的一分子。这也正是霍克海姆所忧虑的:“家庭逐渐瓦解,个人生活转变成闲暇,闲暇转变成连最细微的细节也受到管理的常规程序,转变成为棒球和电影、畅销书和收音机所带来的快感。这一切导致了内心生活的消失”[7]。
很显然,尽管菲斯克反复不断地强调大众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在文化产品的生产发展过程中,始终起着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但大众的辨识力却始终令人怀疑。虽然菲斯克指出,美国青年把新的牛仔裤专门撕成破洞来穿,是为了表示对主流社会价值的否定,对社会商品化的拒绝。麦当娜的“粉丝”们试图从对麦当娜文本的使用,是为了改变同男人的关系,并且把这种变革男女关系的幻想力量延伸到家庭、学校以及工作场所,从而宛如流水侵蚀堤坝一样地去销蚀父权社会的统治机制。但是,在这些穿破牛仔裤的美国青年和麦当娜的“粉丝”当中,有多少人是真正怀有菲斯克所分析的远大抱负呢?又或者说,有多少人只不过是随波逐流的、盲目跟风的消费者罢了。其实,菲斯克不过是把大众化的读者变成了专门的大众文化研究者,用所谓的“裂隙”与“空间”掩盖了文本的浅白与粗陋[8]。应该指出的是,大众文本必须先有蕴含着丰富内容的反应堆,才能见出其催化剂的神奇,如果大众文本不充足,意义贫乏,就不会成为催生大众创造力和识别力的肥沃土壤。虽然大众不需要文化霸权,但随着社会分工的越来越精细,大众已失去了文化原创力。菲斯克本人也承认,大众自己不会生产文本,他们只能改编和利用文化工业的产品。所以我们说,读者是由作品来培养的,他纵然可以对作品加以改编利用,但他那一套改编利用的本领是在长期的文化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其文化底蕴与习惯,也是在具体文本经验的积累修正中形成的。如果其互文语境中充斥着大量的贫困文本,则贫困的文本只能造就贫乏的读者。大众置身于浅陋的大众文化互文语境中,难免会变得浅薄空虚,这自然会影响其文化生产能力的形成。
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化大师杰姆逊曾对平面化、无深度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特征做过深刻的分析,指出其抛弃思想,抛弃理性所导致的文化失重的困境。菲斯克拒绝理性和深度,使文本的能指和所指都自甘沉溺于平面与简单当中,这可能是一种自暴自弃的、缺乏批判性的文化观。他在这里只是少了一份后现代主义的玩世不恭,多了一种乐观主义的盲目自信与满足。他以避免文化霸权为由,赞同大众文本不做任何深层的价值判断,使其浅白、平面的特点合理化。文字平面上的堆积无法涵养丰富的艺术接受心理,无法参与大众日常生活的美学建构,这始终是其文化理论中一个难以克服的缺陷。
三、菲斯克大众文化的审美教育之思
总体而言,菲斯克 “以媒介文本为载体,以媒介受众为核心,以媒介体验为旨趣”的文化理论,在方法论和研究立场上给我们带来了某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比如说,它促使人们把理论的触角伸向了对普通大众和弱势者的关怀[9]。然而,菲斯克似乎过于乐观地肯定了受众主体的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和反抗性,同时过高地弘扬了大众媒介文化的“进步性”和大众的生产力。与此相应,他也过于片面地强调了媒介文本的开放性、多义性和互文性,以及媒介体验的狂欢、快感和抵制。但从美学的角度上看,却有令人忧虑的地方:对大众趣味的迎合,使得这种民粹主义实际上放弃了对文本自身的要求,因而势必导致价值判断的缺失,使大众逐渐失去对美和艺术的鉴赏力。
事实上,菲斯克对精英文化的规避,对审美趣味的抵制,与当代美学的发展态势不谋而合。从20世纪后期开始,特别是在后现代思潮和新实用主义美学的影响下,世界美学走向了后现代美学。后现代美学的主流是冲破“审美无利害”和“艺术自律”的康德传统,倡导对通俗流行文化持宽容的态度,避免一种艺术上的精英主义立场,主张美学与生活的结合,与身体感受的结合。凡此种种,在当下所谓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中,有着最明显的体现。因此,菲斯克对大众文化的乐观和辩护,符合当代美学的主流,有着明显的民主性和解放性。现代美学将少数精英的趣味确立为唯一合法的审美趣味,将“审美无利害性”确定为唯一合法的审美态度,由此强行将趣味划分为高级的与低级的。低级趣味被认为是畸形的、病态的、野蛮的、狭隘的、缺乏教养的,而高级趣味被视为正常的、健康的、得体的、普通的、修养精致的。在菲斯克看来,现代美学使得艺术失去了先前所具有的功能,沦为了纯粹的形式,从而拉开了艺术及“欣赏”艺术的人与“无文化的大众”之间的距离。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尤其随着消费时代的来临,以前沉默的大众走上了社会生活的前台,开始在各方面展示自己独特的审美文化,不再满足于按照社会精英制定的趣味标准来改变自己的趣味,而是力争为自己的趣味谋求合法地位。菲斯克对美学霸权的这种反抗,无疑是值得肯定的。然而,菲斯克大众文化观却也有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首先表现为,现代美学是否仅仅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大众必须加以反抗和拒绝的文化霸权?如前所述,文化学者之所以不再相信现代美学“无功利的”审美判断,主要是因为它把大众排除在了文化之外。但是,我们所应该抛弃的,却是不正确的或不合理的“判断”,而不是“判断”本身。所以,当菲斯克等文化学者拒绝区分趣味的高低好坏,并进而为大众趣味辩解,这种策略虽然貌似在保护审美文化的多样性,但实际上反而可能造成审美文化由于封闭而走向枯萎。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这种看似民主、平等的多元趣味论,实际上也无助于不同文化和亚文化之间的交往和理解,其结果只能是产生文化孤僻症,以及由孤僻导致的敌意。因此,正如国内有学者指出,我们有必要发展出一种新的趣味观[10]。这种新的趣味观肯定趣味的高低之分,但对趣味却采用了“量”的区分。比如说,如果仅仅能欣赏古典音乐而不能欣赏流行音乐,或者仅仅能欣赏流行音乐而不能欣赏古典音乐,那么,这种趣味是低级的,只有能同时欣赏二者,才是高级趣味。换言之,我们不应拘囿于自己的片面视野,而应该试探去欣赏不同的事物,极力扩大自己的欣赏领域,从而突破习惯和文化造成的偏见。
其次,菲斯克对大众文化是否过于乐观和盲目了?当菲斯克满足于将大众文化作为反抗和抵制精英文化的工具,从而为大众文本的“过度”“浅白”“贫困”等特性进行辩解,我们不由怀疑,他是在自甘沉溺于大众文化的平面化与简单化。从美学的角度上来看,放弃对大众文本的要求,则会产生这样的后果:只要人们能够构建出某种意义,即使是路边垃圾,也能形成有价值的审美体验。但公园美景远胜于一地杂草,保罗·高更的绘画比土豆汤或热水袋更能引起审美关注,更能形成高质量的审美享受,这是不容争辩的。冷眼静观当下国人的精神文化,我们不得不心生忧虑,对菲斯克所颂扬的大众辨识力充满了怀疑。
毋庸置疑,“无聊”“傻乐”“山寨”等已成为90年代以来中国大众文化和娱乐艺术的主要特点[11]。当下的各种传媒大多充斥着无聊恶俗的搞笑节目,不触及现实问题、一味拿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民开涮的小品和相声,以及只有喧闹而没有思考的所谓情景喜剧。所有人,无论是台上的还是台下的,主持的、表演的或观赏的,全部在那里傻乐。“一年比一年愚蠢”的春节联欢晚会,可谓是中国当下大众文化最典型的代表。本来,相声、小品或情景喜剧都属于喜剧类作品,其生命力在于站在草根的立场讽刺黑暗势力,嘲笑强权,或者通过喜剧的形式揭示深层次的时代悲剧。但今天,晚会的几乎所有小品都将农民或农民工作为嘲笑对象,原因不外乎这些人都是可以放心大胆去糟践的弱势群体。他们全部被刻画成没有文化、势利眼、傻头傻脑还假装聪明的笨蛋。在2010年的央视春晚小品《不差钱》中,那位农民大叔把“艺术细胞”说成了“艺术细菌”,把“报答”说成了“报销”“报复”,把歌星“刀郎”误为“屎壳郎”,“精辟”误做“屁精”,如此等等,这种低级无聊的“笑料”居然获得了现场观众的满场喝彩。而2001年的央视春晚小品《卖拐》,更是拿残疾人的生理缺陷寻开心,以至于在美国演出时遭到了强烈的抵制和谴责。这些低俗文化的流行,似乎在表明,大众对美和艺术的鉴赏力正在逐步消失。尤其是青少年,在大众文化低俗趣味的引导下,他们的审美能力正在衰退,有些人分不清楚美与丑,以丑为美,以怪为美,以奇为美。他们整日沉迷于“游戏机”,热衷于“追星”。其趣味低级而庸俗,对典雅的书画、高雅的音乐舞蹈、严肃的诗歌小说、传统的曲艺、健康的影视等一概麻木不仁,对一些缺乏深刻思想和艺术意蕴的言情打斗作品却津津有味。因此,可以说,即使真如菲斯克所言,大众对文化工业产品的消费,是一个主动地建构意义的过程,是对宰制性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和抵制,但大众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也许并不像菲斯克所说的那么强。大众的选择和反抗,在旨趣上未必就是趋善去恶,近美远丑的。相反,也许更多是导致拜金主义的回潮,审美能力的衰微,高雅文艺的困顿,人文精神的失落,等等。
与之相对应的第三个反思便是:要救赎大众化时代的病患,对审美教育的价值和功用进行的重新评估。在传统的美学理论中,审美教育一般被认为是培养人们的美感和审美感受力、理解力、鉴赏力,提高审美趣味和艺术修养的重要手段,甚至被视为人类的精神力量和道德源泉,成为改造个人生活和社会的一条重要途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推崇用艺术来培养城邦未来建设者。十八世纪,德国美学家席勒更是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美育理论。他认为,审美是感性和理性的对立和冲突的解决,是人性的全面和谐发展和解放。审美教育“有促进健康的教育,有促进认识的教育,有促进道德的教育,还有促进鉴赏力和美的教育。这最后一种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我们感性和精神力量的整体达到尽可能和谐”[12]。十九世纪,德国思想家尼采对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的推崇,马尔库塞对于通向人的本能解放的“审美之维”的强调,阿多诺对于作为挽救现实社会途径的审美的乌托邦的坚持,无不体现了审美教育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而中国的孔子同样强调美育是提高人性修养、塑造人格美的重要途径。到了近代,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等人更是试图通过美育而改造民性,促进社会变革。
虽然自大众文化占据“霸主”地位以后,美育似乎变得“过时”了。但是,随着低俗文化的泛滥,大众对美和艺术的鉴赏力的衰微,谁又能否认美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呢?昔日,柏拉图呼吁,让青年们“天天耳濡目染于优美的作品,像从一种清幽境界呼吸一阵清风,来呼吸它们的好影响,使他们不知不觉地从小就培养起对于美的爱好,并且培养起融美于心灵的习惯”[13]。今天,我们同样要呼吁,要让大众在美育的指引下,规避大众文化的商业性、浅薄性、庸俗性、娱乐性等,培养深层次的审美体验,在功利化和物质化的大众浮躁时代,静心沉思,尽情体会并享受有品位的艺术之美和生活之美。
[参考文献]
[1] 约翰·菲斯克. 传播符号学理论[M]. 张锦华,等译. 台北:远流出版社, 2001.
[2] 约翰·菲斯克. 理解大众文化[M]. 王晓珏,宋伟杰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3] D. McQuail,D. McQuail.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M]. Sage Publications, 2000.
[4] 约翰·斯道雷. 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5] John Fiske.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d television, in R. C. Allen (ed.) [M].Channels of Discourse, London: Reassembled, 1992.
[6] 陆道夫. 菲斯克媒介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反思[J]. 河南社会科学,2011(2).
[7] 霍克海默. 霍克海默集[M].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7.
[8] 秦海英. 假想的凌空建构——质疑费斯克的大众文本[J]. 长江大学学报,2005(2).
[9] 陆道夫. 菲斯克媒介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反思[J]. 河南社会科学,2011(2).
[10] 彭锋. 回归当代美学的11个问题[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11] 陶东风. 无聊、傻乐、山寨——理解当下精神文化的关键词[J]. 当代文坛,2009(4).
[12] 席勒. 美育书简[M]. 徐恒醇,译.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4.
[13] 柏拉图. 文艺对话集[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