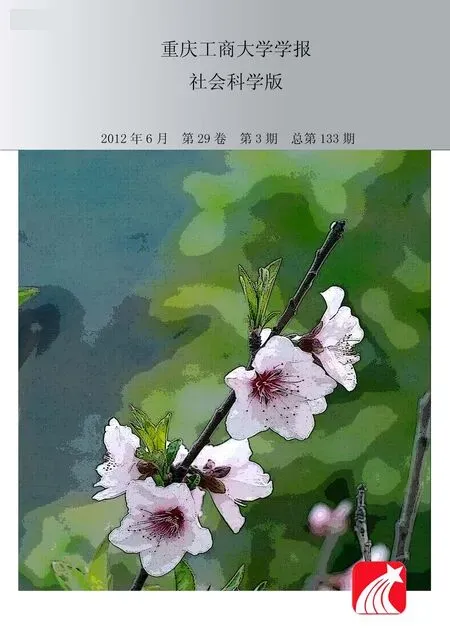抗战诗歌再认识
2012-03-31周晓风
周晓风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047)
2001年,本人在拙著《新诗的历程》一书中,曾用了接近全书一半的三章篇幅去处理抗战时期的诗歌部分。除了以“新诗的逆转——歌谣体”为题,把抗战初期歌谣体诗的出现看作是“抗战与诗的双重选择”的结果外,还以“另一种范式——新写实体”和“必要的张力——新现代体”为题,对抗战中后期诗歌的发展和诗体的凝聚做了进一步的叙述。[1]当时之所以这样做,主要的考虑就是希望避免此前对抗战诗歌过于简单化的理解和非美学本位的处理,以达到对抗战诗歌更为准确的认识和把握。多年之后的今天,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拓展,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无疑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不仅有关抗战文学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取得新的进展,而且学术界对于抗战文学乃至整个抗战文化研究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尽管如此,我仍然感到学术界对所谓“抗战诗歌”的了解和理解有待进一步拓展,对于抗战诗歌美学的讨论有待深入推进,对于抗战诗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一
在我们一直以来对于抗战诗歌的理解中,有一种刻板认识是比较普遍的,那就是把抗战诗歌仅仅理解为“战声”,理解为国统区的朗诵诗和解放区的街头诗。这种认识似乎自郭沫若1938年的《战声集》开始,一直延续下来,至今几乎仍然没有得到改变。[注]郭沫若的《战声集》是他1936年至1937年的诗歌作品,1938年1月由广州战时出版社出版发行,后收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这样的理解固然是有道理的,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抗战诗歌的基本情况。但是,这样的对于抗战诗歌的理解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和充分的。而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抗战诗歌的概念作了一种简单化理解,把文学史上的抗战时期的诗歌简单理解为作为一种文类的抗战诗歌,从而形成认识视野上的遮蔽。
文学史上的“抗战诗歌”是一个仍然有待进一步深入拓展认识的文学史概念,包含了丰富而复杂的历史和文学内涵。从时间演变的角度看,抗战时期的诗歌一般指的是从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这一历史时段的诗歌。它们既具有主题风格的某种一致性,同时又因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存在不容忽视的区别。
在抗日战争初期,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诗歌迅速感应时代的脉搏,发出高亢的战声和激越的呐喊,进入“最蓬勃发展的阶段”。[2]这也正如胡风所说,“抗战以来,普通用文艺形式发表的作品,最多的一是报告,一是诗。……诗歌之发达,是由于在这个神圣伟大的战争的时代,对着层出不穷的可歌可泣的事实,作家容易得到感动以至情绪的跳跃,而他要求表现时代所采取的形式,就是诗。”更进一步说,由于这一时期的诗歌需要唤起广大群众的抗战热情,需要适合悲壮、乐观、慷慨激昂的情绪,因此,“抗战初期,诗作品主要的潮流是热情奔放的。”[3]抗战初期这种热情奔放的诗歌主要表现为国统区的朗诵诗和解放区的街头诗。有研究者从诗歌文类角度把抗战初期的诗主要概括为“抒情诗”,[4]而如果用诗体来描述,可以把它们称作是一种“歌谣体”诗,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现实性的审美价值取向,即在诗歌价值取向上追求强烈的现实功利价值,希望用诗歌作为唤起民众的工具和武器,发挥诗歌现实的战斗的作用,反对此前具有唯美倾向的“现代派”诗风;其次是追求诗歌大众化和平民化的审美品质,在情感内涵的选择上明显倾向集体的、大众的情怀,而较为排斥那些属于个人的、一己的悲欢;在语言方式上则进一步追求平民化、口语化艺术旨趣,突出地借鉴了民间歌谣的语言方式;第三,抗战初期的歌谣体诗在审美体认上更多地从“五四”以来的新诗转向了中国传统诗歌的音律化,易颂易记,朗朗上口成为普遍的趋势。一般人们常常谈到的高兰、光未然的朗诵诗,田间、柯仲平的街头诗以及蒲风等人的抗战诗歌,大都是这一阶段创作的代表。人们过去所谈的抗战诗歌,其实主要就是指的抗战初期的歌谣体诗歌。然而,抗战时期的诗歌并不是只有抗战初期的“歌谣体”诗歌。随着战争的进入相持阶段和抗战的深入发展,抗战中后期的社会生活和文艺生活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新阶段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一方面,战争不只是带来激情与鲜血,而且还掀开了生活中令人窒息的丑陋的一面;战争也不可能凭着热情就可以一朝取胜,而是一个艰苦的漫长的过程。这样一种现实情势势必要求把抗战初期的浪漫激情转变为一种更富有韧性的战斗的现实主义精神。另一方面,中国新诗以至整个新文学自身的发展逻辑在此时也酝酿了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和创作的逐步走向成熟。胡风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以及以“七月派”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出现,其意义也正在于此。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和文学背景下,抗战时期的诗歌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我们的学术界对这一点的意义显然估计不足。
抗战中后期的诗歌,在坚持现实性的审美价值取向的前提下,现实主义新诗成为诗坛的主流。其发展明显表现出新的历史的和审美特征。首先,较之战前和抗战初期的诗歌,抗战中后期的诗歌对现实生活有了更为真切、细腻和丰富的展示,诗歌的写实性得到了增强。抗战中后期诗歌写实倾向得到增强的一个突出表征是战时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得到更为多样细致的表现。这之中,抗战题材仍然占有主要地位,但较之此前有着更为多样化的反映。王统照的《正是江南好风景》、天蓝的《队长骑马去了》、苏金伞的《我们不能逃走》、罗铁鹰的《劫后的古城》、柳倩的《在太阳下》、覃子豪的《废墟之外》等,都是当时优秀的以抗战为题材的现实主义新诗。其中,一些国际题材的诗作显得尤为别致,可以说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展示了战争生活的侧面。如王平陵的《期待着南斯拉夫》把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与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联系起来加以表现。李震杰的《给日本士兵》写日本士兵因远征他乡,而使“徘徊樱花林下的岛国女儿失去季节的狂欢”。当然,日本士兵失去的绝不仅仅只是这些,而是还有更多。这正如程千帆《一个“皇军”的墓志铭》中所写到的:
异国的呼喊夹着枪声,
一阵昏眩,使你
就倒下了。……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帝国的臣民?可是
你的手册使来者翻开了
日本现代史。
…… ……
除抗战题材外,对战争年代现实生活丰富性和多样性的体验和描绘,也是抗战中后期现实主义诗歌的突出现象。这之中,对于民生疾苦的反映占有突出的地位,是现实主义诗歌的长处所在,同时战时现实生活的其他方面在现实主义诗歌中也得到了广泛展示。臧克家这一时期的诗作无疑是其中的主要代表。臧克家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有《从军行》(1938)、《泥淖集》(1939)、《呜咽的云烟》(1940)、《泥土的歌》(1943)等诗集和长诗《走向火线》(1939)、《淮上吟》(1939)、《古树的花朵》(1942)、《诗颂张自忠》(1944)等。值得注意的是,臧克家这一时期诗歌的代表作并不是抗战初期以抗战为题材诗作,而是稍后那些表现中国农村生活题材的作品,现实生活的多样性、情感体验的丰富性以及艺术表现的含蓄凝练是其主要特色,表明抗战中后期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其中,初版于1943年的《泥土的歌》被认为是臧克家抗战期间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该诗集在题材及情感内蕴上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回到作者所熟悉的和亲切的中国农村,在艺术表现上则摈弃了抗战初期那种激昂的战歌和直率抒情,代之以白描的手法,描绘出一幅幅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国乡村生活的典型图景。《饥馑》《复活》《三代》《送军麦》《生的图画》《死水》《社戏》等都是相当有代表性的作品。如《送军麦》:
军麦,孩子一样,
一包一包
挤压着身子,
和衣睡在露天的牛车上。
牛,咀嚼着草香,
颈下的铃铛
摇得黄昏响。
燎火一闪一闪,
闪出梦的诗的迷茫,
这是农人们
以青天作帐幕,
在长途的野站里
晚炊的火光。
该诗实际上是把战争作为背景和底色,集中表现的仍是战争挤压下的乡村生活秩序。另一首《社戏》则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叙述农民们晚上去观看“社戏”前后的过程,语言生动简洁,极富艺术表现力。值得注意的是,《泥土的歌》中的作品大都写于远离故乡农村的大后方城市,更多的是作者的记忆和思念的产物,因而带有对故乡农村特别浓郁的情感体验和牧歌情调,显示了现实主义诗歌在抗战中后期发展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除臧克家以外,堪与臧克家早期的《老马》相媲美的有方敬的《背夫》:
不毛的羊肠小道上,
寸寸的步履,寸寸的艰辛,
从这座山到那座山,
坚毅而沉默有如屹立的岩石。
江村的《灰色的囚衣》描绘出一幅灰黯的山村景色:“天/板着死灰的脸,/挂下绵绵的雨丝;/像无数根铁柱/围成了人间底囚室。/雨声/滴出深深的烦厌/像一个年老的狱吏/叨叨地吐着怨言。”作者借此抒写了对于生活在“山国的人民”在苦难里煎熬的深切同情。胡明树的《两栖类》写纤夫的艰辛,夏渌的《白庙子》写一群矿工“躺在碳层里用丁字锄敲下煤块,/再蜷伏着像鼹鼠一样,/把碳车推移出来,/像这样遣送他们无边的黑夜。”郭风的名为《春天》的诗仍充满阵阵冬的寒意。
田野
以交错的田路网络住
裸露的胸膛
土地的辛勤的垦殖者——
农民们沉思地站立在田亩上
那以万把锄头掘松的田亩上
而又以迟钝的目光
凝视浑浊而暧昧的天边
…… ……
这荒凉的旷野上的
苦恼的动物呵
孤独而没有人注意地跛行着
步伐是怎样的沉重呵
而那四周
依旧是从天穹下垂的鬃毛
卷来的阵阵的冰寒……
也有一些优秀的现实主义诗作对现实生活中的情景有独到的发现和典型的描写,且能做到含蓄隽永,耐人寻味。如厂民(严辰)的《蒲公英》写对母亲的怀念,朴素而真切;杜谷的《泥土的梦》把“泥土的梦”写得细腻动人,包孕了丰富的情感内涵;鲁丁的《高梁熟了》写庄稼人在收获季节里,“一把镰刀/放倒一个梦/黄昏/一溜鞭响/大车载回/庄稼人的辛苦”;程康定的《荒店》描写动乱年代羁旅荒野小店的情景颇有特色:
夜色浓了,
月光泼一地冰冷,
行路人长长的影子,
紧挤在一堆,
荒店豆大的光,
在风中摇红
——招引他们到店中过夜。
一壶土味的水酒,
醉去八百里的疲劳,
一床金黄的草,
好编制旅途的长梦,
对着陌生的耳朵,
店主东细细地
告诉人明天的路。
门前的灯火
亮着:鸡鸣早看天。
上述这些作品虽然还不能完全代表抗战中后期的现实主义新诗,却也能反映出其中的大体情况。
抗战中后期现实主义诗歌写实倾向的另一个突出表征是,一些过去以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诗风见长的诗人,也普遍转向现实主义的真切描写。一种“客观的抒情诗”代替了此前“主观的抒情诗”。抗战初期诗歌的那种“空洞叫喊”以及此前现代主义诗歌的晦涩病得到了初步克服。例如,何其芳在战前是汉园三诗人之一,其作品风格华丽,充满浪漫情调和梦幻色彩,同时某些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现代主义诗歌的朦胧晦涩。然而何其芳写于抗战期间的《夜歌》则明显趋于朴实明朗,现实主义写实成分大为增强。其中的代表作《成都,让我把你摇醒》不仅表现了对于现实的沉痛感,也反映了诗人在时代压迫下的惊醒:
从前在北方我这样歌唱:
“北方,你这风瘫了多年的手膀,
强盗的拳头已经打到你的关节上,
你还不重重地还他几耳光?”
“北方,我要离开你,回到家乡,
因为在你僵硬的原野上,
快乐是这样少
而冬天却这样长。”
…… ……
然而我在成都,
这里有着享乐,懒惰的风气,
和罗马衰亡时代一样讲究着美食,
而且因为污秽,陈腐,罪恶
把它无所不包的肚子装饱,
遂在阳光灿烂的早晨还睡着觉。
…… ……
让我打开你的窗子,你的门,
成都,让我把你摇醒,
在这阳光灿烂的早晨!
何其芳的这些作品虽然还说不上是优秀的现实主义诗作,但其诗风向着现实主义的转化却是非常明显的。另一位“现代”诗人戴望舒的转变亦相当典型。戴望舒前期诗作中浪漫主义和象征方法相交织,形成其独特的“现代”风格。抗战爆发后,戴望舒流亡香港,亲身经历了民族革命的斗争实践,特别是经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特窗生涯的考验和屈辱困苦生活的磨练,诗风变得朴素凝重,具有浓郁的现实主义特征。《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待》等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当然,戴望舒的现实主义仍有自己的特色,并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是从“现代派”向现实主义的简单回归。戴望舒现实主义诗歌的特点在于写实与象征的结合而不仅仅是现实主义的写实。这既是戴望舒对自己的一种超越,也是中国新诗中现实主义的一种有特色的表现形式。此外如“现代”诗人卞之琳,浪漫主义诗人穆木天、蒲风等,在抗战中后期都明显发生了向着现实主义诗风的转变。尤其值得提到的是,随着抗战的深入和新诗的发展,中国新诗在抗战中后期逐渐形成“七月诗派”和“中国新诗”两个较为成熟的新诗流派。前者突出体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诗歌的结合,后者则更多表现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诗歌在特定语境下的融合。他们的出现把新诗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抗战中后期诗歌写实倾向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叙事诗得到了较大发展。其情形大约如臧克家所述,抗战中期,“诗人们从战地、从农村,回到大后方的都市,生活比较安定了一些;较之抗战初期,诗人也真正深入了战时生活,初期的那种高昂的情绪,浪漫主义的幻想,逐渐地淡化了,破灭了,希望的光辉,也暗下来了。这时候,诗人有时间、有心情回忆、整理、消化蓄积下来的生活经验,酝酿较大的诗篇。有的为英雄烈士作传;有的记述抗战的行迹和个人的感受,名副其实的长诗产生了。”[5]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力扬的《射虎者及其家族》,艾青的《他死在第二次》《火把》,老舍的《剑北篇》,臧克家的《古树的花朵》《诗颂张志忠》等。这些长诗创作的具体情况和所取得的成就不尽相同,但普遍反映了抗战中后期现实主义诗歌发展的一种趋势,是抗战前期诗歌发展所没有的现象。
二
对于抗战时期诗歌的再认识,除了需要在时间上注意抗战时期的诗歌存在着不同的发展阶段而表现出极其丰富的精神内涵和审美表征的演变外,还需要从抗战时期诗歌在空间上的不同分布而加以辨证考察,有的甚至还需要结合现代区域文学互动发展带来的变化加以认识。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到抗战时期,一方面因为统一抗战的需要而具有鲜明的现代民族国家文学的共同性,另一方面又因为政治地理的分割而表现出不同的区域文学发展趋势。不仅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孤悬海外,即使是在中国大陆,在抗战时期实际上形成了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分割的政治地理格局,影响到抗战文学和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中国现代抗战诗歌的发展,不能不受到这样一种基本格局的制约。原本统一的中国新诗显然需要某种新的区域文学的阐释框架和阐释话语。
相对于解放区和沦陷区而言,抗战时期国统区的诗歌和文学是研究得较为丰赡的一个领域,已有的有关抗战诗歌研究的对象大多集中于此,有关抗战诗歌的历史演进、诗人的创作梳理以及诗歌作品的评价,大多是就国统区诗歌而言的。其中,有关抗战时期现实主义诗歌潮流的研究、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的研究、抗战时期大诗人艾青、臧克家、田间以及戴望舒、穆旦、冯至等的研究,都取得了公认的成就。但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国内学术界对于抗战时期国统区诗歌研究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也是明显的。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对抗战诗歌样本的选择上,较为注重作品的思想倾向,相对忽略作品的语言艺术锤炼;而在对作品的思想倾向的关注上,对于政治立场属于左翼作家的诗歌创作较为重视,而对于大量其他作家的诗歌创作较为忽视。其次,在艺术风格上对于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给予较高评价,而对于现实主义以外的其他诗歌创作评价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对于抗战时期国统区诗歌全面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抗战时期解放区诗歌仍有诸多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中国现代史上的解放区作为一个政治地理概念,泛指在民族民主革命战争中由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控制的区域,以区别于国民党控制的国统区和日本侵略者控制的沦陷区。抗日战争时期的解放区概念同时具有动态性,随着战争的进展而不断变化。陕甘宁边区是当时最大的解放区,除此之外还有鄂豫皖、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东等著名解放区。这些解放区从总体上讲,社会经济基础较差,国民党的控制力也比较薄弱,具有开展革命斗争的良好基础。同时,伴随着抗战的深入发展,大批文化人涌进延安这样的解放区,造成前所未有的文化激荡。这样一种大的政治地理分野和解放区的基本面貌决定了解放区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解放区的抗战诗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抗战初期,随着全民抗战的高潮,解放区诗歌同样处在一种激情和亢奋的状态,朗诵诗和街头诗仍然是当时主要的诗歌样式,直抒胸臆则是当时主要的诗歌方式。《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中收集的大部分诗歌作品均体现了上述特征。但由于解放区诗歌作者和受众的特点,抗战时期解放区的诗歌更具有简短、朴素和歌谣化等大众化特点。田间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义勇军》、阮章竞的《秋风曲》、方冰的《歌唱二小放牛郎》等无疑都是这类诗作的代表。但抗战时期解放区诗歌也并不是只有《歌唱二小放牛郎》之类的作品。特别是随着大批文化人的涌入解放区,文学报刊得到了发展,诗歌的作者和读者结构有了明显的改变,诗歌创作也因此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例如,艾青在战前已创作了许多优秀诗作,1941年在周恩来的帮助下从重庆辗转到了延安,他的生活和诗歌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也给解放区诗歌带来新的气息。在延安,艾青仍然保持了自己的现实主义诗歌特色和艺术水准。他在延安创作的《古石器吟》《风的歌》《秋天的早晨》《村庄》《给太阳》《黎明的通知》《野火》《献给乡村的诗》等,既是艾青这一阶段诗歌创作的代表,也展示了抗战时期解放区诗歌创作的丰富性。在他的《献给乡村的诗》里,艾青写到,他要把他的诗献给中国的一个小小的乡村。这是一个怎样的乡村啊!
我想起那些简陋的房屋——
它们紧紧地挨挤着,好象冬天寒冷的人们,
它们被柴烟薰成乌黑,到处挂满了尘埃,
里面充溢着女人的叱骂和小孩的啼哭;
屋檐下悬挂着向日葵和萝卜的种子,
和成串的焦红发辣椒,枯黄的干菜;
小小的窗子凝望着村外的道路,
看着山峦以及远处山脚下的村落。
艾青那种对现实特有的敏感,他的忧郁和同情心在这些作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他的现实主义诗歌艺术也得到了提升。
另一位抗战时期来到延安的诗人鲁藜的《延河散歌》显然也不是现实主义诗歌所可以简单概括的。
在夜里
山花开了,灿烂地
如果不是山底颜色比较浓
我们不会相信那是窑洞的灯火
却以为是天上的星星
如果不是那
大理石般的延河一条线
我们会觉得是刚刚航海归来
看到海岸,夜的城镇的光芒
我是一个从人生的黑海里来的
来到这里,看见了灯塔
但战时的延安毕竟还有诸多并不理想的一面,这在诗人的笔下也间接得到反映。更重要的是,战时的延安虽然生活艰难,却仍然保持了一种宽松的文化氛围。“口诛笔伐、针锋相对、直接坦率、不讲情面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延安一种基本作风。”[6]这使得延安时期的诗歌在抗战主题的前提下,仍然能够保持多样化的题材和风格,而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单调。下面是一位并不著名的解放区诗人吴越的《布谷鸟》:
清夜醒来,
布谷鸟
把它的浸渍着心血的歌声
滴进我的灵魂……
啊,热情的鸟啊,
你比我醒得更早;
你已久久睁着你那燃烧的双眼,
望穿了沉沉的暗夜而迎接天明。
啊,你,
你终于冲出了重浊的浓雾封锁的林谷,
以你的锋利的翼尖劈破潮湿的夜空,
把你的歌声注向大地……
像这样完整而成熟的意象抒情诗不仅在延安,就在整个抗战诗歌中也是不同寻常的。
抗战时期沦陷区的诗歌发展在过去一直受到忽视。这主要是因为沦陷区文学本身的特殊性以及研究材料的诸多限制。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研究资料的发掘和一批研究成果的问世,抗战时期沦陷区诗歌的风貌开始逐渐展示出来。其中尤其是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主编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的出版填补了该领域的重要史料空白。与当时整个沦陷区文学一样,沦陷区诗歌一方面不得不受到侵略者文化管制体制的严厉限制,另一方面又在合法外衣的庇护下含蓄表达了“抵抗文学”的声音,有的则以表现出与沦陷区主流意识形态相对峙的审美趣味的姿态出现。其中,丁景堂、南星、路易士、吴兴华、毕基初等是较有影响的代表诗人。
毕基初(1919—1976),山东威海人,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西语系,上世纪3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华北沦陷后在北平的中学教书,为当时有影响的青年作家。毕基初的创作以小说和散文名世,诗歌创作亦有影响。毕基初的诗歌创作多写寂寞忧伤的情感体验,在梦幻般的想象中抒发身处国破家亡的身世之感。代表作有《废宅》《幸福的灯》《射击》等。下面是他的一首散文诗《长门怨》,可以从中感受到毕基初诗歌的基本风格。
你门前生满青青的草,忧郁的长相思堆满了贴着日子的手册。
(书页里夹着丁香树的心形页,犹未忘情于书里的故事,仍指点着
一串逝去的恋歌。但褪色的木叶上却多斑斑的泪痕了。)
怀念远方的海上,你乃在桌子上摆设了一支小银船。银船上有泪雨
湿了帆,沉重的载负,沉重的怀念。
无弦琴悄悄的啜泣于秋风里,想念春天熟稔的抚摸,如今春天是夕
阳外的记忆,我的手指感伤的弹着异地夜里的蜡花。
你冷落了往日我们走过的路,听孤独的蛩音,会想起远行人。
梦里有橄榄味的清苦,灯光朦胧有如黄昏雨,你桌上是长久的阴
雨天,雨天的忧愁,雨天的哀怨,织成了你新的凄凉,新的苦愁。
这样的作品自然不可能做到把诗歌当做匕首和投枪,直接刺向侵略者心脏,但把它放到当时日本统治者企图把中国纳入所谓大东亚文学圈的背景去看,如此独特的凄苦风格仍然从美学上显示了诗人的爱国情怀。
南星(1910—1996),原名杜文成,笔名南星、石雨、林栖等,河北怀柔人。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上世纪30年代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著有诗集《石象辞》、散文集《松堂集》等。南星的诗歌创作处于沦陷区日本侵略者的严密控制之下,难以有更大的作为。南星一方面在文字中为自己解脱,认为“人生是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摆弄的,于是有无数无可奈何的惆怅,而悲叹,叹息或呼喊都没有用的,我们除了安于命运之外再没有更聪明的办法了。”[7]另一方面,南星在看似平和的诗句中透露出特定的故国情怀。
不知从哪一个窗格透出来的
人语中似有旧识的声调
那不是几个生客么
我在他乡度过了多少岁月
灯尖已没有踪迹了
只有一丛丛的花木仍在
它们的黑影是柔和的
虽然这季节里充满了严寒
——《深院》
诗中流露出某种怀旧的情绪,“旧时的声调”“他乡”“季节里充满了严寒”等都指向某种故国的眷念情怀。南星的诗具有较为成熟的现代诗歌方法,同时不少作品包含着繁复的古典意象。张中行在《诗人南星》中评价南星的诗歌“词句清丽,情致缠绵,常常使人想到庾子山和晏几道。”[8]
丁景唐(1920— ),原籍浙江宁波,1920年出生于吉林市,3岁时随父亲回到宁波镇海乡下,1937年随姑姑定居上海,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中文系。丁景唐上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文学创作,主要写诗和散文,上海沦陷后曾在“孤岛”编辑文学刊物,参加文学活动,出版有诗集《星底梦》,被认为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富有民族自尊心的青年学生,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上海沦陷时期的苦闷彷徨与期盼冲破沉闷现状的双重心情,亦寄托诗人纯真的童心与向往。
晶莹的是满天的星星,/纯真的是无邪的童心。/黑夜中的孩子伸手
向天:/“——星星,给我!”/惹得母亲笑:/“宝宝睡觉,妈摘给你!”
孩子的脸/漾浮着笑靥,/喜悦满天的星粒跌落胸兜里,/学姊姊栽
花把米撒在黑土地:/“星星——开花!”
“愿孩子,你多福!/ 星光下的梦,/会在未来的日子中开花!”/
于是母亲关上窗, /便也有一个星光的梦,/依偎作长夜的温存。
——《星底梦》
丁景唐另一首《向日葵》写作者怀念荒郊中野生的向日葵“生就有一付倔强的性格,/——钢铁铸成的脊骨。/在荒郊中,它撑住了黑暗,/在风雨中,它喜爱逞斗!”该诗具有一种在沦陷区诗坛是很少见到的清新和明澈的风格,更直接表达了一种热烈的战斗的精神。
路易士(1913— ),本名路逾,原籍陕西周至,1913生于河北清苑,1924年定居扬州,1933年毕业于苏州美专,1929年以路易士笔名开始写诗,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阵营的重要成员。抗日战争爆发后流转于汉口、长沙、昆明、香港、上海等地,曾任国际通讯社日文翻译,主编诗歌月刊《诗领土》,是上海沦陷区有重要影响的诗人。1948年,路易士易名“纪弦”,离沪赴台湾,创办了《现代诗》季刊,发起成立现代诗社,提倡所谓“横的移植”,引起台湾诗坛关于现代诗的大论争,成为台湾现代诗派的开创者,1976年后定居美国。路易士在上海沦陷区期间创作出版的诗集主要有1945年4月出版《三十前集》。该诗集为作者1931年至1943年代表作品的编年集,共收录诗人作品212首,注明为“诗领土社丛书第一种”。其中《我之出现》被认为颇有代表性,被认为是路易士自我形象和他在沦陷上海文坛形象的一个绝妙刻画:[9]
十足的Man。
十足的Man。
十足的Man。
哦!一组磁性的音响。
修长的个子,
可骄傲的修长的个子;
穿着最男性的黑色的大衣,
拿着最男性的黑色的手杖,
黑帽,
黑鞋,
黑领带:
纯男性的调子。
予老资格的小母狼
以吻之触觉的、味道的
慷慨的布施的
是植在唇上端的
一排剪得很齐的冬青列,
满口的淡巴菰臭。
哦,十足的Man!
哦,十足的Man!
哦,十足的Man!
一匹散步的长颈鹿。
一株伫立的棕榈树。
吹着口哨,
出现于
数百万人口的大都市之
最豪华的中心地带,
比当日耶稣
行过耶路撒冷的闹市时
更具吸引力的啊。
路易士的另一首《傍晚的家》则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沦陷区的生活,受到同为沦陷区作家张爱玲的关注。
傍晚的家有了乌云的颜色,
风来小小的院子里,
数完了天上的归鸦,
孩子们的眼睛遂寂寞了。
晚饭时妻的琐碎的话——
几年前的旧事已如烟了,
而在青菜汤的淡味里,
我觉出了一些生之凄凉。
如果说上述两首诗作还只是间接与抗战主题有所关联的话,下面这首《五月为诸亡友而作》则更为直接切入战争和时代,颇类似毕加索的名画《格尔尼卡》,在看似凌乱的意象中表达了抗战的主题。
我的记忆是一个广场,其上立着有许多尊我的朋友们的铜像。那些写诗的手,刻木刻的手,拿画笔的手是我握过的。那些作曲,弹piano,演奏小提琴的手是我握过的。他们也我痛了我的。啊啊多么悃挚,多么温暖!那些友谊使我怀念,使我流泪,使我伤感。那些心胸都很宽厚,那些灵魂都很善良,和我一样。他们的年龄也都和我相仿。但是他们死了,连一个也来不及饮我的房·胡登朱古力了。有的死于坠马,死于轰炸;有的死于咯血,死于肺病;有的死于贫穷,死于饥饿;有的死于忧郁,死于疯狂或自暴自弃。他们死了。剩下我的岩石般的孤独和遣不
去的哀愁。我的哀愁是和五月一样的……
大时代的轮子辚辚地辗过去。铜像沉默,而我心碎。
纪弦(路易士)晚年在台湾出版的《回忆录第一部》曾对他在沦陷区生活有所涉及:
是的,抗战期间,我没有从过军、当过兵、开过枪、放过炮,也没有杀死过一个敌人。但我也不是什么“文化汉奸”,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国家民族的事情。我没有“认贼作父”,我没有“卖国求荣”,我手上没有血,我心里也没有阴影。
有研究者撰文指出,[10]路易士1942年的《巨人之死》诗实为悼念前苏联大革命家托洛茨基,并非为悼念一名被抗日特工用斧砍死的汉奸而作。另一首《炸吧!炸吧!》也不是所谓赞美敌机轰炸重庆。同时,路易士在1938年9月6日香港《星岛日报》还发表过一首《诗人们,到前线去!》的散文,鼓动诗人搁下他们的笔,荷起枪来,走上前线去。但该文同时也披露过去未曾注意到的一则史料,说是路易士1944年11月12日在南京参加由亲日的伪政权组织的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时,写有《巨星陨了》一诗悼念汉奸汪精卫。如果上述材料均属实的话,路易士确属一位具有复杂的政治倾向和诗歌创作的沦陷区诗人。他在沦陷区期间的诗歌创作也应该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加以区别对待。
不过,随着近年来有关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研究的深入,另一位重要诗人的名字逐渐浮出水面,他就是被称为燕园才子的吴兴华。吴兴华(1921—1966),原籍浙江杭州,生于天津,笔名有兴华、梁文星等。青少年时期随父母在津京度过,曾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和北京崇德中学,1937年初中毕业后即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1941年毕业留校任教,曾在北平的中法汉学研究所供职。1945年抗战结束后回到燕京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吴兴华曾任北京大学西语系副教授、副系主任。“文化大革命”中惨死于非命。吴兴华的诗歌创作开始于1936年,1937年16岁时在戴望舒主编的《新诗》杂志上发表无韵体长诗《森林的沉默》,受到诗坛重视。日军占领北平期间,由于父母双双亡故,吴兴华一方面要担负起抚养几个弟妹的责任,另一方面却继续在几个朋友所办的《燕京文学》等刊物上发表诗作并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吴兴华诗歌创作受到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洋诗歌的双重影响,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诗人在时代重压下的家国身世之感。如他的《绝句三首》:
一
黄昏陌上的游女尽散向谁家
追随到长巷尽处不识的马车
一春桃李已被人践踏成泥土
独有惜影的红衣掩映在长河
二
高揖马鞭于熙来攘往的路崎
万户千门垂杨下我伫足沉凝
一夜的西风长安为落叶之国
不得不珍惜多年无尘的素衣
三
断肠于深春一曲鹧鸪的声音
落花辞枝后羞见故山的平林
我本是江南的人来江北作客
不忍想家乡此时寒雨正纷纷
吴兴华的这些诗意象繁复,词句整饬,音律协调,与新月派时期朱湘和现代派时期的何其芳有相似之处,被认为具有一种新古典主义风格。吴兴华也有的诗写得较为平易,以一种更为成熟的现代主义诗艺表达诗人对时代的感知。
巷口的小学在五点钟/关门了,静默重新阔步走来,/惟有几丝幼小者的啜泣,/似乎被人留下。
炊烟凝定在空中,/木叶如一群灰鼠爬着/空气的阶级梯,上,上,又上,/然后头朝下地落下来。
点亮了灯,小店又呈露活气——/一个女人围着白的围裙,/用苕帚敲着地,/咒骂一条似在深思着的狗。
月,夜的浅蓝胸衣上/一颗不很亮的扣子,/然而有着异常魅惑的光辉,/升上来,正缀在学校的旗上。
——《随笔》
吴兴华曾被认为30年代中国诗坛出现的一颗新星,可惜好景不长,仅在抗战时期沦陷区短暂如流星划过,不然理应有更大的成就。
对于抗战诗歌多样性和丰富性的认识,除了受到审美客体的诸多复杂限制外,更重要的是还受到来自审美主体视域障碍的遮蔽,其中有关审美意识形态的纷争更是成为影响抗战诗歌审美评价的主要原因。这就涉及另一个更为重要也更为复杂的命题,本文暂不涉及,希望留待今后另作探讨。
[参考文献]
[1] 周晓风.新诗的历程(第四、五、六章)[M].重庆出版社,2001.
[2] 艾青.中国新诗六十年[A].艾青全集(第3卷)[C],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1994:493.
[3] 胡风.略观战争以来的诗[A].胡风评论集(中)[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62.
[4] 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385.
[5] 臧克家.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诗集序[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6] 吴敏.宝塔山下交响乐[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1:205.
[7] 林栖(南星).读闻青诗[J].中国文艺,1943,(9):2.
[8] 张中行.负暄续话[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77-78.
[9] 张曦.诗人档案——从路易士到纪弦[J].书屋,2002(1).
[10] 吴心海.“巨人之死”与“巨星陨了”[J].名作欣赏,2011(13).